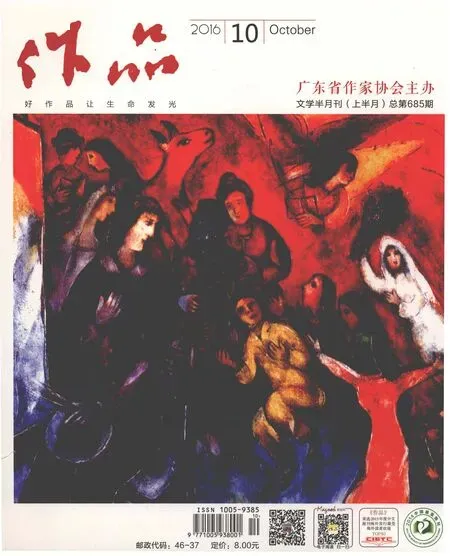背离是另一种抵达
文/杜永利
背离是另一种抵达
文/杜永利
杜永利男,1990年生,河南修武人,毕业于河南理工大学。作品见于《延河》《 美文》《佛山文艺》《 躬耕》等,曾获“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征文大赛散文组二等奖、诗歌组优秀奖。
一
争执后,父亲的屋子月光通透。
我辗转反侧,脊骨被凉席上的沙子不停磨削。我知道这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更多的沙子已经钻进父亲体内,长成他骨头的凸起。抽屉里的膏药暗藏止痛颗粒,它们已被放逐,对于一心挣钱的父亲来说,刮骨术更为直接。取出的珍珠质地密实,仿佛加了明确注解:脚手架上的父亲已不堪重负。
这些认错人的沙子不停尖叫,一遍遍加重我内心的悔恨。其实刚才我就后悔了。听到我的斥责,父亲颓丧地跌坐在地板上,往日的强势顷刻间瓦解。我没想到他会哭,他仰着脸,咧开嘴巴哭。他的两颗门牙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这种缺失像是无告的呼喊,我的强横就此陷落。他摇摇晃晃地走出去,坐在门口抽烟,母亲让我喊他进来,我却羞于开口。
我想他真的老了,时光替我夺下江山,却颠覆了整个世界的秩序。
二
之前父亲一直是强硬的,他是绝对权威的领导者。他握着瓦刀,在别人的工地不停垒砌,借此垒出一家人安身立命的砖房,以及我和弟弟迅速拔高的躯体。
那时候他年轻、脾气火爆,下工之后喝一瓶啤酒就能解乏,留下的力气用来同我母亲吵架。我和弟弟时常在摔锅砸碗的声响中溜出去,守在门口,等他睡了才敢溜进屋。我们因惧怕而疏远他,父爱成为成长之路的稀缺品。我在学校被污蔑偷钱,被老师搜身,被跟踪,委屈只能装在自己心里。他无意中得知后,也不管冤不冤枉,先操起擀面杖打一顿。又一次,我被同学整哭,含在嘴里玩的图钉不小心滑进肚里,事情被全村人知道,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送我去医院,而是用皮带抽我,因为我丢人了。
他的暴躁是我童年的巨大阴影,而他对读书无用论的迷信,则使我和弟弟的求学道路充满坎坷。也许是太穷了,他不给我们缴书费,借来的旧书版本不符合,害得我们常常跟不上讲课节奏。读完小学,他不愿意让我继续读书,母亲和他大吵一架,他把酒杯摔碎,溅湿了我的通知书。母亲只好请亲戚们游说,他方才松口。
他时常说:“上学有什么用?大街上擦皮鞋的都是大学生。”他的想法简单实际:读完初中回家挣钱,过几年娶媳妇,他就可以松口气了。在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像泄气的皮球一样,没有学习的动力。中考如他所愿,我落榜了,本来父亲已经决定让我去打工,英语老师却在这时候到访,她替我在父亲那里争取到复读的机会。从此我开始发奋,每天偷点蜡烛,和负责安全工作的校长打游击,冬天还在教室熬通宵,终于考上了高中。而两年后弟弟同样落榜,他运气不好,没能等到游说的老师。父亲说:“我不可能同时供你们俩读书,太累。”弟弟没有办法,只能听从安排,到小饭馆打杂去了。
弟弟的梦想是当画家和演员,可是有什么用呢?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出门前他把自己心爱的画册与颜料转手送人,只留几页画作在柜子顶层,目睹着时光的碎片对理想进行活埋。他在外面染了一头黄发,打了耳钉,以此填充青春期的空洞;他常常在后厨被教训,挨打之后灰溜溜离开,一分钱薪水也讨不回。他用人生第一桶金给父亲买了一条裤衩,还给我十块充当伙食费,我突然就哭起来,我们对不起他啊!他的前途被我们断送,他却傻兮兮地选择对我们好。
三
又过了几年,我们都到了快结婚的年龄,父亲开始利用一切空闲时间来添盖房子。他没有请工匠,仅仅依靠我母亲的协助。大夏天四十度的高温,别人都停工在家,他和我母亲却开车去装土;大冬天上冻,手都伸不开,他们却点上一盆锯末,忍着烟熏往墙上抹白灰……点点滴滴的时间被堆积起来,终于垒砌成了一整座崭新的庭院。到这里我们家就有两套房子了,我知道这是父亲给我留后路呢:读完书不还得回家种地?
他在我面前再也没提过读书无用论,却在背地里一再抱怨我母亲:“是你让他读书的,我倒要看看他能有什么出息。”闻知此事,我不敢选择文科了,大家都说文科找工作太难;在填报志愿时,我在汉语言文学这一栏停留几十秒,然后果断选择了热门的冶金、机械、采矿。我违背了自己的理想,想以此增加自己获胜的筹码。其实结局已定,父亲在起点就赢了,他在潜意识里对我指手画脚,我选择的永远是屈服。
而弟弟却选择了背离。父亲让他去学习安装铝合金门窗的手艺,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心想着去大城市闯荡。终于有一天,他的理想被快乐男声的报名消息唤醒了。他在母亲协助下偷运出一包粮食,换来路费,去西安参加海选。那时候我已经读大学了,看到他在空间发表的动态,真替他高兴。顽强的弟弟,这么多年过去了,残忍的现实没有磨灭你高贵的理想,反而使它熠熠生辉。当初我们信誓旦旦地说,一个当作家写剧本,另一个当明星来演主角,而现在呢,我每天学着毫无趣味的力学与绘图,早把理想弄丢了,寻梦的路上只剩下你一个人。
现实真的很残酷,没有出过远门的弟弟在海选时被评委耻笑:“你五音不全我就不说了,但作为中国人,你竟然连普通话的发音都不准……”弟弟愈挫愈勇,他用所剩无几的钱买了一张去成都的火车票。可悲的是海选依然没有通过。他没钱了,下一站要去哪里?走在成都的街头,他的眼里布满泪水。也许他想到了命运,想到了几年前如果中考成功,他在高中会不会选择当艺术生呢?也许他还恶狠狠地想到父亲,以及正在大学里养尊处优的我。想到两个“仇人”,他再一次拥有了力量。他把手机卖了30块钱,吃了一碗面,然后用最后的几块钱买刮刮乐。没错,他赢得了去往杭州的路费。
我不忍心再说下去了,你知道吗?结果和西安一模一样,我怀疑评委是同一个人,他和我弟弟上一辈子是冤家。什么叫山穷水尽?睡了这么多天大街,挨了这么多蚊子叮咬,忍受了一路的饥饿与冷嘲热讽,我的弟弟都没有半点动摇,可是这一次他却彻底动摇了。他用最后一块钱给我打电话:“哥,我想回家……” 我借了同学的钱给他打去。
我流了很多的泪,一直以来我都把他当成我活着的另一种方式,让他代替我去追逐梦想,可如今连他也动摇了。
四
母亲一直是父子矛盾的缓冲地带,她用柔弱来承受疼痛,竭力为儿子们争取成才的机会。她反对父亲的独裁,却没有多少话语权,父亲的一句醉话就能把她噎死:“有人养活饿不死的,你让他读书,你去挣学费啊!”母亲没有力气,也没有做生意的头脑,故此只能听凭父亲抱怨,然后偷偷流泪。
忍受久了,她也需要关爱。她不能去年迈的外公外婆那里告状,因为女儿家庭的不睦会使他们后悔不跌;我和弟弟飞走了,电话里一听见父亲的恶行就反感,母亲只好闭口不说;她只能选择邻居,那些听众的同情被她误认为是真心实意。殊不知,那些长舌妇惯于看笑话,惯于添油加醋,父亲的名声因此坏掉了。
日子就这样磕磕绊绊地过着。盖完房子,父亲继续为结婚的彩礼奔波劳碌。而我放弃了考研,开始找工作,大城市、高薪是我对工作的期许,这其中满含着我对父亲那句谶语的恐惧。弟弟从杭州归来后,并没有放弃明星梦,他在朋友的鼓动下跑到了大连。
各自忙活,原以为日子可以这样过下去,却被一个电话打破了平静。
电话是从大连那边打过来的,陌生人说弟弟蹭了他的车,必须掏出五千元作为赔偿,要是不给就卸掉一只胳膊,末尾是弟弟带着哭腔的自责。父亲气冲冲地摔了电话,母亲却吓得瘫软在沙发上。过了一会又打来电话,问卸掉右胳膊还是左胳膊,母亲一下子就哭了,央求他们千万别动手。父亲说他这是掉进传销了,别理他就好了,一旦得手他们会变本加厉的。道理都懂,可是放在一个母亲身上,她怎敢押上儿子的胳膊去赌一把?
母亲偷偷汇去了五千块钱,父亲知道后把家里的碗全部摔碎了。五千元可不是小数目,他一个人搬砖抹灰得干上好几个月呢。眼看着大儿子就要毕业了,结婚的彩礼还没备齐,谁家女儿愿意跟随他?父亲越想越气,但是事已至此,除了喝酒解愁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喝了很多酒,把母亲数落了一晚上。别人都劝说父亲赶紧去救人,而父亲却说:“打不通电话,世界那么大,我上哪找去?”他不再过问此事,依然累死累活地挣钱。而母亲却一遍一遍地拨打电话。我后来才知道这件事,父亲的冷漠让我直打哆嗦。
母亲受不了父亲的责备,只好去工地挣钱。她肠胃不好,为了不让工友说她“懒驴上磨屎尿多”,只好尽量少吃饭,因此时常挨饿。她太瘦小,即使非常卖力,仍然不能逃脱被嫌弃的命运。工头给她少开工资,工友给她脸色看,她都忍着。
我宁愿相信老天爷是善意的,他仅仅想借用疼痛来终结疼痛。那天架子倒了,母亲摔了下来,断掉两根肋骨。我从学校跑回家,问她为什么不住院,她只是沉默。我在工友那里问清了来龙去脉:包工头送她去医院,路上不断暗示,母亲领会了他的意思,在拍过片子之后居然顺从地回家了,而到了家里,父亲居然也选择了忍气吞声。我受不了,包工头怎么可以这样?为了自己少出钱,他居然忍心让我母亲受疼。我在电话里义愤填膺,母亲无力地走过来夺手机。我跑到院子里,母亲在屋里哭了。我听见她说:“得罪了他,我到哪里干活去?别人都不用我啊!”
原来如此,她想用自己的疼来保住工作机会!我慢慢挂了电话,几滴泪噼里啪啦滚下来。劝她瞒着工头去住院,她看了看父亲没说话。我知道了,那五千块还没挣回来呢。
此后的几个月,她用偏方来欺骗自己,偶尔买来排骨还不舍得吃,非要把肉留给我们。她很疼,手捂着右腹,躺不下去,整夜整夜地坐在沙发上。她的每一次喊疼都如刀片一样割着我的心,我想我总要自立的,到时候绝不会再让母亲受罪。
五
弟弟从传销窝点脱身了,他到了北京,靠跑龙套养活自己。他把自己上过的节目用截图发过来,画面中弟弟傻乐着,我却感到恓惶。他在电视里依然是观众,眼巴巴看着舞台上的主角,台上是某过气演员,他不甘心消失,花了钱请这档不知名娱乐节目炒作自己,而台下的都是五十块钱请来捧场的。我呢,我签到了一家车企,离家几个小时的车程,虽然不是大城市,但是工资还行。父亲到底输了,我没有沦落成擦鞋匠或者种地的。
我不知道父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显出老态的,在我发现的时候,他的老已经由动词变成名词,冒号之后是染发剂遮掩不住的白发、被岁月犁头深耕过的额头、膏药下磨损的膝关节与腕关节……坚硬的性格也出现了松动,他开始喜欢找我说话了。我怀疑那几次刮骨,不仅刮去了沙子化成的骨刺,也刮去了他体内石头般的沉默。我不习惯他柔软的表达,依然离他远远的。他会在父亲节用一整天来等我的电话,事后让母亲传达他的失落。
当然他依然是家里的权威,我时常对他进行冒犯,比如在他逼我相亲的时候,在他骂我读书读傻的时候。他仍然和母亲吵架,我一劝解他就对我开骂。我不想回家,在大四最后一个寒假选择了去昆山打工。我必须挣一笔钱来还助学贷款,因为毕业之后就要开始计算利息了。
过完年,父亲在一次大吵之后离开了家,他恶狠狠地说不会再回来了,让我母亲一个人过。我们母子俩在电话里笑,说早该如此,分开了才清净。
其实我们都误会了他,他不是被母亲气走的。两个月后我在做毕业设计,母亲告诉我他回来了。我隔了很久才抽空回家,没想到他躺在床上,两眼无光。见我进来,他让母亲给我拿出福建带回的特产,有槟榔和橄榄,也有即将腐坏的枇杷。这是他在火车上买的,一直不舍得吃,纵使放坏了也要等我回来。说话之间才知道他去了龙岩,那里一天可以挣两百,可惜一直下雨,没有几天可以出工。他在那里感染上了肺结核,不过已经快好了。
父亲因为我的到来而十分愉快,但是没多久又陷入了愁闷。母亲说不是因为病,而是因为惹上了麻烦。
眼见着雨没有停住的意思,父亲只好和工友商量好了一起回去。离开时,只要到一小部分工资。老板让集体办一张卡,没有人肯拿出身份证,除了父亲。这一部分钱打进了父亲的卡,回家后将要平分。父亲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骗局。
到家之后,父亲提议等工资全额到账后再分发,很多人不愿意,但是父亲一再坚持。期间有人向老板催要工资,老板说已经给过我父亲了,之后再也打不通电话。一伙人来到我家讨账,任凭父亲怎么辩解他们也不相信,还差点动起手来。他们的理由很充分:“难怪你一直不肯分钱,原来想独吞啊!”听到这里,我说可以去银行查账啊。母亲苦笑一声,查过了,他们非说也许用的是另一张卡,鬼才知道。
母亲压低了声音埋怨道:“烧包,别人都不掏身份证,他逞什么能呀?”
后来父亲病好了,他打算把家里的粮食都粜了,我帮忙往车上扛粮食。父亲说:“本来想借用他们的钱替你还贷款呢……”我的泪水不听话地落下去,染湿了一小片麻袋。
六
我毕业了,穿上蓝色工装,每天如蚂蚁一般蠕动在几千号工人的队伍里。每天过得很忙碌,但是下班之后却莫名其妙地涌起一阵空虚。有一天我突然想明白,这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打一开始就不应该荒废写作梦。后悔已经没有用,我只能从现在开始补救。
父亲那边也开始忙活,只要我回家,他就有说不完的话,主题永远都是泡妞攻略。他说:“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居然说机械行业碰不见女人!百合网不让你找?微信附近的人不让你约?世纪佳缘——”我打断他:“大街上的女人也多,我能看见一个就追一个吗?”把他晾在那里走了。
我只关心写作,其他的都被我排斥在外。错失了太多青春好时光,我只能这样使劲。父亲不可能支持我,不是吗?他从来都是按照自己的步骤来对我们进行培养,我读大学以及弟弟出逃仅仅是两场意外而已。如今我自立了,再也不愿受他的影响。
弟弟混成了跑龙套代理,需要一笔钱来扩大事业。他找到我借几千块,我不敢借给他。事情过去半年多了,我始终不能原谅自己。我拥有许多理由,比如害怕他又一次进传销呀,比如我攒钱只是为了凑个整数等过年时报答母亲呀,等等,这些理由都是真实的,也是充分的,却无力弥补我和弟弟之间的罅隙。
他两手空空回家了,穿的是离开时的那身破旧的袄子,肠胃也饿坏了,回到自己家居然也会水土不服。我给他买了一身羽绒服,他勉强接受下来,却不愿意同我说话。有天母亲让他去理发,他说没有钱,母亲给他钱,他不接,还用尖刻的语调挖苦:“千万别给我,我是无底洞。”这句话是父母一时的气话,弟弟确实也不小了,在别人眼里他符合不务正业者的所有特征。
我责备了几句,他离家出走了。羽绒服脱在床上,天蓝色的布面仿若童年时无忧的天空。一整晚我都睡不着,弟弟也是心重的人,我怕他想不开。其实兄弟反目的原因不在于借钱之事,母亲告诉我攀伟一直在挑拨是非。攀伟也没错,他只是说出了一个事实:“你爹和你哥都欠你的,别傻了,自己要争取。”攀伟的弟弟在市里娶了媳妇,房子是父母买的,一碗水没端平,攀伟一直想把他们撵到老二家里。我读大学时宁愿贷款也不愿花父亲的钱,正是出于这方面考虑,而父亲却用粮食取消了我在弟弟面前硬气说话的资格。
第二天是除夕,弟弟回来了,我和父母都很高兴。弟弟搬梯子贴对联,父亲让我去给弟弟递浆糊。太阳升起来,照亮了父亲的笑脸。他一定体会到了家人团结的幸福,所以不久之后他给弟弟买来了电脑,并且告诉他:“是你哥掏的钱。”弟弟的轻蔑响在鼻腔里。是的,我们想得太美了,以为这些小恩惠可以补救情感的债务。弟弟再也没碰过那件羽绒服,他也不和我同床了,自己搬进简陋的配房。这个年过得真不是滋味,如果时光倒流,我一定把上学的机会留给他。
七
父亲出钱让弟弟考驾照,他领情了;父亲托人给他说媒,他也积极响应。本来父亲的计划就要成功了,却被一场车祸搅了局。有时候生活充满了扯淡,让你难以接受,但是它非要那么真实且生硬地降临在你头顶,你除了接受还真是没有办法。
弟弟在去约会的路上撞了一个人,她再有十九天就要成婚了,而且有孕在身。弟弟把她扶起来,问清楚了没事才离开,谁料女子的公公生了歪心思,想借此捞一笔钱。很意外,父亲慷慨地掏出钱来,我甚至怀疑他有些庆幸,因为弟弟花的钱马上就要和我的学费持平了。
交清了钱,弟弟一头撞在门外的石磙上。一群人赶紧去拽他,幸亏没事。经此打击,他再也没心情待在家里。又一次他飞走了,到北京重操旧业。
父亲很生气,抱孙子的计划又落空了,他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背着我,他托媒人多次去说亲,女方都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同学,她们对我知根知底,对我们家又怀有深浅不一的鄙视,故而不可能同意的,到头来落了许多没趣。我知道了此事,越发对相亲反感,有段时间竟不想接他的电话。
我没想到他如此不堪一击,竟然会就此沉沦下去。邻居告诉我:“你爸每次去别人家随礼都喝得醉醺醺,回家后和你妈吵架,半夜大哭。”另一个邻居说:“你爸在小卖铺抱怨你们没本事,别人家的儿子都满街跑了,你们居然连个对象也找不到。抱怨完掏出一沓钱说,不过了,给我来最好的酒!”
这些都没什么的,我不能容忍的是,他拿走母亲的钱去KTV挥霍。母亲的肋骨愈合之后,又去了工地,她不堪重负,足跟骨很快长出骨刺,每天瘸着腿干活,老板快烦死她了。如此辛苦换来的钱,父亲居然忍心拿去唱歌。
就在刚才,我和父亲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冲突,他跟我说:“咱们这里也有歌厅啦!有个二十六的陪唱女,一会我们一起去,我跟你说啊——”
“别说了,是个女的就可以和我结婚吗?你想赶快松口气,你就是害怕自己累死,是吧!”
他跌坐在地板上,居然哭起来。
我妈让我去门口喊他,我不去。睡下后我十分后悔,其实父亲是非常老实的人,他去歌厅都是被工头拉去的,仅仅是唱歌罢了。他花母亲的钱只是为了还工友的情。就是在微微沉沦时,他想到的仍然是儿子的婚姻大事,这样的父亲,我竟然忍心伤害他……
我在床上想了很多往事,思前想后,觉得父亲只做错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爱错了方式。他用自己的方式给予我们一切,却没有收获预期的效果,爱灌溉出了恨,我们因爱而恨,或许也因恨而爱得更深沉、更不易察觉。这种爱就是棉被里的线,偶尔露出很小的一段,更多的却藏在棉花里,在千里冰封的季节率领棉花替我们默默抵御严寒。
我相信所有的背离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方向去奔赴,而最终我们必然会抵达共同的目的地,原因是我们拴在同一根柱子上,绕来绕去终究逃不出四个同心圆。我相信父亲终究会抱上孙子,那些他倾尽大半生力气想要得到的,只不过是绕了一段远路,它们终归会奔赴到父亲的手掌心。我相信飞走的弟弟会荣归故里,到时候他想要做的是向我和父亲炫耀,然后我们抱在一起痛哭,把所有的亏欠与恨意统统交给泪水……
八
父亲见我守在他床上,便在沙发上躺下了。
我一夜都担心他不能原谅我,但是第二天他却喊我起床吃早饭。我起来时他已经去工地了,桌子上放着小笼包,那是村口卖的,他一直舍不得吃的小笼包。
(责编:郑小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