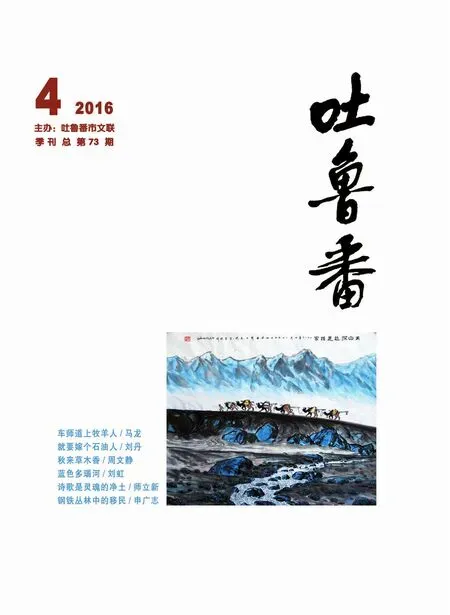风拍大西北
支禄
风拍大西北
支禄
鱼儿沟
鹰,拍打着翅膀。一拐,一下子飞进了一个人的骨头。
顿感,一阵口干舌燥,蚂蚁一样爬遍全身。
一棵草照样匆匆赶路。
一棵树,背着两三个干涩的果实,正气粗马吼地翻越了夏天。风来时,叶子哗哗地响着,像一个人大声地说:宁让牛挣死不能让车翻。
没有目光安慰的云朵,如此孤独,拄着风的拐杖,一高一低地能去到哪儿呢?
沙丘上,轻轻地一声咳嗽,就从高高的天空射杀一朵干渴的云。
干渴,像一道又一道闪电飞来,打在心上。
顿时,目光起飞了,像扇着翅膀的鸟,去遥远的雪山筑巢。
七克台
故事太多了,压着红柳翻不起身。
一棵草尖上,挑着神话国的狐狸精。
行走大漠,海市蜃楼来了。
等于一脚踏进秦汉的宫殿,坐在唐朝的阁楼上,听吹箫的女子,古典的一曲完了又吹一曲。
像是有水声哗哗地响着,让喊渴的沙子到死都不松手。
暴雨一样的阳光,压弯半个天空。
七克台,鹰的眼睛里住着一窝子传说。
七克台,一只羊让神话养着,翻年后就膘肥体壮。
七克台,一匹马奔跑成一朵火红的云朵才算奔跑,一堆篝火打一个响亮的唿哨,它们放慢脚步才收回肉体和骨头,像天空收回雷声和闪电。
在七克台,天空的蔚蓝从眼眶倒进去。
一下子才能镇住辽阔的戈壁。
风起
正午,又起风了。
辽阔的塔克拉玛干大漠汹涌着无边无际的荒凉。
天边边上,一头毛驴拉着车颤悠悠地跑来。
一路上,晃荡起淡淡的沙尘,像一条丝巾向着辽远的天空甩去。远远地,太阳也在那缕沙尘上跳荡。
此刻,买买提·卡德尔大叔怀抱一把镰刀沿着大唐的烽燧小跑而来。
雪山样的刃口闪出三四处光点像三四个小太阳不停地闪亮。细细一看,宛若内心久存的玻璃碎片让风一下子吹了出来。
荒凉好重啊!
一丁点落在买买提·卡德尔大叔的心里,大叔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趔趄,一刃锋利就划破头顶的钢蓝。
顿时,天空流云乱溅。
鹰,像鬼样在云朵里探头探脑。
当风,把鹰的翎羽吹成一天空的黑云,雷鸣闪电就来了。不论鹰走到哪里,闪电的鞭子总是够着鹰。
那么大的天空,鹰却无处躲藏。
哎!大漠中,其实鹰的日子也不好过。
鹰
鹰,长长的尖叫一声。
一把黑色的刀子,扔向天空。划出一道长长的口子,顿时,雷鸣电闪,暴雨砸向那拉提河的两岸。
车行草原。雨雾连天。
鹰站立过的石头,如一只只白羊让浪涛赶进了河水;鹰站立过的树木,让风雨连根拔起,纷纷下水;鹰站立的山头,让雨雾死死地裹着。
而鹰,在哪?
当电光鞭子一样劈开云朵的那刻,我看清:
鹰,在风雨中,把翅膀练成剪刀。
鹰,在狂风中,把骨头飞成刀子。
鹰,在黑夜中,血肉河流样哗响。
一场暴风雨,就是天赐给鹰的磨刀石。
世间万物,雷电才配做鹰的磨刀石。
多少枯骨,锯末一样纷纷而下。
多少坏了的翎羽,麦草一样纷纷而下。
多少衰老的血肉,如水而去。
暴风雨中,鹰在提炼生命的精华,鹰用电闪雷鸣在不断完整自己。
鹰要用翅膀,飞出另一座灵魂的草原。
饮酒
几个走远路的人,饮酒烽火台下。
“四季红”“五魁首”……一个个雷霆似的喊着酒令。
夜越来越深,众人的喧哗让一条蜥蜴无法入睡,就从库木塔格沙漠深处跑来助兴。
蜥蜴在月光中,来回飘过。
就像鬼影一样,忽来闪去。
此刻,唐朝的鬼、宋朝的鬼从沙丘后面灰头灰脑地出来,一个个诡秘地望着我们。荒漠中,一年四季喝着西北风,这次总算沾了点酒味。
听到酒令声,楼兰女也从遥远的罗布泊出发,一路上艳丽的衣襟飘成波浪状拂过高高的星群。
片刻而至,她古典地斟酒,我们满口说着大话。
她美丽的脸宛如三月的桃花开在黑夜的枝干上,一次次芬芳着悠远的传说。
当年的烽火台台长也从夜色中沧桑地站起,想起多少驼队让风吹成了一把把的沙子,一个名叫楼兰的古国让风像吹起纸片般从此了无影踪……
此刻,一个劲儿唏嘘不已。
马帮、商旅、剑客……在月光下一一复活。回望北方,让风不停地吹着多毛的胸部,像吹着一滩滩荒草。
后半夜,一个个醉卧成一座座沙丘。
天狼星高高地、温情地注视着。
白克力·艾海提指着天边的一朵云深情地说:“楼兰国就在那朵云的后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