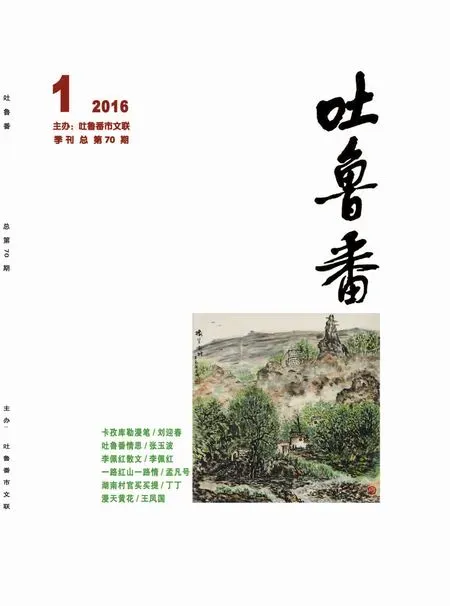想起那棵老桑树
卢柏莉
想起那棵老桑树
卢柏莉
记得小时候起,我家门口的马路边,一年四季都站着一棵老桑树,巍巍然横跨整个路面,并将部分树梢搭在一户人家的院墙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凉棚。它的支撑着沉重树冠的枝干并不高大,甚至有些部分还弯曲得厉害,像个佝偻着身体的老人。两三人合抱那么粗的主干上,逡裂的树皮沟壑纵横,上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疙疤,疙疤处隆起一团皱巴巴的皮,活像一只只目光慈祥的眼,含着一丝温和笑意的眼,为我们上学时迎来送往的眼,每与其对视,总有点点温暖阳光般在心尖儿上抚慰。树的底部不知是腐朽了,还是小孩子的所为,形成了一个门似的大洞,我们常躲在里面密谋几个小小恶作剧,然后笑翻在地,在老桑树的脚背上打滚。老桑树的树冠并不显老,总是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稳稳当当铺展得很开,密密实实铺展得很均匀,就像一位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的老奶奶,端庄而体面。
民间有个说法:“前不栽桑,后不栽柳,院中不栽呱哒手。”父母这样告诉我,是为了解释为什么我家的院子里没有大桑树“桑”与“丧”音近,民间忌讳其不吉利;“柳”与“流”音近,有金银财宝流出之嫌,因此汉族人的庭院里,门前是绝不会见到桑树的,当然这些都是迷信的说法,我是不会相信的,但小小的我改变不了大人们的思想。在托克逊,维吾尔族人却恰恰相反,他们酷爱桑树,家家院子里前前后后都会种几棵大桑树,有结黑桑子的,有结白桑子的,也有结紫桑子的。维吾尔族人对桑树的喜爱是怀着一种敬意的,有时生产队分地盖房子,假如这块地里有一棵大桑树,维吾尔族人是绝不会砍掉它的,因此在我们这里的农户家里,经常可以看到屋顶长树的奇观。真正让我羡慕不已的是我的小邻居祖木热提古丽,她家的屋子里就有这样一棵好得不得了的大桑树,这棵树的身子在她家盘的土炕边,而巨大的树冠则撑在屋顶外的整个上空,像一把太阳伞,祖木热提古丽说起他家人躺在屋顶上桑子自己往嘴里掉的时候,我羡慕的口水直往肚里流,眼红的要冒火。更让我眼热的还是她家里的那部分,树身靠近屋顶的地方,有一截粗大的树干斜向旁边,因为在屋子里不见阳光的缘故,上面只稀稀拉拉长了几片黄绿色的小叶子,而她慈爱可亲的阿塔,用一根拴驴的长绳子搭到树干上,下面两端固定住一个自制的小木凳,祖木热提古丽在上面就荡起了秋千,想荡多久荡多久,甚至可以在秋千上睡觉。晚上躺在妈妈身边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经常浮现祖木热提古丽坐在秋千上甜甜入睡的样子,家里有桑树真好,我甚至产生想成为她家人的念头。幸亏我聪明能干的老爹猜透了我的心思,及时拿一根粗绳在我家门口马路边那棵老桑树上也做了一个秋千,才打消了我大义灭亲的想法。后来又有好几个秋千在老桑树身上安了家,这里成了我们的乐园。
马路边的那棵老桑树结的是紫桑子,据说是吾甫尔队长的爷爷年轻时种下的,现在已经100多岁了。听说当年吾甫尔年轻聪明的爷爷突发奇想,决定搞桑树嫁接的实验。春天乃万物生发之际,他选中一棵两岁的结黑桑子的小树,用宰羊的刀子,割掉树干1.5米以上的小树冠,在这棵树干割口处的皮层里,转圈插进几根结过又大又甜的白桑子的鲜活枝条,然后用湿泥糊在接口处,再用稻草裹住,最后用布条子缠几圈绑好,小树像个因贪玩摔断了胳膊被打上了石膏的孩子。一个夏天过去了,接上去的枝条居然长满了一片片手掌似的叶子。两年后,嫁接过的小桑树长到了碗口粗,结出了一颗颗又大又长的紫色桑子,这种桑子完全没有了黑桑子的酸,也不像白桑子那么甜的腻人,清甜之中还透着淡淡的玫瑰花香,深得各族村民的喜爱,因此家家效仿、家家种植,家家在青黄不接的春天里,就都拥有了一段甜蜜的生活。现在这种桑树在托克逊已经形成连网式绿化带,无论西去乌鲁木齐还是东到吐鲁番,所经之处、沿途两边都能看到整齐密集的桑树林。而那棵老桑树依然站在我家门前的马路边,没有离开过一步。想起那棵老桑树,耳边似乎又传来儿童清脆放肆的笑声,鼻尖又有淡淡的玫瑰香味萦绕不绝,而对老桑树一年四季的记忆也在脑海中清晰地再现。
桑子是托克逊熟的最早的水果,它成熟在春天里。当你欣赏完了美丽的杏花、桃花、沙枣花;当你品尝了鲜嫩的蒸榆钱、蒸苜蓿、蒸槐花;当你参加了植树、拔草、种棉花,热出捂了一冬的臭汗后,下意识地躲进老桑树凉爽宜人的身影下,一抬头便发现了几颗泛着粉红色的小桑果儿,于是你惊叹:“哟,桑子要熟了。”桑子熟了,老桑树下就热闹起来了,大人小孩儿都来吃桑子。大人一般会站在树下,随手拉下一枝来,摘一颗习惯性地吹一下浮在上面的尘土,然后从容的塞进嘴里,一丝清凉的甘甜便顺着干渴的喉咙沁入心脾。小孩子们则会爬到树上去,找个安全又舒适的树杈,骑坐上去,晃悠着两只小脚丫,一大把一大把地往嘴里捂,直到吃饱了才肯离开。有些维族洋冈子不敢爬树,就给小孩子一根长棍,让他们在树上敲,她们则扯个大花床单在树下接。不知哪个调皮孩子脚下使劲一跺,满树的桑子便下雨似的往下落,砸在大花床单上,砸在花头巾裹着的脑壳上,树上树下就荡漾起一串串清脆的笑声,让老桑树下忽然变得有趣起来,男女越聚越多,都来帮忙接桑子。老桑树像个疼爱子孙的老人,总在第二天人们来到之前,又准备好一树的熟桑子,让人们天天吃却总也吃不完。
炎热的夏季,村子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喜欢聚在老桑树下纳凉,维族洋冈子最勤快,她们会树下打扫得干干净净,再用葫芦瓢均匀地洒上水,然后把家里的大毡拿来铺上,各族巴郎子就都爬到上面打滚。嘻嘻嘻……哈哈哈……说也好,比划也好,语言通不通无所谓,开心的笑容一样的灿烂。男人们扎堆儿打牌、吹牛,光着脊梁的上半身,健壮的肌肉伸伸缩缩地跳动。女人们纳着鞋底东家长西家短地闲扯,手里的顶针闪着银光,上下飞舞,时不时拿针尖在头发里摩擦摩擦,好像这样针尖更容易穿透厚实的鞋底。好多维族洋冈子就是在这棵老桑树下跟着汉族老婆子学会了做鞋,给自己的男人做,给自己的巴郎子做,也给自己的阿塔阿帕做,维族男人的脸上洋溢着知足的笑容。老年人们最悠闲,拿个蒲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拍打裸露着的静脉曲张的双腿,闲散的目光一会儿看看这儿,一会儿看看那儿,有时忽然地冒出一句自言自语,只有他们自己听得到、听得懂。
到了秋天,五谷成熟、瓜果飘香,大人小孩都奔瓜地、葡萄园去了,老桑树就一声不吭地瞅着脚底下蚂蚁搬家。就在人们将雪白的棉花采尽,将硕大的高粱头搬到大场上去晒,将豆啦、果啦都收回家的时候,霜降了,老桑树的叶子一夜之间变得金黄,噼噼啵啵往下落,树下就像铺了一张黄绒绒的大地毯。这时候,养了牛羊的人家拿着扫帚、口袋来了,装金装银似的把树叶扫回去,牛羊一冬的口粮准备妥当了,这一个冬天便过得很安心。老桑树一片叶子都不会保留。
冬天,是不怎么会有人顾及到老桑树的,只有老尼亚孜每天会去给拴在树下的老牛丢一些干草,然后就由着它自己吃自己反刍,自己把自己拉的牛粪在树根部踩得稀巴烂。老桑树呢,赤裸着全身一无遮挡,我以为它会孤独,我以为它会难过,其实不然。你看,一群麻雀落在它的肩上,多像一片片奇特的树叶,一片片能飞去飞回的树叶。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分明听到了微风中,老桑树呜呜呵呵的笑声……
虽然离开小坎子村近20年了,那棵老桑树却如刻痕般留在了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