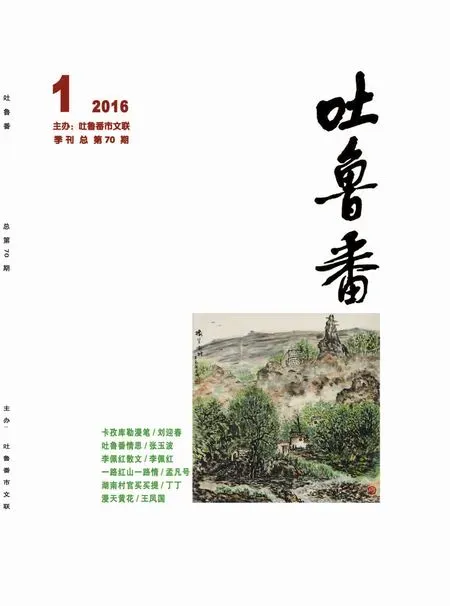筑巢容易比翼难——《空巢婚姻》守空巢的三代女人
赵海燕
筑巢容易比翼难——《空巢婚姻》守空巢的三代女人
赵海燕
“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自古以来,鸳鸯就被中国人视为忠贞爱情的象征。事实上,“鸳鸯双栖蝶双飞”的诗意美景背后,并不是纯贞浪漫。鸳鸯不过是一种“吃饱喝足”后就一拍两散的风流种。而对于人类来说,伴侣长久的恩爱甜蜜,是不变的梦想。简媛的长篇《空巢婚姻》,从女人的视角,从三代女人身上描绘了这个梦想要照进现实的艰难。
小说的主角是胡静。但她的母亲胡丫、外祖母姚澡花,一样品尝着婚姻中“空巢”的苦果。姚澡花是怀着胡丫就守了寡,因为世俗迷信而没能改嫁,年纪轻轻就带着遗腹子守了几十年寡,为了生存,她成了村长的姘妇。可以说,她主要是社会恶习下的牺牲品,在旧时的封建制度下,充当了牺牲品的女性可以说是尸骨累累。
第二代的胡丫是红旗下产的蛋,自我意识已经苏醒,有着强烈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抗争意识。她认为自己的不幸是环境使然,于是费尽心机攀上了有回城机会的知青白宁,但城市并没有让如愿以偿,城市生活现实与她的幻想之间的差距,造成她心理上极度的失衡。胡丫身上厚重的怨气,使得白宁不再敢靠近她。于是,虽然婚姻存在,但她却成了实际上的活寡妇。胡丫是作者在三代女性中塑造最成功的一个角色,我们在现实中四处可见“胡丫”——守着名存实亡的婚姻,满腹牢骚,用力把自己极为在乎的男人往外推而不自知,一旦男人表示要解除婚姻,马上就极度恐慌,抓住婚姻的空壳死死不放。“胡丫”们在家里保持着强势的面孔——比如书中胡丫让独生女跟自己姓,但这种强势正是心虚无安全感的弱势体现。
第三代人胡静,是文革结束后一代女性的代表。这一代女性,仍保留着传统道德观的影响,重视婚姻里身体的忠贞,同时面对着整个社会更大的诱惑,这种矛盾的交织使得人物格外纠结。与母辈和祖辈不同的是,胡静的空巢是社会资源更开放后的产物。小说中有着强烈的时代烙印:现在的70后80后甚至90后确实都面临着事业与亲人如何平衡的世纪难题。男人们从原始社会起就肩负猎食大任,这是维护家庭稳定与延续的物质基础。“狩猎”战利品的丰厚程度,成了评定男人能力的标杆。因此,越来越多的男人摩拳擦掌地涌向“猎物”更集中的地方。城市如此,农村如此,这也是社会上形成各类贫富阶层不等的留守儿童的原因。胡静的家庭,是这个时代背景下比较典型的一类空巢家庭。
胡静的丈夫王国庆,为了自己的事业远行千里,留下年轻的妻子独守空房。胡静作为新女性,虽然在情感上对丈夫有依恋,但还没到想把自己的事业抛下去追随男人的地步。对于分居两地的夫妻来说,距离是最大的考验。生活上需要照应是一方面,比如孩子有病痛时做母亲的特别需要援手。心灵上的支持也是一方面,遇到工作上的打击,会希望有亲人陪伴和倾听自己的难过。肉体上的寂寞更是不言而喻,正当壮年生理正常的中青年男女,都会有起码的性需求。于是,作为男人的王国庆也好,作为女人的胡静也好,都面对着来自外界的诱惑,得承受心底的煎熬。
书中除了胡静式的空巢,还有李岚式的空巢——身为小三无名无份地与有妇之夫偷享鱼水之欢,灵魂无从寄托婚姻也无归宿;还有苏芬和诺纤式的空巢——远在异国,干脆背叛丈夫悍然投入新欢怀抱。无论哪种,迷局只能由当事人自己走出来。这都是女性视角的空巢迷局。作者身为女人,有着女性视角独到的纤细敏感。相比之下,与胡静演对手戏的几个男性角色的塑造相对薄弱。
筑巢虽辛苦,比翼守巢却更难。这是这部叙事平缓严谨的小说里揭示的一个现实。作者的笔触及的不只是同时代的胡静,也囊括了前面两代,这就在讨论女性的生命意义更为立体。在心理学上有个术语,原生家庭。每个人身上的生命轨迹都逃离不了原生家庭刻下的烙印,有时甚至在无意识地复制长辈。胡丫有意识地反抗,但却逃不过实际的孤寡魔爪;胡静有学识有素质,但也有跨不过的心理障碍,母亲会间歇性的精神病发作,而她自己也遭受了抑郁症的打击。幸运的是,到胡静这儿,她对自己反省得更为深刻,更多地从自身来寻找解救之道,而不是把自己拴死在男人身上。这样就有了逃脱怪圈的可能。
不管处于什么婚姻状态的人,在追随人物的悲喜时,都值得观照角色思考自身。故事最后展现的镜头是温暖的,阳光的,充满希望,也是对所有婚姻的善意祝福。
《空巢婚姻》内容简介:
小说以独特视角展现了在中国历史变迁中,身处不同时代的三个空巢女人的命运。三十年代出生的姚澡花,五十年代出生的胡丫,七十年代出生的胡静,她们骨子里都深埋着对生命的坚韧,痛恨与冷眼旁观一切,所有一切都围绕着三代空巢女人的情感波折进行。她们都坚守着自己对生命的判断,冷静而又尖锐地面对生活以及所有。
随着外出打工人员的增多,尤其是从事路桥、水电,建筑、铁路、勘探等行业,留守妇幼、老人逐年增多。空巢家庭的产生已经成为越来越受重视的社会现象。全文跨越半个多世纪之久,用一家三代女人相似的悲凉命运向读者诉说着女人挑起家庭的重担的种种辛酸和不易,深刻揭露了社会现实,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