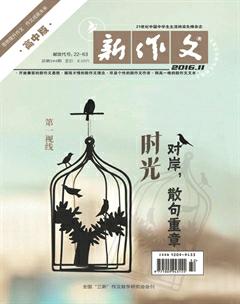寻常物的不寻常
高临阳
不久前,我在潍坊拍一部关于老风筝艺人的纪录片,主人公叫杨红卫,是杨氏风筝第十四代传人。杨家不仅做风筝,还要保证每只卖出去的风筝都能飞上天,因此经手的每只风筝都要试飞,是放风筝的好手。拍摄间隙闲聊时,她无意中提起一个发现。放飞时,当风筝飞到一定高度,弹拨风筝线,可以听到古筝般的弦音。她推测,这是风筝之所以取“筝”字的原因。
这件事一下子震慑到我,有两个原因。一来风筝不是什么稀罕物件,我从小就会玩,但似乎从来未想过风筝为何叫风筝。二来我回去翻阅资料,发现主流看法认为最初风筝叫纸鸢,后在纸鸢上面挂竹弦,风力强大时,竹弦会发出筝音,所以才改名为风筝。但在我看来,杨老师的经验在视觉上更贴切,即使这个说法并未流传开来。
风筝是寻常的,但当它与古筝产生了这种联结时,开始变得不再寻常。我沿着杨老师的思路乱想,是否有可能让风筝真正变为一种乐器,甚至举办一场风筝演奏会?通过控制风速风量,让乐手弹拨线绳发出音响。倘若成真,也许音乐史也会改写。这件事促发我想聊聊,写作中寻常物的不寻常。
从小老师就教导我们,写作要从水滴中见太阳,意思要窥一斑而知全豹。我当时就想,如果阴天没太阳呢?水滴是否一定要见太阳?单聊水滴不可以吗?写作其实可以轻松些,把宏大的意义先搁置,先看水滴本身,就充满着变化。连一个字看久了,这个字都会陌生起来。水本身,也可以不寻常。
在蔡明亮的电影中,水不寻常。他的电影,到处在漏水。天漏水(下雨),天花板漏水,地板漏水,身体也漏水(出汗、排泄与哭泣)。水原本很寻常,但当水无处不在时,水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水。我在台北生活近半年,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城市都在下雨。也许这种潮湿的天气赋予蔡明亮一种灵感,让他的电影也永远是湿漉漉的。但与此同时,他电影中的人物,又时常处于一种干渴的状态,渴望水,渴望摩擦出有效的戏剧反应。水有浮力,他电影中的人,也常处于漂浮状态。这种漂浮,依托于他电影中的水。水最原始的功能在他的电影中被降低,而成为其人物的底色。除了水,他的电影还有许多寻常物,常散发出另类的光芒。高丽菜寻常,西瓜寻常,但他把这些物体“身体”化,比如他在《爱情万岁》中给西瓜挖出两个眼睛,在《郊游》中给高丽菜画上表情,西瓜和高丽菜被塑造成人。在他设置的语境中,孤独的概念在西瓜和高丽菜中无中生有。西瓜之后又可以被当成保龄球抛掷,高丽菜又被当作食物啃咬,这些寻常物由于属性一直在流动,变得不再寻常。尤其是西瓜,在蔡明亮的镜头下,西瓜不仅是西瓜,它的每条纹路都特立独行。当西瓜处于不同的位置时,西瓜也开始为不同身份代言。在《天边一朵云》与《爱情万岁》中,西瓜被不同程度地赋予了身体。这可能也与他喜欢水有关,毕竟西瓜是水分最多的水果。
除了物件,寻常的空间,有时可以显得极不寻常。一个冬夜,我和朋友在北京郊区常营附近压马路,在路边看见一家烧烤摊。摊位很简易,只用蓝塑料布搭了个棚子,旁边停着一辆废弃的公交车。棚子里人差不多满了,我问老板,还有位置么?老板指了指那辆公交车。原来那里面才是主战场。车里的椅子被拆卸掉,改装成一个吃饭的地方。一个寻常的空间,因为功能的转换,立刻显得荒诞与怪异,但别有一番风情。冬夜在一辆公交车里吃烧烤,热气往窗户上扑,觉得自己好像在印度开个大篷车,吃饭好像流浪。即使在一个普通空间,也可能因为光线的变化而显得不同。一个无聊的人,如果对光产生兴趣,他的生活就会丰满而充实。你想想,你一生曾经路过多少影子,如果你逮住那些影子,去观察一个空间内光的来源,光的路径,尘埃在光中的变化,一个无聊的人就会变为掌握无数秘密的说书人。光让一个空间有了呼吸,不再死气沉沉。影子在跳,在躲,在爬,空间不再是空的,而满了起来。光让一个寻常物不再寻常。对于写作来说,发现事物的光同样重要。
写作前,有必要确立一个常识,就是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寻常物。就像凡人本身是一个伪词,哪里有真正的凡人?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敢把自己完全地呈现给你,都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小说或纪录片。杜海滨导演有一部纪录片叫《石山》,讲一群东北的农民工开采石头的生活。乍看,影片如开凿这个动作本身一样,机械重复,但看久了,尤其是影片最后,一个大哥将一年辛苦劳动的工资砸进妻子高昂的医药费时,回头再看工人周而复始的开凿过程,会发现他们凿出了生活的荒谬与无力。这些工人在烈日下映在石头上的影子,像极了西绪弗斯。他们是我们每天路上遇到的工人,不曾留意的工人,形同陌路的工人,也就是所谓的凡人,但那种力量让我张大了嘴,我不敢再错过任何寻常。换句话说,哪有真的平凡?所谓的平凡,只是相对于改造外在世界而言的,有人贡献大,有人贡献小,贡献小的显得平凡。但对写作而言,这种贡献不是写作的标准。写作是挖掘。贡献可能是一个人在海平面上所露出的高度,挖掘是去探求海平面下的深度,深度与高度不存在正比关系,不是高度越高,深度就越深。人性的幽深,是永远的未知。在一个寺庙的住持都可能是在逃杀人犯的世界里,写作的意义与高度无关,与深度密切相关。
尿池极其寻常,但当尿池被杜尚扛进美术馆,就变得不再寻常。文艺理论家丹托在《寻常物的嬗变》中,以杜尚的尿池为引线,考究了艺术与实物的区别,追问艺术的魔力到底在哪里,让寻常物不再寻常。而在文学史中,对寻常与不寻常,描述最精准的理论来自俄国形式主义理论提出的陌生化概念。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说:“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 感觉到事物的存在, 为了使石头成为石头, 才存在所谓的艺术。艺术的目的是要使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手法就是使对象变得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为达到这种陌生化,写作者可以通过各种修辞隐喻,反常间离等种种手段达到陌生化的效果,让寻常显得不寻常。陌生化属于方法,它与定位寻常物的不寻常同样重要。
寻常物的不寻常,对主体来说,是一次考古,对客体来说,是一次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