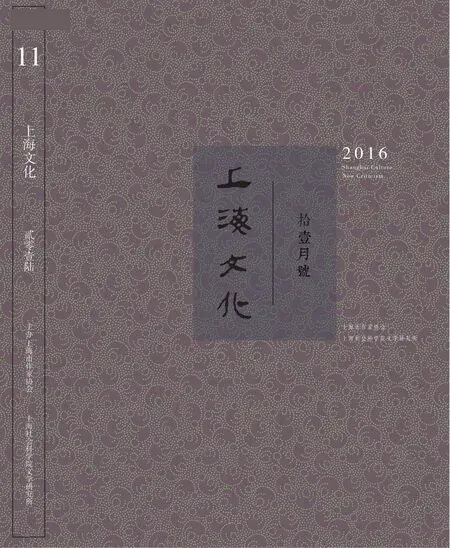“窗”在里尔克作品中的诗学含义
唐际明
“窗”在里尔克作品中的诗学含义
唐际明
前 言
1920年8月27日,里尔克在给友人纳莉·温德李-沃卡特(Nanny Wunderly-Volkart)的信中写道:
有谁来写篇窗的故事啊——这个圈出我们居家存在的奇异之框,也许是真正能衡量它的尺度,满满一盈窗,总是一扇又一扇汲满景物之窗,我们自这世上不可能再收获更丰了;而我们各自拥有的窗形又怎样影响了我们的性情啊:囚徒之窗、宫殿之窗、舷窗、阁楼天窗、大教堂的玫瑰窗——这些不正等同于我们天性会产生的如许希望、前景、振奋与未来吗?
其实,里尔克自己在抒发这个感叹之后的诗作,再加上之前的作品,就替“窗”写了篇动人的故事了。这个其重要性最迟自西方浪漫主义开始益加突显的文艺作品主题,不仅贯穿里尔克的创作生涯,甚至还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可以想见是因为长年在窗边书桌前的创作经验,让诗人深刻体认到“窗”的不可或缺。而诗人的书信则透露了“窗”在他眼中之所以重要,主要在于其延展空间的功能。在写作与阅读的时候,诗人希望透过身边的窗子看见的是远方,是能抚慰人心的自然风光。他毫无窥视他人家居生活的心态与藉此寻找创作题材的念头。在耗费诗人十年心血,而于1922年始完成的毕生巨作《杜伊诺哀歌》(DuineserElegien)之后,里尔克在晚年还以法语撰写多首诗歌作品,包括了十三首以“窗”为主题的诗作,这些作品——三首写作于1924年夏季,另外十首则完成于1926年春季——之诞生,定居于巴黎的波兰籍犹太裔女画家芭拉汀·克罗索薇丝卡(Baladine Klossowska)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1920年8月底,诗人和这位对他晚期的创作与生活施以重要影响的情人同赴德国弗莱堡旅游,两人在当地兴起共同创作一本“窗”
的图文诗集之念头,本文一开头引用的信函即是书写于此时间点。后来,在克罗索薇丝卡的提醒与督促之下,诗人又重拾这个计划,惜最后仍未能完成此“爱之效劳”,即于1926年底因病辞世。LesFenêtres这部诗集因此是由女画家选诗,编排,加上插画,来年在巴黎出版问世。这十三首法语诗作与同期写就的一首德语诗,其首句为:“早已,脱离我们尘居者,移至繁星之下的”(“Längst,vonunsWohnendenfort,unterdieSterneversetztes”),则不可避免地成为“窗”带给诗人启示的最终纪录。我们看到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再熟悉不过之物成为象征人类存在的符号。
藉 意
“藉意”这个诗学概念基本上师承象征主义的诗观,其中心主旨是藉由描绘外在世界来反映诗人的内心世界。里尔克早年作品中出现的“窗”往往直接取自个人经验,而且多涉及过往。我们看见年轻诗人写触发三十年战争的窗,写意大利作家西尔维奥·佩利科(Silvio Pellico,1789-1854) 的窗,①写古老建筑物上的窗子,例如:座落于布拉格城堡区(Hradschin)的哥特式大教堂圣维特(St. Veit)之窗、无人居住的宫殿之窗、或者这个废弃的城堡之窗:
一座城堡。大门上
悬挂着腐朽的徽章
其上伸出树梢
似祈求的手。
在慢慢塌陷的
窗里,升起一朵
耀眼的蓝花展现风姿。
未见哭泣的女人——
它是这栋残破的建筑物里
最后的挥手致意者。
诗人的童年之窗也会入诗,比方出现在这首1897年写就的无题诗,其首句为《而我的母亲当时十分年轻》(UndmeineMutterwarsehrjung):
我时常在秋天目睹
她的双手如何温柔地
在窗台上忙碌着;可怜的
杜鹃花却从不为她绽放。
或者是在下面这首对本文的主题而言更值得加以留意的诗作《我出生的房子》(MeinGeburtshaus)里:
熟悉的童年房子
未被记忆所遗漏,
我在那儿的蓝丝绸
沙龙里翻阅图画书。
……
在那里我追随
莫名所以的招唤写诗
还坐在窗阶上
玩缆车或小舟。
歌德在自传《诗与真》(DichtungundWahrheit)里同样也写到自己的童年之窗,他回忆少时独自待在面向阳台花园的房间里,透过窗子眺望远方的景色、变化万千的夕霞、与邻居孩童的嬉戏,从而自觉到自身的与众不同。如果歌德以及里尔克皆将最初于窗边度过时光的经历与后来的写作生涯连结在一起,这应当不是巧合。倘若他们幼时仅是依照直觉行事,到了年长必定在其中看出诗人这个职业与“窗”之间的深刻关联。“窗”不只引导他们观察外界,还刺激他们的想象力。
当里尔克在1903年写下下面这两句诗行时,极有可能是在回忆自己的童年:
那儿的孩童俱在窗阶上长大,
总有同样的阴影落于其上
诗人后来以法语为“窗”赋诗时,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再度上演:
沉醉于莫名的无聊里
小孩斜倚着呆在那儿;
他在做梦……②
与浪漫主义的文艺作品相仿,里尔克早期的“窗”也常笼罩在渴望的氛围下。而这些从窗子后面或者是对准特定的窗子所抒发的渴望,又多与诗人切身相关。在一首题献给早熟的天才诗人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1929)的诗里,灯火辉煌的皇宫所象征的是高度的艺术成就,是当时诗艺尚未成熟,站在“窗外”的作者所向往的对象:
在宫殿里与红木管乐器相伴
我多么希望成为他们今晚的座上宾。
窗牖灿亮,帘褶低垂,
我洁白的愿望招唤
我踏出壁炉火焰熊熊燃烧的宫殿。
至于《吉普赛男孩之歌》(LiederndesZigeunerknaben)里出现的“我”,乍看之下似乎是在渴望酒馆内洋溢的温暖与舒适:
发自灯盏的明灿光芒
透过窗子投下光线
我总站在门外,
满怀渴望地往里瞧。
事实上,如接下来的诗句所揭露的,“我”渴视的对象是酒馆内跳舞的女孩们。同样地,年轻诗人投向窗的渴视也多发自爱情,并显露出将自身的渴望投射给植物或者鸟类之倾向。我们看到他写常春藤满怀渴望地爬上情人的窗子,以及“我”的渴望如何引导小鸟飞向情人的窗子,将爱的信息传递给她。引人注意的还有,里尔克的窗自始即与女人密切相关,诗人认为窗框具有使身在其中的女人更加美丽的作用,还能成就她的不朽。
此时期的里尔克如何倾向于将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画上等号,也可在《梦》(Träumen)一诗里得到印证。我们看到诗中的“我”视被上帝遗弃,窗子也被狂风打破的小教堂为自己的心:
我的心彷佛是被遗弃的小教堂;
狂野的五月天在祭坛上大肆吹嘘。
暴风,这个盛气凌人的小伙子,
早将小窗子打破了。
而在甫出版即成为畅销书的叙事谣曲《旗手克里斯托弗·里尔克的爱与死》(DieWeisevonLiebeundToddesCornetsChristophRilke)里,则出现了会尖叫的窗子。诗中控诉旗手为体验爱情而玩忽职守的,并非他的军中同袍,反倒是窗:
是窗在尖叫。它们尖叫,红,喊声直入外头的敌军阵营里,他们环伺于火光闪烁的大地上,它们尖叫着:失火。
我们看到窗在这里如何取代人类主动表达感情。而在《观看者》(DerSchauende)一诗中,其实不是易受惊吓的窗子,而是被喻为“恐惧诗人”的里尔克自己害怕暴风雨的来袭:
我在群树里看见风暴
自变暖和的日子迈出
拍打我易受惊吓的窗子,
一边倾听远方在诉说。
最后,在题为《歌》(Lied) 的诗作中,窗框内所见的花园正是屋内情侣关系的真实写照:
窗前的花园
仅是一幅
无止尽的绿景,
让我俩在其间绽放。
赐福予其感官的
被冬季覆盖其上的:
也于我们的年岁间
日照及冥想与落雨。
花园有其法则,
恰似我与你:
两株拔伸的灌木
向彼此绽放。
总是出现在这对情侣眼前的花园宛若是他们爱情的教科书,诱导他们效法自身依遵的法则,以让爱情能够无止尽地成长茁壮。我们看到在这里虽存有窗内与窗外两个世界,但实际上它们是合一的。
以上这些诗例皆指明了里尔克早期的作品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必须要等到他克服了此种倾向,才迈入成熟的创作阶段。
物
里尔克的中期创作——约从1901年至1910年——的首要特征是从主观转向客观化。“物”这个诗学概念萌芽于诗人积极地接触造型艺术作品,其中尤以两位法国艺术大师对里尔克的诗艺养成影响至深,第一位是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里尔克于1902年首次有机会与这位大师做面对面的接触。第二位则是画家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诗人是在1907年——即是画家离世一年后——才注意到这位现代派之父的画作。
除了《新诗集》(NeuenGedichte) 与《新诗续集》(DerneuenGedichteandererTeil),里尔克中期创作最重要的作品非长篇小说《马尔特手记》(DieAufzeichnungendesMalteLauridsBrigge)莫属。藉由马尔特这位尚在摸索前进的年轻诗人之口,作者在多处表达自己的艺术观。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小说开始不久主人翁就数次强调正在学习“看”。马尔特先在第四篇手记里记下这些字句:
我正在学习“看”。我不知道为何如此,但一切都更深入我内里,而没止步于通常终止之处。我有个我不知道其存在的内在世界。如今一切都往那头奔去。在那儿发生了什么,我不晓得。
紧接着在第五篇,他又再度声明自己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
我说过了吗?我在学习“看”。是的,我才刚开始。进展得仍不顺利。不过,我愿善用我的时间。
一位陌生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感受力往往会变得更为敏锐,因而会比当地人留意到更多的事物,被激发出更多与更深的感受,尽管可能只是日常生活中一个毫不起眼的事物或行为,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可能也是激起马尔特此种感受“一切都更深入我内里”的成因。
不过,观察力的培养与锻练不正是一位未来的艺术家应当接受的第一步训练吗?不知道里尔克致力于这方面的学习是出于自发,抑或是来自罗丹的督促?为了撰写《罗丹》 (AugusteRodin) 专书,当时新婚不久的年轻诗人于1902年夏天告别留在德国的雕塑家妻子克拉拉·里尔克-韦斯特霍夫(Clara Rilke-Westhoff,1878-1954)与刚出生不久的女儿,独自一人从沃尔普斯维德(Worpswede)这个位于德国西北部,前往巴黎,并在9月1日首次登门拜访这位雕塑大师。十七天后,诗人在一封信里记录下他在罗丹处的所见所感:“然而,特别是工作。人们能在罗丹那儿感受到什么:那是空间,那是时间,那是墙,那是梦,那是窗与永恒……”因在1905年9月12日至1906年5月10日这段期间担任罗丹私人秘书之故,他有充分的时间与机会,深入认识这位雕塑大师,还将其有名的口头禅“总是工作(toujours travailler)”奉为自身创作的座右铭。
相反,当里尔克知道塞尚时,这位深居简出地于普罗旺斯作画的艺术家业已去世。诗人是在塞尚的纪念画展——1907年10月6日至22日于巴黎秋季沙龙举办——上,才亲眼目睹其影响现代绘画深远的作品,然后几乎天天造访,并给在德国的妻子写信报告自己的参观印象。克拉拉后来在1952年允许这十五封信付梓出版,题为《论塞尚书简》(BriefeüberCézanne)。此作在帮助世人了解诗人的艺术观上,贡献极大。至于错失与这位划时代艺术家亲身接触的遗憾,诗人则是透过阅读法国画家艾米尔·贝尔纳(Emile Bernard,1868-1941)的《纪念保罗·塞尚》(SouvenirssurPaulCézanne) 一文稍做补偿,因而对塞尚所奉行的工作伦理有所认识,进而引以督促自我。塞尚对工作的专注与狂热比罗丹还更加极端,他将生命完全奉献给艺术,甚至连母亲的葬礼也不出席。除此之外,受到塞尚的影响,里尔克在写诗时更加注重客观化与贴近事实。③身为一位诗人却选择造型艺术大师作为学习典范,看似是个不明智之举,曾是里尔克的情人,对其创作生涯有重要影响的俄国女作家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é,1861-1937)就针对此点向他提出警告。不过,后来的发展证明了透过这种看似绕道而行的磨练,让里尔克最终得以另辟新径,写下收录于《新诗集》与《新诗续集》里,诸如《豹》(DerPanther)、《远古的阿波罗躯干像》(ArchaïscherTorsoApollos)、与《红鹤》(DieFlamingos)等杰作,攀上个人诗艺成就的第一个高峰。
在此情况下,若诗人直接取材于艺术作品中的“窗”赋诗,就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了。首先让人注意到的是,哥特式大教堂与其彩绘玻璃窗特别能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最初可能是肇始于参观巴黎圣母院,因在他1905年9月14日写给妻子的信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叙述:“这是我今天第一次走进圣母院;他们正在唱小弥撒,一切如昔,唯有玫瑰窗绽放得更为璀璨”。几个月后,一首令人印象深刻的《玫瑰窗》(DieFensterrose)就于1916年7月8日诞生了:
那里头:其脚掌慵懒的迈踏
造就一个沉寂,令你神智近乎迷乱;
然后好似猫群中一只其原先
来回搜寻的目光突然盯住它,
粗暴地拖入它硕大的猫眼内,——
目光,那,如被一道漩涡
攫获,浮游一会
然后沉没并失去了意识,
假如这只眼,看似静止不动的,
睁开并咆啸地扑来
将它拖进鲜红的血液里——:
那么往昔的大玫瑰窗也是
自圣母院的阴暗处伸爪抓攫
一颗心拖进上帝内。
诗人深刻入理地描绘玫瑰窗吸引观者的凝视至无可自拔的催眠效果,令后者全然任凭这朵——宛若猫科动物目光锐利的大眼——玻璃花的宰割。自幼受天主教教养的里尔克,长大后却屡屡对这个宗教采取批判的态度——在1925年11月13日写给其波兰译者维托尔·胡莱维奇(Witold Hulewicz)的信里,诗人即强调《杜英诺哀歌》里的天使与基督教的天使无关,反倒与伊斯兰教的天使形象比较相关——在此则是批评其藉由崇高的艺术以麻醉信徒,夺取他们信仰之心这一手段。无可讳言,如同著名的《豹》,这首诗也是诗人观察力极致运用——里尔克中期创作的首要目标——之展现。甚至在完成这首诗后,玫瑰窗对诗人的吸引力还依然持续着,而在一封写于1907年7月19日的信中表露欲亲眼目睹兰斯(Reims)大教堂的大玫瑰窗之心愿。
绘画作品中的“窗”也会激发他的赋诗灵感,比方说这首《80年代的仕女图》(Damen-BildnisausdenAchtziger-Jahren)的诞生就得归功于法国印象主义大师克劳德·莫内(Claude Monet,1840-1926)所绘的妻子画像:
她伫候于折裥厚重织有
地图图案的深色窗帘边,
……
仅在窗口挥手一次啊;
这只纤手,初戴婚戒的,
就足够依恋数月了。
出现在最后三句诗行的主题:女子立于窗边告别,可谓贯穿里尔克毕生的创作,从早期的诗作《一座城堡》与诗剧《白衣侯爵夫人》(DieweißeFürstin)到晚期的法语组诗作品《窗》(LesFenêtres),都可见到其芳踪。在与“别离”主题结合之下,“窗”不可避免地成为上演人生特定情境之舞台。
至于就题材而言,“窗”之母题在里尔克中期创作时期尤常被运用于“伟大的恋人”、“被弃者”、与旅行印象之刻画上。“伟大的恋人”是诗人毕生歌咏不倦的对象。在他眼中,历史上的人物诸如贝蒂娜·冯·阿尔尼姆(Bettina von Arnim,1788-1859)、玛琳娜·阿尔科福拉多(Marina Alcoforado,1640-1723)、路易丝·拉贝(Louize Labé)与嘉丝帕拉·史坦姆帕 (Gaspara Stampa,1523-1554)这样不需占有爱情的对象,却能维持爱情强度以及提升了的爱之感受的女子,皆是“伟大的恋人”。因不占有、不具有对象之故,这样的爱情始能摆脱一般具有对象的爱情在发展上受限的困境;因爱情不再取决于爱情对象之反应,故能无止尽地增强与延伸(Rilke 1996: Vol.2,615)。在1907年8月完成的诗作《恋人》(DieLiebende) 里,“伟大的恋人”即是以如此的姿态上场:
这是我的窗。我甫才
轻柔地醒来。
我以为: 我飘飞起来了。
我的生命止于何处,
夜晚又始于何处?
我可以说:我能
揽抱万物;
透明宛若水晶般的
深睿、黯化、寂声。
我还能拥星子
入怀;感到
我的心是如此宽广;乐于
再放开他
那位我也许会爱恋,
也许会想占有之人。
……
这位刚从睡梦中醒来的恋人独自站在窗边,感到自己的心是如此高亢满涨,好似能无限地延伸。对她来说,驻足的窗边并非标示自身存在的界线,凭借不占有对象的爱情所迸发出来的巨大力量,她感到足以征服夜晚空间,揽抱夜空于怀中。然而,即使处于恋爱情绪高涨的巅峰状态,这位恋人却依然能够顾虑到爱情对象对自由的需求,愿意放开他。因此她独自站立夜晚窗边这样的情境,并非意味着孤独,实为一种不依赖情人的状态。
后来,这样站立于夜晚窗边的恋人形象成为代表人类最高成就的典型进入《杜伊诺哀歌》中,在完成于1922年2月的《第七哀歌》里,诗人向天使探问是否这样的恋人要比高塔,或者夏特(Chartres)大教堂,甚至音乐更足以企及伟岸崇高的祂:
……
然而难道仅只
一位恋人——哦,独自站立于夜窗边……
她也无法企及祢的膝吗?
“窗口”在这里好似化为天梯的起点,以供“自给自足”的恋人向上攀爬。藉由不求回报因而无限提升的渴望之助,她比其他的世间之物更接近天使的伟大。
穷人、流浪汉等社会低下阶层的人与不治之症的患者皆是里尔克中期创作阶段特别关注的对象,他称之为“被弃者”。一首写作于1907年、题为《疯子们》(DieIrren)的诗就是在刻画此等社会边缘人。与上面提到的“伟大的恋人”相仿,诗中描绘的疯子也于夜间走至窗边,接着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夜里常如此,当他们踏抵窗边:
一切骤然都好了。
他们的双手摆得端正,
内心高涨而能祈祷,
眼睛平视
未立定嗅听、时常曲扭变形的
花园于歇止下来的四方格里,
在陌生世界之光的返照下
持续增长而永不消失。
这扇夜窗以其提供的、对纵使扭曲变形——不禁令人联想起荷兰画家梵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的风景画——却显示于方方正正的“窗框”内的花园之眺望,像是一帖医治疯狂的良药。这种想法可说是里尔克特有的,类似的情境若出现于晚一辈的奥地利诗人乔治·特拉克尔(Georg Trakl,1887-1914)的笔下,则会有截然不同的处理。在其一首约写作于1912至1914年间、以“DieStillederVerstorbenen”(逝者的寂静)开首的诗作中,同样有位疯女在傍晚时分现身于窗边,却是为了放下窗帘,好似不愿让情绪因为看见窗外的花园而受到干扰。再次的,“窗框”在里尔克的笔下施展了奇妙的功能——。
身为一位四处旅行、不断迁居的诗人,里尔克自然有机会认识各地“窗”之风情。《复活节前》(Vor-Ostern)这首诗描写的是拿波里人正在为即将举办的宗教仪式游行做准备,然而全诗却以一个具有亵渎意味的窗景作结,而且呼应前面提到的西班牙圣母之圣物匣:
……
然而在那头的窗子里
出现一只猴四下乱瞧
还以狂妄的态度快速
比划了个不得体的手势。
进入里尔克作品中的,还有他在罗马及威尼斯所遇见的“窗”。与《玫瑰窗》诗中的主角相仿,它们皆不仅是被人看视,还是主动看视之物。一条出现于《罗马坎帕尼亚》(RömischeCampagna)诗中,以拟人法表现的名为“挖掘者”之道路,即感到背后农庄上的窗户对自己持续投射不友善的目光:
最后一排农庄的窗子
皆目光凶恶地紧盯着它。
而在《威尼斯的清晨》(VenezianischerMorgen)一诗中,相较于易被美丽的事物所迷惑,屡屡无法看穿假象的人类,“窗”俨然是饱览世事的全知者,因为它们屹立在当地已有数百年之久,而且还会继续屹立下去:
侯爵般被宠坏的窗子总能瞧见,
偶尔屈尊敷衍我们的:
这座城市,苍穹微光与澎湃
情感相遇之处,总一再地,
成形而无真实存在之时。
这首诗1908年初夏完稿于巴黎,内容却是在写1907年晚秋的威尼斯之旅,也就是说,诗人耗费了近一年的时光来消化此次旅行留下的印象,才得以写出一首他认为完善地处理了这个题材的诗作。有关一个经历如何转化为一首诗,以及里尔克如何看待这个往往历时漫长的过程,在《马尔特手记》里有详尽的描述,即是在时常被学者引用,被誉为诗学手记的第十四篇里。诗人在此欲纠正一般人对诗歌艺术普遍持有的误解,强调一首诗的诞生绝非全凭感觉,而是必需累积许多不同的体验,慢慢酝酿而成。他说为了写一行诗句,得先见过许多的城市、人群与事物,得认识各种动物与花草,观察其动作与姿态,得拥有童年回忆与许许多多爱之夜的回忆,此外还有:
但也必须曾与死者相伴过,共处于一间窗户开启的小室里,室内断断续续地响起噪音!而拥有回忆还不够。还必须将之遗忘,假如它们繁多的话,必须有极大的耐心等候它们再度回返。因为这还不是回忆的本身。要等到它们化成我们体内的血液,化为眼神与手势,无名的,并且与我们自身再无区别之时。一直到此时最罕有的时刻才会出现,一行诗的第一个字自它们的中心升起,并且由此开展出去!
成名之后深受早年轻率发表不成熟作品而苦的诗人在此坦诚分享自己多年创作之后得到的领悟,敦敦不倦地提醒年轻诗人耐心等候的重要,因为好的作品往往得经过漫长时间的累积孕育,如同一棵树的种子在长期的灌溉与日照之下,才终能萌芽,抽枝,茁壮,与绿叶成荫。
形
贝达·阿勒曼(Beda Allemann)在《晚期里尔克的时间与形体》(ZeitundFigurbeimspätenRilke)一书中,对里尔克的诗学概念“形”有深入的分析。根据他的研究,这个概念具有以下诸项特征:“形”在空间中,具有组织的力量,其本质兼具遥远与动态的特质。此外,“形”还能成就动态与静止的统合,是个汇集之处(Allemann 1961: 62)。里尔克作品中,除了“玫瑰”、“镜子”与“星辰”,“窗”也是体现这个概念的最主要形象(68-69)。阿勒曼的这些论点确实有其合理之处,也易于理解。“窗”作为汇集之处的身份显而易见:开启的窗子无疑汇集了内与外。再者,因“窗框”通常被赋予的几何形状,十分适合用于观察大自然。在完成其毕生巨著《杜伊诺哀歌》之前,外在世界对于成长于大城市的诗人而言,过于广阔,难以掌握,因此必须透过“窗”的中介,即是立于窗后,透过窗“框住”的局部范围,逐步领略自然界中细微的动态变化。换言之,“窗框”提供给观者一个易于掌握对象物之秩序。在此之前,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们即已发现“框”这方面的功能,藉以辅助作画,进而发明影响欧洲绘画深远的透视法。
“窗”作为一个建筑物的基本组成要素,很明显是个静态物,却能让动态物穿越自身。在里尔克一首题为《手》(DieHand),惜未完成的诗里,即出现此种行进的刻画:
瞧这只小山雀,
误入房间内:
历时二十下心跳之久
它躺在一只手上。
人类之手。……
此刻站于窗台上
自由了
却仍然处于惊吓中
……
除了小山雀飞行穿越窗框之外,通过的动态物也可能是无形的声音。下面这两句诗行正是描绘声音的此种行进,出自一首献给格特鲁德·欧卡玛·克诺普(Gertrud Ouckama Knoop)的诗作:
它们轻柔地降临,好似屡从公园飘来
自窗子入侵的种子;
或许就是因为“窗”提供发生行动的可能性,故常会激起观者心生远行的冲动,如同里尔克在《童年的延续》(DauerderKindheit)一诗所言:“窗于他,意谓道途。”
里尔克作品中的“窗”,不仅涉及此种水平行进的、隶属尘世间的运动,还能引发垂直上下的、宇宙间的运动,因为所谓静态的“形”实际上是由纯粹的、原则上直达宇宙的运动所组成。由是之故,诗人挑选了数个“形”,创造了他个人的星座。其一首晚期的诗作如此申明道:
从已知的形体我们
创造夜空的星宿。
在诗人自创的星座里,其中有个即是“窗”。它最先出现在《第十哀歌》中:
在更高处,星宿。新的。苦痛国度的星宿。
她慢慢地喊它们的名字:─此处,
看啊:骑士,棍杖,及更圆润的星座
她称之:果冠。然后,更远处,朝极圈去:
摇篮;道途;燃烧的书;玩偶;窗牖。
也许是朝向星空开启的窗口启示了诗人发明这个星座,如一首写作于1926年的法语诗所透露的,里面出现“la fenêtre stellaire”(灿星之窗)这个名称:
从房间的深处,自床上,仅是一缕苍白的晨曦,区隔之,灿星之窗退位给悭吝之窗,后者宣告白日的降临。④
在诗人眼中,开向夜空繁星之窗远较让白日上场之窗来得富有与大方。之后还有一首德语诗,其主题即是“窗星座”:
早已,脱离我们尘居者,移至繁星之下的
窗啊,辉煌与永恒;
你,竖琴与天鹅之后,幸存下来的,最后的
逐渐成为受崇拜之形象。
我们依然需要你啊,于房舍轻盈框出的
形状,许诺我们以辽阔。
然而最僻远的常是尘世之窗仿效
你的神化!
命运投掷你过去,其无止尽地被用以
衡量失去与流逝之尺度。
来自永恒天体之窗,因转化而激动地升起于
指引者之上。
这首惜以未完成的面貌流传下来的诗作写作的时间距离诗人的辞世仅六个月。诗人在此继续发展之前在《第十哀歌》仅能点到为止的主题,即是“窗”之神化,并解释为何它能够享有此荣耀的地位。对晚年的里尔克而言,“窗”无疑是个能够与“失去”及“流逝”相抗衡的最有力的反证。两者皆是现代人无法避免的痛苦经验,而诗人对之感受尤深。就如同西洋文艺传统中的“竖琴”以及里尔克中期作品里的“天鹅”,“窗”在这里同样也是诗人的象征。值得注意的还有第二段所描绘的“尘世之窗”与“苍穹之窗”之间的交流,它正是前面所提到的在宇宙间进行的运动之体现。
而当里尔克计划以法语写一部窗的组诗作品时,其实就是无意地——亦或是有意地?——追随法国象征主义的两位前辈大师之脚步。首先是波德莱尔在1863年写了一首题为《窗》(LesFenêtres)的散文诗,他视一扇关闭着、但被烛光照亮的“窗”为激发诗人创作灵感的泉源。三年后,其后继者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也写了一首同样以《窗》(LesFenêtres)为题的诗作。不过,与波德莱尔散文诗的松散形式相反,这位对诗歌形式特别讲究的诗人安排了一个仿照两面窗扇的对称形式。全诗篇长总共十段,前五段代表着左边的窗扇,描绘一个濒死的重病患者出于对生命的渴望,以及对过往甜蜜时刻的回忆,紧紧攀附着医院窗子上的十字窗棂;后五段则是刻划右边的窗扇,描绘着厌恶生命,受尽世间折磨的“我”向往从前充塞着崇高美的湛蓝天空。然而,正如同濒死者逃脱不了死亡,诗中的“我”也注定得堕入万劫不复的永恒。
相较于波德莱尔将“窗”比拟为诗学原则,以及马拉美将“窗”喻为生命、死亡与艺术的象征,“窗”在——规模上要比两位前辈诗人的诗作来得浩大——里尔克的组诗里,则是代表存在的形象。对里尔克而言,“窗”实能概括人的一生,诸如成长和恋爱经验皆与“窗”脱不了干系。以“窗”为舞台,诗人向我们展示恋爱的各个阶段:从初遇,历经摆荡于相互吸引与排拒的紧张时期,到无法避免的别离。以下面四句诗行,他扼要地点出“窗”在我们生活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你难道不是我们的几何形,
窗啊,极简的形状,
却轻松地概约了
我们繁浩的生活?⑤
若同时代的作家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及霍夫曼斯塔尔有机会读到这四句写于1924年的诗行必定会心有戚戚焉,因为他们都曾在作品中表达过“窗概括人的一生”之想法。
最后,还要特别一提的是:“窗”在里尔克的笔下如何成为一个“形”的过程,在《杜伊诺哀歌》里面即可观察得出。十首哀歌中,“窗”总共被提及五次,前三次分别出现于写作于1912年的《第一哀歌》(Rilke 1996: Vol.2,202)与《第二哀歌》(Rilke 1996: Vol.2,207)以及写作于1922年的《第七哀歌》(Rilke 1996: Vol.2,223)之中,“窗”在这几首诗里除了有标明地点的作用之外,还蕴含着跨越界线的意义。而在后面的两处,即是均写于1922年的《第九哀歌》与《第十哀歌》里,“窗”这个字则单独出现于两个标点符号之间。这样的转变清楚显现出“窗之母题”逐渐获得其自主性与绝对性。而这个过程除了揭露“窗”在诗人心目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此一事实,还透露出在完成《杜伊诺哀歌》的那一年,诗人是如何强烈地感到单是提起这个日常之物的名字,即可在读者心中唤起某些特殊的联想。
世界内空间
即使针对“世界内空间”这个里尔克晚期的重要诗学概念已有为数不少的研究,然而它依旧予人深晦之感。笔者认为若透过诗人晚期作品中窗的形象来阐释之,将大大有助于对其主旨的了解。这个里尔克自创的组合词是由三个德文单字“世界”(Welt)、“内在”(Innen)、与“空间”(Raum)所组成。一般来说,第一个与第二个互为反义词,因为“世界”通常会令我们与“外在”产生联想,但在这里却和“内在”合并在一起,因而产生一种矛盾冲突感。对里尔克而言,不论“世界”——也就是“外在”——或者“内在”皆是其创作灵感的来源。两者在他的作品里也常彼此相互映照,如我们已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见到的。第三个德文单字“空间”频繁地出现于里尔克的作品中,而且还会与隶属于各种领域的字词相结合,例如:“心空间”(Herzraum)、“溪流之内在空间”(des Baches Innenraum)、“黯黑时刻之/过渡空间”(Zwischenraum / dunkler Stunden)、“陌异之严酷空间”(raue Räume der Fremdheit)、“母亲─空间”(Mutter-Raum)、“玫瑰空间”(Rosenraum)、“看视空间”(des Schauens Raum)、“我的声音之空间群”(Räume meiner Stimme)、“夜晚空间”(Nachtraum)、与“过渡空间(Zwischenraume)介于两个/被轻声念出与被感受之字眼”等。
然而,“世界内空间”在里尔克作品中却仅出现一次,即是在一首写于1914年的无题诗中,其首句为“几乎所有之物皆招唤着联系”(EswinktzuFühlungfastausallenDingen)。它的第四段如此写道:
一个空间穿经万物延展:
世界内空间。鸟儿静静地飞
穿越我们。哦,盼愿它成长,
我向外瞧,而我内里长起一株树。
我们看到诗人是藉由“鸟”来传达“世界内空间”之内外统合的本质,因为对于飞越空间,并以鸣叫声充塞空间的“鸟”而言,内外之间并不存有界线。“鸟”在里尔克的笔下常与“窗”产生连结。最早的例子大概是这个出自《一栋贵族豪宅》(EinAdelhaus)的诗句:“窗台上有只鸽子在打盹。”在《来自四月》(AuseinemApril) 一诗中,窗则转变成一个宛若鸟一般的生物, 像似欲模仿前面提及的云雀:
所有受伤的
窗子皆惊恐地拍打翅膀。
在前面已讨论过的,题为《手》(DieHand)的诗稿里,“窗”是鸟进入人的世界,进而与人有亲密接触的入口。而在“世界内空间”一诗中,除了鸟,还出现另一个重要的“形”:树。早在1912年撰写的散文《经历(一)》(ErlebnisI) 里,里尔克就已描述“我”如何藉由与“树”产生的连结,进入到自然的另一边,因而得知过往的事物仍持续存在于当下的秘密。故推测“世界内空间”诗中的“我”可能是透过窗看见树,感到树在自身内生长,诗人没提及“窗”,可能是担心它在多数读者的脑海里会唤起内外区分的意识,进而摧毁整首诗所要营造出来的内外统合之状态。不过,这里的“树”可能并非指一般的树,而是诗。对里尔克而言,一首诗的形成与一棵树的成长有极大的相似之处。⑥
“世界内空间”不单是一个表现统合内外,并及于一切二元对立之设想,还指向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绵延性。针对此层意义里尔克设计了一个特殊的模型:“意识金字塔”。他在1924年8月11日写给诺拉·波契-温登布鲁克(Nora Purtscher-Wydenbruck)的信中提到此一模型:
纵使“外面”如此地延展,但以其恒星的总间距也不足以与我们内在拥有的规模相比,后者甚至不需有如宇宙般的宽敞,即能近乎无边无尽。所以,如果死者,如果未来的死者需要居留之地,有什么归宿会比这个想象空间更能让他们感到惬意,而且真有供应的呢?我越来越觉得我们惯用的意识好似栖息于金字塔的顶端,而其基座在我们的内在(并且在一定程度之下,于我们之间)充分地往横向发展,以致我们若有能力越深入地栖身其中,我们就显得越能普遍纳入地置身于尘世的、以及就最广义而言,世界的存在之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的情境里。自还极年幼始,我即如此猜测……在此座意识金字塔较深处的横切面上的简单存在,即是所有那些在自我意识上层的“寻常的”顶端只允许作为“过程”去体验的,那个牢不可破的现有存在与同时存在,对我们而言,也可能成为重要事件。
“意识金字塔”模型主要建立于诗人的此种思想:“时间是空间”,而其影子也显现于这首诗《费力地抗拒烈夜》(SoangestrengtwiderdiestarkeNacht)中:
……谁还能将前额抵着夜晚空间
好似抵着自己的窗子?
“窗”以其透光的功能与时间密切相关,身处室内之人在无其他工具的辅助之下,唯有透过“窗”才能觉察到白日或夜晚的降临。再者,作为内外之间的“分界线”,“窗”又与空间息息相关,因此最适合用于表现时间与空间的统合。
值得注意的是,透过里尔克的“意识金字塔”模型还能进一步发觉到当时欧洲思想界彼此交流的痕迹。首先是,它雷同于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在《物质与记忆》(Matiéreetmémoire,1896)以及《精神式能量》(L’énergiespirituelle,1919)两本著作中提到的自我模型。因诗人在1913年至1920年间曾专研过这两部著作,故“意识金字塔”极有可能受到这位法国哲学家思想的启发。事实上,柏格森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哲学界,其有关时间与空间的思想还对当时物理学的进展影响至深,譬如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在1905年构思的“相对论”(Relativitätstheorie)即是基于时间与空间统合之思想。而从里尔克在1921年携带着一本谈论爱因斯坦的书去旅行这件事上,⑦我们也可看出诗人有意了解这位物理学家的理论。笔者认为“相对论”和里尔克的时间观还有个相同之处,即是皆认为过去、现在与未来同时存在。这种时间观在《马尔特手记》里已详细地陈述过,而且是藉由对书中一角色的描绘——主人翁的外祖父老布莱伯爵(Graf Brahe):
时间的顺序对他丝毫不重要,死亡仅是渺小的偶发事件,他全然加以忽略。人们只要一旦纳入他的记忆内即存在,对此他们的死去一点也改变不了什么。老绅士过世数年后,大家谈起他在把未来的事情当成现在正在进行的事情这方面也是同样的任性。据说,祖父有次曾对一位新婚的年轻妇人谈起她的儿子们,还特别提及其中一位所做的旅行,当时,这位女士只不过初次怀孕三个月,坐在这位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的老人旁边,惊恐得几乎要昏厥过去。
后来,诗人在1925年一封写给胡莱维奇的信里,又特别强调:“老布莱伯爵将一切不论已发生过的,或者未来的事物都当成‘现有的’。”显然地,相较于多数人,这位布莱伯爵已达成《杜伊诺哀歌》里的天使托付给人类的任务了:
祢迫切委托的任务,若非转变,会是什么?
下一章即是要探讨“转变”。
转 变
“窗”与里尔克晚期另一个重要的诗学概念“转变”之间最显著的关联,即是前者是后者的实现。或者该反过来说,事实上,正是“窗”的形象催生了这个诗学概念。因为“窗”很早就向诗人展示“物”行使转变之潜能,例如在已提过的早期诗作《来自四月》中,“窗”就仿佛化作小鸟。
“窗”在诗人毕生创作当中历经了多种转变,尤其最常化作“镜子”。下面这两句诗行——出自1906年致玛德琳·德·布罗意(Madeleine de Broglie)的献诗——可能是当中最早的例子:
如果夜晚降临了——会有怎样硕大的星子
反射在这些窗子上啊……
一年后,诗人在《贝居安会院》(Béguinage)一诗中还更进一步地仔细描绘窗玻璃在白日上演的反射现象:
但教堂的窗子以其千片窗玻璃
倒底反射了什么进入庭院内啊,
其中沉默、光束与返影彼此
交融,酌饮,变浊,提升,
宛若老酒妙不可言地陈化。
教堂彩绘玻璃折射出来的瑰丽光影,在里尔克的笔下转化成佳酿,令人沉醉。而在另一首写于1908年的诗作《单身汉》(DerJunggeselle)里,则上演了神秘的反向转变。我们看到主人翁研读祖先留下来的书信直至深夜,然后喃喃自语道:
……以你对我的认识;
逗趣地叩敲椅子的扶手
但镜子,其内无边无界,
让一片窗帘轻声开启,一扇窗:
因为那头立着,几已成形,一尊鬼魂。
他看见镜中映照出来一个形影,以为看见了一位祖先,而没意识到其实是自身的形影。德语诗歌中常会出现“窗”与“鬼”相互对应的情况,主要的原因推测有二,其一:窗在欧洲民间信仰中普遍被认为是亡灵离开世间之出口,故有死者咽气后必须马上打开窗子的习俗。其二:适合押韵,因这两个德文字Fenster(窗)与Gespenster(鬼)的尾音一模一样。倒是这里的“镜”在除去另一边的遮盖物而转变成的“窗”,本身也是个幽灵,因为它只不过生成于单身汉的幻觉罢了。读者在这里所面对的着实是个层层迭套、易令人迷乱的意象。诗中的“窗”最先是引申意,意指祖先的信件,因为透过它们让单身汉认识了一个好似自己“镜中影”的亡者,行文至此,诗的含意从“窗”变成“镜”;接着这“镜”再又转变成“窗”,并且从中走出一个重返人世的亡灵,它与主人翁极其相似,宛若是他的孪生兄弟,所以最后又有“镜”之含意蕴涵其中。藉此复杂之意象,诗人欲批评单身汉无视自己所处的时代,仍固守世袭的贵族骄傲过日子,并更进一步批判风行于19世纪的历史主义(Historismus),如其名称即已透露的,这个艺术潮流不以追求创新为宗旨,仅是重复堆砌既有的风格而已。
“发生转变,甚至转变为无形之所在”,是阿勒曼对里尔克笔下“镜”的评论,同样地也适用于“窗”(Allemann 1961: 135),下面这个出自诗人一首晚期法语诗作的描绘可供印证:
镜玻璃,骤然,反射我们面容的,混入了我们透过它所看见的;⑧
不同于与前面所看到的例子,这里的窗反射出的形象是来自室内,在窗玻璃未加以掩盖的情况下,必然地与透过它所见的影像重迭一起,因而产生了“我”与“世界”、“内”与“外”相互交融的现象。
之前已提到“窗”在里尔克的作品中会转变成星座。而在其晚期法语诗作中,它更是展示了种类繁多的转变,例如:变成一容器或者扣子:
窗子,其饮下的景象于大玻璃罐中萌芽。环扣,拴住我们眺望之宽腰带。⑨
在这位对视觉艺术感受特别强烈的诗人眼里,一扇窗里面若有人逗留其中,窗框会将之如一帧图画般摄住, 因此整体看来就像是一本图画书:
这个散漫的家伙,那个懒惰鬼,是你把他摆放于书页上:他稍微酷似自己,他变成了自己的图画。⑩
“窗”变换多端,宛若海洋或者潮汐:
或者变成竖立起来的盘子,给我们供应各形各色的视觉飨宴:
直立的盘子,给我们端上清淡的饮食,令我们饱受折磨,与太甜的夜晚和常是太苦的白日。
无终止的一餐,以湛蓝调味——,以眼嚼饮,人们应当不会厌倦。

前面诗例呈现出来的转变,基本上都是诠释“窗”的诸多可能性。而在《第九哀歌》出现的转变,则是藉由“颂咏”来进行。诗人要求我们呼唤:
……屋
桥,喷泉,大门,壶,果树,窗,——
至高地:柱,塔……
人们若“颂咏”这些物,它们即从实体转化为语言,虽无形,实才进入了无边无界之境。对此,诗人在一封写于1925年11月13日给胡莱维奇的信中有更进一步的解释:
对于我们的祖父母那辈而言,一栋“房子”、一个“喷泉” 、一座他们熟悉的高塔、甚至自己的衣服、他们的外套:还拥有无止尽地更为丰富的、无止尽地更为亲密的含意;几乎每个对象皆是容器,他们会在其中发现属于人的事物,并且能够在其中储存属于人的事物。而今从美国蜂拥而至的空洞冷漠的对象、虚假的对象、生活的模型……地球没有别的逃避之处,只能化为无形:在我们里面,而以本质的一部分,我们也参与了此项化为无形的过程,(至少)握有其股份——在我们处于现世时,对无形的拥有还能有所增长。——此种亲密且持续的、从有形至无形的转变,不必再依赖于有形的、可触摸的存在,唯独在我们里面才可能顺利达成……
里尔克认为将具有历史的“物”化为无形,是将它们保存在已是拥挤不堪的地球上唯一可行之道。而《马尔特手记》里的布莱伯爵正是此种办法的真实体现,因为:“人们一旦纳入他的记忆内即存在,对此他们的死去一点也改变不了什么。”
❶ 佩利科的代表作为悲剧《FrancescadaRimini》(里米尼的弗兰西斯卡),1920至1930年间因政治因素被监禁于总督府。
❷ 译自德文译文: “Verloren in unbestimmter Langeweile stützt sich das Kind dort auf und verharrt; es träumt …” 。
❸ 就这点而言,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之前就已是里尔克的导师了。
❹ 译自德文译文: “Von der Tiefe des Zimmers aus,von Bett aus,war es nur ein blasser Schimmer,der trennt,das sternene Fenster weichend dem geizigen Fenster,das den Tag verkündet.”
❺ 译自德文译文: “Bist du nicht unsere Geometrie,Fenster,sehr einfache Form,die du ohne Aufwand unser ungeheures Leben umschreibt?”
❻ 此种思想与歌德的有机体艺术观十分类似。
❼ 在1921年5月20日一封写给纳莉·温德李-沃卡特的信中,里尔克提到他携去旅行的书籍当中有一本是谈论爱因斯坦。
❽ 译自德文译文: “Spiegelglas,plötzlich,wo unser Gesicht sich reflektiert,beigemischt zu dem,was man
❾ 译自德文译文: “Fenster,dessen getrunkenes Bild in der klaren Karaffe keimt. Schnalle,die den weiten Gürtel unseres Ausblicks schließt.”



Die endlose Mahlzeit,gewürzt mit Blau,man darf nicht überdrüssig werden,sich durch die Augen zu ernähren.
Wie viele Gerichte setzt man uns vor,während die Pflaumen reifen; o mein Augen,Rosen-Esser,ihr werdet vom Mond trinken!”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