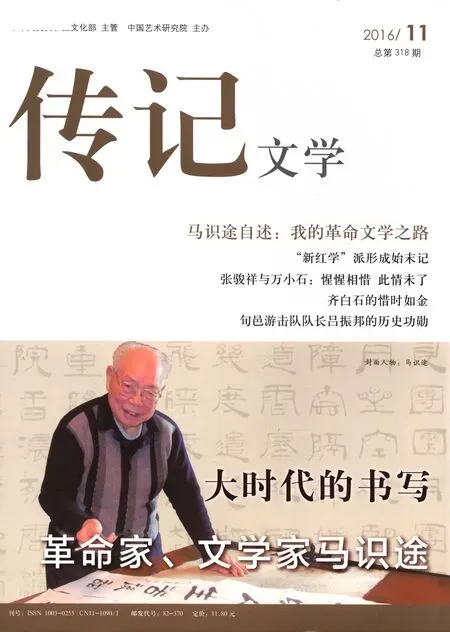反思历史之影──评《好莱坞的黑名单》
文|黄隆秀
反思历史之影──评《好莱坞的黑名单》
文|黄隆秀

电影《好莱坞的黑名单》海报
《好莱坞的黑名单》(Trumbo)上映于2015年11月,由杰伊·罗奇(Jay Roach)导演,布莱恩·科兰斯顿(Bryan Cranston)、海伦·米伦(Helen Mirren)、黛安·莲恩(Diane Lane)、艾丽·范宁(Elle Fanning)主演,约翰·麦纳马拉(John McNamara)编剧,改编自布鲁斯·亚历山大·库克(Bruce Alexander Cook)所写的传记《Dalton Trumbo》。电影的故事线索是以编剧达尔顿·特朗勃(Dalton Trumbo, 1905-1976)为中心,讲述了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好莱坞内部共产党员进行清洗与审判,在经历了著名的“好莱坞十人案”之后,特朗勃借着匿名的“地下写作”在好莱坞电影体制内继续艰难地生存,直到60年代紧张的政治气氛松动,作为过去因政治原因被否定的作家,他重新受到体制正名的过程。
1905年,达尔顿·特朗勃生于蒙特罗斯科罗拉多州,3岁时全家搬到大章克申市,在读高中时,开始尝试写作。在科罗拉多大学读了两年书,直到其父亲去世,特朗勃有9年的时间,在洛杉矶的一家面包店做夜班的包装工作,之后,考入南加州大学。在此之前,他写了几十篇短篇小说都无缘出版。1934年,特朗勃被雇为《好莱坞旁观者》(Hollywood Spectator)的管理编辑,之后离开杂志社到华纳兄弟旗下的故事部门工作。1935年的大萧条时代,他出版了第一本小说《蚀》(Eclipse),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他在家乡大章克申的生活和人民的变化。1937年,他的反战小说《强尼拿了他的枪》(Johnny Got His Gun)使他赢得国家图书奖。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他已成为好莱坞收入最高的编剧之一。1943年,他加入美国共产党。随着二战结束后,美苏由合作关系转向对立,1946年,特朗勃被《好莱坞报导者》(The Hollywood Reporyer)的一篇专栏文章《为斯大林投票》点名为共产主义分子的同情者,紧接着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唤被同时点名的“十君子”出席听证会。十人均拒绝指控他人是共产党员,被判蔑视国会罪。被美国电影协会列入黑名单后,特朗勃藉由匿名写作创造出多部经典,如《罗马假日》《铁牛传》《出埃及记》《斯巴达克斯》等等,并获得奥斯卡奖项。直到1960年政治限制的松动,特朗勃的名字才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当中。1970年,他被美国编剧协会授予桂冠,1976年去世。
《好莱坞的黑名单》试图再现50年代美国好莱坞电影史上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但却巧妙回避了关于达尔顿·特朗勃作为美国共产党员身份在冷战时期得到历史必然性的遭遇的原因,把历史放置在公民身份角度的个人偶然经验,而把大部分看不见面貌的社会阶层面临的集体压力的差异性排除到视野之外,划一为时代的集体受害者,诉诸一段关于美国民主化属于民族国家范畴的历史。冷战时期,国际上两大阵营对抗的背景、美国以反共意识形态为内核在国内对劳工运动的镇压以及对外输出反共文化,在电影文本中,转而表现为个人挑战程序、抵抗威权政府、争取公民权利。影片中淡化了主角的共产党员身份,对于构成他罪名的真正背后因素、所有事件发生的根源,做了有意向的模糊化处理,这导致使故事整体在叙述时不一致地分散开来。
此片要向特朗勃致敬,就应在对过去历史中的受难者去污名化的同时,对历史做出清理与批判。而电影坚持好莱坞颂扬的价值形态和往常作风,复制此前贯彻始终的二元的伦理价值观——正/邪、善/恶、好/坏等等,不免过于简单化地处理历史构成的复杂性内涵,名义上将结构产生历史遗留的问题给予解清、去污名化,反过来说,藉由重新建构一套历史诠释的新话语以巩固、伸张当前全球的普世价值。电影的叙事情节发展出四条线:(一)以当时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上听证会的新闻纪录片,结合特效制作的仿纪录片形式,混合经典电影的画面,以穿插的技巧作为历史叙事的时间轴,使观众产生回到过去的历史感;(二)好莱坞“十君子”在此案中面临的考验与好莱坞保守派内部的角力;(三)达尔顿·特朗勃个人在整起事件当中的遭遇,他与同行在被列入黑名单后,如何通过匿名方式创作出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并在社会公众中重获身份的正名;(四)黑名单对达尔顿·勃朗特家庭造成的影响,伴随着他整个家庭内部发生的变化。在四者之间互不扣连的关系发散式地陈列于影像之上,最终将达尔顿·特朗勃塑造成一名捍卫人权的自由斗士的形象。

电影《好莱坞的黑名单》剧照(一)
白色的“爱国主义”
影片开头重现黑色电影《双重赔偿》的片场拍摄,从爱德华·G·罗宾逊(Edward G. Robinson)举着枪的黑白画面,一百八十度回拍切换到彩色的画面,站在镜头背后的特朗勃,由黑白到彩色,从电影穿梭回历史。反讽的是,“回去的历史”是剧情片选取的记忆材料对历史的建构。历史叙事藉由黑白新闻纪录片代表每一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与推进时序发展的标志,新闻纪录片画面作为每一时期重大事件发生的客观定位,另一方面,搭配交叉着历史/再现历史的旁白言说的画外音,携带了历史不可质疑的权威性质,即当时面临“红色恐惧”意识形态的言说意向。藉由将历史画面安插在“好莱坞十人案”来呈现事件的真实性、新闻纪录片画外音的权威性,对比出特朗勃作为中心人物在时代下的遭遇,虚构叙事和纪录片安插的这种设计产生了一种张力,强化了个人选择遭遇不公义、抵抗腐败威权的这一命题,却忽略了前面梳理的美国作为民族国家在冷战中所代表的主导性位置。
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集团随即展开了新一波在世界范围内的冷战对抗。电影没提到的历史背景包括:美国内部进行“红色恐惧”(Red Scare)的反共产主义宣传与对海内外共产党的审查、清洗;1948年到达反共产主义情绪的高点;1950年美国国会颁布《管制颠覆活动法案》(Subversive Activities Control Act of 1950),整个50年代上半期都笼罩于麦卡锡主义的一片白色迷雾之中。
美国国会众议院下属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成立于1938年,最早可追溯到1918年到1919年期间,面对俄国十月革命,欧洲大陆的掌权者对此产生了反共情绪,在美国,当时则成立了针对美国国内与德国布尔什维克分子调查的奥弗曼委员会(Overman Committee),其宗旨在于反对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活动。1945年二战后,美国面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发生数万次集体罢工事件,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借此声称美国工会遭到共产党渗透,同年9月,在美国各社会阶层进行对共产党员的逮捕,并以“违反美国”的罪名逮捕了美国共产党主席丹尼斯及与其相关的“左”倾知识分子。影片中与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暗送秋波的右翼娱乐新闻记者海达·霍珀(Hedda Hopper)的旁白搭配黑白仿新闻纪录片,谴责好莱坞电影工会演员进行的抗议罢工,指出主角为“入了共产党的共产党员”抗议行动的首谋。紧接着,旁白带出三K党党员、同时作为共和党身份的J·帕内尔·托马斯(J. Parnell Thomas)担任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主席发表的反共声明——“共产主义并非久远的威胁,它最危险的特务都在这里。他们控制了电视广播和电影银幕,操控着它的雇员和工会。”托马斯随后全面调查美国电影业,并进行了为期9天的听证会。

电影《好莱坞的黑名单》剧照(二)
此后,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展开了对社会各阶层的审查,在另一起案件《美亚》杂志间谍案后,1947年3月21日,美国当时的总统杜鲁门颁布施行了“忠诚调查计划”,政府每一层级机构设立忠诚调查委员会并予之进行监控、审查,只要与共产主义沾边的人士都将遭到调查,并剥夺其在政府单位工作的权利,限制出入国自由。1949年9月,J·帕内尔·托马斯公开宣布紧急法案,将共产党人送往集中营。1951年到1954年间,威斯康新州的国会议员、同属共和党员的麦卡锡在美国国会煽动反共主义的情绪,并加强了对共产主义的肃清、调查。
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50年代界定了一套关于“爱国”的标准话语,是谁持有爱国的话语体系?爱国的话语体系的边界在哪?这一爱国的价值体系为何与当年的共产主义理念相抵触?
“爱国”价值贯穿整部电影的概念,将共产党员在50年代的被洗清弥合到“爱国”话语里,是一种失败的话语弥合。如不去追问二者的区分,就无法解释叛国者在什么意义上背叛了美国。不讨论爱国价值的属性,就无法解释电影里为何50年代罗纳德·威尔逊·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会作为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友好证人,出庭对好莱坞内部的共产党人进行检举。现实之中,70年代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施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跨国企业在世界布局扩张,劳动力外移,在国内则以公司的名义解雇劳动力,更大力度地镇压手无寸铁的工人,这一僵死不变的白色的“爱国主义”价值内涵本身无法对应到民众的生存处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加物。电影里不断浮现的对立的逻辑,除了以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代表的对爱国、忠诚的审查、官方与资本的打压工人运动的结盟,这一爱国/叛国对立逻辑的背后是,战后美国施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强调国家全面现代化的建设,扩大社会的公共设施,两大集团对军备、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诠释权的争夺,美国战后为稳固经济基础之外、藉由镇压工人运动压抑分配平等争取的问题,帮助资本集团的资本积累。在这一前提之下,“爱国”的价值得以成立。
共产党人在工人运动里要求的分配平等及言论集会自由,威胁到了随政府政策方向获益的资本家,也违反了政府所指认资本家、企业主带来国家安全的“爱国价值”。在这种对立逻辑之下,共产党人带领的工人运动成了叛国者的行为。这一对立逻辑在《好莱坞的黑名单》里,前者所代表的爱国价值,突兀、粗糙地嫁接在作为叛国者身份的主角特朗勃的身上,当他像精神病似的不断重申自己的爱国立场时,电影文本弥合了历史中对立关系背后的具体利益分配冲突。“爱国价值”巧妙地转移历史概念的能指,以证明特朗勃形象是延续过往爱国精神的新政治正确。它体现出一种双重矛盾的逻辑,将特朗勃的言说植入对爱国价值的臣服,但只属于前者资本家所代表的立场的内涵,这本身是一种错误。它消解了历史中的对立关系,两种理念走向平行无关,最终以去阶级化、爱国自由民主的空壳来替代二者的对立关系。共产主义价值本身的内涵,除了作为电影中凸显叛国者定罪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它包含的性质不同于前者的爱国倾向,强调国际连带、工人互相声援的国际主义面向本身包含爱国爱民这件事,却被压倒性的单一诠释夺去了其内涵的真意。
电影大量着墨于家庭关系的描写,强调特朗勃私生活层面的关系,为维生经营起地下写作的家族事业,将家庭价值打造成象征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其中一员。这一对中产阶级家庭的想象,将他的共产党员身份神秘化,并用庸俗简化的对话虚构对共产党身份的想象,抽离其社会对应关系,将家庭关系非政治化,描述成亲子情感关系的需要,取消对国际主义怀抱理想的激进主体处于时代遭遇下组成的另类家庭形态,前者的方式展现了对现下典型美国中产家庭主体的想象,一致性地达成国家、民族召唤的爱国话语。好莱坞牵强地将惯用的价值观念照搬到一个遭到遮蔽而重新建构的历史人物身上,施以观众情感召唤,以对国家民族的认同作为诉求,绕过阐明人物的精神信仰理念,再次以单一的历史叙述双重遮蔽白色现代性的历史之影。
一种民主史观的限制
封闭于一种民族国家政治体制的框架之下、轻描淡写冷战事件的对内肃清、只要是“非美国的”就视为敌人的敌我逻辑,这是只有一种意象的白色的“爱国主义”。电影从游泳池派对上特朗勃与电影联盟创始人山姆·伍德(Sam Wood)之间的冲突拉开序幕。在爱德华·G·罗宾逊家中,好莱坞“十君子”讨论对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展开的对好莱坞工业与共产党相关人士的听证调查事件。电影界人士连署和当时与联邦调查局合作的约翰·伟恩(John Wayne)在电影联盟(MPA)举办的“保护美国生存之道”演说会上的演讲内容,恰恰与1791年通过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发生了冲突,特朗勃复述了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法案的内文:“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伸冤的权利。”
由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所带来的白色恐怖,对美国共产党人与相关嫌疑人员的调查、审判、监禁,在针对好莱坞十人案的叙事上,略过在好莱坞工业内部的工会运动及其共产党人的主体,遮蔽或放弃代表民族国家主体的公民所应该拥有的自由权利、对于“十君子”抵制最高法院审判结果的蔑视国会罪的背后实质,将冷战自由阵营的白色恐怖改写为美国内部民主自由奋斗的一元史观,并未敞开对其信仰的追问。自由概念的引用取自于美国,是全球化时代私有产权制度下的诠释。这一诠释,则将美国二战后产生的工人运动、为何参与工人运动并有共产党员身份的特朗勃等人官司败诉的具体问题的根源搁置,造成电影整体的不一致性。后者争取的自由价值,被遮掩了争取工人劳动的权益。历史事件影像的再现过程绕过立场冲突发生的根源,并予以一种对“左”翼廉价的同情,将这一群体虚无化、个人化,排除白色恐怖的历史条件,延续好莱坞一贯的主流话语特色,将历史去政治化的诠释结果纳入到主流历史叙事之中。
电影的前半部分叙述了好莱坞十人案在司法官司上与国会抗衡的失败,情节转折于《双重赔偿》的男演员爱德华·G·罗宾逊为求生而妥协于电影联盟,背叛同志,变成映衬特朗勃的角色,叙写转向者和受难者的关系。50年代初期,镇压变得更加强硬,被划入好莱坞黑名单的编剧,起初尝试以司法程序破除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战术,已经失效,拒绝听证质询后被判为蔑视国会罪。前半部分谈及的理念在同志的出卖之下,电影表述为集体“输了这场战役”,溃散成个人面临生存的难题,混淆了理念信仰与生存处境之间的关系。关于信仰的理念消隐于后来的发展,不协调地嫁接为关于个人奋斗价值的内容。这个转折将特朗勃的身份生硬地断裂,影片前半部分因共产党身份入狱,中期、后期则聚焦表现于作为编剧的特朗勃在工作中奋斗求生,原先致力于争取好莱坞工会运动的工人权益的特朗勃,在出狱之后转向了一个只认工作不问政治的被动的虚无主义者。
在本应作为关键塑造的、视共产主义为精神信仰的核心人物群身上,侧写则选择了摇摆不定、忽隐忽现的视角,无关紧要的对话缝隙中,钻出对共产主义刻板印象的片面理解,扁平化并白痴化地呈现人物精神,尤其刻意选择了向体制暴力低头而犹豫不决的转向者爱德华·G·罗宾逊,性格怯弱、情绪不稳定、最终死前身份无名的阿伦赫德(Arlen Hird),以及特朗勃手不离烟的糟老头虚无形象之外,影片并不再给予关于理念的另类形象解释。模糊特朗勃以及他周边历史人物的生命精神,以带病的身体、懦弱无能的男人隐喻所处社会当中的负面形象,将特朗勃的信仰与其同志的理念精神拆解成四分五裂的不明状物,重新包装成一种受创伤的受害者姿态,使之附属于扁平化、多元化的主体,消解具体理念在不同的阶层位置带来的冲突。影片的这种演绎,其背后的主导力量仍是担任美国意识形态传声筒的好莱坞式的文化诠释权。
以创伤治疗之名
影片收尾于特朗勃在洛杉矶的美国编剧协会的颁奖典礼上的演说:“黑名单作为一种邪恶的存在,那些从中幸免的人多少受到影响。这样一种情况已经超过个体可以控制的范围。每个人都有着本能的反应。他的需求、他的信念,还有他的特殊情况强迫他做出反应。那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时期,没人可以幸免。很多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家庭分裂,失去了一切,有些甚至失去了生命。”今日的民主转型之下,将普世价值植入历史再现的结构,将历史发生的事件视为一种在今日需要被治疗的创伤,抽离历史所处的具体条件,将创伤淡化为情绪形态来感染观众,其实试图将再现的主体的整体性削弱,将之演绎为一种对受害者进行创伤治疗的叙事。电影以创伤治疗的结论,呼应“民主与选举援助国际组织”在其手册《在暴力冲突之后的和解》中写到的关于今日民主转型的定义:“转型正义目标在于持续调查真相、正义、谅解和治愈,并致力于承担帮助人们远离过去的敌人。简单来说,‘过去的历史必须被提起是为了到达未来’。然而,甚至影响或触及转型正义看起来边缘,但它最终的结果仍值得努力。”
今日的正义、真相、谅解与治愈的标准制造了新政治正确的判断,它将过往处在麦卡锡主义时代政治正确的表象结构颠倒过来,表征体系因权力结构的改朝换代带来更替。《好莱坞的黑名单》除了好莱坞一贯的美学观点之外,也延续了白色恐怖历史至今无法被电影工业内部意识形态所包纳、始终被排除于电影叙事之外的历史之影。若简单地颠倒逻辑,面对被掩藏的历史,无感于结构变化的警觉,无感于现今反对过往真相的暴力姿态,且无所谓真相是否被重新发现,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借新修辞改写历史,回避直面历史的真实。
责任编辑/于溟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