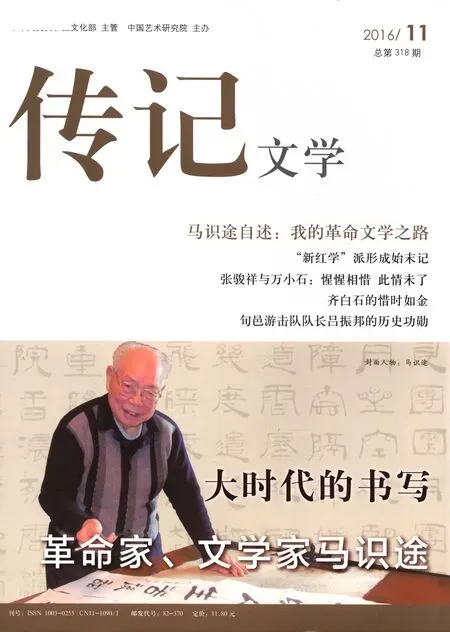张恨水传选章五
文|解玺璋
张恨水传选章五
文|解玺璋

婚姻
张恨水一生经历了三次婚姻,有三个女人曾经陪伴着他,她们是徐文淑、胡秋霞和周南(周淑云)。
第一次大约是在民国四年(1915)至民国五年(1916)的冬春之季,年纪在二十与二十一岁之间,而非很多书文所言之民国二年(1913)。那时,张恨水亡父不久,失学在家,堂兄张东野邀他到上海读书,后报考苏州蒙藏垦殖学校被录取。二次革命失败,学校被迫停办,他不得已返回家乡潜山。这是他第一次出行,无果而返。这期间,母亲似乎还没有和他谈到婚姻问题。很快,他因求学心切,再次离开家乡,来到南昌,进了一家补习学堂,补习英语和数学,为考大学做准备。但由于经济上难以支持,他离开学堂,借了一笔川资,到汉口投奔本家叔祖张楚萍去了。他在汉口时间不长,小报馆的工作并没有把他留住,民国三年(1914)岁末,张东野来汉口演戏,介绍张恨水加入剧团,随后张恨水就去了湖南,并于半年后辗转来到上海。这时,郝耕仁、张楚萍都在上海,他们一同过着潦倒的生活,却也自得其乐。这一年的“七夕”之夜,张恨水与张楚萍“落拓过金陵”,散步江边,随口作《七夕诗》一首:“一度经年已觉稀,参横月落想依依。江头有个凭栏客,七度今宵尚未归。”诗中不仅感叹了张楚萍的身世,而且隐含着规劝之意,只是没有提到他自己。可见,当时他还是单身,还不存在婚姻问题。到了十月,秋风渐凉,他又害了一场病,在上海就住不下去了,于是,他便借了路费,再次打道回府。
他与徐文淑的婚姻,大约就发生在此次回乡之后,与民国五年(1916)五月为营救张东野、张楚萍三赴上海之前。张恨水很少谈及这次婚姻,他的长篇回忆录《写作生涯回忆》及《我的创作和生活》对此事都只字不提,只有《我的小说过程》中提到过一句,为了说明问题,我把这段文字抄在这里:
二十一岁,我重别故乡,在外流浪。二十二岁我又忽然学理化,补习了一年数学。可是,我过于练习答案,成了吐血症,二次回故乡。当然,这个时候耗费了些家中的款子(其实虽不过二三百元,然而我家日形中落,已觉不堪了),乡下人对于我的批评,十分恶劣,同时,婚姻问题又迫得我无可躲避。乡党认为我是个不可教的青年,我伤心极了,终日坐在一间黄泥砖墙的书房里,只是看书作稿。我的木格窗处,有一株极大的桂花树,终年是青的,树下便是一院青苔,绝无人到,因此增长了我不少的文思。在这时,我作了好几部小说,一是章回体的《青衫泪》,体裁大致像《花月痕》,夹着许多词章,但是谈青年失学失业的苦闷,一托之于吟风弄月,并不谈冶游。
张恨水的这段回忆,或有不准确之处,抑或有忽略、简化之处,但他无意中讲到遭遇婚姻问题的时间,是在二十二岁的时候。据谢家顺先生考证,他在这篇文章中所用年龄为虚岁,推算下来,实际应是二十一岁。如果这时他已结婚,那么,只能是民国五年(1916)五月前,因为,五月后,他已到达上海,陈其美殉难后,参与其后事料理的人曾合影留念,在当年的这张照片中,我们看到了张恨水的身影。
关于张恨水的这次婚姻,坊间流传着多个版本,且人云亦云,真伪难辨。大致说来,此事系由母亲一手包办,女家是潜山县源潭乡徐家牌楼人,虽非名门望族,却也是当地大户,与张家相比,算得上门当户对。媒人是一位本家婶子,她们约好借看戏的机会去相亲。说是相亲,可双方家长并没有见面,而是由媒人指着远处看戏的人群,让张母望了一眼那个姑娘。张母的确看到人群中有个姑娘长得很标致,以为是自己未来的儿媳,亲事就这么定下了,接着,下了聘礼,新人进门的日子也随之定了下来。不料,姑娘娶进门,却并非她看中的那一个。儿子更感觉受到愚弄,十分委屈,遂在新婚之夜逃离洞房。家人连夜将他从后山找回,并责以孝道,母亲也流泪向他表示歉意,许他将来有中意之人,再另娶一房。张恨水既不能抗拒慈命,又有怜香惜玉之心,最后,只能由他默默地吞下这枚苦果。
至于所谓“调包计”,我以为,基本上是民间的一种想像。根据徐霁旻的考证,徐文淑的叔祖是清代戍边武将,以军功被赐予正一品建威将军;父亲徐海山是源潭乡有名的经馆塾师,文才极好,且相貌堂堂。他有四个女儿,依次为徐文淑、徐蕙淑、徐荷淑、徐杏淑。徐文淑在家时曾随父亲读书,“三百千、四书五经”都读过,还能背诵,而且,能写“工笔小楷,一手好字”。她不曾留下一张照片,我们无从了解她的“真相”,但据见过她的后人回忆,她的长相虽说不上漂亮,却也不像有些人描写得那么丑。这样一个女子,何愁嫁不出去,而非要采取“调包”之计?徐霁旻认为,在这件事上,张家、徐家都是受害者,问题出在媒人身上。然而,难以解释的是,如果徐家没有要求,那么,媒人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她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
当时的情形既难以复原,我也拿不出证据说事实不像民间传闻那样富有戏剧性。或许做母亲的确有难言之隐,娶进门的这个姑娘,不是自己相中的那个姑娘;抑或张恨水也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受这场突如其来的婚礼。但民间传说抓住这两点加以夸张,就有了张家中了“调包计”,娶回一个“相貌丑陋”“目不识丁”的村姑,洞房内吓跑了张恨水的故事。其实,徐文淑既不是丑女,也并非没有文化,至于“文淑”这个名字,更非大姑子张其范于新婚之夜所赐,当然也没有张其范教她识字、写字,鼓励她给丈夫写信的情节。张其范写过一篇《回忆大哥张恨水》的文章,其中对人们称赞她的这两段“闺房佳话”,只字未提。
尽管如此,张恨水对于母亲送给他的这个“礼物”很难说是满意的。新婚不久,他便离开家乡,去了上海。虽有很堂皇的理由,但他心里想什么,我们并不知道。而且,营救堂兄张东野、叔公张楚萍的行动失败之后,他没有选择返回老家,而是跟着李君磐的文明话剧团来到苏州,随后又到南昌,在外奔波达数月之久,冬天才回到潜山。试想,如果家里的这个人真的为他所爱,新婚燕尔,正是难分难舍之时,以张恨水才子佳人的心性,哪能把她一个人放在家中,自己在外游荡?即使重任在身,未必不归心似箭。他的不归,已透露了他的态度。在家没住多久,过了年,郝耕仁来信邀他出游,他又欣然前往。就在此时,他还动了隐居的念头。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说明,这次婚姻不仅没有使他感到幸福,反而增添了他的苦恼。这期间他作过一部小说《青衫泪》,因不曾发表,已湮没无闻,我们今天并不知道他在其中都写了些什么。有人望书名而生义,以为小说“反映出他婚姻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徐氏的不满”,我们也只能姑妄听之。
其实,张恨水的不满不是针对徐文淑的,当然,也不针对他的母亲。有人觉得,张恨水既读了那么多的古书,又仰慕才子名士的生活,对婚姻的想像和憧憬,也就逃不脱“才子佳人”“红袖添香”“闺中唱和”一类的俗套,他不肯亲近徐文淑,是因为徐文淑没能满足他的这种想像和憧憬。这种分析固然有其道理,但不是唯一的道理。这时的张恨水,虽然中了些名士才子的“毒”,对其“佳人”和夫妻情感生活有自己的要求,然而,除此之外,也不排除还有其他一些理由。我们知道,张恨水的青少年时代,正处在晚清和民初之间,这是新知、新学的蓬勃生长期。张恨水固然读了不少古书,却也读了很多新书。他是喜欢读小说的,旧小说他喜欢,新小说他也不拒绝,尤其是他还用心阅读了林纾翻译的许多外国小说。这些小说,除了教会他写作方法和技巧,新的思想和婚恋观也不可避免地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文学史家认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吴趼人的《恨海》与符霖的《禽海石》的发表,“预示着一个写情小说、甚至是写哀情小说的时期的到来,这也是西学东渐之中,中国青年男女欲争取婚姻自主的先声”。特别是后者,不仅把矛头直接指向孟子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且大胆提出了“更定婚制”的要求。而林纾所译外国小说如《巴黎茶花女遗事》之类,对于生活在礼教束缚下的中国青年来说,更是一种“诱惑”。张恨水是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他还没有勇气喊出自己的心声,他只能接受母亲的安排,但他的内心世界未必没有对自由婚姻的渴望,那些老旧婚制下男女青年的痛苦,未必没有引起他的共鸣。1926年7月8日《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发表了11年前他在长江边所作的那首《七夕诗》,特意加了前序后注,他在最后慨然长叹:“婚姻不自由,诚杀人之道哉!”既为张楚萍,也为他自己。
张恨水深藏着对“自由婚姻”的向往一路走来,他真心想要的,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他安排的婚姻,而是婚姻由自己做主。他曾委婉地表示:“这时,我的思想,完全陶醉在两小无猜、旧式儿女的恋爱中。”这也许就是此时此刻他对自由恋爱的一种理解。1929年3月3日《上海画报》刊登他的《旧年怀旧》一文,其中就讲到他在少年时代的一段“初恋”,曾与一个名叫秋凤的同庚女同学,“朝夕过从,相爱甚昵”,“私心好之,未敢言也”,“此事至今思之,觉儿童之爱,真而弥永,绝非成人后所能有”。直到1947年他五十二岁时,还不能忘怀此事,又于2月5日在《新民报》副刊《北海》发表《看灯有味忆儿时》一文,旧事重提。
这样看来,把张恨水婚姻的不幸,归结为“调包计”而强加给他一个“丑”媳妇,既是对徐文淑的不公,也是对张恨水的不敬,是小看了张恨水,把他庸俗化了。张恨水1929年5月22日在《世界晚报》发表了一篇《妻的人选》,文章不长,且抄录下来,留此存照:
绿荫树下,几个好友,谈至择妻的问题。有人说,要美丽的,我以为不如赏花。有人说,要道德好的,我以为不如看书。有人说,要能帮助我的,我以为不如买架机器。有人说,要能让我快活的,我以为不如找各种娱乐。说到这里,朋友不能再找出好的标准了,就问我要怎样的?我说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要一个能了解我的。
能了解我,我自然心满意足了,好看不好看,是不成问题的。道德二字,更是和我合辙了。至于如何帮助我,如何使我快活,她当然知道,那又何须说呢?一个人要得一个人了解,这却要得人家相当时间的认识,所以男女双方由恋爱而进到结婚,至少要有一年期间的过程。
了解二字,看似平实简单,要做到却不容易,有的夫妻,厮守了一辈子,都不敢说互相了解。张恨水对幸福婚姻的渴望和追求,正可以这两个字来概括。而他与徐文淑之间,缺的也恰恰是这两个字。然而,徐文淑毕竟出身儒生之家,谨守妇德,知书达礼,举止贤淑,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嫁到张家之后,作为媳妇,侍奉婆母,作为长嫂,关照弟妹,不仅赢得了全家人的尊敬,张恨水对她也多了一份怜惜与歉疚。虽然他们之间聚少离多,缺乏交流,但张恨水并没有遗弃她,而是尽职尽责地养了她一辈子。在张恨水的收入中,总有一份是徐文淑的生活费,并为她在家乡潜山添置了房屋和田产。1922年,他托二弟把母亲、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和徐文淑迁至芜湖;1925年,又把母亲和全家接到北平,徐文淑也随同前来。此时,他已娶了胡秋霞,一大家人住在一所前后五个院子的四合院,张其范在《回忆大哥张恨水》中写道,“大哥住北屋三间”,“妈妈嫂嫂和我姐妹,住在后进”,这个嫂嫂,就是徐文淑。她与胡秋霞姐妹相称,处得很融洽。她生过两个孩子,都不幸夭折了,为此她一直觉得愧对张恨水,于是,胡秋霞的孩子都被她视如己出,十分疼爱。据说,张小水出生时,因为是小产,落地不哭,俗称“闷地生”,徐文淑当即解开贴身衣裳,将血糊糊的婴儿“焐”在自己胸前,救了小水一命。直到晚年,张小水还说:“我的命是大妈妈捡来的。”他与徐文淑建立了深厚的母子情谊。1958年,徐文淑在安庆因脑溢血去世,张恨水因病不能出行,遂命张小水带了700元钱,千里奔丧,护送徐文淑的灵柩回到潜山老家黄土岭安葬。弥留之际,徐文淑拿出珍藏的两枚戒指,分送胡秋霞和周南,以表达她对两位“妹妹”的心意。如今她的墓碑上,立碑人写的就是:男晓水、孙继,即小水、张纪之误。
张恨水的第二个妻子叫胡秋霞。他们的结合不会晚于民国十二年(1923)10月。张恨水大弟张啸空于1923年10月2日在芜湖《工商日报》副刊《工商余兴》发表《游北海记》一文,其中写道:“癸亥仲秋节,恨水兄有一日暇,适北海开放,兄遂约予及秋霞嫂,共往游焉。”
张恨水与胡秋霞的结合见诸文字,这应该是比较早的一次。他在《〈金粉世家〉自序》中也间接透露了与胡秋霞结合的时间:“吾初作是书时,大女慰儿,方哑哑学语,继而能行矣,能无不能语矣,能上学矣,上学且二年矣,而吾书乃毕。”《金粉世家》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上连载,始于民国十六年(1927)2月15日,截止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5月22日,而慰儿正是他与胡秋霞所生的第一个孩子,由此或可推断,他们结合的时间,大约在民国十二年(1923)秋天。
关于胡秋霞的来历,综合各家说法,得到如下一些印象:她是四川人,乳名招弟,出身在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是挑卖江水的苦力,她四五岁时,被拐卖给上海一个姓杨的人家当丫鬟,后随这家人来到北京。杨家的人待她很刻薄,打骂是常事。一次,她摔坏了一个花瓶,被罚跪在雪地里,她不堪凌辱,鼓起勇气,逃出了杨家。先在街上流浪了几天,后被一位巡警送到了妇女救济院。按照她女儿张正的说法:“一个好心的巡警告诉她,石碑胡同有个妇女救济院专门收养无依无靠的女孩,妈便投奔去了。”她在救济院里糊纸盒,也学了一点劳动技能,长到可以婚配的年龄,院里便张罗着为她择偶。张正说:“1923年的一天,院里的女工头,送给妈妈几张男子的照片,让她选择一个作为丈夫。女工头主张她选一个中年商人,说这样有固定收入,女孩嫁了他,今后生活有保障。妈却选中了年轻的读书人——就是我的爸爸张恨水。”
张友鸾的女儿张钰在《恨水伯的婚姻》一文中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大约在1923年至1924年之间,有个朋友向他介绍了救济院的一位姓马的姑娘。那时,救济院里收养的无依无靠的女孩子,如若被人看中,只要双方同意,便可按规定办手续领娶。他去了救济院,一见之下,双方都很有意。那马姑娘人很灵秀,也有点文化,他有心娶她。不料当他向院方提出申请时,竟遭到拒绝。原来马姑娘已被别人看中,只是她自己不同意,那人便疏通院方,对她施加压力。这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马姑娘无奈之下,便把救济院里的另一位姑娘介绍给恨水伯,这姑娘就是胡秋霞。”
胡秋霞来自北平妇女救济院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不过,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材料中,有时也被称作“贫民习艺所”“社会福利院”或“福利救济院”,这些大约都是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出来的说法,抑或与这个机构在民国期间的几次演变也有些关系。北京的贫民救济机构最初发生在清末预备立宪期间,光绪皇帝当年批复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中,就曾涉及到一些城镇乡善举的内容,如:“救贫事业、恤嫠、保节、育婴、施衣、放粥、义仓积谷、贫民工艺、救生会、救火会、救荒、义棺义冢、保存古迹,其他关于本城镇乡善举之事。”民初,在京师习艺所的基础上,成立游民习艺所,直属内务部,以内务部部长朱启钤为首任监督。民国六年(1917)3月,内务部将游民习艺所移交京师警察厅管理,开始设立妇孺习艺所。到了民国十七年(1928),北京改称北平特别市,习艺所归属于社会局,游民习艺所和妇孺习艺所改称“妇女习艺工厂”和“妇女救济院”,并专门制定了这些机构的“收容妇女请领规则”。这样看来,张恨水的后人认为胡秋霞来自“救济院”,也不是没有道理,虽然民国十二年(1923)还没有这个称呼,但其渊源有自,而民间记忆通常会在时过境迁之后接受某个最流行的说法。
按照《北平特别市妇女习艺工厂、妇女救济院收容妇女请领规则》的要求,打算请领厂、院女为妻室者,首先“应由请领人填具详细声请书,附最近四寸像片两张,并取具本市区内曾经注册之商店三家保结,送请本厂、院审核”。同时规定,“一、无相当财产及职务者;二、有不治之疾病或残废者;三、无固定住址及确实铺保者”,不能领娶厂、院女为妻室。请领人的声请书经厂、院审核通过后,请领人还需缴纳被领娶女子在厂、院期间的生活费,并酌情缴纳慈善捐若干。这个规则虽然是民国十九年(1930)制定的,但考虑到其中的延续性,七年前,张恨水领娶胡秋霞时,经历过这些程序,也是可能的。他的孙子张纪就曾在《我所知道的张恨水》一书中写道,他爷爷在娶他奶奶时“交了一笔押金,交了照片”,这里所说的“押金”(也有人称为“赎金”),很可能就是《规则》中所要求的生活费和慈善捐。
民国十二年(1923),张恨水二十八岁,已经远离家人,在北京独自生活四年了。经过四年的打拼,他在京城算是站住脚了,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而且收入不菲,不仅个人生活有了保障,还能负担家里日常所需,以及弟妹的教育费用。但孤身作客他乡,到了夜晚或生病的时候,就很不是滋味。一年前,他的确得过一场大病,他在1946年9月15日的《新民报》北平版发表《隔巷卖葡萄声》一文,讲到当时生病的情形:“予居平之三年初秋,患伤寒,甚殆。幸不死,卧床亦久。由中元以至中秋,均缠绵床褥间。予青年困于婚姻,且以父丧失学,备极懊恼,时昏卧会馆,鲜有照顾者,而孀母幼弟正群客芜湖北上未能,月赖吾三四十元之接济。予病,自秘之,家中浇裹(嚼裹)亦勿能寄,枕上无事唯思不得意事自遣。复念病或不起,孀母丧其长子将不能堪,其下除仲弟已冠,可经商外,其余弟妹四人,均弱小将失学,其不幸更甚于卧。以养母育弟,予固跪誓于先君弥留之际也。思极而悲,泪涔涔落枕上。”
他在小说《春明外史》中也写到了这场病,见于第八回“佛国谢知音寄诗当药,瓜棚迟晚唱咏月书怀”:主人公杨杏园生了一场大病,在会馆躺了许多天,身边只有一两个朋友,半夜醒来,胡思乱想,真切体会到“孤身作客的人,这病境最是可怜的”。想来想去,“由追悔不该到北京来,一直追悔到不该读书。心想病一好了,什么事也不干,赶快回家罢”。接下来便写了与他相好的那位清倌人梨云来看他,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作者接着写道:“梨云这一来不打紧,又添了杨杏园一桩心事,心想如此看来,妓女的爱情,不见得全是假的。又想:‘就算假的罢,她能特地来看我,也算难得。我在北京的朋友,尽管不少,除了两三个极熟的人,谁又曾来看过病呢?’想到这里,反而觉得梨云小小年纪,倒是他一个知己,心想我要讨了她回来,也就算万愿皆足了。”
一个成年男子,于漂泊羁旅之中,往往需要一个异性朋友,给他安慰,给他呵护,尤其是在病中,这种心理乃至生理上的需求,就更加强烈。爱情固然是两个人心灵上的共鸣,却也不排除孤寂中的相互慰藉。而张恨水的文人气质,只能使得这种需求更深沉、更细腻。他应该想到了要找一个人在身边,陪伴他、照顾他,但他又很纠结于自己的“困于婚姻”,难以释怀。这一年的旧历新年,他回了一趟芜湖,看望分别数年的母亲、妻子、弟妹。其间他们是否议到了张恨水再婚之事,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他从芜湖回到北京,这件事似乎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对此事,他表现得相当郑重和谨慎。张正在《魂梦潜山——张恨水纪传》中就曾提到郝耕仁的女儿郝漾给她讲过的一件事,郝漾对她说:“我在父亲书房读书,无意中发现了一封恨水伯写给我父亲的信,是在娶你母亲之前写信征求我父亲的意见,信中伯父对包办婚姻态度是明显不满的,他信中原话不记得,大意是这样的:多年来,我漂泊社会,年纪也不小了,仍未解决婚姻大事。现在京认识一位女孩,十六七岁的样子,相貌端正,出身贫苦,我很怜爱她,想娶她为妻,也可以在京安家,解决婚姻的问题。”
张恨水与胡秋霞婚后的生活是和谐而美满的。胡秋霞很小就被拐卖,除了“招弟”这个乳名,她对自己的年龄和娘家的姓氏已没有任何记忆。胡姓是张恨水根据她的四川口音推测的,并以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为她取名“胡秋霞”,并正式申报了户口。胡秋霞不识字,也不算漂亮,但她年轻,有活力,且为人爽直,心地善良。她是苦水里泡大的,能嫁给张恨水这样一个有才情、懂得爱、能让她衣食无忧的丈夫,很满足,也很幸福。最初,她不知道张恨水在老家已有妻室,结婚后,张恨水把实情告诉她,并表示自己对包办婚姻是不满的,她也没说什么。
婚后不久,张恨水便把家从潜山会馆迁到了铁门胡同73号丁宅。他在给友人张香谷的信中提到此事:“水于真日迁入铁门73号丁宅。”几天后,他又在《春明絮语(续)》中讲到这次迁居:“予近迁居铁门胡同73号,为青衣票友蒋君稼故宅。友人张香谷作函贺之,并谓蒋善歌,必有绕梁余音可闻。其事甚韵,予因作骈体文复之。”看来,张恨水的心情很不错,他显然受到了胡秋霞的感染,她的嘘寒问暖、悉心呵护,也让张恨水的饮食起居大大改观。二人世界,本没有太多的家务,闲下来,她就坐在张恨水身旁,安静地看他写作,或与张恨水一起去看电影、听戏。张正说:“妈的绝大多数兴趣爱好都是受爸的熏染与影响。”张恨水还为妻子制订了学习计划,“他手把手地教她握笔,从描红模子开始,每天认几个字”。很快,她就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并且能粗读报纸和小说了,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作品,她都是第一读者。张恨水有一阕《蝶恋花》,写于生日前夕,记载的便是妻子来询问他,明天打算如何过生日:

1935年版《啼笑因缘》
帘钩响动伊来到。屈指沉思,灯下低声道:明日如何消遣好?良辰千万休烦恼。原来生日浑忘了,客里年华,多谢伊关照。我自伤心还一笑,伤心不要伊分晓。
我们不知张恨水因何而伤心,但他在妻子面前掩饰了自己的伤心,而感谢妻子的好意。词作写得十分生动,一个体贴、温存的妻子形象跃然纸上,也为他们的夫妻生活留下一幅逼真的剪影。婚后一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慰儿。女儿的到来,使他得到一种安慰,生活也平添了许多乐趣。民国十四年(1925),张恨水把全家迁到北京,并租下宣武门东大街路北未英胡同36号的一所院子,作为家居。张其范在《回忆大哥张恨水》一文中披露了这次全家不远千里迁移北京的原因:“1925年,我考取北京女师大,大哥怕母亲挂念,遂把安庆的家,也搬来北京。全家十四口人,除二哥工作外,全依赖大哥生活。”这是很重的一副担子,当时,大妹读女师大,两个弟弟读私立大学,小妹妹读高中,每个学期的学杂费就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都得张恨水去筹措。因此,他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白天在家写小说,有时同时写几部小说在几家报纸上连载,夜晚还要到报馆去编报”,与胡秋霞单独在一起的时间自然就少了,她或许有一点受到冷落的感觉,有时会借酒浇愁。她要熟悉、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并不十分容易,但她很努力地要融入这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老太太希望张恨水能给原配徐文淑留下一个孩子,母命难违,张恨水不得不出入徐文淑的房间,胡秋霞则表现得善解人意,令人刮目相看,终于在这个大家庭中赢得了一个“好”字,侄儿辈称她“好妈”,外甥们称她“好舅妈”,弟妹们称她“秋霞嫂”。张恨水对她的评价则是:藏拙、守成、率直。
周南是张恨水的第三个妻子。她原名周淑云,是北平春明女中的学生。周南是婚后张恨水为她改的名字,常使人联想到《诗经》中的“周南”。张恨水与周南的结合,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周淑云因《啼笑因缘》而暗恋张恨水,非张恨水不嫁,其母无奈四处托人说媒,张恨水的妹妹张其范恰在该校任教,便请她将女儿带去与张恨水相见,张恨水一见钟情,于是缔结连理。
不过,张恨水似乎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在1944年出版《夜深沉》单行本时写的自序中说:“可是我内人所爱好的,却是这部《夜深沉》。我们的结合,朋友们捏造了许多罗曼斯,以为媒介物是《金粉世家》或《啼笑因缘》,其实并不尽然。其实《夜深沉》远在我们未结婚以前就已出版,介绍人应该是它。”仔细揣摩张恨水的这段话,其实并不能得出两人结合与《金粉世家》或《啼笑因缘》无关的结论,只是其中被“朋友们捏造了许多罗曼斯”而已。如果剥去所谓的“罗曼斯”,那么,我们看到,他们的相识源于一次游艺会,也有人说,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游艺会,而是北平新闻界和教育界联合举办的赈灾义演活动。据说,在这次活动中,张恨水饰演《女起解》中的崇公道,春明中学的女学生周淑云饰演苏三。不知道这样的赈灾义演在1931年举办过几次,是不是每次都由张恨水出演崇公道一角?根据万枚子的回忆,这一年夏天,武汉大水,北平新闻界确曾发起赈灾义演,地点在湖广会馆,张恨水在《女起解》中担任崇公道一角。难道与周淑云同台演出就是这一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的婚礼就显得比较仓促了。民国三十五年(1946)旧历八月初八,张恨水为纪念他与周南结婚十五周年,复印了结婚照并在背面题字,由此可以确定,他与周南结婚是在民国二十年(1931)旧历八月初八,阳历为9月29日。这个日子离义演的日子是不是太近了呢?

张恨水与周南
总之,他们在这一天结为夫妻。从这次婚姻中,张恨水终于为自己多年来一直期待的爱情找到了归宿。即使是在重庆海棠溪生活期间,他也会忆及当年的闺房之乐。一天,他看到市里有跳棋出售,便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并写下短文《跳棋》:“十余年前,内子归我,如小乔之初嫁,所谓其乐甚于画眉者,闺中亦不能平靖无事,因之予乃劝之读唐诗,作花卉写意,并习赵柳楷字。初一二课或亦感生兴趣,三日以上,即百呼不理矣。及予示之跳棋,则甚喜。北平冬夜,室外朔风虎吼,雪花如掌。而室中则电炬通明,炉火生春,垂帘对坐,盆梅吐艳。围炉小坐,剖柑闲谈,遂亦不思他乐。坐久人倦,乃对案下跳棋。相约予负则明日为东道,陪之观剧。胜则彼亲自下厨调鲜同膳,而十局之战,予必负七八,故彼极乐为此。”于是,他买了一副拿给爱妻,问她还记不记得当年玩过此物,周南则以“马齿徒长”为之一叹,他也就“闻之而兴沮”,继续在昏黄的灯光下,写他的小说。而“内子在旁,共灯为小儿补结旧绳衣,各各默然”。这时,他忽然“停笔昂首,乃作长喟。彼即起夺予纸笔曰:‘尚不思睡,曷温跳棋乎?’予笑曰:‘余子何堪共话,只君方是解人。’乃即移灯布棋,共下三局,而时转势移,三局皆予胜而彼负”。
张恨水与周南的夫妻生活,民国三十三年(1944)夏天写作《山窗小品》时多有提及,这在前两次婚姻中是极少见的。再如《劣琴》,写到他“自幼酷嗜皮簧,几至入迷,及娶吾妇,妇亦嗜此,既得同调为终身伴侣,嗜尤深”,这似乎也从侧面证实了,他们的结合,京剧曾是媒介之一。然而,入蜀之后,看戏的机会几乎绝迹,“终年不复一入剧场”。有了戏瘾怎么办呢?“强细君(周南)低声歌之,吾口奏琴手拍板以合音节”而已。一天,朋友送他一把胡琴,他又在街上购得一批青衣唱腔琴谱,于是,“在黄米饭饱后,山窗日午,空谷人稀,乃掷笔取琴,依谱奏之”,而“每当弦索紧张,细君隔室停针,辄应声而唱”。张恨水是很享受这种生活情趣的,甚至得意地以“吹箫引凤”自喻。
有时他们也谈诗。他说:“内子(周南)随余久,间亦学读古唐诗合解。”自然也是懂诗的。据说,当年她曾以“南女士”之名在《新民报》发表过诗作《早市杂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嫁得相如已十年,良辰小祝购荤鲜,一篮红翠休嫌薄,此是文章万字钱。”“朝霞沾鞋半染衣,街头浓雾比人低,晓凉敢说侬辛苦,昨夜陶潜负米归。”能从清苦日子中品味到诗情画意的人,一定是个有“诗心”的人,这也是周南最让张恨水得意之处。张恨水在《劫余诗稿》中讲到一件事,他们住在海棠溪的时候,一天,周南在窗外晒旧书,发现一张残破的旧报,上面是一首五言古诗,题目为“悠然有所思”,但“独缺署名”。她诵读再三,觉得很像张恨水的作品,便拿给他看,笑着说:“此似君作,发表于《南京人报》者乎?”这件事让张恨水兴奋不已,他写道:“余大笑,因吟曰:‘喜得素心人,相与共朝夕。’”素心人就是心地纯洁、淡然处世、能把日常生活过出诗意的人,这才是张恨水心中向往的人。那天,他大喜若狂,“余复大笑,笑且一日数次”。周南问他为何这样高兴,他说:“三年来,非相与伤感物价,即为群儿顽劣事相争执,闺中之乐,甚于画眉者,此调生疏久矣。窃以为卿仅知予不谈物价,仅知予厌群儿嬉戏,大背人情,今觉殊不然也。乃一见而识吾诗,十余年相聚,诚未白费,焉得不乐?”
我们是从多年后张恨水对往事的回忆中,推想他与周南结合后的满足感和幸福感的。他们的年龄虽相差二十岁,但婚后生活却可谓琴瑟和谐、意趣相投,有着说不尽的喜悦和甜蜜。对于这样一个可人,张恨水以“周南”命名之,倒也恰如其分。可是,他的家里毕竟还有两位夫人在,对他来说,不能不是个难题。婚前,他向周南交代了自己的婚姻状况,请她认真考虑,据说,周南表示:“只要和他终生相伴,并不计较他已有了妻子。”甚至婚后他要对徐文淑和胡秋霞尽一份做丈夫的义务,周南也能体谅,并不干预。但胡秋霞却不能接受张恨水的这次婚姻,她的女儿张正说:“我母亲当时还曾提出过离婚。”站在女性立场,应该承认,胡秋霞的要求是合理的,张正也曾表示,她“由衷地钦佩妈妈作为女性的自尊、自爱与自强”。而且,就在当年5月,《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正式实行,其中特别规定:“有配偶者不得重婚。”当然,国民政府司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又称,娶妾并非婚姻,实际上是为重婚开了方便之门。张恨水娶周南,固然是以正式婚姻对待之,但社会舆论显然并不追究,其实是理解为纳妾的。至于胡秋霞,尽管她曾有过离婚的想法,而面对现实,她又不得不考虑,一个无依无靠的女子,身无分文,又无一技之长,如果离婚,如何维持生活?又如何抚养自己的儿女呢?况且,她的确深爱着这个男人,而张恨水也从未忘情于她。
于是,在婆婆和众人的劝说下,胡秋霞不得不与现实妥协,接受了周南。此时,张恨水将全家从未英胡同36号迁至西长安街大栅栏12号,并另租铁门胡同,与周南建立了新家。此后,他更多的时间是与周南在一起,对徐文淑和胡秋霞,只是尽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他有一篇文章曾借京剧《双摇会》谈及对多妻家庭的看法,认为剧中对多妻的讽刺是很公道的,同时,他又无奈地指出:“一个家庭,自不宜多妻,既已有此事实,就当想法解决,来个‘家和万事兴’。”这自然也是张恨水在生活中的态度,他总是尽力维护这个多妻的大家庭的安宁与和谐,当然很不容易,有时也不得不暂时逃离这是非之地。刘半农1934年1月3日的日记就记下了与张恨水有关的一笔:“与牧野(张恨水二弟)、颖孙(姓郑,系北华美专教师)同往方家胡同看恨水,值出,入其书斋中小坐,牧野云,恨水即将往西北旅行,因有一妻二妾,难乎其为夫,故不得不暂往他处以避烦恼,然他日归来,旧账仍当总算,不悉将何以为计。此所谓自讨苦吃,局外人莫能赘一词。”

20世纪50年代,张恨水(右二)与周南母亲、徐、张羽军在砖塔胡同95号合影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