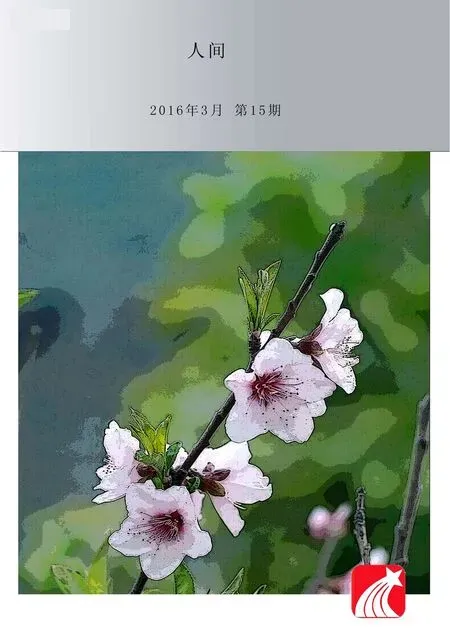潘年英《伤心篱笆》的象征符号解读
何婷(西北民族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潘年英《伤心篱笆》的象征符号解读
何婷
(西北民族大学,甘肃兰州730000)
摘要:侗族作家潘年英借助文学人类学的创作方法,以《伤心篱笆》为代表,展示了文本书写蕴含的侗族文化。本文通过对“符号”这一人类学写作途径,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括符和图片符号的真实记录等方面进行阐释。结合符号学相关知识,在文学人类学创作视野下,对《伤心篱笆》进行象征符号解读。
关键词:《伤心篱笆》;文学人类学;符号
《伤心篱笆》是侗族作家潘年英人类学笔记系列之一,作者深入侗乡的田野调查,以“深描”性的手法和抒情的诗意笔触,借助大量文学人类学独特的创作方式,向世人描绘了一幅幅侗乡的优美画卷和一个个忧伤的民间故事。本文主要借助符号这种独特的写作途径,运用文学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分析《伤心篱笆》的象征符号,挖掘象征符号深含的侗民族历史文化的共同记忆。
一、人类学写作的途径:符号
侗族作家潘年英将自己的《故乡信札》、《木楼人家》和《伤心篱笆》三部作品命名为“潘念英人类学笔记系列”,文学人类学写作是一种新兴的创作方式,它既能达到对文化事象的客观细致描述,又能融入研究者的情感与体验,从而引起读者对文化问题的深思[1]。其中《伤心篱笆》是一部中篇小说集,收录了《伤心篱笆》、《落日回家》等十个优美而哀伤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建构了一幅家乡盘村的人物风俗图,画卷里包含典型的意象描写,犹如一个符号王国。故乡盘村的人事被幻化成一个个生动形象的符号,听觉、视觉等交感手法诠释了侗民族的传统文化及其生存状态,作家借用符号抒发了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之情和担忧之虑。
从象征符号入手对潘年英小说的深刻意义和创作特点进行解读,将会是一个独特而新颖的视角。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将符号分为图像符号、指索符号和象征符号三大类。其中,图像符号指的是符号形体与它所表征的对象之间具有相似性。图像叙事在《伤心篱笆》这部小说中作为一种独特符码,将图像植入其创作中,在传统叙事的基础上融进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相关知识,运用图像符号对侗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了鲜活的记录,抓住民族内部稍纵即逝的记忆。指索符号指的是符号形体与它所表征的对象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因果或接近性联系,使得符号形体能指示出符号对象的存在。侗族是一个热爱唱歌的民族,悠扬动听的声音让人流连忘返,歌声不仅成为那个独特族群的共同记忆,而且侗歌早已成为整个侗民族的指索符号,侗乡人用歌声传承着民族独特的故事传说、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象征符号是基于一定的基础而代表某一事物的符号。《伤心篱笆》中的父亲是传统故乡的典型代表,他古老而沧桑,几经风雨却有屹立不倒,饱受现代文明的冲击,却坚守心灵的净土,将自己那颗勤劳朴素的心牢牢地系在了那片土地上,父亲承载了我对故土深厚的情感,象征了侗民族悠久的传统。符号学家布加齐列夫以石头为例认为:符号化发生于一个物体获得了超出它作为自在和自为之物的个别存在的意义时,一块石头不是符号,当人们将这块石头安放在了田间作为分界时,那么这块石头便成了一个符号。[2]《伤心篱笆》运用符号意象构建了一个侗民族文化的记忆库,在一幅幅图像和一个个括符中,我们存封了那些有关故乡遥远的记忆。歌声、父亲和月亮等众多符号里,一种诗意情感的叙事和理性科学的田野调查交相辉映,发出历史沉重的悲鸣。
法国汉学家安妮·居里安说:“大人、小孩和故乡都是潘年英小说叙述中常见的因素。我觉得《日落回家》这篇小说是一个文化的比喻象征,大概也可以说是侗族文化的比喻和象征。潘年英的很多小说,都可以看作是人类学的比喻和象征。”[3]《伤心篱笆》从某种程度来讲就是一个象征符号的集合。
二、歌声·父亲·月亮:民族文化记忆
(一)歌声:族群的共同记忆
侗族是一个热爱唱歌的民族。侗族大歌尤为著名,山歌、情歌、哭嫁歌、饮酒歌等更是独具特色。歌声一响起,一天劳作的疲惫得以舒缓;长期酝酿的情感得以抒发;古老的民族故事得以流传。歌声成为那个独特族群的共同记忆,而故乡的一切也仿佛荡漾在歌声的海洋里。
翻开《伤心篱笆》,一个个主人公都引出了一段关于侗歌的故事:
生得面丑的四公,日子也过得很苦,但他却凭借吹得一口好木叶,外加天生一副好嗓子,迷倒了不少姑娘媳妇。侗歌也许少了几分华丽和优美,却多了一份古朴和自然,延续了侗乡人单纯美好的情愫。
歌魂附身的小满,歌声悠扬动听。“当大病过后的小满再也不能唱歌时,她便从这世上突然消失了,歌声赋予了她生命力和活力,当歌消失以后,也带走了她的魂魄。不能不说歌声是一种青春活力的符号,一个生命的符号,拥有歌声的侗乡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每一个音符的跳动都为其存在抹上了鲜艳的色彩。
教授民族语言文字的彩秋,她教同学们唱的那首情歌,正如文中所说“这首歌从演唱形式到歌词的内容,都纯粹是用我们的民族语言来表达的,我们的民族语言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语言之一,它音节优美,表达丰富。用我们的语言演唱的民歌,实际上是不可翻译的……”。民歌是不可翻译,歌声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独特语言文化,富有其民族性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在其文字背后更蕴藏着这个族群的独特气息,歌声的符号诉说了那个古老民族的一切。
(二)父亲:故土的遥远记忆
父亲这一人物形象在小说中频频出现:《连年家书》里面父亲的四封家书使其形象跃入眼帘。父亲的信是具有代表性的,传达了家乡的信息,父亲成了一种家乡的符号,连接着家乡的一切和城市中的“我”,把我的心系在了那片故土。信中表现了他用一种乐观精神来面对家人所处的困境,每一封信都深深透露出了父亲直率朴素的真挚情感,父亲成了一种爱的符号,它温暖了“我”那颗漂泊他乡的无依无靠的心,给了“我”在茫茫人海中踟蹰前行的动力和勇气。
《落日回家》里的父亲:一辈子从事农业活动,他对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充满了爱,对那片土地上的庄家更是料理得细心周到。他坚决反对不管理农业生产而热衷淘金的行为。父亲成为了一个符号,一个故乡传统文化和思想观念的符号,他在新兴事物和年轻一代的冲击下显得势单力薄和束手无策,往昔光芒也逐渐消失在落日的余晖里。父亲见证了一个民族摇摇欲坠的诗意家园。
(三)月亮:文化的悠久记忆
月亮和侗族有着深厚的渊源,“月亮文化”的传统一直保持在民族内部,那些与月亮有关的故事在侗乡中世世代代地流传着,月亮走进了侗乡人的生活,包含了侗族人民点点滴滴的生活经历,指示了侗民族遥远的存在。
《大月亮小月亮》中,大月亮指姐姐王月英,小月亮指妹妹王月兰,她们俩不仅人长得很漂亮,而且出嫁歌唱得顶好,“月英和月兰唱起歌来,那声音是非常甜美动听的,仿佛莫名其妙地要勾人魂魄。”[4]看着这些优美的文字似乎也能听到她俩唱出的动听曲调。在哥哥王四海的帮助下,她们进了城,最后以悲剧告终。
曾有人问过潘年英,“你一定要把月兰的遭遇安排得怎么悲惨吗,能不能换一下结局。”,作者回答说,“为什么要换呢,我只不过是把事实呈现出来而已。”侗族人崇拜月亮,它就像自己民族的化身。此时的月亮,既指那一轮挂满清辉的玉盘,又指月英和月亮那不可抗拒的悲苦命运,更象征了整个偏远侗乡所处的尴尬困境:它不能被大城市所容,同时也无法回到其原本的面貌。
三、标号、图像:盘村的记忆符号
(一)文本创作的括符使用
括符在潘年英的《伤心篱笆》中频繁出现,它不仅是作家在双重身份(潘年英既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作家)下跨专业写作的独特标志,而且还彰显了小说感性和理性的双重叙事结构,作家在真实和虚幻中,抒发了对故乡的情感。括符是作家提醒自己,重温记忆,追溯历史的一种象征符码,整个世界都是由运动变化构成的。侗乡盘村建构在括符这种象征符码的背后,蕴含着作家对民族发展的一种担忧、对民族文化的一种眷恋、对民族人事的一种追忆,最终将人们引入到一个反思的境遇里。
“积水人是喜爱打鱼的,而河里的鱼也很多,一个大男人,若早上吃了早饭出去(积水人吃饭大约在九十点钟的光景),到下午太阳落坡(四五点钟左右)回来……”[5];“过去积水地方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鱼随你捕,随你吃,但不许买卖(积水地方旧时鱼多家家有鱼,恐怕也买卖不起来)……”[6];“而两个妹妹则是完完全全的文盲(积水地方自古以来的规矩,是不让女孩子读书的,积水地方的女孩个个是文盲)……”[7]。
括号多出现于科技说明性文章里,标明行文中注释性的话语,起到补充、解释说明作用。小说中括号的使用主要也是起解释说明的作用,但它还具有深层的符号意义:首先,阻断了读者的阅读思维。叙事性阅读给人一种流畅之感,解释说明的括号一出现,读者就会转移注意力,此时的思绪便回到“积水”,原来“我”现在阅读的东西,不是“我”生活中的,而是那个叫积水的地方独有的,积水在哪儿,在那偏远的侗乡盘村。通过括符,读者感觉可以在阅读中去了解侗乡盘村人生活的真实情况,但又被每一个故事拉进一种似真似假的幻觉。其次,括号是作者对盘村的记忆符码。这部小说是作家借助独特的符号为家乡写的,原来那时候我们是“九十点钟的光景”才吃早饭;那时候积水地方鱼很多,几乎家家都有鱼;在故乡女孩子是不让读书的,所以积水地方的女孩个个是文盲。作者的身影在整部小说中穿梭,置身括号里为读者喊出了他对故乡的记忆。最后,“积水地方的女孩自古以来就是个个文盲”,此时的括号,不仅解释了当地的教育情况,同时也点出女孩儿的社会地位,月英和月兰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她们没有受过教育,找不到任何立身之地,最终以悲剧结尾。
括符里发出了一声呐喊,引起了故乡人的注意,更默默地注入了一种反思的哀鸣。悠久的侗族历史文化如何在主流文化中做到“不同而合”,一代又一代的侗乡人如何在高速发达的现代化社会里求取一席生存之地,最终都将本民族的教育问题推上了浪尖,令人深思。
(二)记忆保鲜的图像符号
近年来随着文学人类学的发展,传统的国学方法得以开拓和更新,从20世纪初的二重证据法,到90年代的三重证据法,人类学视野和方法的引进使得中国传统文学研究得到了一个新兴的增长点。21世纪初,叶舒宪先生提出的“四重证据”推动了文学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更新,符号学视域下的四重证据研究得到了拓展,四重证据法的提出将跨学科间的文化整合认知推向了高潮。四重证据法既是物证和图像证,又是物和图像的叙事,图片不仅在民族学和人类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在文学人类学研究中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图像叙事在《伤心篱笆》这部小说中作为一种独特符码,其创作在传统的基础上融进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思维、方法和形式,同时又将其叙事的内容和对象深深地植根于侗民族传统文化中,借用了鲜活的图片记录抓住民族内部稍纵即逝的记忆,为边缘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彰显了生命力。作品中的图片是作者辑录文章是插放进去的,全书一共插入了二十几张图片。自然风景:一条山溪绕村流淌,溪水欢腾着,打闹着,流向远方;故乡的木屋依山而建,绿荫环绕,给人以安宁和平静之感。赶集画面:乡民们挑着担子到镇子上去赶集,还是那些逢古历三、九的日子里,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妇女们总爱赶集,三五搭伴而行,不买也可以去逛逛。服饰装扮:一色的青衣,远远看去,一排豌豆花儿似的,那衣服是盘村人自种、自织、自染和自制的。各种人物:那娘辛勤劳作的背影,拉长在屋角,勾起了遥远的回忆,仿佛她还依然年轻充满活力;故乡儿童的面庞是一幅忧伤的画面,一双双清澈的眼睛好像在渴望着什么,但最终也只能被贫困所淹没;杨家湾发现了大金矿,全村男女老少都上山去淘金了,孩子不去上学,大人也不去地里劳作,大家都沉浸在淘金热中,一种欲望弥漫开来,隐隐地散发着死亡的气息。图片和所写的内容具有一定程度的契合性,是一种虚构的真实,图片犹如一层保鲜膜,使得小说色香味俱全。图文并茂是一种特殊的叙述方式,瞬间增强了读者阅读的画面感,惹人联想,引人置身其中。
图片是一种视觉符号,它为人们展现了一幅幅家乡盘村人、事、物的概貌图,小说还是那些文字,而图片只能是那个时候的那些图片,它是瞬间和永恒的结合体,它让故乡的一切存封在记忆里,永远活在文字故事中。前人用照片记录历史,后人用照片回忆历史,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深刻而动人的故事,既像一首古老的民歌,又像一个遥远的传说,更像一个民族的容貌。照片早幻化成为民族本身的独特符号,就在那些被时间冲刷干净的历史里。
《伤心篱笆》是一个符号王国,潘年英运用了一系列符号意象建构了故乡盘村,他将侗族人熟悉的事物转化成了众多的特殊符码意象,深具民族色彩,使得它们成为侗族文化的表达载体,诠释古老侗族的文化记忆。
参考文献:
[1]刘慧.潘年英的《伤心篱笆》与人类学文学写作实践[J].百色学院学报,2009,(3):10 -13.
[2][3][4][5][6][7][8]潘年英·伤心篱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49.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864X(2015)05 -0001 -02
作者简介:何婷,西北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