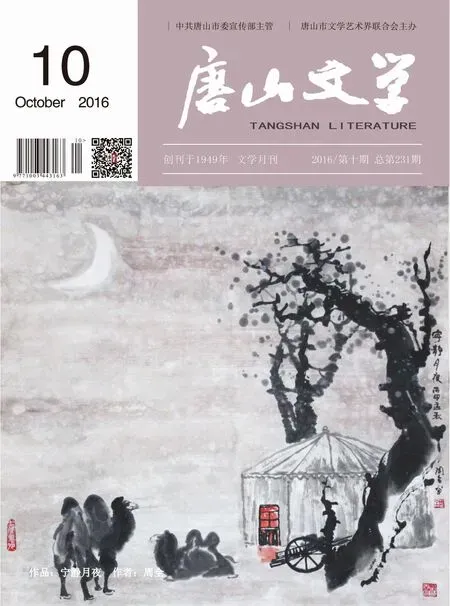生命的华章,人间的赞歌
——李广田创作简论
康明珠
生命的华章,人间的赞歌
——李广田创作简论
康明珠
李广田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跻身文坛,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教育家。他的创作风格正如其人一样,表里如一,独具特色。研究界基本把握了作家创作的思想内容、叙事策略、语言风格探索等方面,但比较而言,立足文本解读的个案研究较多,宏观把握的研究相对较少,据此,结合作家的创作历程,笔者对其创作情况进行简要梳理、概括和评述,以期对李广田创作进行整体把握。
李广田是二十世纪对中国文学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作家,是三十年代文坛上著名的“汉园三诗人”之一,由“诗”入“文”,他的散文可以说是别具一格,他的《悲哀的玩具》、《上马石》、《野店》、《山之子》等散文,至今仍为人们所记忆。此外,他还整理了少数民族民间叙事诗《阿诗玛》,据此改编的电影家喻户晓。李广田的文学观,从他的创作本质看,可说他是一个本能的人道主义者。李广田说,对他写过的人物,他“都爱过一场”。他关心他们的命运,他要表达他们命运的真面目,追问他们命运的由来和去处。他说:“为了吃一口粗饭,人们把什么方法都想到了。你想想看吧:北平的天桥、什刹海,济南的北岗子(最下等妓女的聚集地),泰山下的岱庙,叙永的大桥……我们这人间真够丰富,也真够惨!”(《日边随笔》)“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李广田是一个真正的诗人。“诗”和“人”不能分割,诗、人是相依为命、同体共生的,冯至先生说李广田“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的确如此。他的诗歌也好,散文也好,绝对没有背离生命感的浮华的技巧,李广田是个表里如一、性格坚强的作家,他一生没有背叛纯正的艺术,没有放弃过对生活纯真的热爱和追求。
诗歌:生命的启航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李广田以散文创作著称,但最初却以诗歌创作步入文坛。其初期诗作主要见于诗集《向往的心》。该集共收诗44首,均作于其从宋明理学的桎梏中挣脱出来之后的1925年至1929年。因为它们写于不同时期、不同心境下,所以内容比较驳杂,其中既有“空虚的哀伤” ,也有进击的执着。诗集也由此构成了两组意象:第一组是“寂寞”、“春”、“夕阳”等,第二组有“希望”、“爱”、“阳光”等。这两组意象相互对峙,极具张力地并存在一起。通过这两组意象,我们既可以发现诗歌内容的驳杂,更可以悟出经历了“五四”迟到的启蒙的诗人心灵的矛盾。第一组意象在诗集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以至于李广田在论及其早期诗作(包括《向往的心》)时称它们“内容是空虚的哀伤”。“空虚的哀伤”之感主要是借助于这一组意象传达出来的。它在诗作中反复出现,渐渐积累起了其象征意义,成了一个带有原型意义的主题意象。这个感觉意象在诗中不断出现,无疑传达出了这样的信息:即诗人最初的吟唱与孤寂哀伤结下了不解之缘。“春”与“夕阳”是“寂寞”这一感觉意象的视觉展现,“春”本是美好、希望、生机、活力的代名词,但李广田早期诗作却反其意而用之,使之成为寄托孤寂哀伤之情的符号。这是李广田的个人意象对公众意象的一次颠覆。在他笔下,“春”一方面意味着时光的无情流逝及其对青春、希望的葬送。《向往的心》给人感受最强烈的首先是它的情思的真实性。它是一个纯洁赤诚的青年有感而发的叹息和呼喊,是他的情感和思想的真诚宣泄。由于“这些诗中所表现的真实性”,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人格”,触摸到了一颗诚实心灵的真实的搏动。
李广田的诗呈现着一种原生态的质朴、平实、真诚、厚重。他早年的《地之子》和晚年的《一棵树》一脉相承,厚实、朴素的风格、浓郁的泥土气息都是他人格的反映,他的确是齐鲁大地的“地之子”。《汉园集》之后,李广田完全转向了散文写作,而且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园地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果说,他的诗歌有散文化倾向的话,他的散文则因充满了浓郁的诗情而受到几代人的喜爱。冯至先生说:“广田的散文是独树一帜的”,的确,他以鲜明的艺术个性和风格为20世纪中国现代散文留下了一笔丰富的遗产。
散文:美和真实的抒写
李广田是20世纪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作家。他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跻身文坛,最早以诗歌名世,后来写过小说、文学理论,但成就最高的当属散文。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使人在平庸的事物里找到美和真实。”
李广田散文的核心,一个字也可概括,真,而最能表达这一点的,莫过于《少年果戈理》,它像一只反光镜,李广田的内心世界,毫发不遗地在这里反射了出来。文章像水晶一样透明,但是遭到了疙瘩的时代,仍然是秀才遇到兵,李广田一生命途多舛,这也是一段解不开的悲伤。在昆明时期的散文集《日边随笔》序中,说到他早年曾喜欢并向往过“日边清梦断”、“日色冷青松”这样的意境、境界,以为“要论生活,就应当过这样的生活,论文章也应该写这样的文章,一时大有一切皆了,浮华都尽的意思。”而此刻却感到“生命无时不在烈火里燃烧,就像生活在太阳近边一样”, 恰是生动地画出了他从早期的诗人向后期的战士转化的轨迹。如他在序中所说:“其所以名之曰《日边随笔》者,不过是偶尔想起:藉此聊以见出自己的变化,以及我们这时代的变化而已。”
李广田三十年代就“把散文当作一种独立的艺术创作”,而且“特别注重于提高散文的艺术性”。他的散文钟情于乡土风光、田园情趣的描绘,是一种使人在纯朴中见出华美与真实的诗人的散文。他在谈到写作散文时曾说:“好的散文,它的本质是散的,但也须具有诗的圆满,完整如珍珠,也具有小说的严密,紧凑如建筑。”这就是散文和诗与小说在体制上的不同之点,也就足以见出散文之为“散”的特色来了。
文学批评:思想的结晶
众所周知,李广田的散文成就是巨大的,但他在文学批评方面的成就并没有被他的散文成就掩盖。他是中国四十年代最杰出的批评家之一,司马长风在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就把三李(李广田、李健吾、李长之)的文学批评并提。
过继于别人为子的孤独,又受母亲、祖母的深切关护与影响,养成了李广田绵细善感又善良坚挚的个性;再加上北大外文系学习的外国文化中现代意识的影响,使他既能深深地扎根在这片生他养他的故土,又能接受外来的先进观念。在讨论文学问题时,由于受到西方理论思维的影响以及执著坚韧的性格,则能征引广博、推论严密而富于感性。早于在西南联大讲授文学概论之时,李广田就已开始钻研文艺理论。流亡罗江期间,他阅读了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俄国作家的文艺理论书籍,他接受别林斯基对于文艺创造的看法,认为艺术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一切艺术都生根于实际生活,在这一点上,一切艺术都是写实的;然而又必须经过作者的生命之熔铸而成为一种全新的东西,在这一点上说,一切艺术也都是理想的。
在实践文学创作中,李广田也特别强调“思想”之重要,并一再强调“思想”是创作的根源。作品的血脉,是作家的主体性及其独特生活经验发挥作用所产生的。“思想”应该具体表现于作品中,任何未成熟的思想都不能获得形象、结果,都不能产生具有宣传思想效果的艺术作品。
李广田认为文学批评文章也应写得和文学作品一样具有艺术性,让人爱看,耐人寻味。在《人格和风格》中,他强调“真”是作品风格的主要因素,文章的好坏取决于作者是否具有“真见”、“真感”、“真思想”,具备这些条件,文章才能灌注作者的人格,而人格和风格是一致的。李广田指出没有真实性也即不会有新鲜感,所以文章不能动人。没有风格,反映在文字上是“言语无味”。不人云亦云,忠实地写出自我,写出想要表现的世界,自然能成为一种风格。这关键是要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一九四八年,清华学生自治会编印的《清华文丛》里有这样一段:“至于李广田先生,更是大家所熟悉的。他的‘文学概论’、‘戏剧选’、‘各体文习作’等班上,常是挤满了旁听的同学。他爱青年,自己也有一颗青年的心,常常极诚恳而又有力地拉着山东调子说,‘这时代只有青年才有办法’。创作方面,也指出了一条大家都该走的‘路’,在新的观点上,它又给予大家一个文学的新观念,所以他一直是被大家所爱戴的。”时间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真正有生命的东西是不朽的!
总之,李广田的文学风格,平而不平,淡而不淡,平实中藏有作家自我眼光的深邃与独到,新鲜与机智,令人目不暇接。然而平实却非呆板,处处显示出机敏与创新;淡然并非无味,篇篇见出思想的深邃;质朴而不木讷,时时闪现智慧的火花。他以平直流畅的文笔,平等恳挚的心态,与他的创作对象进行自由的灵魂交流。李广田作为现代文坛杰出的作家和理论家,其人与其文,虽不至令人有高山仰止之感,但其独特的委婉平和风格与质朴清新的审美品质却如一泓清泉,滋润着读者的心田。这位走出梦幻的地之子对人生真理不倦的思索,对艺术美神执著追求的精神穿越漫漫时空,到今天依然散发着光彩。
作者单位:上海农场学校 224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