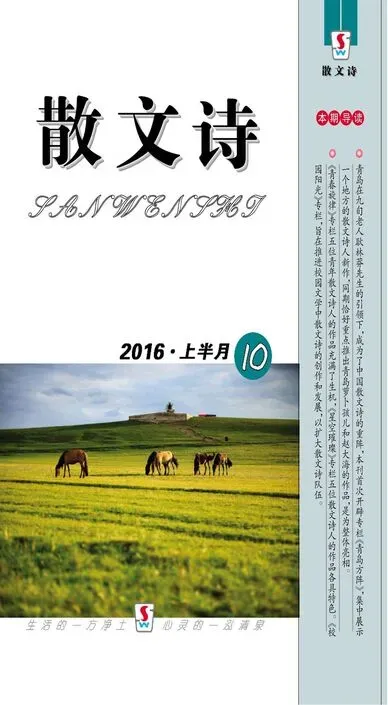在医院
广东◎容 浩
在医院
广东◎容 浩
有一支队伍沿着大腿下去,要赶到灼热的地方。那里有生命的漩涡,疼痛钉入墙壁,药物沉入河流。
所谓万物之命运何其相似:
透过窗子,你看树上的叶子,你看那熙攘的人群。
人生轻微,多有不甘。冬风反复,却又终究回到树枝上。
而时间不断隆起,出生排着队,死亡排着队,欢愉排着队,欲望排着队,疼痛排着队。
所有在寒风中赶路的人们,裹紧您的大衣吧!生命滴入时间,大地抚平哀伤。
世界当然如此,有人冷若冰霜,有人心有玫瑰。
它们都有后来,但不像电影那样发展——那些夸大的、经过修改的结局,反映了人类美好的愿景但并不符合现实——
现实是:护士林姑娘比她们都善良,林姑娘比她们都悲伤。
只有靠近深夜,打电话给小斑马的时候,他才发出动情而艰难的声音。
真实的蓝斑马对着电话里的孩子说:爸爸在出差,爸爸很想你。
破旧的流泪的蓝斑马,被生活的流弹击中,伤口冒出青烟。
蓝斑马跟我说,受伤的事情没有跟儿子说,去年离婚了,感觉挺对不起他。
这炽热的国,曾经将多少东西埋葬。
阳光啊,你照耀它们吧:那欢愉,那热爱,那哭声。
林护士说他儿子甚多,但穿梭于人群,去向不明。
他向我讲述过他与时代纠缠的、离奇而又曲折的人生,黑色暗涌。在他看来旧日都是金属的,金的,银的,铜的。
像蝉的歌唱。
只有深夜里他沉重地睡去,我才会看到他曾有过的灰暗的昨天。
茄子形的张三和李四,比板凳荒凉。我们一起坐在碗里抛骰子。
轮到他们抛的时候当然是由我代劳。但是我总是输,输得不耐烦了我就推倒不玩了。
于是张三和李四,就不存在了。
后来我收到很多60度以上的安慰,我说没什么,我会假设上帝也是一个爱抛骰子的人。
大叔在我身旁,他像一个旧铁罐,狭窄的身体里塞着贫穷、善良和破棉絮。他术后的脚掌被带血的纱布缠绕。铁罐渗出锈迹。
刚才大婶给了我半只苹果。大叔跟我们说:“我要回去了,再见了各位。”然后他一瘸一拐,一高一低,一明一暗地走了。
再也不见。
跳和紧,挨得很近,都是美好的,是十二月里燃烧的玫瑰。
在这里,疼痛是必须的。呻吟是必须的。
我们有坚固的泪水。
很快这一年就要结束,祝愿与钟声一起敲击心脏。
接着我们吃热腾腾的面条,用温暖的语言互勉——我是说这个世界并非冷若冰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