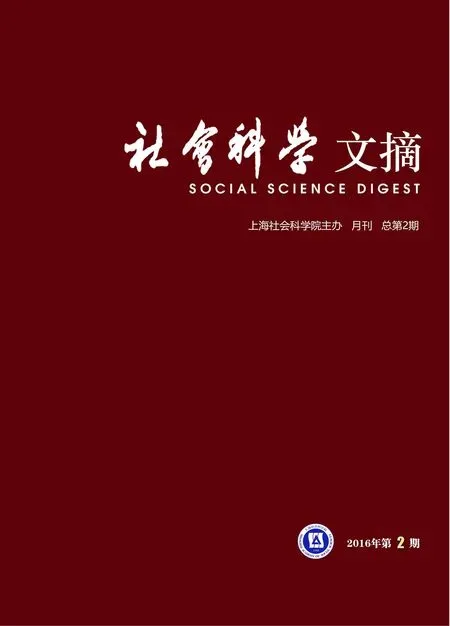网络集体行动的舆论生成及其演化机制
文/杨江华
网络集体行动的舆论生成及其演化机制
文/杨江华
本文的目的在于,以药家鑫案为例,分析在互联网新媒体蓬勃发展的当下中国,媒体舆论如何促使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转化为一场引人注目的网络集体行动事件,并推动网络集体行动的升级演化,进而改变案件的司法进程与最终结局。
理论框架与分析方法
近年来,互联网介入的集体行动正成为一种新趋势。有学者研究指出社交媒体之于集体行动动员的积极功能、助推作用及其推动民主进程的潜在意义;但也有学者认为在数字鸿沟的限制下,不能夸大社交媒体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相对而言,国内相关研究刚起步。
在理论框架上,已有研究主要是依据勒庞的大众心理学理论与斯米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来指导实证分析,而对框架理论重视不够。我们认为后者对分析网络集体行动现象来说更具针对性与适切性。框架理论是一种分析行动者如何通过媒体创造话语符号、传递信息和形成认知解读,进而影响人们关于一场运动的理解与判断的集体行动理论。它从建构主义范式出发,重点关注媒体报道框架与人们主观心理认知之间的互动关联。
框架建构主要通过媒体的舆论话语来体现,在互联网日益普及的当代社会,媒体在集体行动中的框架建构功能大大提升,尤其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媒介舆论与集体行动的关联互动效应更加凸显。因此,从本文研究对象的经验特征来看,我们借鉴框架理论的核心分析概念,将药家鑫案视为一个不同力量参与互动的集体行动事件,从媒介传播形式与参与主体两个维度,建立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以解释媒体舆论框架建构过程如何影响事件的司法进程。
在理论分析框架中,我们将药家鑫案中的行动主体分为四类:政府机构、当事人及代理律师、意见领袖与一般网民;将媒体类型分为三类:传统媒体(报纸、电视)、网络媒体(门户网站)与社交媒体(论坛、博客与微博)。我们重点关注各行动主体如何使用不同类型的传媒形式,表达各自意见主张,制造舆论话语,从而建构大众心理认知框架,使舆论导向朝着有利于自己行动目的发展。我们将框架建构过程中的舆论生成结果分为两类场域,即官方舆论场(代表政府的态度立场)与民间舆论场(代表当事人、网络意见领袖与一般网民等的态度立场)。两类舆论场之间及各自内部存在框架竞争的关系,反映了不同参与主体的舆论塑造能力,它是影响药家鑫案司法进程走向的关键变量。
框架理论强调集体行动中大众心理认知的动态过程,所以与本文理论分析框架相关联的研究方法可以借鉴孙立平等人在研究国家—农民关系中提出的“过程—事件分析”。该方法主要强调对研究对象要从静态的结构分析转向动态的过程分析,认为从事件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新的独立解释机制。
结论与讨论
药家鑫案舆论关注度之高、案件社会争议之大,为近年所少有。本文目的就是在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下来解释这起案件的发生演化过程。为此,我们将案例分析中的关键变量总结出来,并尝试揭示变量间的逻辑关系机制。
(一)网络集体行动的框架建构:结构、话语与策略
其实,药案并不复杂,之所以引起舆论高度关注,并很快演化成网络集体行动事件的一个关键诱因,主要是在药案之前刚刚发生“李刚门”事件。两者案情有某些相似,后者的报道框架(“官民”“贫富”对立)便为药案自然套用,而且发挥了相当显著的建构效果。斯诺等人认为,框架建构的有效性(或框架共鸣度)与基础结构性限制、现象学限制这两大因素关系密切。基础结构性限制,反映的是框架与动员对象的价值信念间的契合程度,契合度越高,越容易思想动员;现象学限制体现的是框架在传递过程中的形式与逻辑,形式越通俗易懂,逻辑越前后一致,就越能引起对象共鸣。在药案前后四个不同阶段,为什么媒体舆论一浪高过一浪、呈螺旋上升的态势,主要是因为框架建构的结构性变量中涉及了转型时期中国最核心且最敏感的几大议题,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司法公正与媒体公正等。
当基础结构性限制条件相似的情况下,现象学限制因素的作用就非常重要。一个时期内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对稳定,但并非所有以此为焦点的框架建构都是有效的,关键在于通过什么方式并遵照怎样的逻辑来建构,而这往往体现为话语符号的创造与利用。网络传媒时代,要想在海量与即时更新的讯息中博得关注,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要善于运用话语符号。因此,富有特色的网络流行语、吸引眼球的标题与富有感染力的图文符号等,都是框架建构惯用的有效策略。药案自始至终,各种挑动舆论神经的网络段子和流行语层出不穷,这些充满情感色彩的话语符号包裹在真假难辨的谣言中,在网上不断裂变扩散,形成一种强大的干预力量,牵制了案件的正常司法进程。
框架建构是一个宏观(结构性因索)与微观(话语符号)相互回应的动态过程,在药案中,这一动态过程通过四种策略机制得以实现。框架链接促使案件在刚开始不久便在性质上发生了重大转化,一审开庭后的框架渲染则将事件推向舆论焦点,在一审宣判至二审前后,社交媒体借助框架扩展将事件彻底置于舆论漩涡;随着网络谣言澄清与网下行动介入,框架建构的转换机制让事件并未因药家鑫的死刑而终止,而是沿着不同的方向继续发展。这四种策略机制是微观话语符号的传递形式、内容逻辑与宏观结构性因素之间契合性的保证,它是药案生命周期如此之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网络集体行动的公共舆论生成:双重动员机制
相对于其他集体行动理论,框架建构理论尤为强调集体行动的互动性与动态性过程,因此会重点关注框架建构过程中参与主体的互动方式及其对公共舆论生成的影响。
政府部门在药案中的出场基本上是按照司法程序的节点。应该说案发之后,当地政府的重视程度与案件审理公开度做得不错,但由于在媒体舆论引导中主要基本没有涉足微博等新媒体,这大大弱化了政府部门在公众舆论生成中的引导作用。面对媒体上的不同声音,当地政府没有及时主动澄清,丧失了话语主导权,被网络舆论层层裹挟,政府司法的公信力由此陷入了恶性循环,并最终出现网络舆论绑架司法审判的尴尬。
相对而言,在药案中网络意见领袖对公共舆论的生成影响最为显著,且多半是通过微/博客等新兴媒体发挥舆论影响力。基于案例分析,我们发现,意见领袖在整场集体行动中主要采取了双重的动员机制:一个是情感与理性的思想动员,另一个是网上与网下的行动动员。由于受“李刚门”事件影响,药案开始的媒体报道框架中就带有较浓的情绪性因素,虽然当时网络意见领袖中不乏一些专业人士的理性声音,但在陷入情绪化漩涡的网络空间中,理性声音几乎没有起到以正视听的效果。而在药家鑫被执行死刑、民意情绪得到释放之后,随着药父一系列的澄清努力和权威媒体的深度报道,关于药案的各种理性反思声音被带回到舆论中心,网民开始同情药家而对以张显为代表的意见领袖报以批评,舆论风向于是倒戈,案件随之出现了逆转。
同时,推动这起网络集体行动发生演化的一个重要机制来自网上与网下的交织行动动员。药案中的一个最大争议是民事赔偿问题,而导致民事赔偿进展频频受挫并最终陷入死局的原因,除了张显等人的网络舆论干扰,更重要的是一些围观网友将行动从网上延伸到了网下。药案后续的舆论关注焦点于是被重新设定,事件进程也由此发生了改变。
(三)网络集体行动中的舆论场竞争:二元逻辑与蝴蝶效应
目前国内的公共舆论生态结构是以党报、国家通讯社、国家电视台等组成的官方舆论场和以互联网为基础、新兴社交媒体为核心的民间舆论场并存的两大舆论场。特别是微博等社交媒体在国内的兴起,两大舆论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对集体行动事件的影响日趋重要。药案恰好出现在中国社交媒体方兴未艾的起步阶段,当时民间比官方反应得更加积极迅速,微博首先在民众中得以流行,而后官方才推出政务微博等新媒体宣传形式。这个基本格局在药案中体现为,两大舆论场在叠合共鸣与争议对立的二元逻辑下,分别经过了“合—分—合”的过程,并左右了事件的发展进程走向。
首先在案发阶段,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方向基本一致,所以两大舆论场的叠合共鸣是案件迅速引发围观并演变成网络集体行动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在案件性质发生变化后,两大舆论场开始分道扬镳。一方面,在议题设置、报道框架与舆论指向上,官方媒体试图体现还原解读的客观立场,因此多关注报道药的个人成长及其家庭背景,而网络社交媒体则沿着案发后的议题设置,一直聚焦在有关药及其家人的各种“问题”线索上,随着各种爆料和网络舆论的情绪化,各种谣言信息已经散开,官方舆论已经难以引导民间舆论。另一方面,在反应敏感度与舆论传递性上,当时的官方媒体也不及社交媒体,后者可以凭借新媒体传播的“蝴蝶效应”,迅速占据舆论场的话语权。所以,两大舆论场的失衡造成了舆论群体极化与舆论绑架。最后,在药案后期,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又开始走向合一,陆续将议题焦点和报道框架集中在案件反思、真相谣言辩驳等问题上,官方媒体与社交媒体之间的重合回应不断增多,舆论场恢复平衡,案件后续走向得以逆转。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摘自《青年研究》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