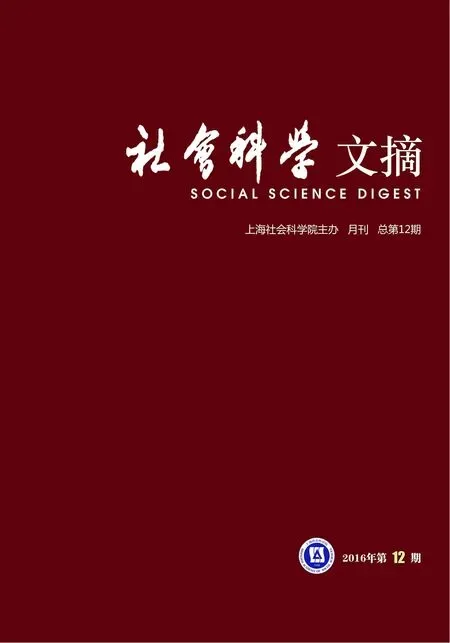论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及三种化解路径
文/徐孝虎 王国平
论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及三种化解路径
文/徐孝虎 王国平
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以新政治史、新经济史和新社会史为代表的社会科学新史学。然而,新史学派囿于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偏于探究微观课题,从而使历史学身陷“碎片化”的泥沼,这也使整个历史学界面临巨大挑战,迫使历史学家不断探求综合化解之路径。自20世纪80年代,美国史学界便开始探究能够反映整体历史发展的综合研究理论与方法。
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倾向及其学术回应
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1yn)在美国历史协会第96届年会上发表了题为“现代史学的挑战”的主席演说。他在深刻分析现代史学的三个发展趋势后指出,未来的历史学家将要面对的最大挑战不是如何深化和拓展探究人类过去生活的技术手段(无论如何,这种努力将会而且应该保持),而是如何将前所未有的具有复杂情节和分析因素的历史再度综合起来,以及如何将可资利用的资料(定量和定性的、统计和文字的、视觉和口述的)融汇成记叙重大事件的可读性强的著作。贝林所谓三个趋势是:第一,融合潜在的事件与明显的事件;第二,描述由核心及其外围组成的大规模领域和系统;第三,叙述人类的内心状态及其与外部环境、事件的关系。贝林正是站在历史学发展全局的高度,结合大量实际研究成果,才对现代史学的发展趋势作出了深入分析;对如何在这种形势下综合各类分析成果,实现历史研究的总目标提出了深刻意见。
为了应对历史研究中出现的“碎片化”问题,历史学家不断探求综合之路。对于美国新史学家来说,最富有吸引力的课题莫过于对历史的综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史学家开始探究反映整体历史的综合理论,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戴格勒提出的“做一个美国人,即做一个合众国公民意味着什么”的模式;另一种是勒奇坦伯格等提出的以“政府的作用”综合美国历史的方法;再一种是本德提出的关于“公众文化的形成”的理论。这些史学家提出的综合历史学的理论,从某种角度可以视为对历史研究碎片化问题的学术回应。
关注民族特性与公民身份认同
卡尔·N.戴格勒(Car1 N. Deg1er)建议历史学界围绕“做一个合格公民,即做一个合众国公民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来研究历史。他不是指应当成为什么样的公民,也不是说谁才是真正合格的公民,而是欲从历史角度给公民做一界定,这里包含一个国家公民在某些重要方面有别于其他国家公民的因素。戴格勒认为,“做一个合格公民,即做一个合众国公民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是建立在历史学的两个目的或者说两个用途之上的。首先,“美国人是谁”这个问题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都十分重要,特别是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民族众多、信仰广泛、富于变化的国家而言;其次,无论是民族的同一性,还是个人的同一性,都主要来自对历史的认同。他指出,通过探求历史同一性,我们会获得一种构架,它能囊括并整合过去20多年通过大量研究获得的新知识。这种探求将为我们赢得一部仅仅发生在我们身上,而在别人身上从未发生过的富有特色的历史。
由此可见,戴格勒是用“做一个合格公民,即做一个合众国公民意味着什么”的模式构建历史学研究框架的。他是为美国人的特殊性寻找依据,也是为美利坚民族的同一性找寻根源。那么,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历史学家应该如何描述美国人的民族特性及如何揭示其身份认同呢?他认为历史学家可以对国别史进行比较研究,这可以帮助历史学家避免陷入狭隘的美国例外论的窠臼,迫使历史学家发现和思考美国发生的事情是否真的与别的国家和地区有所不同,如果确有不同,那么这种不同的原因是什么,说明了什么问题。这种方法并不会削弱以往的研究,恰恰相反,它会将历史学家引向从未注意过的国别差异,并要求历史学家对这些不同做出解释。他提出的历史研究理论有一定的包容性和可操作性,这既有利于说明民族的多样性,又可以解释民族的同一性。历史学家适当运用这种方法审视历史,无疑可以帮助不同的民族的认识自己的身份特征。这对人们克服因民族多样性、复杂性而具有的潜在离心作用将会有所帮助,可以说戴格勒的解释模式是一种有益探索。诚如戴格勒所言:“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赞美自己,而是认识自己。通过探究我们是谁,我们还将开始创建一种解释框架,这种框架或许能提供一种当代历史学家似乎不怎么喜欢的融会贯通的模式或者说是综合。”
其实,戴格勒在1986年提出“做一个合格公民,即做一个合众国的公民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可以说是与其长期思考如何“重写历史”这个问题一脉相承。作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主席,他在1980年发表了题为“重写美国史”的演说辞。这篇演说辞旨在探讨历史学家为何一直都在重写历史以及那一时期历史学发生的变化。可以说,如何重写历史这一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从某种意义上说,戴格勒对于“做一个合格公民,即做一个合众国公民意味着什么”的探索可以视作他“重写历史”的延伸。
可见,戴格勒十分重视民族史的特殊性,他仍对“美国例外论”情有独钟,试图从这一角度探索一种民族国家的过去,为人们深刻理解历史寻求理论支持。他也指出,历史学家只有在全面认识民族历史、外国历史及世界历史的同时将民族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框架内进行比较和考察,才能深刻认识民族历史的特殊性;历史学家只有不断再现历史的复杂面和多样性并弄清其意义,只有努力探索民族历史的同一性和认同感并搞清其价值,才能提出更加有益的综合观点,才能写出更加有益的深刻著作。戴格勒正是通过回答“公民是谁”这个问题来寻求重写历史的理论和方法,以启迪不同民族的历史认同与现实关怀。
关注政府在社会发展与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1986年,威廉·E.勒奇坦伯格(Wi11iam E.Leuchtenburg)在其名为“政治史的适当性:论政府在美国的重要作用”的演说辞中提出史学家的下一个领域应是政治史。他提出这项建议的背景是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在战后史学界已变得不受重视。他认为,对政治史的抛弃与人们对当时政治的厌恶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受到年鉴学派的巨大影响。在年鉴学派看来,政治史不过是政治和外交事件的罗列和展示。受其影响,20世纪的70至80年代,专注于私人领域和隐秘心态的新社会史一度在史学界占据突出地位。但是,尽管贬低和轻视政治史的史学趋势锐不可当,不同的意见已经开始出现,这方面的意见不仅有来自坚持以政治军事史为中心的传统历史学家,甚至还包括那些以鼓吹新社会史著称的历史学家。贝林就曾经在其主席演说辞中深刻指出,新社会史必须从专门探究人们的隐秘领域和内心状态当中解脱出来,因为“将这些私人领域从公众生活中隔离出来,即是把个人的内心世界与外部社会环境分开,也就是忽视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就规避了历史研究的中心任务——描写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及解释此过程的原因”。
勒奇坦伯格提倡的“政治史”,既不是政治活动的简单叙述,也不仅仅是对选举活动的细致描述,而是指分析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表现在政治和公共政策方面,也表现在经济、法律、外交及战争等各方面。他指出,即使历史学家能够妥善处理诸如政府的运转方式、发展原因及杰出人物的地位等问题,但是仍会存在诸如夸大政治史的作用、可能混淆自己与政治科学家的身份及政治史学家和社会史学家严重对立以致分裂的可能。勒奇坦伯格呼吁这两类历史学家互相学习,这样,新社会史就能从研究政府的作用中获益,政治史也会由于吸取了社会史的研究成果而变得丰富。他富有见地地指出:“两者的工作可以使我们更加接近综合,而我们当中最富创见的一些历史学家近来一直在强调综合,我们确实迫切需要这种综合。”
这种建立在分析性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呼吁史学家强调公共领域的核心作用。诚如勒奇坦伯格所言,任何人想要依据公共领域进行综合研究都不能不考虑政府的作用;凡是忽视政府研究的综合都将被证明是不可行的。
如果说勒奇坦伯格关注的是政府在社会公共领域的核心作用,那么理查德·W.利奥波德(Richard W. Lepo1d)关注的则主要是政府对历史学家及历史团体的作用和影响。可以说他们两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政府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1977年4月7日,利奥波德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举行的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年会上发表了题为“历史学家和联邦政府”的演说。他主要考察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独立地位、历史出版委员会的工作重心转移以及政府官员文件的所有权等问题。由于各种历史研究团体不断涌现,以致历史学界四分五裂、相互羁绊,这便严重阻碍了历史学科的发展。他意在探讨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与美国历史协会应该如何对这些问题作出反应。“如果这两个历史学组织想要认真对待政府制定的、影响历史教学、研究和就业的项目并作出适当反应,以便促进自己的利益,那么人员和财力的增加就是必要的。”而这一切显然需要政府的有力支持。他认为对历史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比政府的政策更能影响历史研究的了。这些政策不仅能影响历史研究,同样可以影响历史教学及历史教师的就业等。尽管利奥波德与勒奇坦伯格对政府的关注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强调政府的作用,这些作用不仅对社会公众的生活有强大作用,而且会对历史学家的研究产生直接影响。
如果说利奥波德的演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府在综合历史研究方面发挥的潜在作用,如政府通过设立研究机构、开放政府档案或投入出版基金等影响历史学家的工作,那么阿伦·G.博格(A11an G. Bogue)则对历史学家在从事政治史写作的时候应予注意的问题作了精辟分析。博格1983年4月7日在辛辛那提举行的历史学家组织年会发表了题为“历史学家与激进共和党人:对今天的意义”的主席演说辞。博格对一些历史学家提出的叙事政治史的缺陷做出回应,“如果我们的一些作品能够吸收过去30年来的分析性社会史和政治史的丰硕成果,写出丰富多彩的新叙事史,我们当然该喝彩。另一方面,假如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近来呼吁更加重视叙事史是说整个史学界都应该献身于叙事史,我们就该反对”。由此可见,无论是采用叙述还是分析的方式研究历史,都是围绕历史研究的总目标进行的。只要有助于阐释历史是如何形成的,两种方式都可以为历史学家所用。
关注公众文化及其形成方式
美国历史学家本德对如何综合历史进行了有益探索。本德在《整体与部分:美国史需要综合》一文当中深入探讨了历史学的现状以及如何研究历史的问题。他指出:“我关于综合的独特看法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它建立在当代职业化和公共领域内的史学以及那些为了强化其意义所采取的合理举措的基础上。”本德认为,“公众文化”是一个政治概念,它能通过一种并非政治学和政治史的狭窄定义的方式为缺少政治活力的资料和社会史分析提供一种整合叙述的焦点;而为社会史家和思想史家拒斥的旧政治史——各种政党、选举及行政部门的历史,或许正如雅克·勒高夫所言,那是缺乏深度的。他为读者认真分析了“公众文化”的涵义以及构建“公众文化”的路径。他的“公众文化”概念拓展了“政治”史涵义,给人们理解社会权力带来了启迪。他认为“公众文化”是包括意义和美学的各种力量同台竞技并赢得权威的论坛。因为具有争议性,所以“公众”天生就是一个政治性团体,这使得它与那些仅仅是人群的聚合或文化的拼凑迥异。本德在文章结尾概括了自己的论点:毋庸置疑,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对话展示的关于社会的解释是一项富有建设性和想象力的工作。但是,这项工作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历史学的丰硕成果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历史编纂学基础上的。这项工作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将新史学中的传统力量与新史学对公众(譬如不同主题和读者)及改变我们时代的新的激动人心的史学形式结合起来的机会。
1987年,时隔一年后,本德针对理查德·福克斯和罗伊·罗森茨维格对其依据“公众文化”研究历史的倡议提出的质疑发表了一篇名为《整体与部分:继续讨论》的文章。他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观点:解释“公众文化”的形成过程需要进行综合性叙述,这种叙述能通过充分反映个人生活与“公众文化”之间关系的性质及激发相关历史研究的方式将二者结合起来。由此可以看出,研究历史与综合历史的道路并不平坦,还需要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不断摸索。
结语
综上所述,在面对历史学研究“碎片化”、“社会科学化”研究倾向时,美国历史学家提出了几种研究方法,以便能从总体上认识民族、公民从何而来、民族特点以及民族国家的未来等问题。毫无疑问,他们所提出的历史研究与历史综合模式、理论和方法是颇为有益的,在引起历史学家关注历史“综合”问题的同时,也带给历史学界诸多有益思考。
正如本文开篇所说,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扩展深化了历史研究的内容,出现了崭新的研究领域,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方法,这可以视作现代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其实,历史研究出现的“碎片化”现象并不是西方史学所独有,我国史学界也对历史学研究中出现的这种趋势进行过热烈的讨论。由此看来,“碎片化”问题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关乎历史学的今天和未来,历史学家对此的看法不尽一致。笔者以为,“碎片化”问题是历史学发展中的必然现象,与之相对应,“综合化”也是历史学演变中的一贯要求。两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二中取一,两者都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学的“碎片化”就不是什么问题了。问题的关键不是如何消除“碎片化”,而应该是如何协调“碎片化”和“综合化”。没有“碎片化”,历史学就没有“综合化”的基础和机会;没有历史学的“综合化”,“碎片化”就会失去依托和深入的可能。
因此,历史学只有在保持“碎片化”的同时保证自身综合研究人的特色,历史学家只有在吸收分析成果的基础上保持自己综合叙述变化的风格,才能真正发挥历史启迪世人、影响公众的作用。
(徐孝虎系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与民族学院副教授,王国平系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教授;摘自《东南学术》2016年第2期;原题为《论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及其学术回应的三种化解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