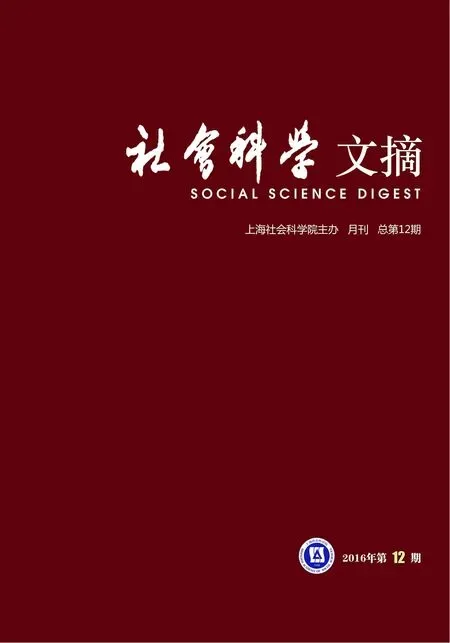国际冷战、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
——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形成的再考察(1956~1965)
文/蒋华杰
国际冷战、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
——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形成的再考察(1956~1965)
文/蒋华杰
作为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之外接受中国援助最多的地区,非洲仅在1956年到1979年间就接纳了总额约62.8亿到72.5亿人民币的援助。中国如此大规模援非,乃至达到“穷国支援富国”的地步,其援助动机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文章重新梳理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重点分析革命外交之下的“国际统战”和国际冷战生成的“道路选择”这两点因素的作用,并以此解释中国对非援助为何忽视经济利益考量。
国际统战与援非发轫
新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接触始于万隆会议。在此前后,毛泽东开始将中国革命外交置于全球视野内加以思考与实践,以期“重建中间地带、扩大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参加万隆会议并与非洲国家接触是其中的关键一步。同时,非洲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自195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发展,这吸引了中国的注意。
在非洲新出现的诸多民族主义政治势力中,中方认为“纳赛尔派”是最容易接受反帝统一战线的民族主义政治力量,由此一开始便将其视为在北部非洲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最佳依靠力量,而苏伊士运河危机事件更是坚定了中方支持纳赛尔的决心。1956年11月,中方无偿援助埃及440万美元,同时斡旋改善埃共与纳赛尔政府的关系,促其形成民族统一战线,中方还向埃共传授斗争经验,并帮助其获得武器。
从1955年到1958年,中国同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建交并与几内亚相互承认,同时建立了依靠纳赛尔政权的对非工作通道。中国当时向阿尔及利亚等北非国家提供的援助主要通过埃及输入。这一时期,中国对西亚非洲的工作方针是“积极开展、稳步前进、细水长流,政治大力支持、经济援助量力而行”。此时的对非援助总体上还处于相对有限的初级阶段,援助总金额只有数千万人民币,毛泽东在军事援助问题上态度谨慎。
不久,纳赛尔派与北非四国共产党矛盾激化,后者相继遭到排斥和打击。这使得既有的单一依靠“纳赛尔通道”的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受到严重冲击,而此时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已高涨。1959年2月,毛泽东认为非洲已经“燃烧起来”,他在支援非洲民族解放问题上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暂时放弃北非共产党,主张非洲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建立社会主义,以此稳固与非洲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的反帝国际统一战线。
中方决定将非洲地区反帝国际统一战线的重点从纳赛尔派转向其他派别。1959年初,外交部正式提出要支持非洲地区一切反帝的“主义”,提议尽快与加纳建交以便在西非建立外交据点,同时加大对其他非洲国家的民间外交活动并调解纳赛尔和恩克鲁玛之间的矛盾。2月,中共中央要求加强对非洲反帝的民族主义力量的援助,帮助其逐渐减少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依赖。
1959年,中方开始采取措施在东非、西非和中非三个方向同时推动建立非洲地区的反帝国际统一战线。几内亚和加纳是中国在西非的重点工作对象。1959年初,中方无偿援助几内亚1.5万吨大米以及一批基础设施、工厂。5月,中国向喀麦隆人民联盟提供留学生奖学金名额、资金与武器。此外,外交部还建议向苏丹提供援助。
冷战竞争下的援非升级
1960年,非洲已经成为美苏各方为改变全球冷战态势而争夺的重点。1959年到1961年间,苏联前所未有地向埃塞俄比亚、几内亚等国提供2.7亿新卢布的贷款。肯尼迪政府于1961年提出“新非洲”政策,开始大幅增加对非援助。日本也于1960年开始将西亚非洲作为仅次于东南亚的扩张对象。为保全联合国席位,台湾与非洲国家建交最为积极。1960年1月到7月间,台湾成功地与新独立的六个非洲国家中的喀麦隆、多哥、马里联邦和马加尔什建立“外交关系”。台湾以经济援助推动政治建交,除优惠贸易手段,最主要的途径是向非洲国家提供农技援助。
面对各方加紧争夺,中国于1960年全面开展对非工作。7月,外交部制定了“积极主动,又要稳步前进”的方针,并确定了九点具体的对非工作任务。此时,量力而行的对非援助原则被适当照顾的政策取代,中国对非援助力度加大。
中国开始全面向非洲国家宣传、传授自身的革命和建设经验。中联部认为大部分非洲政党缺少革命经验,有必要向中国学习,遂开始定期举办培训班。1960年夏秋两季,96名非洲左派和中左派的政党干部来华学习。物资援助方面,中国在1960年继续重点支持喀麦隆、阿尔及利亚和几内亚。被认为是左派政党的喀麦隆人民联盟进一步得到了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支持。正在同法国作战的阿尔及利亚是中国的重点援助对象。1960年4月,中国给予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价值5060万人民币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而1959年只有60万。5月,中国主动赠送几内亚1万吨大米,并允诺在农业合作化、工业等领域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此外,中国也开始加强对刚果和加纳的援助。中国给予卢蒙巴、基赞秘密资金援助。1961年8月,周恩来决定与加纳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协定,援助建设兵工厂、训练军官,并派遣农技专家去加纳进行种植活动。
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与“中国道路”
美国在1962年到1965年间延续“新非洲”政策的基本框架,力图通过援助促使非洲国家选择自由政体,仅在1964年到1965年提供的援助总额就有3.45亿美元。英法两国的对非援助数量也相当可观。美英法等国还通过设立非洲开发银行施行多边援助。1962年,台湾在非洲的“邦交国”增加到14个,已在与大陆的外交争夺战中取得优势。台湾“外长”沈昌焕于1963年七八月间走访16个非洲“邦交国”,借机强化农技合作。从1960年到1963年,台湾与7个非洲国签订技术合作协定并派遣农耕队。
对中国而言,1962年之后非洲地区最大的变局来自苏联。中苏分裂使得苏联成为中国在非洲的最主要的竞争者之一。从1959年到1965年,莫斯科与15个非洲国家签订了8亿美元的援助协议,约占苏联同期对第三世界援助总额的30%。苏联增加对非援助的节奏几乎与中苏分裂同步,1963年,赫鲁晓夫认为应对中国的挑战是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事实上,苏联在几乎所有与中国有接触的非洲国家都采取了行动,重点则在阿尔及利亚、苏丹、几内亚、马里、加纳、刚果(布)、埃塞俄比亚、摩洛哥以及索马里。中苏双方争夺涉及面最广的则是第二届亚非会议的筹备问题。与此同时,中苏双方争夺非洲共产党的竞赛也进入了高潮,到1962年下半年,苏联取得了优势。
中苏分裂以及由此在非洲展开的争夺,加上美国、台湾强化对非活动,使得1963年前后非洲地区出现了极为复杂的中美苏台四方共存、三足鼎立的复杂局面。对于中国而言,美苏同时成为最主要的竞争者使得自己在非洲面临双重的冷战态势。1964年,外交部认为非洲局势错综复杂的外来因素主要是“美苏合谋”。
正当中美苏三国角力非洲之际,1963年9月,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其背后彰显中国对世界形势看法的重要转变,中共形成了对世界形势的新看法:“两大阵营、三类国家”。最晚到1963年9月,中共中央开始认为世界局势已经变成了“帝修马三分天下”,美国、苏联和中国三足鼎立,分别代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其态势是“美苏冷战共存、和平相处,力图包围坚持真正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等少数支持者”。1963年9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讨论了亚非拉地区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独立后的发展道路问题。会议认为,这些地区实质上只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去,另一条是真正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里“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很明显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亚非拉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毛泽东相信中共早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可以为他们提供借鉴。
总之,中间地带理论和中国道路的提出,使非洲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战略地位急剧上升。1964年之后,毛泽东不再坚持1959年所提出的“非洲革命(目前阶段)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立场,而是转向加速民主革命进程、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的做法,中国在非洲的战略开始激进化。
周恩来访非与引荐“中国道路”
然而,直到1963年4月,中国还没在非洲取得明显优势。4月,中国将对非洲未建交国家的工作方针调整为“积极地、审慎地开展工作,利用各种时机争取以各种名义进入这些国家”。1964年初,中国开始筹划通过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进一步推动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和非殖民化进程。这一时期,中国采取的最为重要的步骤则是周恩来访非。
从1963年12月到1964年2月,周恩来和陈毅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埃及(阿联)、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10国。周恩来访问非洲10国既为建立反帝反修的国际统一战线,更重要的是向非洲国家传授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促使它们学习中国道路。周恩来认为:“非洲正处在十字路口,总的说来,有两个前途:一个是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且把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另一个是受新殖民主义的控制,变成半殖民地,只有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才能够解决这些国家的前途问题。”
周恩来同非洲领导人会谈的重点是该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他向非洲领导人提供了12点建议,就内容而言,12点建议来自中共早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措施,它们包括:建立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革命政权建设;发展工农群众组织;土地国有化改革;社会改革;发展积累型的工业和独立的民族经济;发展民族文化;实行爱国主义和革命思想教育;培养民族的新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并争取和改造旧知识分子;肃清殖民统治遗留的西方生活方式;执行独立自主的反帝的和平对外政策。
加纳、马里、几内亚是周恩来重点访问的国家,也是重点引荐中国道路的对象。在加纳,除了提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原则,周恩来向恩克鲁玛介绍了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五方面经验。在马里,周恩来同凯塔举行了六次会谈,重点介绍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经验。在几内亚,周恩来同杜尔深谈五次,双方谈话的内容集中在几内亚的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道路、阶级斗争、外援、对美帝的认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等问题,周恩来介绍了中国的经验。
全面援非的实施与效果
大体从1963年9月开始,中国对非援助放弃了“量力而行”的基本方针而开始为推介中国道路全面援非。在全面援非实施之后,中国的对外援助重点由亚洲国家变成非洲和中东国家。
在东部非洲,坦桑尼亚是重点国家。截至1964年6月,中国向坦噶尼喀提供2800万美元贷款和300万美元赠款,并向桑给巴尔提供1400万美元贷款和50万美元赠款。中国向坦桑尼亚提供的最大的援助项目是坦赞铁路,实际至少耗费18亿人民币。中国对桑给巴尔的援助更为全面,在中国专家的帮助下,桑给巴尔实施了一系列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改革措施。中国的军事援助在1964年之后也开始在这个国家全面铺开,除了向桑给巴尔提供军事物资外,援助主要集中在帮助坦桑尼亚建立培训非洲“自由战士”的基地和网络。
东非的苏丹、肯尼亚和索马里也获得了大量援助。苏丹获得了中国提供的4760万美元的经济贷款。肯尼亚获得了1520万美元的长期免息贷款和280万美元的赠款。1964年1月,中国主动追加援助索马里一座剧场并无偿提供50万人民币的救灾粮和药品。在这之前,中国已经决定给索马里约635万英镑的无息贷款和3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1965年,中国在东非的援助扩展到乌干达。4月,中国决定给乌干达政府2964万人民币的长期无息贷款,同时还无偿提供约737万人民币的财政援助。
中国在西非的援助重点是加纳、马里和几内亚。周恩来访问加纳时将援助额提高一倍。1964年7月,中国向加纳提供2240万美元贷款。1964年,马里左派领袖凯塔总统的助手库亚特来华要求中国给予现汇、粮食、工业交通援助,中方答应了大部分要求,其中,仅援建马里的工厂产值就达到1900万美元。
尽管周恩来因为安全问题没有访问刚果(布),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削减对这个处于“非洲革命中心”的国家的援助。1964年7月,中国向这个中部非洲国家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和商品信贷。此外,中国还派出军事专家训练刚果(布)军队和刚果(利)反政府武装。
中国提供的大量援助此时已经在国际统战和道路选择两个层面对非洲国家产生初步效果。援助在刚果(布)、坦桑尼亚、几内亚、马里、塞内加尔、达荷美、利比里亚等国受到了欢迎。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认为中国的援助是兄弟般的,几内亚总统杜尔认为只有中国的援助才是真诚的。美国大使发现几内亚对美苏的态度冷淡,但对中国却十分友好。刚果(布)的新政权开始倒向中国,他们将中国视为首要的外来援助提供者,并对美国相对缓慢且不足的援助颇为不满。由于援助的推动,中国大陆在与台湾的竞争中取得了优势。到1965年底,38个非洲独立国家中的17个与大陆建交,14个与台湾建交。与此同时,坦桑尼亚等一些非洲国家开始部分地接受中国道路。
余论
革命外交之下的国际统战以及由于国际冷战造成的道路选择这两点目标,对中国对非援助由“量力而行”发展到“适当照顾”并最终走向“全面援非”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援助扮演了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关键性政策工具的角色。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只是国际统战和道路选择这两个因素在中国对非援助政策上产生的结果而非根源。
就结果而言,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国际冷战和革命外交框架之下的对非援助始终难以做到义与利之间的均衡。对非援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利用大量的经济利益换取政治回报,进而实现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治目标。实现毛泽东时代革命外交之下的国际反帝统战,扩大中国在非洲的政治影响并输出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发展模式,让非洲国家学习中国的道路,以此来与美苏等冷战对手在非洲进行角逐,乃是中国对非援助的核心利益。
今天,冷战和革命外交的结束使中国摆脱了传统的政治功能主导、忽略经济利益的对非援助政策,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实行了新的援助与合作相结合的经济交往模式。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实现义与利的平衡发展依旧会是极大的挑战。要在与非洲国家的交往中兼顾政治友谊与经济利益,一方面要对经济合作与发展中新出现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国际竞争采取去政治化的做法,避免重蹈传统援助的覆辙,同时也要注意避免在“利”方面过度挤压非洲国家。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摘自《外交评论》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