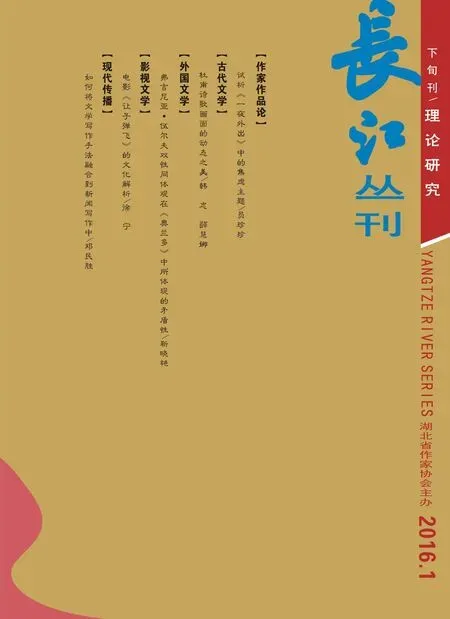荆门方言颤音名物化标志“子”研究
邓 晗
荆门方言颤音名物化标志“子”研究
邓 晗
【摘 要】荆门方言颤音“子”起源于“子”缀,读作r,作为荆门方言词汇的重要语音特,与“子”缀有直接关联。颤音“子”使用方法可以从词性上划分,在人名后加“子”,指小,表亲昵。同时,颤音“子”作为名物化的语音标志,主要有成词、转类、变义等功能,其范围要大于普通话“子”的范围,与普通话也有一定的差异。
【关键词】荆门方言 颤音“子” “子”缀 与普通话的比较
一、前言
(1)荆门市马良镇位于湖北中部,地处汉江江畔,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其方言也受古荆楚方言的影响,留下了颤音这一语音现象。本文主要以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的方言为例,来研究荆门方言颤音“子”现象。
(2)前人已对荆门方言颤音的历史演变、语音及特征、特殊句式、词缀等做出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本文主要是对前人研究的补充。
二、颤音“子”的形式结构
荆门方言中的颤音“子”主要是作为词缀,附在词根后。其使用有如下几种情况:
(1)名词后。凡普通话带“子”尾的名词,荆门方言都念颤音,“子”只是颤音的文字记写符号。如:桌子、狗子、本子、鞭子、疙瘩子(面疙瘩)等。荆门方言颤音“子”可以看作是名词的语法标志,“…子”可以指称多种多样的事物。如动物、食品、人身体上的部位及日常生活用品等。
(2)颤音“子”也有少量出现在动词后,如扳子(扳手)、滚子(车轮)等;出现在形容词加“人子”、“好A子”等特定句式中,如气人子、腻人子、好高子、好深子等;也可以出现在量词后,如桌(一桌子菜),一下(xa)子(去(一)下子、等(一)下子)、有两下子(有本领有办法);也有少量出现在代词后的现象,如么子(什么)、什么子(什么事)等。
(3)颤音“子”出现在人名或动物名后。荆门方言中人名最后一个字加“子”,发颤音,如航子、苗子、晗子、杨子、莲子等,表示一种亲昵的情感。一般情况下是长辈对晚辈或同辈之间的称呼,晚辈则不能如此称呼人名。无论是三个字还是两个字的名字,最后一个字大多可以加“子”读作颤音r。或是小名加“子”,这时“子”前的小名可以是两个字。同时,在荆门,家中所养的动物的名字也可加“子”,如“黑子”(狗名)等,此举体现了人与动物之间亲密的关系。
在陕西榆林,人名后可也加“子”,长者对晚辈的亲昵、喜爱之极便会在人名后加“子”来称呼晚辈。如佳子、妞子、玉子、莲子、东子、旭子等,并且为表达对动物的喜爱之情时,也会在动物的名字后加上“子”,如虎子(狗名)、咪子(猫名)等。在山西方言中,人名中加“子”的也情况较多,如在山西定襄方言中,大多是排行加名(名字后一个字)加“子”、双名加“子”、小名加“子”及姓加小名加“子”等。人名后加“子”在南区的临汾、洪洞、浮山,中区的阳曲也尤为突出。南区人名限指“乳名”,中区的阳曲方言,无论乳名、大名均可加“子”。而在南方江淮方言中,也有人名后加子的现象。但大多限于第二个字是“小”,“大”,“二”,“三”表顺序的词。如陈虾子、毛二胡子、四斗子等,大多都是口语化的表达有表示亲昵的意味。此与荆门方言中人名加“子”的相似的形式和作用。都是长辈对晚辈的爱称、昵称,表达对晚辈的亲昵、喜爱之情。同时,也是表达对小动物的喜爱。
此现象与“子”缀的功能作用有关。“子”缀无论在荆门方言还是其他一些地域的方言中,都有表示小称的作用。《说文解字·子部》曰:“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象形。凡子之属皆从子。”“子”的本义即为小孩子。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说:“《释名·释形体》中说:‘瞳子,子,小称也。’小称是它(子)的词尾化的基础。”由此可以推测,“子”由小孩子的本义首先虚化为表示小称的语素,继而进一步虚化为名词、量词后缀,同时附加了表示情感色彩的意义。在人名后加“子”缀,也就是是表现最亲昵、喜爱的色彩的一种小称词。
三、颤音“子”的作用
荆门方言中的颤音“子”,主要有成词、转类、变义三大功能,其中转类主要是动词名物化,区别词义;变义主要是指小,表示情感色彩等附加意义。
(1)成词。颤音“子”附着在不成词的粘着语素后,具有成词功能。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在动物(昆虫)后加“子”成词,如狗子、猪子、猫子、鸡子、蛾子,蚂蚁子等;二、人名后加“子”成词。在荆门方言中,人名中最后一个字本不成词,但加上“子”后成词,如:莲子、航子、虎子等;三、其他情况。如邪子(疯子)、刁子(一种鱼)、疙瘩子等,这一类主要是由某一词后加上颤音“子”后形成另一类词。
(2)转类。一般情况下,颤音“子”的转类功能主要是是将其他词性的词转化为名词。颤音“子”在荆门方言中是可以看作是名词的语法标志。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将动词转化为名词,如:盖→盖子、滚→滚子(车轮)、包→包子、撮→撮子(渔具)、油→油子(小混混)等;二、将形容词转化为名词,如:干→干子、跛→跛子、老→老子等。
同时,颤音“子”还可将名词和动词词组转化为量词、形容词转化为语气词,但较为少见。一、将名词转化为量词,如:桌→一桌子(菜)、盆→一盆子(饭)、屋→一屋子(人),但这主要是“桌、盆、屋”等借用物量词后才出现的词性转化。而将动词词组转化为量词,主要出现在与动量词“下”(xa)和“点、些”的搭配中,如一(几)下子、一点子(数量少)、一些子等。
(3)变义。“变义”是改变原词根的理性意义,在大多数情况下,荆门方言颤音“子”的变义功能通常是在转类的过程中实现的,转类的同时实现了变义功能。如:油→油子(小混混)、干→干子、老→老子、头→头子等。只变义不转类的情况较为少见,如“肝(指人的内脏)→肝子(指动物的内脏)”等。
荆门方言中的颤音“子”,也有指小,表感叹和表示情感色彩等附加意义。
(1)指小。在荆门方言中颤音“子”可以指小。如刀子、起子、豆皮子等。“表小”是指物“子”尾词的最初功能。上古时期“子”就可以表示“小称”了,魏晋之初的“子”尾也多表“小”,后来“子”尾迅速扩展到较大的形体之上,如“犊子、瓮子”等,“子”尾的指小功能也就逐渐丧失了,以致目前很多“子”尾词已经很难看出“表小”之义,如若表小,则需另加“小”,如“小刀子、小鸭子”等。在荆门方言中,颤音“子”表小称最主要的功用则是体现在人名中加“子”。
(2)表感叹。在荆门方言中,“子”作为语气词,出现在“高、大、深、浅”等表示程度的形容词之后,感叹其程度惊人时,与一定的副词或指示代词相配合,表感叹语气。如好高子、蛮高子、这高子,好大子、蛮大子、这大子,好深子、蛮深子、这深子,好长子、蛮长子、这长子等。还有“好多子、好些子”,既可表感叹,说明其多;也可表疑问,问有多少。
试验结果表明,复方阿胶浆药渣可以替代粗饲料饲喂驴;复方阿胶浆药渣通过提高脏器指数、机体代谢酶、血液生化参数和抗氧化能力等改善机体机能。
(3)表示情感色彩。荆门方言中的颤音“子”可表示多种情感意义,有以下几种情况:一、表亲昵、喜爱,主要体现在人的小名和乳名上,大多用在小孩和年轻人身上,或者是长辈对晚辈、年长者对年少者的称谓,否则会显得不敬。二、表轻蔑,带有贬义,如傻子、瘫子、瞎子、聋子、邪子、老头子、老巴子等,但这些带有颤音“子”的词,在其本身来看,大多已带有贬义的情感色彩,因此颤音“子”带贬义的功用不太突出。
四、荆门方言颤音“子”与普通话的比较
荆门方言里的颤音“子”,是荆门方言词汇中名词的一个重要语音标志。
(1)与普通话相比,只要是普通话中带“子”的词,荆门方言中都可以念做颤音r。如普通话中的桌子、椅子、本子、儿子、镜子、剪子等。
(2)荆门方言的颤音“子”,要大大超过普通话中“子”缀的范围,如羊子、猪子、猫子、八哥子、老巴子等,在普通话中均不带“子”缀。在荆门方言中带颤音“子”而普通话中不带“子”的,有以下几种情况:
大多动物名后。如普通话中除了鸭子、猴子等极少数带“子”的词外,其他如猫、狗、猪、羊、牛等,在荆门方言中都可加上颤音“子”。普通话中可以加“子”的须在前加上“小”,如“小狗子”。
对人的称谓。荆门方言可在人名后加上颤音“子”,如航子、苗子等,这一情况在普通话中较为少见。此外,在荆门方言中有人某类人的称呼,也加上了颤音“子”,如“头子、老巴子”等。
指人身体上的部位或有残疾的人。一、身体部位,如腿子、身壳(kuo)子、胯子、拐子(肘关节)”等。二、身体有残疾、障碍:结巴子、夹(ka)舌子、跛子、邪子等。这一些在普通话中都是不带“子”的,其中普通话中的“疯子”和荆门方言的“邪子”意义相同,但在荆门方言中也可说成“疯子”,由此把“邪子”归为普通话不带“子”的一类。
指食物。在荆门方言中,很多食物的名称都是可以加上颤音“子”的,如麻花子、疙瘩子、米子(炒米)、豆皮子、团子(汤圆)、油果子(油条)等。在普通话中也有“果子”的说法,如“煎饼果子”,但普通话中的与荆门方言中所表达的意义不同,荆门方言中“果子”除了指水果外,专指“油条”。
日常生活用品。如“车子、盆子、袋子、鞭子、奏子(瓶塞)、袱子(毛巾)、背褡子(背心)、尿片子”等。
(3)虽然荆门方言的颤音“子”的范围要大于普通话中的子,但普通话中有一些“子”的搭配是荆门方言颤音“子”所没有的。如:
“哑子”。在普通话中可以说“哑子”,但在荆门方言中则不能,如要说只能说成“哑巴子”。
例:是这样“惜墨如金”。在往年曾有一首《孤山听雨》,以后便又好像哑子。
“逃生子”。“逃生子”在普通话中是“非婚生子”的意思。在荆门方言中没有这种说法,一般为“私生子”。
例:“……叫我爹是‘老畜生’,叫我是口口声声‘小畜生’‘逃生子’。”
“脖子”“颈子”。在荆门方言中,“脖子、颈子”都叫做“jiǔhuàng”。
参考文献:
[1]郭宇丽.榆林方言小称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学术型),2012.
[2]侯超.汉语词缀的功能与皖北方言的“子”尾[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03).
[3]刘海章.荆楚方言研究·荆门方言中的颤音[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4]刘海章.方言腔调辩证[C].荆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5]刘海章.方言辩证的理论基础[C].荆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6]李小凡.苏州方言语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姜蕾.<儒林外史>所体现的江淮方言和语法现象[D].苏州:苏州大学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论文,2003.
[8]芜崧.荆楚方言中的“好A子”句式[J].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15(05).
[9]芜崧.荆楚方言中的词缀[J].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0,25(03).
[10]乔余生.山西方言“子尾”研究[C].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3).
[11]王国珍.社会语言学视角中定襄话的“人名加子”现象[J].修辞学习,2007(05).
[12]王群生.湖北方言的颤音[J].语言研究,1987,2.
[13]邢福义,汪国胜.现代汉语[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贝多芬晚期钢琴奏鸣曲颤音问题研究
——颤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