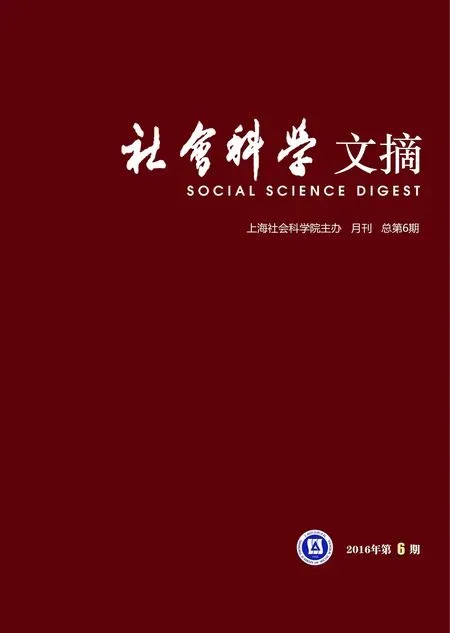“国民”的隐现
——沦陷后期周作人的反启蒙姿态
文/袁一丹
“国民”的隐现
——沦陷后期周作人的反启蒙姿态
文/袁一丹
在北平沦陷后期写作的“正经文章”中,周作人最看重《中国的思想问题》这一篇。以往对这篇文章的解读,主要依据写定于1942年11月18日,发表在《中和月刊》,后收入《药堂杂文》的版本,而忽略了与此相关的两篇演讲稿。其一是周作人在伪华北政委会教育总署主办的第三届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上的讲话,题为“中国的国民思想”,速记稿刊发在1941年9月《教育时报》第2期上;其二是在《中大周刊》上发现的,1942年5月13日周作人在南京伪中央大学的同题演讲。这两篇未入集的演讲稿,不止于版本学上的意义,为《中国的思想问题》的再解读提供了一些新线索。文本链的扩充,关键在处理新材料与常见书的关系。通过不同版本的对读,从演说到文章的措辞调整中,可以发现其思想演变的中间环节,从而修正关于20世纪40年代周作人思想转向的整体论述。
启蒙姿态的调整
《中国的国民思想》作为《中国的思想问题》的雏形,本是1941年9月周作人以伪教育督办的身份发表的一次讲话。以“中国固有的国民思想”为题,看似脱离了沦陷区的特殊语境,周作人却声称这个思想上的问题“好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身体一样的重要”。“国民思想”之所以构成沦陷期间的“切身”问题,乃基于周作人一个相对悲观的基本判断:“中国的国民思想,现在已经到了病得很重的时期了,非请医生检查不可。”
然而到次年5月周作人作为“北方教育当局”的代表南下,受邀至伪“中央大学”发表演说时,完全推翻了此前的悲观论调,称这几年来常有外国或中国朋友和他谈起这个问题,以为中国国民的思想问题很严重,应该有对策,而他自己的态度倒颇乐观,对此种疑虑的回应是“中国国民思想问题并不严重”,“中心虽然缺乏,却不须另建”。
究竟战时中国的国民思想是否构成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周作人这两次演说的时间相隔不到一年,发言立场却整个调换过来。要追究其突然改口的原因,一方面需对照当时的舆论环境,另一方面还得回到他个人的思想脉络上去看。从作于1940年的《汉文学的传统》开始,周作人便极力与“国民性”话语划清界线,称其为“赋得式”的理论,“说得好不过我田引水,否则是皂隶传话,尤不堪闻”。周作人用来破解“国民性”话语的工具,一是衣食住,即生活方式上的细微差别;二是凌驾于民族特殊性之上的普遍人性。用“人性”消解“国民性”话语,明显在偷换概念,实则是一种象征性的反抗策略。《中国的国民思想》这篇讲话中周作人以对谈引出“国民性”的问题:
有一位外国人问我:“中国的国民性怎样?”我说:“中国人是人,是生物,他要生存,这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此外并无什么古怪异常的地方。”
提问者的身份特意设定为“外国人”,无异于暗示其对“国民性”的重新诊断乃是对外发言。将“国民性”等同于好生恶死的“人性”,进而等同于“生物性”,最后归结到生存的基本要求上,这一长串等式必须置于沦陷的前提下才能得出“反抗”的结论:“因为中国人是人,是生物,要生存,所以你不让他生存他是要反抗的。”
在沦陷后期民众的生存需求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周作人以“人性”“生物性”为中介,将中国的“国民性”等同于生存的欲望。然而在五四时期批判“国民性”的启蒙话语中,周氏以为中国人欠缺的正是对生存的执念。“国民性”批判本质上是一套启蒙话语,放弃批判的立场,折射出沦陷下一度以医师自居的启蒙思想家所承受的内外压力。“国民”的概念仍旧是40年代周作人谈论中国思想问题的切入点,只是逐渐由对内批判的立场,转向对外抗辩的姿态。
沦陷之下,何言“国民”?!
沦陷意味着“国”与“民”的分离。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滞留在华北的“国民”,一夜沦为中华民国的“弃民”,乃至于“亡国之民”。沦陷之下,何言“国民”?!若言“国民”,又是哪国的“国民”?现实世界中被分裂的“国—民”,在周作人文章中竟安然无恙,一方面归因于“中华民国”在沦陷区的实亡名存;放到周氏个人的思想脉络中,又可视为晚清经验的复活。
周作人对“国民”一词的特殊理解,在其留日时期杂凑而成的长篇论文中已显出端倪。他对“文章”之意义及其使命的讨论,便是以“国民”的概念为起点。与“臣民”相对的“国民”(こくみん),在近代日语中是nation的对译词。而nation在西方政治传统中指涉的是一种理想化的“人民全体”或“公民全体”。从这个意义上说,nation与state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理想化的人民群体,而后者是这一群体自我实现的工具。所以nation-state在日语中通常被译为“国民国家”而非“民族国家”。nation与state之间的这个连词符,表明二者的关系尚未稳固,其实是被历史地建构出来的。40年代周作人口说或文章中隐现的“国民”,其实是民族国家的代替物。
在晚清“亡国灭种”的阴影下,周作人经由日语转借来的“国民”(nation)一词,包含“质体”与“精神”两个要素。“质体”即民族国家的躯壳:“同胤之民,一言文,合礼俗,居有土地,赓世守之。”“精神”作为构成“国民”的另一要素,所起的作用“犹如众生之有魂气”。清末周氏兄弟标举的“国民精神”,又谓之“立国精神”,换用当时言论界流行的说法,相当于“国魂”或“民族魂”。在“质体”与“精神”之间,周作人更看重后者:
质体为用,虽要与精神并尊,顾吾闻质虽就亡,神能再造,或质已灭而神不死者矣,未有精神萎死而质体尚能孤存者也。
尊“精神”而轻“质体”,是因为“质虽就亡,神能再造”。周氏相信“亡国灭种之大故,要非强暴之力所能独至也”。探讨一国一文明之盛衰兴废,但视“精神”何如而已,不必以“执兵之数”即捍卫“质体”的军事实力为根据。周作人以埃及、希腊等文明古国为例,试图证明在“质虽就亡”的情境下,凭借旧泽与新潮激荡而成的“国民精神”仍能实现“邦国再造”的理想。由此可知周作人对“亡国”的理解,不在乎国家形态之存亡,更看重“国民精神”的再造力。
基于周作人对“亡国”的特殊理解及“质体”与“精神”的二分法,才能明白他沦陷后期为何反复强调汉字、汉文学的政治作用。周作人将文学视为一种象征性的政治工作,前提是“国将不国”,或国家已沦为一种非现实的但又必须信奉的虚体。在被占领的特殊语境下,汉字、汉文学(即国文、国文学)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政治功能,甚至取代了政治生活的所有职能,这些职能在国土沦丧时已被剥夺殆尽。
问题的暧昧性更在于“国民”“国家”这些词在沦陷区并未成为政治禁忌,无论是汪精卫为首的南京伪“国民政府”,还是始终保持特殊化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都不讳言带“国”的字眼。而日本在中国大陆分而治之的统制策略,与经营台湾、伪满洲国不同,亦无力将民国之“弃民”统统改造为“皇民”。故周作人演说或文章中出现的“国民”,就他个人的思想脉络而言,可视为晚清经验的复活;从沦陷区的政治生态与舆论环境来看,其实也毋庸避讳。
“国民”“国家”之所以毋庸避忌,关键在于“中华民国”在沦陷区实亡而名犹存。从七七事变后日伪在北平扶植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到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都顶着“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与重庆方面争夺法统。对滞留在沦陷区,熟悉春秋笔法的文人学者而言,正朔虽在西南,能继续使用“民国”纪年,未尝不是种心理补偿。据竹内好日记,七七事变后与周作人过从甚密的尤炳圻向他讲述新文化人的动向,透露周作人决意在“中华民国”这一名号被取消时南下。传闻的真伪无从验证,但至少反映出北平沦陷后周作人在去留问题上给自己划了条底线。其信守的“中华民国”,与具体政权无关,只是一个虚名及其象征的“邦国再造”的理想。
如果说周作人“落水”前对“中华民国”抱有某种遗民情怀,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是国家与政府的分离,而这点对于周作人由清末种族革命及无政府主义培养起来的政治自我而言,正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1907年周作人针对立宪风潮而作的一篇杂感中,试图将满清政府——种族革命者眼里的异族政府——从中国人之爱国观中剔除出来。他所认可的“爱国”,更接近于诗人对故土,即“生于斯,歌哭于斯,儿时钓游之地”的眷顾之情,而非晚清“志士”所鼓吹的“盲从野爱,以血剑之数,为祖国光荣”,后者被其视为“兽性之爱国”。周作人继而从语源学上厘清“爱国”(patriotism)与政府的关系:
吾闻西方“爱国”一言,义本于“父”;而“国民”云者,意根于“生”,此言“地著”,亦曰“民族”。凡是“爱国”、“国民”之云,以正义言,不关政府。
满清政府在受种族主义熏陶的知识人眼里,不仅是与“国家”相分离的,甚至处于“国家”的敌对面。在异族主政的背景下,爱国即意味着与政府为敌。
“胜国之民,何言政事,何云国民?”国家与政府尤其是异族政府相分离,作为从晚清种族革命经验中形成的思想前提,并不适用于40年代北平沦陷的特殊语境,但对于选择“苦住”的周作人而言,这或许是他赖以维持“遗民”幻觉的救命稻草。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有效的抗弓形虫药物靶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