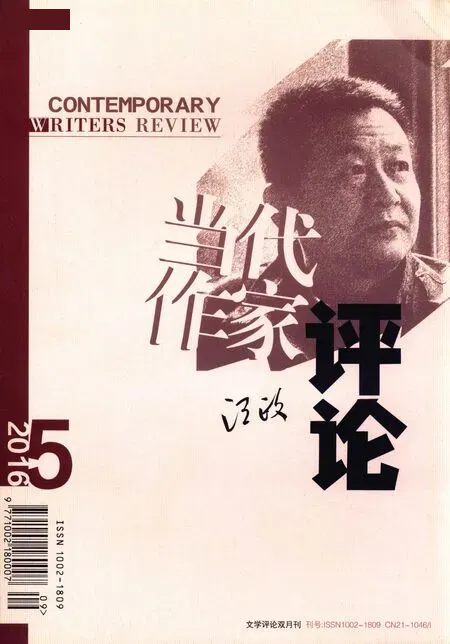文学批评的本色
——论汪政、晓华的文学批评
李新亮
汪政、晓华评论小辑
文学批评的本色
——论汪政、晓华的文学批评
李新亮
在当代文学批评的丛林中,汪政和晓华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从新时期文学伊始,他们初登文学批评的舞台,至今算来已经有30多年。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80年代文学批评的风光,还是90年代文学批评的失落,以及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的众声喧哗,他们一直坚守着这块阵地,从未离开。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么多年来,他们不像某些批评家在文学批评的风光时代大红大紫、独领风骚,而在文学批评备受冷落的时代便改行转业,把文学批评作为立身扬名的手段。汪政、晓华从未把文学批评作为某种工具,而是将之看作是终身的事业,一直坚持文学批评的本色,以开放包容的文学批评理念面对文学发展中所出现的新文学类型,以直击现实的文学批评情怀关注现实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以优雅的文学批评姿态对批评对象饱蘸着同情之理解,他们的文学批评是讲究务实的,是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在指出问题的同时也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总览30多年的文学批评实践,虽然他们的文学批评对象所涉猎的范围有所转变,批评的方法和策略也有调整,但是他们的文学批评情怀则是一贯的。本文将以其《我们如何抵达现场》为中心,谈谈汪政、晓华文学批评的变与不变。
一、开放包容的文学批评理念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批评家是个性鲜明、锋芒毕露的,对事物的分析和理解是睿智而深刻的,但是,他们也偏执而尖锐,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排他性,尤其是形成了自己独特批评风格的批评家更是如此。批评家们对符合自己审美理念的文学作品尽情讴歌、极尽赞美之能事,而对违背自己审美理念的文学作品则穷追猛打、严厉批判,不容其有任何生存的空间。这种批评观念在传统纯文学的批评格局中源远流长,似乎也合情合理。但是,近来的文学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文学的写作方式,还是文学的传播方式,甚至是文学的阅读方式,都超越了传统文学的格局,依然秉持着以往的批评理念是否不合时宜了呢?在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洪流中,汪政、晓华无疑是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我们如何抵达现场》的序言中开宗明义:“与前几本集子比较,不能不说,自己的文学观念正在发生改变。”*汪政、晓华:《我们如何抵达现场》序,第1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他们认为,当下的文学批评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有利于文学的未来发展。在他们看来,“多样化本来是文学发生以来的常态,但是,许多文学现象与文学文本却一直在文学之外,这里面无疑有文学标准的问题,也与文学机构、文学体制等等所构成的文学权力与漠视有关,说你是文学你就是文学,说你不是文学你就不是文学,实际上文学歧视与文学霸权已经长期存在并被视为正常,这其实不利于文学的发展。”*②③④汪政、晓华:《我们如何抵达现场》,第1、7、74、3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因此,汪政、晓华倡导开放包容的文学批评理念,要适时地与时代保持同步,并不固守自己的批评理念,不以多年前的眼光看待新事物,吐故更要纳新,对待不同的批评对象,批评家所选取的角度和立场应该有所调整。
为此,体现在文学批评实践上,汪政、晓华的文学批评视野更为宽广了,以往被忽略和遭歧视的对象都合法地成为了文学批评的对象。他们不仅仅关注传统纯文学的写作,也开始关注那些曾经被视为不登文学殿堂的新型文学类型,如网络文学、推理悬疑小说、类型小说,甚至是轻小说。网络文学的出现曾遭受传统纯文学的围剿,即便承认网络文学具有传统纯文学的文学性,但也认为网络文学不过是将传统文学的纸质媒介转化成数字媒介罢了,并没有多少新奇之处。但是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网络文学逐渐成熟起来,而且在写作范式上也突破了传统文学写作的封闭模式,展现了在互联网技术支撑下作者与读者间更为直接与便捷的交流互动,俨然已经构成了一种新型的文学写作模式。如果再将之排斥在文学的殿堂之外,这样的文学观实在是固步自封、抱残守缺了。汪政、晓华较早地认识到了网络文学这一特性,并指出,“它们应该是与纸媒文学或交叉或并行的新的视听物。”②这样的认识就不再把网络文学视为传统纸媒文学的衍生物,而是将之视为平等的新型文学形式,更有利于对网络文学的全面认识和深入理解。
如果说网络文学是新型文学形式的话,那么推理悬疑小说则可谓源远流长,远之如公案小说,近之如田耳、麦家的侦探推理小说。但是,较之欧美和日本的推理悬疑小说,差距还是十分明显的。究其原因,汪政、晓华认为,一方面是创作推理悬疑小说的作家群整体素质不高,另一方面就是研究和批评的滞后。对于推理悬疑小说,当下的批评往往不得要领,一些批评文字更是隔靴挠痒,这主要因为对当代推理悬疑小说“要进行批评与研究,仅仅从纯文学的理论框架出发‘客串’一下根本达不到目的,而是要建立符合推理悬疑小说的理论体系和范畴”。③这就要求文学批评要理清推理悬疑小说创作的独特性,不能仅仅以传统纯文学的批评标准来评价其创作的优劣。
汪政、晓华也注意到了类型小说和轻小说在当代社会的蓬勃发展。可以说,类型小说和轻小说在当下已经成为大众阅读最为受欢迎的文学文本。“从总体上说,类型小说是一种轻质的易阅读品,难了,就会降低阅读的快乐。从这方面可以看出一点,即类型小说非常重视读者,如果说经典小说是作者的艺术,那么类型小说可以说是读者的艺术。”④轻小说类似于类型小说,其主要特征是在内容上不表现主题严肃、语义复杂的主题,在叙事上,不排斥模式化的叙事,追求娱乐性,把阅读的新奇、刺激和替代性满足作为重要的目标指数。类型小说和轻小说的出现,一反纯文学创作在内容上反映重大社会主题、历史变迁,在表现形式上凸显作家创作个性的创作模式。对于生活在当代社会重压下的人们来说,类型小说和轻小说是生活的调味剂,缓解人们日常生活所承载的压力,因此备受读者的喜爱,其蓬勃发展自有其生存的巨大空间。汪政、晓华对类型小说的本质概括十分到位,他们说:“类型化小说作家秉持的是快乐主义原则。类型小说上承市民、通俗文学,下接消费时代的娱乐文化,快乐、享受并无设定的阅读体验。”*②③④汪政、晓华:《我们如何抵达现场》,第3、254、255-256、296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
汪政、晓华从事纯文学批评多年,早已形成了自己的批评策略和批评风格,然而,在人到中年之后对文学批评能有这样的转变源于他们有着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实感。“问题主要还处在文化转型时期我们批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坚持自己的经典的与精英的立场,是历史地、变化地看待批评,还是以现代学术体制下的文艺批评学作为基本的出发点?我当然是主张前者的。”②他们对网络文学、推理悬疑小说、类型小说以及轻小说的关注与批评,或许以后还有其他新型的文学类型,这并不是放弃了纯文学的批评标准,而是要以更开放包容的批评理念来整体思考如今的文学现场,他们有一段文字比较全面地阐明了自己的批评观,“我不是一概反对现代学术制度,也不是一个对抗语言的反智主义者,而是提倡批评的多样化,不管哪一种批评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当然,对同一种审美对象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却不可以从根本上质疑对方存在的合法性”。③
二、直击现实的文学批评情怀
文学批评应该从哪里出发?现实主义文论会首先选择从社会历史出发,浪漫主义文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从作家出发,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文论自然会选择从文学文本出发,读者导向理论批评会优先从读者出发。其实,无论哪种批评方法,无论从哪里出发,它们都能罗列出一大堆从自己出发的理由。因为,文学作为一个各要素之间交互的活动,从任何一个要素出发都是合情合理的。不过,这些文学批评仅仅是作为一种批评的方法而已,并不体现批评家的批评情怀。汪政、晓华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仅仅将文学批评看作是一种方法,而是要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展示自我的情怀和价值观念。他们的文学批评总是从现实出发的,将文学批评植根于文学现场,从不脱离实际,始终接着地气。无论文学批评针对何种文学类型与文学现象展开论述,它的出发点和旨归都是日常生活现实本身。文学批评并不是钻进文学的世界里自足经营,它更大的价值体现在对现实的观照。文学批评所呼唤的和所针砭的,并不仅仅是出于文学文本的审美分析,而是源自我们日常生活中存在并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所以,在汪政、晓华的文学批评中,现实、日常生活、文学现场、当下社会等等都是常见的高频词。这一切都源自汪政、晓华直击现实的文学批评情怀。
汪政、晓华对文学批评的定位就是关注当下现实社会的。为了更明确地阐明这一立场,他们通过与文学研究的比较这样论述:“在空间上,批评应该是在文学现场的,而研究则不必,它可以在远离噪杂喧嚣的后场;从时间上讲,批评与文学事件的发生是共时性的,它本身即是文学活动的有机构成,而研究则是滞后的,它可以在文学活动经过沉寂、自然筛选与淘洗之后再进行,它更多地面对的是过去时态的、已经成为历史的对象。”④以时空视角来比较,汪政、晓华强调了文学批评迅速有效地介入当下文学的特征。文学批评家不像文学研究者可以从容地静心沉潜,而是要对当下的文学现状做出迅速的回应和评价,文学批评更注重批评的现场感与共时性特征。这就要求文学批评家要具有敏锐的艺术感觉和批判社会的现实感,对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和社会历史的变迁做出相应的评价。
汪政、晓华直击现实的文学批评情怀体现在尤为强调作家与现实的亲密关系。用他们的话来说,文学创作家要有一颗“世俗心”,文学作品要充满人间烟火的气息。所谓文坛天籁,其根源则在人间烟火。一切脱离人间现实生活的文学创作都是虚假的,没有真正的生命力。为此,在他们的文学批评中对王安忆和毕飞宇的一段创作谈表示由衷地赞赏和认同。王安忆说:“从现实中汲取写作的材料,这抓住了文学,尤其是小说的要领,那就是世俗心。”*王安忆:《王安忆说》,第301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毕飞宇则将“世态人情”视为文学的拐杖,他说:“世态人情是要紧的,无论我们所坚持的小说美学是模仿的、再现的、表现的,无论我们的小说是挣扎的、反叛的、斗争的,世态人情都是小说的出发点,你必须从这里起步,你必须为我们提供一个小说的物理世界。”“任何时候,小说只要离开了世态人情,必死无疑。”*毕飞宇:《文学的拐杖》,《上海文学》2007年第7期。这里对“世俗心”和“世态人情”的强调就是要作家保持与现实生活亲密的关系。小说家在作品中所反映的现实生活不要刻意拔高与美化,而要真切地将日常生活的原汁原味书写出来,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看到了“世态”,更体验到了“人情”。这是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原则,是一种伦理写作。
汪政、晓华直击现实的文学批评情怀还体现在对反映当下现实生活的文学题材的特别关注。他们在《我们如何抵达现场》这部论文集中,很大的篇幅都是在关注现实生活的热点问题,例如底层文学、乡村文学、四川抗震文学、弱势群体的文学书写等等。这些都是当下社会在历史文化转型时期所突出的典型问题或应急问题。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文学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和表现方式去关注和表现底层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政治生态和文化建设方面受到怎样的挤压和遮蔽;在突发灾难面前,文学应该怎样积极地介入现实生活,对灾后的日常生活与重建以及对灾难的书写应该持有怎样的审美标准。汪政、晓华的文学批评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指出了文学创作所存在的问题,并试图给出自己的答案。例如,在论述底层文学时,他们认为:“对于文学来说,关键的不是单纯地从外部对底层给予同情,而应该将视角转移到他们内部,唤起他们对自身品质和力量的关注和自信。”*④汪政、晓华:《我们如何抵达现场》,第22、209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在论述刘醒龙的《政治课》时他们认为:“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第一次集中地将乡镇政治生态作为表现的对象,但其意义因为乡土小说、文化批判和现实主义冲击波等概念的挤压与遮蔽,至今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④
三、优雅务实的文学批评姿态
优秀的批评家是时代的预言家,他们对社会现状和文学现象的理解和分析,总是能做到察他人所未察,仿佛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对每个细节都明察秋毫,从细小的端倪就能看到其发展的未来态势,所以,总是能领时代风气之先。优秀的批评家又往往语出惊人、一针见血,在纷乱的现象中轻易地就去芜存菁,三言两语,抽丝剥茧,直击事物的本质。正是因为批评能为批评家带来如此高的声望,很多批评家不免十分向往获得这种声望,其下笔为文时更注重批评在社会中所产生的效果。这导致有些批评家其用心便不在分析批评对象上下功夫,而更为在意批评的表达方式如何能更引起广泛的关注,将文学批评实践当成了自我批评姿态的彰显。*李新亮:《当下文学批评的三种病症》,《天府新论》2011年第6期。于是,批评的风格更趋向于汪洋恣肆、天马行空的表达方式,批评家们就不免指点江山、激昂文字,更加放言无忌,批评自然也就不免夸张和矫饰起来。用今天时尚的话语叫“酷评”,所谓酷评的基本原则就是根本不用理会批评的理性分析而只在意批评效应。
我们在阅读汪政、晓华的文学批评时,几乎看不到他们抛出些耸人听闻的观点,以博得批评的轰动效应。多年来,他们的文学批评保持着一贯平和的心态,富有建设性而非破坏性,很少在他们的文学批评文字中见到那种剑拔弩张或义愤填膺的情绪化表达,他们的批评以文本细读为基础,不刻意夸饰猎奇,逻辑严谨,用语平易,娓娓道来,展现出一派优雅务实的文学批评姿态,这在当代批评家中是很难得的。有学者曾评价:“汪政、晓华的许多批评就是如此,他们的观点往往平和而有个性,敏锐而不失温文,方法更是落到实处,从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入手,仔细而真诚。”*贺仲明:《批评的美丽——汪政、晓华批评论》,《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4期。这是十分公允的。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汪政、晓华明白,真正本色的文学批评剑心所指并非贪图名气和效应,而在于批评家是否真切地理解了文学对象本身,并给予时下文学现状诊断并开出药方,不能只破不立,而要务实地给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批评家要对作家做到同情之理解。唯有同情才能理解,唯有理解方能深刻。汪政、晓华的文学批评向来都是从对批评对象满怀着同情之理解出发的。例如,在论述当下文学现象时,他们总是从当下的文学环境出发。因为,在他们看来,当下文学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文学环境正是文学批评活动的真正起源,“在这个起源中,我们可以析出它的一些可能为今天的学者们所忽视或不齿的但却是批评的先验构成,比如,它和艺术创作与消费的共时性关系;它与艺术品制作、出版、流通的信息性关系;它与艺术消费的商业性关系”。*④⑤汪政、晓华:《我们如何抵达现场》,第257、28、18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虽然这些因素被“忽视或不齿”,它们更多的是非文学性的因素,但是真正的文学批评不应该避讳,因为这些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甚至左右着当下文学的发展,我们的文学批评如果戴着有色眼镜将这些都过滤掉,那么,我们的文学批评则是无根的批评。再如,汪政、晓华在论述青年作家尤其是“80后”作家的创作时指出,“从目前国内文学院研究与文学批评来说,对‘青年创作’还未曾有切实而具体的了解,如果将青年创作作为独立的批评对象就必须承认有许多问题我们还知之甚少。比如当我们接触到我们自以为清晰的研究对象时,我们甚至不明白什么是‘青年’”。④汪政、晓华文学批评的这种同情之理解并不仅仅针对当下文学,他们在谈到先锋文学时认为,文学批评应该重新认识先锋,“先锋更重要的品格与特征显然是思想上的,是主体与世界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自身与世界的意义,而不仅仅是这些元素如何以文学的语言方式呈现”。⑤这种认识观区别于以往对先锋文学的认识,真正的先锋并不体现在形式上,如果在思想上是守旧的,无论怎样离经叛道的形式也不是真正的先锋。先锋就是语言实验,先锋就是形式,这种文学批评观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达成共识,但是,汪政、晓华却在时隔多年之后又给出了较为传统的理解。这不是文学批评的循环或者倒退,反而恰恰是经过时间的沉淀,我们对先锋文学的认识有了更为深刻的同情之理解。
汪政、晓华的文学批评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特别追求务实性。我们常常看到,他们在文学批评中不仅对批评对象进行剖析与评价,而且还乐于提出些建设性意见。这在当代文学批评中也是很少见的。对于批评家们只诊断不开药方的批评模式,我们早已屡见不鲜,并且已习惯于批评家的只破不立,潜意识地认为,开药方并不属于批评家的职责范围。但是,汪政、晓华并不认为给出建议的文学批评是画蛇添足,这原本就是义不容辞的职责所在。他们在谈到生态文学时,由衷地呼唤:“生态文学固然应该关心环境保护,关心日益严峻的生态现实,但它主要的目的不在于科学而在审美,不在于外而在于内,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①汪政、晓华:《我们如何抵达现场》,第147、148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生态文学要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内心感受,“生态小说不应该只有对立与批判,它还应该回忆、展望与肯定,在将人们从现代化、物质、欲望与功利中拉出来的同时给人们描绘曾经存在的美丽与温馨,唤醒迷失的感觉,肯定精神的价值,宣示理想的未来……”②汪政、晓华:《我们如何抵达现场》,第147、148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在谈到乡村文化书写时,他们倡导一种慢的艺术节奏。因为,现代社会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提升了生活的节奏与速度,而作为原始朴素的乡村文化与这种节奏是不合拍的,更何况以文字为媒介的文学艺术绝不能因为追求速度而丧失自己的美学特质。
汪政、晓华的文学批评一直款款而行,从容不迫。在文学批评理念上,不固执己见偏执一隅,秉持开放多元的理念;在文学批评情怀上,从现实出发,回到文学现场;在文学批评姿态上,满怀着同情之理解面对文学批评对象,追求务实而不凌虚蹈空。一言以蔽之,行走在当代文学批评的丛林里,汪政、晓华从未迷失自己的道路,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心底一直有文学批评的本色。
〔本文系河北民族师范学院2014年度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404)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李桂玲)
李新亮,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后,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