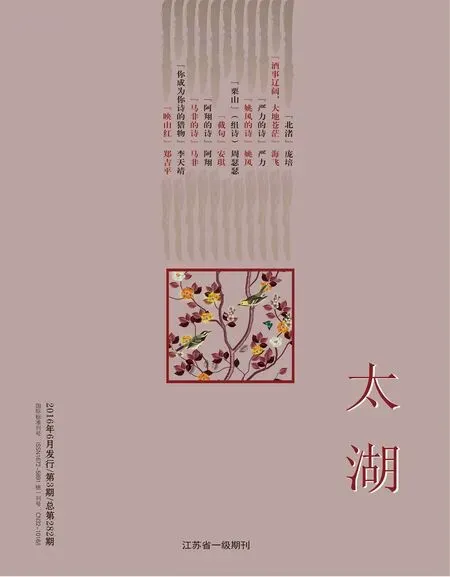映山红
郑吉平
映山红
郑吉平
乌蒙从塔吊上下来的时候,西下的太阳离远处的支嘎阿鲁湖还有一竹竿高。支嘎阿鲁湖是修电站形成的人工湖泊,海拔1140米,水域面积达80平方公里。在塔吊上往西看它,仿佛是在天上,烟波浩渺,果然称得上 “贵州第一湖”。乌蒙从吃罢午饭爬上塔吊,一直忙到现在,总算把修施工栈桥用的最后一根大钢缆从西溪的这边崖岸送到那边崖岸去了。
乌蒙手脚并用地下完塔吊上百根梯棍的最后一根,就见崖头爬上来一个背背篼的农妇,他赶忙走出塔架,飞快地将进入塔架的铁栅子锁上了。这是必须的,否则住这附近的村民说,等我爬上去看一眼,那就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每年三四月份,黔西北高原杜鹃花开,山民们紧紧张张地赶着栽包谷。刚刚爬上崖头的这个女人乌蒙认得,她是下边河谷的小寡妇,人称 “映山红”,最爱收拾打扮。看,即便今天的活儿是背粪送到崖头的地里,她也穿着波鞋牛仔裤,上身是一件粉红色短袖衬衫,黑漆漆的长发绾起来,扣一顶鸭嘴般长沿儿旅游帽。乌蒙现在一见她就发怵,因为今儿早上他从塔吊上下来的时候,她刚巧背着倒掉了草粪的空背篼从塔架前过,嘴里叼着一朵路边随手摘的和她名字一样的杜鹃花 (映山红是杜鹃花的一种),站在塔架脚仰着颀长并且雪白的脖颈朝塔吊的驾驶室望了半天,突然说道:“小帅哥,我问你一个事咹!”
乌蒙说:“什么事?”
映山红指着高高的塔吊驾驶室:“不晓得在 ‘天楼’上做那种事是什么感觉噢?”
“做什么事?”乌蒙问道。
映山红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咬在嘴角的花儿都掉了,兀自笑得花枝乱颤。
“看来你还没结过婚吧!”女人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他说。
乌蒙一明白过来,他的脸倏地红了,朝工人住地的活动板房逃去。背后映山红还在笑着:“别跑呀,你带我上去体会体会!”
却也是巧,还是这女人特意过来的?偏生从塔吊上下来就要碰到她!
“哟,你别锁 ‘天梯’呀!早上给你说的那个,你还没带我到 ‘天楼’上去呢!”映山红隔老远就笑嘻嘻朝乌蒙嚷了起来。乌蒙不敢回言。小路窄窄的,他见人家背着大半背篼油黑的草粪,便站到路旁的石脑包上让她。
映山红偏不过去,反手将手里的 “拐爬子”往身后一站,背篼往 “拐爬子”上一顿,两腿一叉,就在乌蒙旁边当路歇了下来,舒舒服服地吁了一口气——顿时,那两眼,火辣辣的,盯着乌蒙只管看。
乌蒙的两眼闪避不迭。
映山红嘻哈打笑地唱了起来:
小路弯弯么小路窄,
弯弯小路么遇着谁?
麻布洗脸么初相会,
哪里天黑么哪里歇!
乌蒙感觉得出,这女人的目光把他的脸都烙煳了。
女人大笑:“没见过大男霸汉的还会害羞嘞!”
这时和映山红一个寨子人称 “烂路毙”的光棍儿老男孩不知从哪里撮了二两来,跩来倒去地从上边走来,隔老远惊喳喳道:“哟,一根棒棒插进映山红的胯里去了!”
乌蒙一惊,忙抬眼一瞟,忍不住咕地笑了。原来那 “拐爬子”无非就是一根棍子的顶端斗一个 “V”形弯木,看上去可以说是两齿钉耙一把,如果将 “V”儿扳抻了呢就是一个“丫”字。映山红将棍子倚着屁股一站,背篼顿在“V”儿上,两腿一叉,恍眼一看,果然就是烂路毙说的那样。
映山红朝烂路毙破口大骂:“瞎子母牛都不要的烂仔!你哪里灌马尿水水回来,还不快去跩岩打死!”
说完,两腿一蹬起了背篼,搂着歇棍,两只大白果眼在乌蒙脸上荡着秋千走过他跟前,风风火火往上头去了。烂路毙躲闪不及,孤拐上先吃她 “一不小心”扫了一小棍,接着故意一个踉跄,背篼在他肩膀上用力一撞,这厮仰面翻叉倒在路边搓着脚杆鬼哭狼嚎起来。
乌蒙觉得好笑又不敢笑,赶忙朝山坳里的工棚走去。那边,映山红的山歌又飘了过来:
小路弯弯么小路夹,
弯弯小路么遇着他。
麻布洗脸么初相会,
哥要歇觉么到我家!
烂路毙直起脖子扯开破锣嗓子朝上头报复性地吼道:
刚才过路是喃 (啥)人?不是男人是女人!
男人是我亲舅子,
女人是我当家人!
歌声未落,就被映山红 “孤寡……秃尾巴……癞格宝想吃天鹅肉……你也不屙脬尿照照自己”痛骂一顿。一边乱咒,一边到了自家地里,腰肢一弯,屁股一翘,肩膀一斜,背篼里的粪便倒在地头,扬起歇棍拍打几下背篼,不使草粪残留。烂路毙怕她追来又打,顾不得脚疼,跩来倒去地朝下面逃去。
映山红哈哈大笑:“别跑嘛!挨大炮砍脑壳的!有本事别跑!挨我揪倒不提你胯胯甩河里喂鱼!”
烂路毙叫嚷:“你来!你想男人就来……”话音未落,叭哒绊了一跟斗,爬起来搓了搓手,跑得更快。他也晓得自己酒醉,不敢抄崖头近路,只顺着乌蒙他们施工队修的施工便道,盘旋着往河边逃去了。
映山红说:“要没他们这条马路,你妈短命儿不跩岩摔成几丫!”
乌蒙见她一张葵花般脸朝这边望来,忙走进活动板房将门关上。机械组的组长郎贵和乌蒙同处一室,见他慌里慌张,便开门一看,不禁笑了,回头对乌蒙说:“你倒怕她把你吃了!”
乌蒙红着脸把头低下。
郎贵再朝门门外的映山红看了一眼,叹道:“大方姑娘一枝花,这话不假!”
郎贵和乌蒙同属贵州桥梁公司员工,乌蒙是塔吊司机,郎贵开挖掘机。目前他们驻扎的地方是大方县最南边一条名叫西溪的小河北岸大岩头上。从大方通往省城贵阳的高速公路必须从西溪峡谷上面经过,架一座桥的任务就落在了他们所在工程队的身上。
这是2013年的4月。三十年前,就在大方县境发现了世界上最大原始杜鹃丛林。正当山花烂漫之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络绎不绝前来 “百里杜鹃”看花,而西溪两岸的山民却在忙着准备播种包谷。所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时,施工队进驻这里来了。开工炮仗一响,听说要修高速公路 ,这些山里人祖祖辈辈做梦都没想到过咧,放的放了锄头,插的插了犁头,扔的扔了撮箕,甩的甩了背篼,全都跑出地头,拥过来看。
这条路的要修,村民若说不晓得,那是假的,因为施工队进场之前,大方县必得将征好的建设用地一寸不差地交给施工队。在征地过程中,干部们不知往群众家里跑了多少趟!不知发生过多少故事!
映山红家在崖头有一块地要被征用,她这人爽快,说,男人死了,娃娃还小,我一个人种不了好宽,征就征了呗。干部们倒希望她别这么爽快,好做她工作天天到她家里来,什么山遥路远,看她一眼腿就不疼了。相反那个烂路毙,干部们看着也恶心,他却熬得凶。那是他爷爷的坟,只这一冢坟竟比别人多熬五千元赔偿,干部们跑了十遍八遍,他家门槛都快被踩断了,还是咬着四千不松口。县项目指挥部的小王雅号 “王端工”,为了征地拆迁,真的是“端工挨鬼打,是法都设尽”,访到烂路毙有个三代以外的老表在地勘队工作,便请他做说客。烂路毙这个老表做了几十年地勘工作,对相山看地颇有一套,人称 “贾阴阳”。小王和这老贾熟,嬉儿不嗤地对他说:“你老表倘若堵工,你就要负连带责任,叫你们队长开除了你!好生劝他去来。”姓贾的道:“这有何难!”这家伙去到表姑爷爷坟头,左看右相,放声大哭。烂路毙忙问他何故伤心。贾阴阳也不答,只嚎啕说:“我还说我这表弟为什么至今一个人过!姑爷爷哟,这是哪个千刀万剐的,给你看了个断子绝孙的地方!该死,该死!”第二天,小王还没起床,烂路毙的电话就打了来,哭兮兮道:“我迁了……”
工程队进场这天,小王也来了,他听见村民纷纷议论:
“从这边岩头如何到得了那边岩头?”
“是呀!”
“搭木桥,没有这么长的棒棒……”
“砌石桥,没有这么高的撑木!”
是的,这座即将建设的高速公路特大桥,全长一公里多,河面距桥面垂直高度近两百米,按照山民们所知道的办法修桥,哪会有这么长的搭木和撑柱!
烂路毙见了小王,蹭过来和他套近乎,发了根一毛钱的纸烟给他,刺探道:“都说你的办法多,不晓得这个桥怎么修哟?”
小王竟也不嫌他烟烂,点了就咂。小王深谙做群众工作就是要下得烂。倘若钻进人家家里,你要抹了板凳才肯坐,他就要锁门下地去了。更有甚者,一碗酒他先喝一口,故意用刚刚捏过粪坨的手在碗口抹一抹才递给你,倘若你端起就喝,一切好说,倘若说什么胃出血肺穿孔不肯喝,他就与你 “够得摆”(Good-bye)——大方话的意思,懒得说了。
小王笑道:“这个,我却无法。不过,他们有的是法子,或牵绳或架梁,总之要把桥搭起来,那叫科学。”
这就用上了乌蒙的塔吊。原来,他们要先在两个崖头之间用钢缆架起一座施工栈桥。四根碗粗的钢缆在这边崖头固定后,乌蒙用塔吊将它们一根一根牵到对面崖头,早有工人过河爬到那里等着,将四根钢缆分别也打桩固定,两根在下,两根在上,以这四根为本,再拿些钢缆来,无非钩钩挂挂,像织网一样织出步道和护栏,这就成了一座缆桥。之所以叫施工栈桥,因为施工人员管理人员可以从桥上两头往来,不必为了送一样小东西,先要从这边崖头下到映山红们寨子,踩着小桥过河,再爬上对面崖头。
乌蒙和郎贵吹了几句牛,食堂的铃铛便叮铃铃地响了起来,又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这一阵活儿还不是很紧,晚饭一般都开得早,五点半就拉铃。两人从屋里出来正要往餐厅去,两辆越野小车爬了施工便道上来,在活动板房前的空地上停下。头一辆车上下来当地镇政府的一个副镇长,二一辆车上下来县指挥部的小王和一个脖子上吊着相机的 “90后”女孩。小王说她是省里来的路记者,专门采访大方县重大项目建设的。
“别去食堂吃了,你两个,一起下河边吃农家饭去!”小王对乌蒙和郎贵说。
原来路记者得知西溪大桥是这条高速公路最大的控制性工程,这座桥修不好整条路就甭想通车,就想找两个施工人员采访采访。小王与这大桥的项目经理联系,经理出差在外,让他带小路来找乌蒙和郎贵采访。
当下郎贵上了镇里的车,乌蒙和记者同车——小王做了许多群众工作以后形成一张烂嘴,故意跟路记者把汽车的 “车”说成象棋的“车”,说,我们有幸同车,实际想说的是 “同居”。那记者虽然年轻,一则看上去结过婚了,二则作为记者走南闯北啥没听过,并不以为意,所以气氛相当融洽。乌蒙倒没注意听他们聊些啥,只全神贯注看那被最后一抹残阳染过的西溪,像一条缎带飘去那座天上的湖泊。哦,湖的名字叫 “支嘎阿鲁”,据说支嘎阿鲁是黔西北彝族远古时候的英雄,这时残阳如血,湖水仿佛被他曾经拯救人类的鲜血染红!
真是!正如映山红唱的那样,世间路何其窄也,你再怎么不想相遇也是不可以的!乌蒙还以为去哪家吃饭,谁知竟是到了她的家里!
两部车在映山红家门口的晾坝里停下,小青瓦木屋里头只有一个头十岁的男孩,正提着一桶猪食出到晾坝里来喂猪。一见这阵势,他便将猪食桶往地上一顿,连忙跑到河边去叫妈妈。谁知一头架子猪在晾坝边圈里闻到猪食香,跨栏运动员那般,嗖地从圈门上的空格里飞了出来,一落地便似短跑运动员直向猪食桶奔来,一挨近那桶,顿时又变成摔跤运动员,两只前腿朝桶上一搭——说时迟那时快,副镇长也跟一个跳远运动员似的,一个箭步冲上去掌住猪食桶,否则非被那挨刀煪腊肉的给扳翻了不可!副镇长搧它一掌,趁着它闪避的间隙,赶忙将猪食倒在猪食盆里,说:“吃吧吃吧!”这厮旋转身,一嘴插进盆里,一口等不及一口地吃了起来。
小男孩奔到河边:“阿妈,两个车开到我们家!”
映山红换了一袭彝家百褶红裙,蹲在河边洗今天劳动穿的那一身。河水清且泛起涟漪。
“啥子车哟,阿龙?”女人问。
阿龙说:“一个是 ‘贵尖’,一个是‘贵下’。”
映山红三把两把清了衣裳,扭在提篮里挎了往家来。进晾坝一看两个车子,顿时又好笑又好气地戳了阿龙一指头:“你呀,书不好好读,成日家只晓得打扑克!这一下连个车牌都认不得了,‘贵A’说是 ‘贵尖’,‘贵F’说是 ‘贵下’!你这么不长进,也该去神龛脚下跪一跪下了!”
阿龙伸伸舌头自去喂猪。
乌蒙一见孩子他妈,恨不得变成一张纸缩进墙缝里去。偏偏映山红一见他就笑:“小帅哥,坐在天上好玩不?”
小王不知就里,说:“是呀!我们的塔吊工人,哪一个不是神仙!小乌,你最高开过多高的塔吊?”
一只大灰狗不知从哪里冲来,昂头摆尾的望着小王。映山红笑了,轻轻在灰狗的脑袋上拍了一下,说:“小乌,人家没有叫你!”
小王道:“难道姐姐这宠物名叫小乌?”
映山红抚狗头:“农村里叫啥宠物,就是个看家护院的,无聊时和它说说话儿,嘻!”
她撩了乌蒙一眼。
乌蒙极不自在地说:“唔,两百多米。”
“啊呀!”映山红叫了一声,说,“站了半天,还没给你们抬板凳!”这才将提篮挂在杏树的一根花枝儿上,去屋里抬了几根板凳来晾坝请大家坐。
副镇长说:“山红姐,这是省里下来采访的路记者,听说你的牡丹豆腐点得好,要来品尝一下。”
映山红一听,忙让阿龙去园子里摘花,她则去堂屋里开了打浆机磨豆浆。
“顺手摘几颗樱桃给娘娘叔叔们混嘴哈!”她朝阿龙喊道。
小王说:“路记者,这是开挖掘机的郎师傅,修施工便道时他曾经抽空帮这寨里的群众挖过地基,因此群众对施工队的印象很好;这是塔吊司机小乌——嗳呀对不起乌蒙——女主人的狗别又冲来——他是这条高速公路上最年轻的技术工人,你可以先采访他们。山红姐是征地拆迁最积极的一个,现在她忙,吃过饭了再采访不迟。”
采访完他两个,映山红的牡丹豆腐刚好出锅。“哇——”小路望着半白半紫这一大锅,口水都快流了出来,先咔嚓照了一张相。“山红姐,这是你开 ‘农家乐’餐馆的招牌菜吧?”
映山红说:“乱做呗,没有你们城里的好。”
小路把头摇得似拨浪鼓:“城里哪里吃得上这么自然的美味!唉,想吃也吃不上……”
副镇长道:“不!高速公路一通,贵阳到这里就个把小时,那时想吃就来,我们随时欢迎!”
指挥部的驾驶员说:“等高速公路通车,从贵阳到大方都不用这么久!说得夸张点,在这里上路前往贵阳打个电话,让朋友早餐店里叫一碗肠旺,赶过去刚好吃得!”
副镇长的驾驶员嗤的一声说:“贵阳人到大方来吃蹄花还差不多!俗话说,城里人下乡——杀猪宰羊,乡下人进城——你来赶场……”
副镇长生怕路记者尴尬,连忙打岔:“不管怎样,我们西溪峡谷可以借助高速公路大力发展观光农业,到时候,欢迎你们这些省城的客人和县城的客人前来体验我们的 ‘农家乐’!”
吃过晚饭,小路马上掏出采访本。映山红一看手机:“哟,八点过了,可不敢影响路记者回县城宾馆休息!”
小路道:“姐,今晚我不走了!我就同你在你这河边果园里睡!”
映山红看了看副镇长和小王:“那你们呢?又是周末又是晚上的都不得个闲……”
小王说:“嫑管我们!我们‘五加二’‘白加黑’‘夜总会’那是搞惯了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征地拆迁时来你们这里通宵召开群众会都开了好几次……”
“慢着!”小路止住小王,“你刚才说的‘五加二’‘白加黑’‘夜总会’是啥意思?”
小王说:“都说西溪大桥是这条路上最大的控制性工程,其实呢,最大的控制性工程是征地拆迁!因为征拆工作什么时候完成,施工队伍什么时候才能进场。因此,为了抢进度,上班五天加上周末两天,白天加上黑夜,我们都在工作,由于常常白天下乡晚上开会,有人戏言这是 ‘夜总会’……”
“好!”小路说,“这有意思!”她唰唰在采访本上记了下来。
小王说:“县领导听说我们高速公路征地拆迁直到结束都没有一个群众上访,开玩笑地说,我们这叫 ‘五加二等于零’。”
映山红一听,朝阿龙喝道:“还在这儿听,不快做作业去!难道你也想 ‘五加二等于零’!”
阿龙慌忙到窗前的书桌上做作业去了。
“那不是!”映山红怜爱地瞪着儿子,说,“如果读了五天书,回家过两天周末,学的啥全交回给老师去了,岂不是 ‘五加二等于零’!”
一屋人都笑了。
小王见小路兴头很高,便王顾左右而言他道:“阿龙,除了这 ‘五加二等于零’,我们和你还有相同之处!比如你做加减乘除,我们同样也做加减乘除!”
小路果然感兴趣:“什么意思?”
小王说:“哦,这是我们自己总结的 ‘四则运算’工作法则。”
小路说:“天,好新鲜哟。快说来听听,王哥,快!”
小王说:“好的。一是 ‘加法’。这之一呢,就是刚才说到的 ‘五加二’‘白加黑’,设法增加工作时间;这之二呢,是增加人手,交通建设不是我们 ‘铁公机’一家的事,可说是举全县之力……”
映山红插嘴道:“铁公鸡?”
小王不得不解释一下:“铁路公路机场建设指挥部嘛。这是我们县专门设置的一个机构,主要服务于大方机场、铁路和高速公路等重大交通建设项目,知道了吗,山红姐姐?”
“哦,是这个 ‘铁公机’哟!”映山红点了点头。突然,她咕的一声笑了,说:“我还说你们咋那么抠,征地款一分不肯多给,原来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哈!”
说得一屋人又开怀大笑。
小王说:“我家姐!那是多一个角也不能多赔的!该赔的地方,卫星从天上拍了照,我们无非按照图纸像分蛋糕一样,甲群众家我们该赔哪一块,乙群众家又该赔哪一块,就这样甲乙丙丁照着赔,实际丈量的面积和卫星扫描的面积不能超过千分之三的出入!”
映山红伸伸舌头,说:“我给你们倒茶去。”
小王继续对小路说:“‘减法’嘛,减少工作失误,减少问题矛盾,刚才说了,我们是‘零上访’,正因为如此,全省高速公路征地拆迁工作经验交流会就是在我们大方召开的。‘乘法’主要是改进工作方式方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忽然映山红叫了一声。乌蒙一个箭步上前,脱口问道:“怎么啦?”
原来,女人一边倒茶一边朝人多这边张望,一不注意,洒了几颗开水在她手上。
那边也一齐问她怎么啦。
映山红说:“没事没事,杯子险些落去,吓了一下。你们快继续呗!”
她偷偷瞅了乌蒙一眼。乌蒙已为自己刚才的失态而脸红。他才要转身,她说:“别走,帮我端茶!”
女人一双大眼忽闪忽闪,悄声道:“我烫我的手,又不是烫你的,你心痛个啥?”
乌蒙觉得自己的脸都可以烤豆干了。
女人噗哧一声轻笑,大声道:“小乌,茶倒好了,快帮我给他们端去!”
一道灰影一闪,那狗又不知从哪里跑了进来。映山红虚空朝它踢了一脚:“你能端吗!去!”灰狗闪身出去。
小王抢先从乌蒙端着的茶盘里捧了杯茶给小路,说:“女士优先!”
小路一听就笑,说:“我想起昨天的事来——他怎么就看扁了我们女士!”
映山红朗声说:“谁看不起你告诉我,我去啄他两脚!”
小路说:“这两天跑了机场跑铁路,跑了铁路跑公路,昨天不是采访成贵快铁建设工地吗?黔西北山区修路不像平原地方到处是人,真个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其实人都在山洞里,于是我想进隧道看看,可是,一个戴红帽子的男人硬不让进,说为了我们女同志安全——呸!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规矩不让女人进去,是怕以后火车出轨!”
映山红咬牙切齿:“就我们女人会出轨么!嗳,你刚才说,那个臭男人戴什么颜色的帽子?”
小路说:“红的。”
“咋不是绿的呢!”映山红用力跺了跺脚。
满屋子又都是笑声。
自从今晚,乌蒙有点喜欢这个女人的性格了。
映山红在崖头上栽完包谷,缆桥也彻底架好了。
两帮人分头从两岸往中间架,仿佛一群忙碌的蚂蚁。栽包谷的女人不时望望那些 “走钢丝”的 “红帽子”,不禁拄着锄头出神。钢盔帽,牛仔装,一个二个的好健壮,让女人看着都眼馋……
“山红姐,还没收工么?”这天,太阳正往支嘎阿鲁湖后面落,乌蒙主动朝她走来。
映山红的心咚啊咚地跳得飞快起来。平时伶牙利齿,这一分钟却半个字也说不出来,就跟魇住了一样。
乌蒙说:“山红姐,你的脸涨得好红,发烧了么?”
映山红这才一惊,下意识地伸起手来推挡,生怕乌蒙摸她脸蛋。随即一想人家比个姑娘都还姑娘,连跟你说话都会脸红,怎么会摸你脸蛋呢!她不好意思了,故意撩了一下粘在脸颊上的头发,说:“没有啊……”
说罢,慌乱地挖了几锄。
乌蒙说:“山红姐,盖好的包谷你咋又把它刨开了呢?”
“啊?”山红低头一瞅,要死,怎么会把一窝盖好的包谷刨了出来!
女人以羞作恼,朝乌蒙啐了一口,道:“天快不见亮了,人家一个人在土头,你到人家这里来,想要干什么嘛!”
乌蒙说:“我的女朋友明天要来看我,我想请你点一锅牡丹豆腐。”
女人的脸真的沉下来了。
“花都谢了!”她没有好气地说。
“啊?”乌蒙好失望。
女人瞅瞅他,又心疼,肿声烂气地说:“我晒得有干花放起!”
“啊!”乌蒙喜出望外,帮她放花。
映山红将锄头撮箕放进背篼,手杆弯勾起一支背系,将背篼斜款款地挂在肩膀上,一言不发地低着头从乌蒙面前走过,噌噌噌地往下走。
乌蒙说:“山红姐!”
女人站住了。不回头。像被雪凝住似的,一动不动。
乌蒙四下里瞅瞅。郎贵站在工棚那儿,好像在看落日。
乌蒙低声说:“山红姐,明天我……我……她……她可、可不可以在你家……住,一晚上?”
一只名叫贵贵阳的鸟儿一扇一扇地朝崖头飞来,它正想歇在女人的背篼上,背篼突然动了。女人噌噌噌噌走了。贵贵阳扑闪一下,重新高了高,一扇一扇地飞去女人家土边的林子,声音洪亮地叫了起来。
留下乌蒙一个大红脸,恰似多了一轮夕阳。
第二天,郎贵给了乌蒙半天假。吃过中饭乌蒙就去镇上车站接人。镇子离西溪不远,大方到贵阳的老马路就从映山红家旁边经过,河上有座老石桥,从桥头这儿算起至镇上是四公里半。不过,十多年前重新修了一条高等级公路通往贵阳,客运班车不再从老路走,这,乌蒙并不知道,他站在桥头等了半天也不见有客车,着急了,一顿脚,干脆走路去!就在这时,突突突突一串儿响声过了来,只见映山红黑皮裙黑风衣黑眼镜,红皮鞋红背包,骑着一辆天蓝的轻便木兰,在乌蒙身边歇下。
“上来吧!”女人在墨镜后面白了乌蒙一眼。
乌蒙迟疑着。
“不要女朋友了不是!”女人将墨镜往额头一掀,让乌蒙瞧见了她两个恼怒的大白果眼。
乌蒙一个激灵,一抬腿跨上摩托后座。
这时,一辆轿车载着一家四口到河边来玩,当家的摇下车窗对映山红说:“我们来吃你的豆腐哩!”
映山红道:“今天有事不得闲,你去五龙山庄吧。”
“好吧。”一家子去了。
“看喃,又不是没见过你老妈!”
乌蒙不知她骂谁,原来烂路毙在一旁歪门邪道地瞅着她。
“帮小帅哥接女朋友去啦!”这一句是说给全寨人听的。然后一踩油门,一溜烟扬长而去。
“都把老娘想得——”映山红正不知唠叨给谁听,一只大白鹅横穿马路,急忙一踩刹车。乌蒙合身扑到她背上,忙不迭撑起身子。
“给你预热预热!”女人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一松刹车一踩油门又走,哪管他乌蒙在后面一张脸红得喷血。
不一会来到小镇车站。大方至贵阳高速公路设了一个站在这附近,取名 “百里杜鹃西”,正在如火如荼地施工。
女人对乌蒙说:“在这等我,我去趟商店!”
一辆从县城开来的金杯车进站停下。乌蒙跑过去看,直看到所有乘客下完。他掏出手机打了出去:“你来了么?”
那边:“唔……你在哪?”
乌蒙说:“我在镇上车站接你。”
那边银铃般笑了起来,好像是笑喷了。
“二百五!二千五二万五!怕我说要嫁你今夜就和你洞房花烛你也信?农民工叔叔,你在那里慢慢等着吧,拜拜!”
“喂喂——”乌蒙望着手机傻了眼。
正在发呆,映山红回车站来,手里一个包装盒,没好气地往他怀里一塞:“给你两个晚上刚刚买的新被套!”
乌蒙傻呆呆的。
“你怎么啦?”女人歪头问他。
“被……被骗啦……”乌蒙傻傻地说。
“什么!”
“被骗啦……”乌蒙一动不动。
女人一把扯了乌蒙就走。
“去哪?”乌蒙被拉得歪歪倒倒。
“去派出所报警呀!”
乌蒙一挣停了下来。
“报什么警!”
女人急得说:“你不是被人骗了吗!”又拽乌蒙衣袖。
乌蒙将手一顿,脸青面黑。
“她……她骗我的……”他左手指着右手拿着的手机。
“谁?”
“……女朋友!”乌蒙勾下头。
女人的头发飘起来扫在乌蒙的脸上,他也懒得去理。他的心情相当沉重。映山红默默地驾着摩托,她理解他此时的心情。
转过一个山嘴,摩托在路边停住了。足足有五秒钟,乌蒙才发觉。
女人说:“我们下去坐一会儿再走吧。”
乌蒙机械地和女人一块儿坐到路边。这儿视野开阔。
“看——”女人手指并不算远的远处。乌蒙顺从地望去,夕阳西下,风生水起,支嘎阿鲁湖闪着金光。
“看——”女人又说。这一回,她指的是一座桥,西溪入湖之前大约半公里的地方,那是现在从大方通往贵阳的交通主干道,十多年前通车的高等级公路上的西溪大桥。“像不像把木梳?”女人问他。乌蒙点了点头。其实呢,他觉得这座桥好像一架竖琴,枕于高山流水之上,风儿弹琴,鸟儿静听。
“看——”女人往东一指。
乌蒙一看,一座塔吊像一把金黄的角尺站在那里,那是他的。施工栈桥像一根晾在两座悬崖之间的带子,几座桥墩像破土的笋子略有形状。
“再看——”
女人指的地方,是下边河谷开阔处,她家寨子那儿,小桥流水人家。“那座桥听说民国以前就修了的,以前从大方到贵阳,贵阳来大方,坐汽车都要从这座桥过。”
乌蒙木木地说:“唔。”
映山红说:“路记者讲的,你们正在修的那座桥往东不远,成都到贵阳的快速铁路的西溪特大桥立马就要开工。那么,你说我们西溪这条河上,一共有好几座桥?”
乌蒙发呆:“几座?”
“你数呀!”映山红拐了拐他。
乌蒙:“一……二……三……四。”
女人说:“还不止呢!你看,我家上头一点,我常常洗衣裳的地方,那儿原来有一座桥,后来有一年发大水,被冲断了,只剩两边几块石头,我们都叫断桥。你猜,断桥是谁修的?”
乌蒙:“谁。”
女人说:“奢香!”
乌蒙说:“奢香……是谁……”
女人说:“我摆个白话给你听吧。我们大方讲故事叫 ‘摆白话’。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或许你就不再难过了。好不好?”
也不管乌蒙同意不同意了,映山红就摆了起来。但她摆了两句就要求乌蒙集中精力听故事!乌蒙只好勉强听了。
原来这个大方竟然很有历史底蕴。诸葛亮南征时,大方彝族首领名济火者助其有功,被封为罗甸国王,辖今黔西北大部分地方。到了明朝初年,罗甸国王的后人名蔼翠者,又被朱元璋封为贵州宣慰使。在贵州,除了都指挥史马烨,蔼翠是最大行政长官,可惜他三十多岁便去世了。蔼翠死后,因其子年幼,由他夫人奢香代子袭职,出任贵州宣慰使。
峡谷里面的这条河之所以叫做西溪,因为黔西北地区在明代叫做水西,即乌江支流鸭池河以西的黔西北地区。水西彝族有四十八部,四十八部尊称奢香为 “苴慕”(君长)。奢香在大方城北的 “九层衙门”办公,马烨在贵阳却算计起她来,找个借口把她骗到贵阳当众剥开后背用树枝抽打。马烨的用意,裸笞奢香以激怒水西四十八部。君长被辱,四十八部果然要反,但奢香识破了马烨阴谋,不反而去京师,到皇帝面前告状。朱元璋听说马烨竟然要逼反西南,汗都惊了出来,虽然他是马皇后的侄儿子,也揪了回来 “咔嚓”。朱元璋感叹道:“奢香归附,胜得十万雄兵!”奢香为报皇帝圣明,回来就修路,打通了贵州连接云南、四川、湖南、广西的道路。黔西北到贵阳的驿道,当时千山万水,不知她是怎样铺设的线路,现在从大方到贵阳的公路、铁路,基本上都是顺着古驿道的线路来修的。可惜奢香三十多岁就因病去世,按今天的说法叫 “积劳成疾,因公殉职”。钦差大臣前来大方吊唁,传朱元璋圣旨谥封奢香为 “大明顺德夫人”。
说到这里,映山红望着水西圣水支嘎阿鲁湖,轻轻地对乌蒙说:“阿龙的爸爸和你一样,也是打工仔。在我二十五岁那年,他在修高楼时……奢香夫人其实比我还惨,二十岁就死去丈夫。可人家不仅没有消沉,反而做了那么多大事。乌蒙兄弟,你才失去一个女朋友,难道比我还惨,比我们的老祖母还惨?”
乌蒙想不到修路这个地方,竟然有这么一个女杰。他点了点头,站起身来朝着支嘎阿鲁湖 “啊啊”大喊几声。西溪大峡谷隐隐传来“啊啊”的回音。
“走吧,咱们回家!”映山红对乌蒙说。
女人一直唱到断桥:“不等三更过天晓白,奢香夫人赶月归来,她把目光画心上,照得漆黑的夜亮堂堂、亮堂堂……一座山翻过一条河,千山万水永不寂寞,你来过,年华被传说,百里杜鹃不凋落。我寻着你的路,让风都停住,依然清晰看见你那坚强的脚步。如果天留得住,如果地也能把你挽住,愿你就在这片云水间常驻!”
乌蒙恍然大悟:映山红屋里贴的宁静,身着彝装,原来就是她在二十八集电视连续剧《奢香夫人》里饰演奢香,映山红那么崇敬奢香,她那一套女式彝装,竟是跟宁静身上的一样;而映山红领着寨里的女人们在河边跳的被烂路毙称为 “僵尸舞”的广场舞,用的音乐就是凤凰传奇演唱的这首 《奢香夫人》。
为了安全起见,除了工程队的人,施工栈桥是不让人走的。可烂路毙看见施工队的人在上面走来走去,摇摇摆摆的似乎还好玩,就很想上去走一遭。令人着恼的是守桥的乔老者特别严厉,烂路毙每次挨到缆桥口口边,都被他轰鸡轰鸭般撵走。
烂路毙每月领着170多元低保金,并不用怎么操劳,心想老子有的时间,怕你不屙屎屙尿!这天,他果然候得一个机会,乔老者拉肚子,接连跑工棚后面的厕所。烂路毙等他再去厕所,便隔老远冲来,跑到桥上去了。觉得桥晃,便不敢跑,一步一步往前走。但走也晃,就抓着护栏半步半步往前挪。一低头,这桥并没铺板,自己站在一张网上,脚下通花大见亮的,万丈之下河水在淌。烂路毙魂飞魄散,大叫一声就趴下,伏在桥上一动也不敢动,身上抖得桥摇不止,“妈呀妈呀”叫个不停。
当时西溪特大桥到了架梁的阶段,乌蒙负责在空中吊送附件,正在暂歇着,烂路毙上桥他早就看得清清楚楚。乌蒙知道烂路毙是绝对安全的,就只怕吓得够呛,便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给地下的郎贵。郎贵忙上桥去,拎鸡拎鸭般这才将烂路毙顺下桥来。那厮紧紧抓着郎贵,一路走一路紧紧闭着眼睛,爹呀妈地死叫死喊。乔老者刚好从厕所回来,一见就吼:“你上桥去找死!”郎贵对烂路毙说:“路哥,我们这桥主要方便施工,老百姓除非情况特殊,否则是不让上去的,以后你别再有事没事都往上面走。”烂路毙好不容易才下了桥,就跟过了一趟鬼门关,刚从奈何桥上回来,摇手道:“不要说了,嫑说了!你就是花钱买我上去走我也不走了!”说罢,就走了。
“路哥?”乔老者望了望烂路毙软兮叭哒的背影,对郎贵说,“你才喊得起!烂路毙……”
郎贵正色道:“老乔,以后你要注意对本地人的态度。人家路要修成 ‘连心路’,桥要修成 ‘连心桥’。俗话说,‘好话一句三冬暖’,凡事 ‘三思而后行’,做到这两个 ‘三’,按照他们说的 ‘乘法’,‘三三得九’,我们才能在一个陌生地方住得 ‘长久’,也才能得地方群众的 ‘酒’喝。”
乌蒙发现映山红其实也想上缆桥去走走的。她一张圆圆的脸蛋儿像葵花一样,远远地瞅着在桥上来来往往的工人,很神往的样子。乌蒙打她手机:“牛吃草莓了!”她连忙回头一看,果然一条黄牛从坡边蹭到地边来。这一大块草莓她是栽给到西溪体验农家乐的游人摘的,游人还没吃呢,牛嘴臭烘烘的倒来尝新!她揣上手机,连忙过去把牛赶走。她仰起头,只见乌蒙的塔吊正在工作。
女人求过乌蒙:“你带我到你那 ‘天楼’上去嘛,悄悄的,嫑等人看到。”
但乌蒙拒绝了。一是纪律不准,二是确实上面危险,更何况他发现她恐高。
河的那边崖头上有个土医师,医术高明,乌蒙曾和映山红一块儿在她家旁边走过桥去,爬上去找土医师。土医师住的木屋和施工队工棚所在的位置一样高,从这边崖头都看得见,并且喊得应,但从谷底爬上去要爬好半天。一条小路挂在悬崖上,女人尽量靠着里侧走,看都不敢看峭壁下面的西溪一眼。
女人喃喃自语:“雄鹰从岩边飞走,燕子在岩壁做窝。红军啊红军,当年你们怎样从这样的地方走过?”
从那一次,乌蒙知道她恐高。
据乌蒙说,高速路桥一架好,这座施工栈桥便要拆除。女人觉得可惜,当时这桥也怪难得铺的,拆了多可惜,不拆它,以后游人到西溪来玩,可以上去走走,在上面观看峡谷里的风光。但乌蒙说,按规定桥是一定要拆的。女人对乌蒙说:“既然要拆了,你快带我上去走走。”乌蒙正在犯难,女人笑了。“摆你的!”她说,“你押我走,我还不肯走哩。我怕!”
在这儿施工都一年多时间了,“摆”(骗)啊,“押”(逼)啊这些大方话,已经用不着映山红给乌蒙解释,他一概听得懂了。而且,他还能用大方话朗诵下面这首 “诗”:
“早上起来打开‘窗’(cōng),见妹站在‘对’(dòng)门山‘坡’(pāo)上,太阳亮‘光光’(góng gòng)。哥(guō)啊,‘我家’(wā)妈不肯,你说要 ‘怎样’(zàng)?”
乌蒙问女人:“你们大方话咋没有卷舌音;‘红’‘黄’不分;两个字说成一个字……?”
女人:“你问我,我问山王菩萨!反正‘斗是’(就是)‘这样’(zàng)嘞(的)!”
还别说,乌蒙望着快要合龙的桥,倒巴不得它慢些合龙。他在想:“这桥整整修了二十个月,到时候有机会坐车从上面过呢,只怕两秒钟就飙过去了,连她家在哪儿都来不及看,更甭想看清楚她在河边洗衣裳!”
他望着映山红,两眼流露出几多不舍。
晚上,他梦见自己变成那个 “小乌”,活蹦乱跳地跟着她在果园里摘樱桃。体验 “农家乐”的游人笑语喧哗,他想舔她一下,又怕给人看见。恍惚间,就来到工棚斜对面的那块包谷地里。她提着竹篮,一个一个地抈包谷装在篮里。她对他说:“大方糯包谷又糯又甜,你也吃一个。”说罢,她剥开一个又粗又长的包谷,笑嘻嘻地问他:“这像什么?”他忽然懂得她说的“什么”意思了,心咚咚跳。可是就在这时,天上打了个雷,把他从睡梦里惊醒过来。
“刚才什么响声?”他惺惺忪忪地问。
对面床上的郎贵,一直在用手机上网同老婆聊天,回答说:“可能是成贵铁路加夜班修隧道放炮呗……”
天蒙蒙亮乌蒙便起床,满心怅惘地准备到崖头去俯瞰一下映山红的村庄。刚到半路,就见一个穿着大红滑雪衫的女人扑爬礼拜地爬上崖来,好像一只雪地火狐。
乌蒙还说这件滑雪衫怎么有点眼熟。是映山红。她身上这件滑雪衫是上星期他从网上给她买的。
乌蒙说:“大雪天一溜一滑的,你不走施工便道,倒爬岩走小路,滑且不说,你忘了你是恐高的?”
女人说:“急着上来看你嘛!昨夜我梦到你从那上面落下来!”
她指了指银白的塔吊。
“没事了!”她吁了口气,“你好好的!”
乌蒙说:“何必爬上来呢,打个电话不行?”
女人说:“不行,要亲自看一眼。”
突然她又不安起来,起眼将塔吊溜了一眼,说:“你,你还上去么?”
乌蒙说:“我不上去了。等雪化,安装组就要把它拆了。”
“唉……”女人遗憾地说,“我还没有上去过呢。”
她转头瞅了瞅缆桥。
“包括这桥……”
女人话音未落,乌蒙哎哟一声。急回头看时,原来路上结冰,乌蒙一不小心滑到路坎下,崴着了左脚。
女人看他神情,竟是伤得不轻。果然,站起来都有点吃力了。
女人急得不行,左瞟瞟,右瞧瞧,看有没有一根棍子可以拾来给乌蒙拄路,忽然望见那边崖头上的小木屋。
她背向乌蒙一弯腰道:“快!”
乌蒙呲牙咧嘴说:“干嘛……”
言犹未尽,女人反手将他一搂,就把他背了起来,一溜一滑踩着小碎步朝缆桥跑去。
乌蒙急了:“你去哪儿!”
女人躬起身,将他往上耸了一耸,说:“找医生!”
说着就上了桥。
乌蒙说:“你忘了,你恐高!”说罢要从她背上下来。
女人说:“你嫑扭!看你把桥都扭得摇了起来!”
桥果然在晃。
女人迟疑了,紧紧闭着眼睛,牙关咬得紧紧的。
乌蒙说:“快放我下来……”
女人用力把眼一睁,将腿一蹬,“噌噌噌”朝对岸走去。
哦不,女人几乎是一口气跑过缆桥。
总算是过来了!她转身望去,只见缆桥还在摇哩晃荡。
乌蒙说:“你呀!”
女人双颊喷红,大口喘气,“嘿嘿……嘿嘿”地笑了……
缆桥很快就拆了。
在河边洗衣裳的时候,映山红总会习惯地抬头往东朝上看。塔吊早也不在了,但她总能看到乌蒙坐在高高的驾驶室里,微笑着偷偷朝她看来。
桥上通车是2014年的最后一天。从断桥这儿往上看,建成的西溪特大高速路桥像一张长长的板凳架在大峡谷上。“板凳”这是烂路毙说的。映山红说叫 “天桥”。阿龙说叫 “天路”。差不多寨里的人都到河边小广场上来看桥上车子过。烂路毙一辆一辆地数着:“一架,两架……”数到一百多辆,说:“数不起喽!”两手笼进袖子家去。映山红叫住他:“肚皮里的酒虫在爬了吧!阿龙,和你光棍伯去家里,把你乌叔叔喝剩在碗柜里的那半瓶酒拿给光棍伯喝!”
工程队离开大方的头一天,郎贵领着机械组人员在 “映山红农家乐”包了两桌河鱼火锅,吃掉女人给他们点的两大锅菊花豆腐。听说这些男人又将转到别的工地,女人疯了似的和他们擂酒,穿着宁静穿的那一身火红彝家衣服,唱着大方彝家的敬酒歌:
阿表哥,端酒喝!阿表妹,端酒喝!
阿表哥,喜欢不喜欢也要喝!
阿表妹,喜欢不喜欢也要喝!
喜欢呢,也要喝!不喜欢,也要喝!
管你喜欢不喜欢,也要喝!
喝得倒,也要喝,喝不倒,也要喝!
管你喝倒喝不倒,也要喝——
‘直夺’(彝语:喝)!直夺直夺!
乌蒙当场醉倒。郎贵对他说:“你走不动了,就在 ‘阿表妹’家歇了……”
乌蒙说:“不,不……我是什么……天上浮云水……里……飘萍!”
女人送他们出来。雪染断桥,泪洒西溪。
乌蒙步履维艰,步步回头,一个人落在后面,声音嘶哑的唱什么:
夜半三更盼天明,
寒冬腊月盼春风,
若要盼得红军来,
岭上开满映山红……
突然,女人的山歌飘了上来:
大方姑娘一朵花!
可惜生在山旮旯。
百里杜鹃无人见,
支嘎阿鲁无人夸。
西溪白岩对白岩,
一座长桥架上来。
高速公路寨头过,
贵阳赶场卖蒜薹。
贵贵阳来贵贵阳!
你是山中老雀王!
枉自你的声音大,
喊不回来修路郎!
修路哥来修路哥,
你要赶快把亲说!
年轻本是山间水,
一去大海无着落。
大路长来大路宽!
一头挂在姐心间!
要走你就对直走!
对直走到天边边!
郑吉平 男,白族,贵州省毕节试验区大方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2015年7至8月在鲁迅文学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