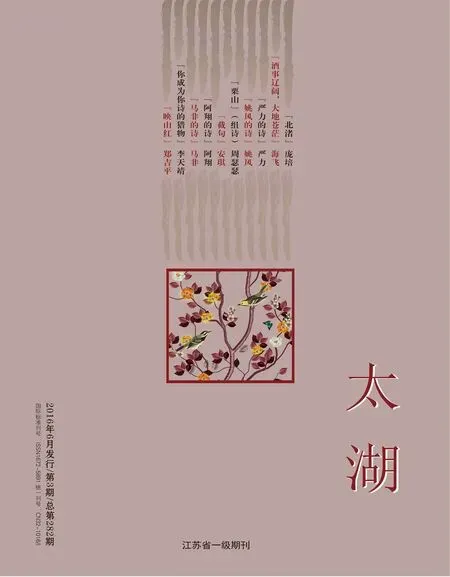高邮不止有咸蛋
张新
高邮不止有咸蛋
张新
高邮咸蛋之出名,以至于对许多上海人而言,高邮即是咸蛋,咸蛋亦是高邮。在 “民以食为天”的国度里,高邮虽以咸蛋而闻名,却也被咸蛋所遮蔽。对高邮人来说,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著名的现代高邮籍作家汪曾祺对此既郁闷又无奈,说:“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端午的鸭蛋》)
确实如此。一个秦观,一句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就该使高邮名扬天下!然而汪曾祺先生也不用气馁,高邮咸蛋之所以能扬名天下,必有与高邮的某些基础性元素有关,而这些基础性元素又和产生秦观这些文化精神互为因果。因此,这次去高邮虽然确实怀揣着 “带些高邮咸蛋回家”的心思,不过着实也更想了解高邮咸蛋之所以闻名的理由以及寻觅一些高邮咸蛋之外的东西。
高邮咸蛋产于何时,已不可考。宋代诗人曾幾在歌咏苏轼和秦观等在高邮把酒论诗的《文游台》诗中写道:“忆昔坡仙此地游,一时人物尽风流,香莼紫蟹供杯酌,彩笔银钩人唱酬。”显然,那时诗人 “唱酬”的酒席上是没有高邮咸蛋的,不过却也有产于高邮广袤湖泊湿地的 “香莼紫蟹”。北宋高邮籍诗人秦观有描写自己家乡自然风光的诗:“吾乡如覆盂,地处扬楚脊,环以万顷湖,天粘四无壁”。有高邮这“万顷湖”在,高邮咸蛋也是迟早会问世的大概率事件。高邮咸蛋晚至清代即已闻名天下。清代作家钱塘 (今杭州)人袁枚在 《随园食单·小菜单》“腌蛋”条目里,就夸 “腌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红而油多”。描述中的 “腌蛋”已与当下的高邮咸蛋几无差别。
高邮咸蛋能够传承至今,得益于高邮湖所赐。当旅游车在大运河和高邮湖之间的道路上驶过的时候,远远地望去,高邮湖轻波涟漪,水天一色,确实是产高邮鸭蛋之麻鸭的好地方。因此,要吃到上品的高邮咸蛋,背后是一条完整的生态链。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培育一方特产。从袁枚到我辈,数代人享用着美味的高邮咸蛋,这不能不感恩于高邮湖的惠赐和代代高邮人对生态环境的执着呵护。
高邮人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与高邮的历史文化传承有密切关系。秦时在此筑高台设邮驿,是高邮发轫之源,至今驿站尚存。之后,又得隋开大运河之利,高邮有了发展的后劲。邮驿与运河,既是国运之根本,又是经济之手段。生态与经济相得益彰,人文与民生共生俱荣,演绎着可持续的高邮城镇化发展历史。这一点,在当初拓展大运河与保护镇国寺的关系处理上,凸显高邮人的聪明睿智,堪称经典。
1956年,在原京杭大运河拓宽方案中,位于运河畔的这座内有始建于唐代僖宗年间的古塔 (俗称南方大雁塔)的镇国寺本在拆迁之列,后经反复研究评估,并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想出了一个拓宽运河与保护古寺两全其美的 “让道保塔”方案,即在塔四周填土筑堤,形成运河中的一个小岛,从而呈现一塔高耸,双水分流之势。另外,以一座古朴、典雅的廊桥接通小岛,同时又与镇国寺构成浑然一体的自然人文景观。
我倚靠在廊桥的长椅上,微风拂面,船笛低鸣;廊柱间:古寺映照,河水拍岸,杨柳柔,芦苇轻,一派宁静祥和的气氛。心里顿时冒出现代诗人卞之琳 《断章》里的诗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近年来,高邮湖沿岸又相继因地制宜地开辟了一些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既保护了环境,又吸引了游客。当然高邮湖麻鸭也高兴。麻鸭高兴了,“舌尖上的中国”就少不了高邮咸蛋的一席之地。
渐渐地,回归自然成为城市人的新时尚的时候,人们在冲着高邮咸蛋去高邮的同时,也开始把兴趣投向高邮的湿地公园。于是,每年菜花黄的季节,迎来了高邮的旅游旺季。而诸如秦邮驿、镇国寺、文游台等,只是捎带的景点。导游跟我们说:“这个季节一过,整个一年几乎是没有人来的。所以,当我听说现在这个时候还有上海旅游团来,而且是特地来看这些人文景点的,我大吃一惊。”她的话不久得到了验证。因为我们马上发现,在许多地方寺院的门票已经动辄百元的时候,煌煌若镇国寺竟然是免费的。即便如此,寺内还是稀稀然少人迹。我们在庆幸之余,不免为这人杰地灵之地被忽略、冷落至此而唏嘘不已。还有,我们要去的清代著名乾嘉学派文字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故居纪念馆,竟然连当地导游也迷了路。她连连抱歉说:“对不起,因为很少带队来参观,所以忘了路。”也难怪,又有多少人在高邮咸蛋之外还知道这些历史文化胜地呢?
临走时,导游对我们说:“回去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回答说:“这是一定的。”其实这也是我们参观后的心里话。然而,此时,我心头却忽然泛起一丝喜忧参半的莫名心绪。喜的是,高邮真的不止有咸蛋,一定会有更多人了解这一点。忧的是,将来的高邮,在强劲的城镇化的发展潮流中,还能容得住农耕文明的残痕余迹吗?这个担心不是多余的。听系里陈允吉先生说过,他现在回无锡老家,一路上已经看不到多少农田与绿地了。我有同感,上海松江过去属于远郊,是著名的鱼米之乡。高中时坐长途汽车去松江二中读书,一过漕河泾,满眼农田连片,江河织网,一派秀丽的农村风光。现在回母校,在地铁车厢里望出去,高楼断断续续连绵数十里,全然没有了曾经的面貌和气氛。据说,素有 “苏 (苏州府)松 (松江府)财赋半天下”之称的江南,如今多半大米反要靠东北、苏北等外省引进。这次去高邮的途上,不仅苏南的情景如陈允吉先生所言,而且曾经是 “穷地方”的苏北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头。在高邮的地图上,高邮湖沿岸醒目地划出了不少 “开发区”。有朝一日,高邮湖会不会被污染?麻鸭将游往何处?高邮咸蛋会不会销声匿迹呢?此时,“让道保塔”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张新 复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出版有 《20世纪中国新诗史》、《戴望舒:一个边缘文化型诗人》、《新诗文化散论》等著作多部。在 《文汇报》等报刊杂志发表散文数十篇,担任多部电视专题片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