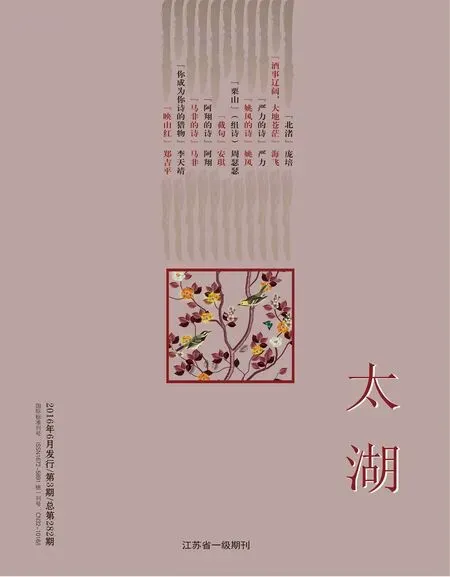倒退着回来的青春 (外二篇)
翠薇
倒退着回来的青春 (外二篇)
翠薇
这里有一丛丛的绿,一堆堆的绿,远远近近,漂浮的,隐约的,像绿的潭,绿的云,绿的缸,我走进其中,就被染绿了,仿佛我也是一掐一股水的花枝呢。
鸟在喊我们呢。
听见了。
花在叫我们呢。
听见了。
我与室友一问一答,每天我们都是被花香与鸟鸣唤醒。
济南南部山区,山东省第十六届中青年作家散文高研班,长清培训基地。山清水秀,春风摇曳,到处是一派盎然生机。青山绿水,鸟语花香,良田沃土。许多小草刚冒芽,刚开出淡淡的小花,像毛茸茸的小鸡仔。树上的叶子,是刚长出的新叶,嫩黄、纤细,在清风中微微浮动,如没有经历过风雨的顽皮少年。进大门的路两边是两排粗大的柿子树,走上山坡向左拐大约有三里路,路边全是长着小刺的花椒树。花还没有开,刚有米粒一样的花骨朵。采几枚花椒叶子下来,放在鼻下,就是浓浓的新鲜花椒的香气。一个同学告诉我,将花椒叶子洗净,剁碎,放了盐,刷在活好的面上,烙熟,就得到喷香的花椒饼。一开始一大群同学去散步,还不太熟悉,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同学叫王克。去年的时候,在中国林业局第二届美丽中国散文大赛中,我与他曾经同时都获得二等奖,今年在这里有缘相见。
接连七天,我们四十八位同学坐在同一个教室里,聆听九位老师谆谆教导。从一场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开始,第一天上课的李一鸣先生,他娓娓道来,深入浅出,从一朵花开,从一匹马的命运,讲到人文,讲作家怎样用心灵感悟世界。他精彩的讲述一气呵成,其回声至今在我们耳边绵绵不绝,连讲课时间都把握得恰到好处。接下来彭学明先生有理有据,用自己的一套理论,阐明散文写作的五种语言之美。张莉女士教我们怎么摆脱平庸,找出不合众嚣,独具我见,属于自己的那一座宝藏。耿立先生告诉我们,散文的精神就是人的精神质地,取决于个人的内在纹理与品格,异质化才是散文的出路……
我们这一群,上课时,都完全张开耳朵,瞪大眼睛,不肯错过老师讲的任何一个字,做笔记,求老师解惑、答疑。这是一次珍贵的学习机会,更像一个约定,一种机缘。这个高研班,给了我们一个远方,一种怀念,一个铭记。给了我们飞翔的翅膀,给我们加速、加油,给我们每人配了一副 “望远镜”、“显微镜”。
课余时间,看见张世勤院长与几位同学聊天。他说做学问,要像一个木桩子,结结实实地楔到那里,不断地矫正自己,打实基础。一听课,就有了很大的决心,想着按老师教的方法写。过了一段时间,又放松了,还是恢复自己之前的写法,那不行,还是得不到提高……围在他身边的同学都频频点头称是。
拿出我的那本小诗集送给他,并说,这本书一出来,我就不满意了,在这里听这些天的课,更是不满意了。但我还是想送给您,请您指点一二。
张院长说,不满意这就对了,是有了收获,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来,聚到一起,是来寻找同类的。”
“撕开你身上的壳,无障碍写作。”
“我喜欢刘亮程的散文,我就反复地看,反复地看,也要写出一个地方,一个地域的哲学。”
下午的小组讨论会上,大家都非常真诚,敞开心扉,说自己的经验、困惑,相互解答问题,相互珍惜,相互照亮,相互握手,一副相见恨晚的样子,场面热烈而亲切。
饭后大家上山散步。槐花将开未开,有微微的小骨朵。趁着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我们摆好多姿势合影。有资深摄影爱好者,教我们摆姿势,站在一排柏树的后边,把身子藏起来,只露出头。这样照出来的人影极可爱、风趣。有一位姐姐,一开始不知道叫什么,后来知道了,是武城的赵艳红,穿一身白衣,直接坐到公路的中间,双手合十,一张精彩玉照瞬间出炉。山间盘旋而上的碎石路,树上缠绕的藤萝,看不见影子但听得见鸣叫的各种鸟,都在侧目看着我们。
那些槐花,见我们来了,不几天,就开得耀眼、灿烂,花枝颤抖,用香气簇拥我们,缠绕我们,缭绕我们。因我们的到来,它们似乎更加浓烈,加剧对我们的吸引。我们要被花香淹没了,淹到嗓子眼了。一吸鼻子,就是一股一股的香,进了我们的口、胃、肺、心。简直我的全身鼓荡的都是花香,头发里,衣褶里,都被槐花香浸透,只要我一吸气,进入我身体的就是香气。我就是一个盛满花香的容器,我觉得我是一尊透明的青花,能看得见花香的涌动,像有无数的槐花在我身体里荡漾、鼓胀、新鲜。
顺着林荫大道,去西南方向,有一片山楂树林。总有一些同学朝着山楂树的方向走去,一路上说说笑笑,来到山楂树身边,在石阶上,在秋千上。聚在那里,偎着它,倚着它,靠着它,说着话,唱着歌,把我们的欢喜心留下,留在这个世外桃源。满树五个瓣的山楂花把自己开到一百八十度,它细小的蕊在风中轻轻摇动,为我们鼓掌。我们是一阵俏丽的春风,花枝招展,滑过山坡,开在山间,洒下一路芬芳,连山楂树对我们都羡慕嫉妒恨了。
有时我们也会漫步到西北角的六号四合院里。这里种着两棵柿子树,预示好事成双。一棵金银花树,叫做金银满箱。金银花,现在正开了满树的星星点点,纯洁无瑕,香气四溢,直袭心扉。我们在树下陶醉。树和我差不多高,我与它平视,如同我的一位老友,有一种让我肃然起敬的柔软,它展开着丝绸般一院子迤逦的香醇。在无数个夜里,夜空的黑丝绒缀满金色的别针,我们一群串门的客人在清澈的夜色里既访友又留恋着金银花细腻的芬芳。
初见同学,面孔陌生。有些名字是神交已久,只是今天才得以见到真神。就是那些不熟悉的名字,不熟悉的面孔,坐下来深聊,也都是一座山一般令人仰止。辞掉报社公职,一年出版好几本书,靠拿版税生活的八零后小伙盛文强;同样是八零后的江苏帅哥严正冬,其美文早就登上了高中课本;看起来非常纤弱的张佐香妹妹,已经是江苏当地的畅销书作家,就在我们分别的那一天,她又赶着到某学校去签名售书……
我们的遇见发生不少有趣的故事,夜晚攀爬千佛山;凌晨探望徐志摩;李玉梅带来一套精致的茶具,为我们沏上红茶,盘腿坐在床上讲她的 《糖三角》;与璎宁、彩霞、月新姐姐小亭子里吟诗弄月,池塘边惊起一片蛙鸣……我们来时,山路边的青杏还没有指甲盖大,我们走时,已经有鸽子蛋一样了。是我们的到来,让它们激动,更快地成长吗?它们是想用更完美的眼神,透过枝叶,天天看到我们飘过一段段山路么?
见过有一种黄叶子的树,是一种浅黄,透明的黄,像黄色的云堆积着,飘逸着,让人眼前一亮,望到它的第一眼,似乎天地瞬间明亮了许多。我一直不知道它叫什么树,问过别人,也说不知道。在这一片白马山的风景里,我又看见这种好看的植物,树上挂着牌子,我终于知道了,它叫金叶榆,就是金色叶子的榆树。仔细看看,叶子还真是榆树叶一样。对普通绿叶子的榆树我并不陌生,从前老家的房前屋后,院里院外到处都是,只是如今它摇身一变,每一片叶子都像一枚金箔、金币,变得大气而又明亮。
所有的离开都是为了重逢,所有的出发都是为了抵达。我们还是我们,我们也不是我们。从四月十五日以来,经过十四天精神洗礼的这一群,在春雨的浇灌里,都有了思想的拔节。在一场精神的契合中,悄然成长。如同那一片金叶榆,有了耀眼的光泽。
“上帝说:无论你遇见谁,他是你生命里该出现的人,都有原因,都有使命,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回家之后,当我看到一株槐树,一棵山楂,一片杏林,一丛金叶榆,一枚金银花,怎会忘,怎能忘!都会想到那些天的神采飞扬,倒退着回来的青春。
驾鹤逐青云
它们在黄河口湿地自由地漫步,它修长的身躯昂首前方。它优雅地踱步,像T台上的模特,迈动的不是猫步,而是它自己的仙鹤步。它的眼睛目不斜视,它的羽毛明亮丰满,有锦缎的光泽。它不紧不慢,从容淡定。一米六的体长,昂起头来,与我差不多高。它的腿细长,典雅、斯文,步态轻盈,有着贵族的风范。有两只鹤要跳舞了,莫非这是欢迎我的仪式?它们轻轻展开翅膀,抖动着,硕大无朋。它们向前踱步,转身,单脚独立,扬天长鸣,那骄傲的红顶愈发鲜艳。天地间霎时因它们洁白的翅羽,自身的坦然和从容明亮了许多。仙鹤尽可以在这里随意漫步,日行千里,夜行八百。
在电视上,报纸上,书本上,无数次看见过飞翔的丹顶鹤,长啸的丹顶鹤,松鹤延年的丹顶鹤,梅妻鹤子的丹顶鹤,龟鹤遐寿的丹顶鹤,一级朝服黄袍马褂上的丹顶鹤,在寺庙里被铸成铁质、铜质的丹顶鹤。当我今天第一眼看见鲜活生动的真实的丹顶鹤,它与我近在咫尺时,它们围在我周身跳舞、漫步时,我还是比从前更加被震撼了。
我与丹顶鹤面对面,眼神碰撞,产生出细微、玄妙的精神对流。
这是女神吧?这是绅士吧?我揉了揉眼睛,不愿意走开,此刻我变得贪婪了,痴迷了,它那种无视旁人的姿态,高傲得如同公主,直击我的心灵深处。直透到骨子里的大气、高贵,令我在她面前,出神地凝望,凝望着……我想把两个手指放到嘴唇上发出惊呼。
这上天的尤物!
她的周身洋溢着一个光环,浑圆的弧线,清晰的边界,自然天成的优雅与大气,玉树临风,雍容华贵的姿势与步态。我看任何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哪怕身价百倍,在她面前都是逊色的。
小时候看戏,但见戏台上,穿着绣有丹顶鹤样子长袍的,都是大官儿,他们高高在上,可以呼风唤雨。后来我知道了,他们都是一品文官,丹顶鹤样式的朝服,是仅次于皇家专用的龙凤标识,因而仙鹤也被称为 “一品鸟”。那五彩锦缎的朝服上,以黑色做底,绣有海浪、祥云,象征五福的蝙蝠,象征祥瑞的寿桃。一只展翅的丹顶鹤凌空高蹈,仰天长啸,看得我出神、入迷。古人尊崇仙鹤已久,在殷商时代的墓葬中,就有鹤的形象出现在雕塑中。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钟,鹤体造型的礼器就已出现,被奉为吉祥、尊贵和长寿的象征。
怪不得古有 “张道陵可骑鹤往来”的故事:黄老道学在东汉兴盛,有许多人推崇喜好黄老养生术,把黄帝、老子作为神仙祭祀。由道家发展成为道教,成立教团组织,创始人是1900多年前的张道陵 (公元34~156年)。他说太上道君将要降临,授他 “天师”称号,创立了五斗米道。他学道的地方就是鹤鸣山,这里还有待鹤轩、听鹤亭等建筑。道教著作 《云笈七签》中说张道陵可骑鹤往来。道教是修今生,认为人这个生命,经过修炼,灵魂和肉体可以升天,长生不死,从而达到神仙的境界,“与天地同休,与日月同寿”。在道观中供奉神仙的帐子上都绣着飞翔的鹤,名为 “云龙鹤幡”。而道教的高功法师礼拜时穿的法忏衣,道教的高功法师做法时穿的绛衣,也是绣有丹顶鹤。连道士作法时行走的姿态也与鹤步十分相似。这里有鹤鸣山,有待鹤轩,有听鹤亭,还可骑鹤往来,看来仙鹤在道教里是被无限尊崇的。传说,南极仙翁的坐骑也是一只丹顶鹤呢。
丹顶鹤的美貌与风度是大自然的造化,是上天的赐予。它是见过世面的国际公民,一年之中就要飞临好几个地区或国家。每年十月下旬,丹顶鹤从东北成群结队路过黄河口,飞往长江下游,到江苏盐城去越冬。来年的春节前,又集体长途跋涉,再次经过黄河口,飞往东北的扎龙、蒙古或者俄罗斯、日本等地区,去繁衍后代。年复一年,从不改变。黄河口湿地成为东北亚内陆环西太平洋鸟类的国际机场,它们以东营湿地为中转站,飞累了,就在这里休息、修养。
我看见有关丹顶鹤的标示牌上这样写着:丹顶鹤的繁殖地在中国东北平原的松嫩平原、三江平原以及俄罗斯的远东和日本等地,在中国南方沿海各地和长江中下游,以及朝鲜海湾、日本等地越冬,在云南也有少量野生种群。还有一块更可爱的标示牌:观赏鸟类百态,保护生态平衡。亲,离我远点,我的嘴很锋利噢!这个可爱的标示牌令我抿嘴一笑。
怪不得那个驯鹤世家出身的徐秀娟,十七岁开始在扎龙国家自然保护区跟随父母驯养丹顶鹤,爱鹤如命。大学毕业以后,还要到盐城鹤乡去,整天为鹤避暑、降温、驱蚊而忙碌。据说丹顶鹤有六七岁小孩的智商,能通人性,能听懂饲养员的语言。与仙鹤一起生活的人,相信也会沾染仙鹤优雅的气质,洁白的品性吧。徐秀娟视丹顶鹤的生命如自己的生命,当她喂养的那只叫 “黎明”的丹顶鹤走失之后,她豁出自己的性命去寻找。最终,“黎明”回家了,而徐秀娟却没有回来。最终,她永远住在了保护区的滩涂上,一直会看到闲云野鹤。鹤鸣九皋,而她也成了一只云中白鹤了。
我带着敬意,带着感动,一遍遍聆听着朱哲琴演唱的 《丹顶鹤的故事》,旋律在我周身起伏、飘逸,如同有鹤在我身边起舞翩翩。从心底里飞出来丹顶鹤,起舞翩翩。
怪不得唐代诗人孙昌胤,将仙鹤描述得这么傲群:“灵鹤产绝境,昂昂无与俦,群飞沧海曙,一叫云山秋。”仙鹤成长于极远的地方,气宇轩昂的样子无与伦比,它们成群结队地飞翔,迎来了沧海日出,一声高亢的鸣叫,给云雾缭绕的高山增添了无限秋色。
怪不得宋朝的林逋就是成语 “梅妻鹤子”的出处。宋朝临安有个诗人名叫林逋,字和靖,以学识渊博闻名于世,但他不慕名利,不愿为官,在西湖旁的小孤山盖了几间茅屋,常年足不出户,隐居起来。林逋一生有三个爱好:诗、梅花与鹤。因此他在房前屋后,遍植梅树,待到腊梅开放之时,阵阵花香,沁人心脾。在他的家里,养了两只白鹤,他常常把白鹤放出去,任它们在云霄间翻腾盘旋,林逋就坐在屋前仰头欣赏。读梅、望鹤、做诗,就是林逋的全部生活。他无妻无子,以种梅养鹤以自娱,人称其 “梅妻鹤子”。
从网上见过范曾先生的一幅 《梅妻鹤子图》,题款:林和靖鹤子梅妻图。林和靖左边是鹤,鹤首低垂,如羞涩的小儿。右边是梅,梅枝亲切,扶着他的肩膀。林和靖穿曳地红袍,带白色方巾,神态安详自若。白鹤有灵,红梅传情,他们都是幡然陶醉的样子,俨然一家人一样亲密呢。
在遥远的宋朝,诗人就能过梅妻鹤子,超然物外,恬淡而知足的日子,实在是心胸辽阔,一种精神生活的实现与重生,令今人望尘莫及。与自然和谐共处,让自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吸引,是每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目的地。驾鹤逐青云,骑鹤下扬州,也许不只是一个梦幻!
初到东营看大海
我纱巾的形状,裙子的形状,就是大海的形状。
大海想把我吹起来,吹动我的衣衫、纱巾,让我变成飞扬的样子。大海已吹动我的心,到海面上飘飞啦!
本来我与我的老师、同学们坐在客车里,四月天气,一车的人,车上已是极为闷热了。而一路驶来,到了海边,刚打开车门,咸腥的海风就甩了过来,呛得我们一个个打趔趄。一股凉风也随之而来,带队的陈主席嘱咐大家多穿件衣服再下车。心急的人,看见了大海,哪还听得进有人说话!都等不及了,都一骨碌地往车下边挤,都想着尽快地去亲近大海。敏感的人都打了喷嚏,聪明的赶快穿了外套下车,胆大的根本不怕,穿着短袖照样说不冷。西藏来的,宁夏来的同学,都惊喜坏了。对于平常很少看见大海的人,是多么兴奋和新鲜啊!
宁夏姑娘王黎明,她站在海边,高呼着,不停地挥舞着红纱巾,一会儿围在脖子上,一会儿披在肩上,一会儿舞在空中,她想用她的红纱巾,把海风兜起来,把海浪提起来,她想用她的红纱巾,做一叶扁舟,而她就是那个凌波而过的仙子;同是宁夏来的彦妮同学,就冷静得多了,他使劲瞅着大海,盯着大海,那蓝黑的海水,那深不可测的浑厚,那没有边界线的荡漾和咆哮啊!他想着,这么多的蓝墨水啊,如果都能吸进我的笔管里多好,都便变成我激荡、昂扬的文字有多好!那个宁夏来的鸽子,不停地拍照,摆着各种姿势拍照。她都站到大海的边缘了,海风灌进她的耳朵里、眉眼里,她仍然不怕,她甚至想掬一捧海水,沾一身大海的咸腥,她大声叫喊着,与波浪的声音伴奏!
席卷而来的蓝黑的波浪,到堤岸边上甩出洁白的浪花与泡沫,浑厚的,高傲的,一遍遍地摔着,不停止,甚至不因为我们的到来减慢一点速度。“海上涛头一线来,楼前指顾雪成堆。”我的心情咋与当年苏轼在望海楼的心情一样呢?!那边是谁,吟出了曹操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大海咆哮、起伏,有韵律地一刻不停地向前簇拥,一排浪头接一排浪头,开出硕大的花朵。我一直好奇,海水为什么是咸的,万能的度娘这样告诉我:科学家认为,地球在漫长的地质时期,刚开始形成的地表水 (包括海水)都是淡水。后来由于水流冲刷侵蚀了地表岩石,岩石中的盐分不断地溶于水中。这些水流又不断地汇成大河奔腾入海,使大海成了盐类的最后归宿。随着水分不断蒸发,盐分逐渐沉积,天长日久,盐类越积越多,于是海水就变成咸的了。风从海面刮来,冷从海面伸展。站在陆地与大海之间,似乎,陆地这边是艳阳高照,而大海那边是天低云厚一样。
海堤上,围着一群人,是有人收购了刚刚打捞上岸的海产品。地上摆着几个大盆,有两个装着牡蛎、海红、嘎啦、蛏子、花蛤、海螺、扇贝等等,还有几只海马呢,色彩斑斓的。这些新鲜的海物一动不动,在大盆里装醉。另两个大盆里有各种各样的鱼,鲈鱼、鲳鱼、石斑鱼,还有的像泥鳅,又细又长,也有的长成中华鲟的样子,我认识的就这几种了。船上下来的打鱼人,穿着棉袄呢,问及他们,说海上冷,在海上,像呆在冷库里。我们远远望去,深蓝的大海一望无际,蓝得发黑、发青。海水像疯狂的马匹,不停地奔腾向前。
我们也忘记了冷,忘记了凉,只顾着新鲜,顾着好奇,瞪大眼睛,尽可能地将大海留在眼底,留在心底。征得船主同意,我们相互扶着,跳到一艘渔船上去。船舷很高,以我们这些人,很少做体力劳动,柔弱的身体,爬进船舱,还真费了些力气呢。但我们不怕,我们到以海为家的船上去,到锈迹斑斑的船上去,到被海风、海浪无数次来回吞咽的船上去。铁锚,浮子,渔网,雨鞋,堆满了船舱后面的船舷。船舱里便是船员的家,锅碗瓢盆一应俱全,他们在船上吃、住,他们以船为家,以海为家,一年中只有过年的几天到陆上的家里去团圆、过年。平常打鱼,几天一个往返只是到达码头,卖掉捕捞所得,再往船上装些淡水,蔬菜,以及其他的供养。在船舱里,我看见贴着一张船员全家福的照片,心里涌过一股暖流。
这只船响起了马达声,船员又要出海了。我们翻过一摞摞铁锚,爬上岸去,我们向船主挥手致意,祝福他好运,盼望他满载而归。
大海的另一端有铁质的栈桥。我走上去,有些紧张,大海毫不理会我,它依然在我的脚下,透过栈桥的缝隙扑过来,毫不留情地拍打着石头,海水几乎要溅到我身上。海水裹着石头,缠着石头,石头上沉淀了海水的颜色,被海风、海浪、海水疯狂地噬咬,拥抱。锋利的海水一遍遍卷浪重来,条件反射一般,机械地进攻。
大海的灵魂是骚动的,有着动荡和不安。一些海蛎子非常不幸,被海风,被浪头推到大石头上,命都没有了,而它的外壳又被海浪巨大的力量牢牢地粘住,石头上白花花的一片,粘了一层又一层。我蹲下来使劲掰,都掰不下来,像是被最牢固的胶水粘上的,被最好的工匠镶上的。那些石头,现在已经不单单是石头了,像文物一样,像标本一样,展览着一个个海蛎子的空壳。
在海的另一边,有一排露出水面大约一米的石柱。再往前走几步,看见有大吊车过来,叼住横在海堤旁边的一根根石柱,摁进海里,楔进海里,钉进海里,吃进海里,每根柱子都有一根电线杆那么长。那些石柱,电线杆长的石柱,大部分都楔进了海里,露出水面的那一截,只是冰山一角,像是一棵树地下有更长的根。它与大海较着劲,纹丝不动,稳若泰山。像一个个卫士,起到守着海堤,护着油田的作用。
极目远眺,看不到海的边缘,海浪发出有节奏的韵律、声响,像是天地间有一位伟大的钢琴师,一直不停地弹奏、弹奏。两只海鸥在海天相连处隐约起伏,那是从海水里飞跃出来的两枚音符吧。
翠薇 本名崔会军,女,山东聊城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聊城市诗人协会副会长,东昌府区作协副主席。作品散见于 《诗选刊》、《诗歌月刊》等。出版诗集 《在内心,种植一盆兰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