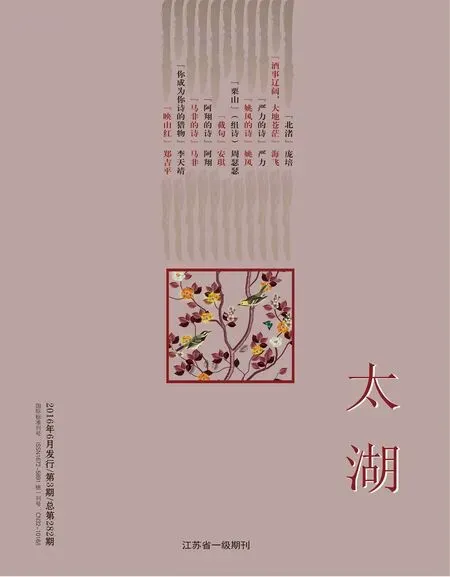年年戈壁不开花
彦妮
年年戈壁不开花
彦妮
1
老板把我们拉到一个荒凉的戈壁滩上,卸下工具,搭起帐篷,然后就开车回城里去了。好像我们五个人都是工程师,至少是开过三十年岩矿的老工人,他根本不用仔细斟酌,就完全可以等着我们给他挖出宝来。
事实上我们没有辜负老板的希望。一台风钻、几把铁镐,还有一辆天天要打气的小推车,就靠着这几样东西,我们硬是采出了质量不错的白云岩!
正是春天,戈壁滩上卷起一股一股狂风。原等着风小了再出工,却是一阵比一阵大,只好带上工具,极其无奈地打眼、放炮、选石、出渣……没有人督促我们,自己反而一天也不敢偷懒,生怕到时候老板回来,看见我们没有干出半点成绩而影响工资。
不到一个礼拜,戈壁滩便变成 “戈壁坑”了。没有人烟、荒草稀疏,几棵透着点暗绿的冬青树也被炸飞了。三三两两的山羊匆匆疾走着,像过客似的。距离我们十多里的地方,有一个小村庄,隐隐约约的,被一片浑黄的沙尘包围着,清晨出去遥望,有点海市蜃楼的感觉。
出门在外,原本不是来看风景的。在忍受了巨大的寂寞和繁重的劳动之后,看见送水的四轮车从远处一步一步地逼近,人的心里会忽然有一种感动。萝卜沾着泥土、土豆沾着泥土,望着这些 “山外来客”,鼻子忍不住地就有些酸:我们还没有被隔绝、我们还与外界有着联系啊!
司机说:“这地方一年只刮两场风,第一场从春天刮到夏天,第二场从秋天刮到冬天……”我们想笑,却没有一个人笑出声来。默默地捡拾柴禾、悄悄地淘米洗菜,只当风是家里的常客,来也随它去也随它。我们破坏了石头的宁静,却和风做了朋友。这戈壁也许沉睡了一万年,四周的沙漠和骑着毛驴背着水壶的牧羊老汉,曾经是这里飘渺的梦境,如今,是我们让它苏醒了。一顶破帐篷、一盏老油灯、一副残缺不全的扑克牌,使戈壁滩的黑夜变得长而又长。独自出门小解,踩着疙疙瘩瘩的石头,看远处村庄里的灯火和天上密密麻麻的星星,我觉得我们几个像幽灵一样,侵占了这块阔大的空间。
十几天以后,老板又来了一趟。他好像带着试探的心情,看着我们开出的矿坑,抚摸着乌蓝乌蓝的白云岩,眼睛不禁有点呆。他前后左右地丈量了一番,然后雄心勃勃地回去。很快,大量的设备拉上来了,大批的民工操着不同的口音,使我们孤单的帐篷无处下脚。“占山为王”的我们一下子成了老板手下的小沙弥,敲着木鱼、诵着长经、合着隆隆的炮声,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2
半年多时间,我们给老板挣了不少钱,而老板对我们却总像哄小孩一样,今天发一点,明天借一点,既不让你觉得无望,又不让你觉得跟他两清了,实实地要将你耗在这块荒凉之地。
时间长了,人心就有些涣散。
风过猛了,民工便躲在帐篷或 “地窝子”里不出来。他们或打牌,或下棋,吵成一团。尤其年少一点的,他们既无牌打,又无棋下,掰了几下手腕之后,面对阴暗脏乱的窝棚,竟有人想出了解决寂寞的办法。
打一壶凉水、搁两只碗,然后猜拳。输着饮,赢者乐。起先只有几个人,拳划得高兴了,其他的大人也加入了,他们放开嗓门,伸出拳头,样子像是要击碎一块石头,吆五喝六地闹腾起来。水喝多了,肚子很快胀了,人就多了心眼,说用碗喝水不公平,要用杯子,杯子有刻度。
便又换了杯子。
杯子就难耍赖皮了,一厘米一厘米标得很清楚,输者只好 “咕嘟咕嘟”地大灌一气,顺便往外撒出一些,以减少腹部的承受能力,那样子,简直比喝酒还要难受些。
在吵杂声中,《忏悔录》是我打发寂寞的最佳良药。要么独自去沙漠迎风狂歌,还可以边走边拾那些被风磨得又光又滑的小石子儿。它们或圆或扁、或红或紫,不知道在风雨的促成下,经历过怎样的爱情。另外,在我们炸过的石头坑内,还能捡到天然生成的 “石花”。石是蓝石、花是黑花,上面有山有水、有狮有人,还有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花朵;树或高或低、花或开或闭,样子逼真极了!
翻着一块块的石头,仔细盯着乌蓝色的石面上那些发黑发紫的纹路,忍不住浮想联翩。几万年前,这块荒凉的戈壁滩上,究竟经历过怎样的变化?
有人已经撑不住了,睁着眼睛耍赖,有人频频出去小解,侄子简直都快吐了,脸色发白、眼睛发直……
3
几片破纸箱、一条破麻袋,似乎已经成了工仔们的法宝,只要垫在地上铺上被褥,就可安顿他们疲惫的身体。连续数日啃干馒头,没有米饭吃,所以很多工仔的嘴唇都干裂了,笑也不敢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累得连衣服都不想洗,洗澡就更为奢侈了。浑身脏兮兮的,每日往返在工地与帐篷之间,像深山密林中的幽灵。
打眼放炮,装石修路,本应是我们分内的工作,而且一日八元的报酬,也使我们没了话说。但叫我们难以忍受难以预防的是,每日须要面对的 “黑羯羊”。它精力旺盛、躯体肥美,常洋洋于茅厕之内,洒洒于腐肉之上,加上一对漂亮的翅膀,总是招摇在我们的面前,令人难以招架!除了帐篷顶上黑压压的一层,厨房的墙壁上、锅台上、凉水缸沿上,到处都是“黑羯羊”的眠床。
如果单是这些地方听到久挥不去的嗡嗡声也就罢了,它还嫌我们饭菜单调,总是多情地浮游在我们的面条碗内,静卧在黄澄澄白花花的馒头里面,使我们可以最近距离地欣赏到它玲珑的躯体和优美的舞姿。
扶着钢钎、抡着大锤,在炮声隆隆中抢修公路,一面还要猝不及防地接待 “黑羯羊”的光临,时间一久,有的同伴就病倒了。我忘记了是哪一位工仔的 “灵感突发”,从而使苍蝇跟“黑羯羊”有了联系,但是当时当地,在我们一天天麻木与习惯之后,我们确实不再奇怪和惊诧,反而认为苍蝇的 “嗡嗡”之声简直就像我们最熟悉的那首 《久违的哥们》;“黑羯羊”的不期造访也使我们平淡如水的寂寞生活更有了别一种滋味。
时间慢慢地过去,我们的手上满是老茧和被石擦伤的痕迹。因为深山里没有小卖部,有人高价买得几瓶劣质白酒,他们喝着、跳着、唱着,像一群疯子在闹。他们扭动着僵硬的身体,挥舞着沾满泥沙的脏衣服,把帐篷内的苍蝇扰得四处乱舞轰鸣不止……看着他们,盯着无处不舞的苍蝇,我又一次觉得,这帮与石头为伍的同胞和那些长着四只脚的 “黑羯羊”,在唱同一首伤感的歌。
4
那时我还叫不出它的名字。它孤傲地立在沟底,树冠如云,密密匝匝,树干遒劲伟岸,一人难以合抱,树皮粗糙坚硬,宛如岩石的棱角。
那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周围是茫茫的沙丘,沟里卵石堆集、枯枝交叠,静寂得可以听到树皮爆裂的声音。如果不是炸矿石,谁也不会想到,我们的乡邻会是一棵沉默不语的树。可能此树已经在此孤寂了百年,当我们冒冒失失摆开家什放炮的时候,树上的喜鹊忽然四散奔逃,以为末日来临。
后来遇见牧民,无意中问起那棵树,他有些轻蔑地说:“胡杨都不知道?活着千年不倒,倒下千年不朽啊!”
真是惭愧!就知道扛着钢钎和大锤,整天挖山不止,连这么有名的树种也不识。可话又说回来,认识它又能怎样?认识它就不再钻这深山老林了?狂风卷地、沙尘蔽日,我们的头上满是沙子。可能是我们惊扰了胡杨的梦,也可能是飞起的石子打在了胡杨身体的某个部位,在慌兮兮忙兮兮的 “战斗”间隙,我分明看清胡杨低着头,在微微颤栗。
尽管有时眼睛都睁不开,但我们还是不能停下来。我们十几个人就像收了老板的订金,必须在短时间内将矿石挑出来,然后用蹦蹦车拉出去,再用大锤将其整成拳头大小的碎块,一分钟也不敢耽搁。
一个月以后,原有的山头被我们变成了矿坑,那些比较平整的地方,堆满了灰白色的矿石。大卡车一辆接一辆开来,啤酒瓶、饮料瓶、方便食品袋开始出现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们给这个叫不出名字的地方聚集了人气,却破坏了自然的静谧。想家的夜晚,月亮是这里最璀璨的灯火。地窝子里那盘几至看不清字的象棋只够两个人对弈,余者只能点一堆小火,在繁密的星空下,大家围成一圈,说说闲话、看看月亮,或者敲着破脸盆,吼几嗓子。天地空旷,我们的声音毫无阻拦地传到极为遥远的地方,就连那棵孤独的胡杨,也在淡淡的月光下,听到了我们离家打工的愁肠。
我们记着老板的承诺,也渴望能凭自身的苦力换取糊口的酬劳,但是,在一车车矿石被拉走之后,我们听到的却是拖延和扯皮的敷衍之词。脚上的鞋子已经换了两双,身上的衣服也大多磨破了,我们在土豆和白菜的滋养中,神经在一天天麻木,斗志在一天天消弱……
有人也嚷嚷,但大多选择了叹息,这些长年在外谋生的同胞,他们似乎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常常露出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我矛盾、犹疑,不知是进还是退。有时去山头努力地远眺,有时在沙漠里寻找新的足印,更多的时候,我还是愿意去沟底,一个人抚摸着胡杨粗裂的树皮,问它春天还有多远?
天愈来愈冷了,而我们的工薪却愈来愈渺茫。看见胡杨还是一如既往不卑不亢地在沟底迎着风,它挂着秋天尚未落尽的黄叶,似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5
刘亮程说:“我没有天堂,只有故土。”
于是我决定离开。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走。我的足迹被这里的狂风吹得一干二净。仰望高天,轻抚石头,我觉得这里有过非常坚硬的东西在我的心上划过。原想用自己的勤劳和诚恳感化这片处女地的,但是老板的推三阻四与言而无信的承诺,使我看清了工仔们将收获什么。
一纸箱 “石花”,是我惟一的安慰,我真的想把它们带回去。可是因为赶车,我几至连行李都扔掉了,哪里还顾得上它们?我急慌慌、忙兮兮,像个阿富汗难民一样,逃也似的抓住车帮,一边跑一边喊,就是跳不上车去。风把我的头发吹起来,沙子见缝插针地钻进我的衣领,他们留恋我似的,把沙漠的祝福悄悄装进我瘪瘪的口袋。
扬一扬手,看大漠一点一点在我的视野消失,那一刻,眼里忽然滚出几滴东西,令人禁不住打一个寒噤……
6
回家一个多月,忽然来了电话。
说侄子被石砸伤,生命难以自保!
这样的消息!
我们连夜赶到了医院。在抢救室里,侄子躺在病床上,缠满绷带,双眼紧闭。他们说,病人已经休克20多小时,严重缺血,左腿要马上截肢,右腿粉碎性骨折,腰椎已分裂错位……
输血、输液、打针、清洗,人总算没有生命危险了,但医生的一句 “病人也许就永远这样躺在床上了”的话,令我们在场的所有亲人心碎胆寒!才20岁不到的人,高位截瘫,全身三分之二的部位没有知觉,一把屎一把尿的日子,会是如何的滋味?
在床上躺了一年,侄子终究没有抗过石头,在阳光下数过院子里的每一片梨树叶子之后,终于在大家都不在他身边的某个夜里,顽强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故乡的山上没有石头,侄子的坟地选在一块麦地的边上,秋天的黄土潮润而深情,它将一副残缺不全的躯体埋了进去,没有鲜花,没有追悼会,只有一把黄土,把侄子短暂的一生悄悄做了总结。
坟丘上长了一片绿色的苦子蔓,苦子蔓没有开花。也许这些美丽的花朵没有来得及孕育,就让寒霜变成了死胎。
老板又一次没有兑现他的诺言。
为了要钱,我无数次地去过内蒙。戈壁滩上没有我的足迹,只有侄子的血液沾满那里的每一块石头,它们在高温下迅速异化,使那片只有冬青树的荒凉之地,开满了花朵。没有带走的 “石花”更是一个奇迹,上面鬼斧神凿的山峦和树木,统统变成血一样的赤红,它们刺眼地散布于戈壁滩的每一个角落,使那里的每一声鸟鸣,都变得嘶哑和惊心!
我再也不需要什么 “石花”点缀我的日子,那些沾满鲜血的东西灼痛了我的双眼,我感觉我活得有些矫情,矫情得有些伤感。
在无边的夕阳下,我看见一大堆一大堆的石头,被我的同胞装上卡车,他们擦着汗水,说着土话,把最有限的青春奉献给了这片不能说话的戈壁滩。石头拉到城里,在冶炼厂变成了贵重的金属,侄子埋进土里,最终不知能变成什么?令人起敬的是,这些在石头缝里寻找口粮的同胞,他们并没有因为一个青年的惨死而停止手里的活计。他们四平八稳的劳作和平静的神态,使我懂得了什么叫做 “坚强”。
是的!石头能开出花朵来,但那又怎么样呢?
彦妮 1967年11月生于宁夏海原县关桥乡。中国散文学会会员。1992年发表处女作,先后在 《青年文学》、《雨花》、《青年作家》、《朔方》、《黄河文学》、《北方作家》、《六盘山》等报刊发表散文小说约二百余篇,部分作品被《散文选刊》、《散文百家》、《意林》选载。出版长篇小说 《出息》。散文曾获宁夏文学艺术作品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宁夏首届朔方文学奖、孙犁散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