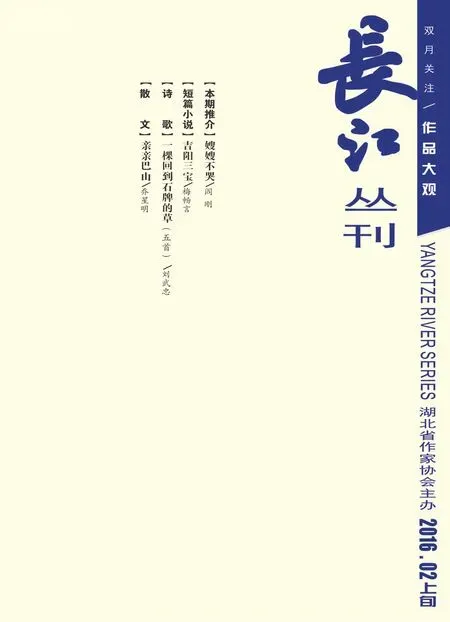怀念母亲
佳 玉
怀念母亲
佳 玉
一
公元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二日(农历九月十五)十六时二十分,患病9年的母亲停止了呼吸,溘然长逝,母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几个月来每当我看到电视上那些母子亲情、母子离别等画面时,我泪水充盈着眼眶,心酸痛酸痛的,打开电脑相册看着母亲的照片与她对话,母亲啊,女儿想念您……
我的母亲叫郑福秀,有着辛酸、苦难的一生。经历幼年丧父丧母,11岁那年被送童养媳来到我爸家,那个年代我爸家里也穷,爸有六姊妹,加上母亲就是七个了,母亲从小到大都没有尝过什么是幸福,到我爸家后,小小的年纪承担起全家的洗衣做饭打猪草等活,冬天一双手全是张着大口小口,淌着鲜血,脚也是大脓疮小脓疮,走路一拐一拐的,夜晚睡觉刺骨的疼,没有地方倾吐,只有在黑夜中望着她那个娘家的方向偷偷地哭泣,泪都流干,娘家还有两个弟弟……母亲当时的生活可想而知是多么艰辛,就这样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中忍辱负重,我的母亲长大成人了。其实并不是说爷爷奶奶不好,而是当时的环境就是这样,有些事都是不得已。之后母亲就和我爸结了婚,便有了我们这个家,母亲生下了我们这五个孩子,在我们儿时成长过程的背后不知流了多少母亲的泪水和汗水,不知道让母亲历尽了多少艰辛和困苦。然而年幼无知的我们哪里会知道如何去报答。
然而母亲是一个不会被命运主宰,有自己主见的人,虽然她是个文盲。就在解放前的1948年底,母亲就让爸来到了邻县湖北公安县郑公渡镇上,一个人来闯天下,爸是一个奇才,手感特好,什么东西在他手上掂量一下,就知道多重,与秤一样,神奇得很,爸对数字也特敏感,没有上过一天学,按照现在的说法,他是自学成才,到郑公渡一年后当上了郑公粮管所的会计。母亲也来到了郑公渡,母亲说,可算跳出了那个大家。因为爸是老幺,哥、姐妹6个,爸从不管家务事,母亲基本上挑起了那个大家的重担,在当时,母亲很辛苦,很劳累,因为大伯,姑姑们都不愿做家务活,爷爷奶奶把他们看得比较娇,觉得我妈是该做的,特别可恨的是我四姑、幺姑,不做事不说,还经常为难我母亲,自己在外面弄丢了衣服什么的,强加于我母亲,说是我母亲故意把衣服丢在河里或者偷了给娘家。大伯,他身上长疮、长疱,他却说我母亲不讲卫生,衣服没有给他洗干净,骂我母亲,邋遢女人,我可怜的童养媳母亲,您真的不知受了多少苦……
母亲一生很平凡,虽没有做过什么大事,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业绩,但她有远见。解放的时候老家分田分地,我爸想回去,但我母亲阻止了爸的行动。如果回了老家,如今我们后代全都在农村的几亩地讨生活,不会是现在这样。当然她不回去也是因为她害怕爸的那个大家庭,让她受尽欺负。就这样,解放后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回家分田分地后没几年就把田入了合作社,农民越来越苦,越来越穷,面朝黄土背朝天,没有了城里人的任何优越。后来在自然灾害的三年里,也就是当时的大跃进,连年饥荒,家家户户都没饭吃,当时很多城里人往农村跑。我母亲老家的亲戚也接我们搬回老家湖南乡下,回去可以分大瓦房,房子后面还有一片大竹林、菜园,我母亲一口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宁愿多吃苦,不愿带孩子又回到她所跳出的那个地方。我们佩服母亲的伟大决定,也可以说决定了我们的一生命运。
为了能让我们吃饱肚子,度过饥荒,她天天没日没夜帮别人洗衣、拖板车、轧棉花包、补麻袋、洗油布,在镇郊农村帮别人薅草、捡棉花等等。勤扒苦做的母亲把正式工辞了(粮管所职工),去打几分零工。为了让她的子女们能上学读书,生活能过好一点点,每天都是起早贪黑拼命的做事。当时父亲在离家较远的粮管所上班,家里的一切基本交给了母亲,用现在的流行语,母亲是一个女强人,把家里里外外都管理得井井有条。母亲含辛茹苦养育大我们,多少年来,为了我们,母亲在这个家里流尽了她的汗与泪。
可是就在儿女们都长大成人时,中年丧夫,她五十岁守寡,父亲去世时,我和弟弟还在读书,家庭的重担一下子落在了我单薄母亲的身上,坚强的母亲拼命的打零工挣钱,供我弟读书。老年丧子,我大哥因病住院遭误诊,惨死在医院。可这一切母亲都默默承受了下来。
从我记事起,一年到头,母亲总是忙忙碌碌,白天出去打零工做事,在外面劳累一天后,晚上回家总有理不完、做不尽的家务事。春夏秋冬,深夜一觉醒来总有母亲勤劳的身影。儿时的我常常是在母亲不熄的、温馨的灯光中入睡,又总是在母亲明亮的灯光中醒来。母亲非常关心我们几姊妹的的学习。那时家乡小镇没有电灯,就是煤油灯里的油也要凭票供应,每月半斤煤油用不到10天,通常用松脂和松节照明。做完作业,往往是黑鼻孔、花猫脸,学习的艰辛难以言状。母亲从不吝啬,只要有煤油,总是将煤油灯拿给我们做作业,母亲对我们说,只要你们好好学习,再穷,砸锅买铁、卖血我和你们父亲也要让你们读书,有文化好;母亲没有文化,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把她的希望全寄托在我们身上。
1970年响应党的号召,我们全家下放,母亲带着我、三哥、弟弟被下放到一个偏远的湖区农村(父亲在粮管所上班,大哥在北京卫戍区部队当兵,二哥知青下放到另一个地方),当时我只有9岁,到一个陌生的乡下开始新的生活,可想而知是多么的艰难,在镇上有房子、菜园、计划粮、油什么的,乡下什么都没有,可以说一无所有,白手起家。没有房子,我们租住在一个生产队二隔间的破房子里,开始了艰难的生活。让我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是:在我满10岁那天清早起来,提着一个长藤条篮子跑三、四十里地到镇上的房子后面菜园去摘豇豆、南瓜、冬瓜,然后提着满篮的菜向乡下下放的家里摇摇晃晃走去,肚子空空,饿得我东倒西歪,一路上自己给自己鼓劲、提神,嘴里唱着歌,自己跟自己说话,当时我感觉路好长好远,像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程来回近八十里),晚上9点才摸到家,母亲眼角淌着泪花说,幺姐(小名)今天是你10岁的生日呀,对不起你……。我朝母亲笑了笑说,我们有新鲜菜吃了。
能干的母亲像乡下人一样,扛着锄头开垦荒地(生产队给的一块山坡茅草地),不到一年把它变成了菜园,什么萝卜菜、韭菜、大包菜、土豆等,长势旺盛,一下子解决了家里吃菜的问题。母亲为人善良和蔼,与乡下的左邻右舍关系处理得非常好,还攀上了几个亲戚,与他们建立了深厚感情……
母亲的一生多灾多难,但总是化险为夷。最让我难忘的一件事是,发生在我们下放期间,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本来我妈是到镇上照护我爸去的,我爸高血压犯了住院,爸住了几天就出院了,出院后的第二天准备回到下放的农村家休息,晚上住大婶娘家,热情的大婶娘一家招待了我爸、母亲,母亲晚饭时吃了一个烧烤的红薯,半夜时上吐下泻,折腾几个小时,人已虚脱,发起高烧,爸说可能是食物中毒了,赶快去医院,母亲说不去,等一会就会好的。其实我母亲是想节约几个钱。爸看母亲不行了,不管母亲的反对,坚持要把母亲送往镇上医院。在半路上母亲全身开始变凉,不省人事。到医院后进行抢救,医生给母亲输液打针打不进去了,母亲在生死线上徘徊挣扎。医生递给我爸一张“病危通知书”,那张薄薄的纸片,在我爸手里如千斤重,医生又对我爸说,她(母亲)瞳孔都放大了,你们准备后事去吧,食物中毒太厉害,送医院太迟。当时我爸我哥都惊惶失措,不知该怎么办,大声哭叫起来,我哥求医生救救我母亲……通过几个小时的抢救,母亲终于从死亡线上回来了,成为一个奇迹。母亲病好后,对我们说,有个阳无常跟她做工作要她过去——阴间,说那边很好,安排她去做什么工作。我母亲说不行,我的几个孩子都还小,他们还需要我……母亲挣脱他们的拽拉,拼命往回跑,终于跑到了家里,慢慢苏醒过来,听到我爸我哥在他身旁的叫喊她。
当时母亲只有40多岁,我无法想像如果那一次母亲永远睡着了,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下去。从此以后我就特别依恋母亲,总想日日夜夜都呆在她的身边,担心有一天她会悄悄地抛下我们离我们而去。
全家下放的7年里,我们已融入到了乡下人不中,和当地的社员一样,天天出工,挣工分,到年底分红分粮……在下放的第二年就做起了三间大茅草房,养鸡,养猪,渐渐有了生气,把苦日子当甜日子过,还过得挺好。母亲非常勤劳,在那个生产大队里是出了名的。平时她除了干满队里的劳动日外,其他时间就积肥、砍柴、卖柴、养猪、养鸡,还带着我和弟去田间捡谷子、麦子、豌豆等等来补充家里。母亲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做一手好饭菜和针线活。当年沙市下放的知青、插队的工作组和蹲点人员,都非常喜欢到我们家吃母亲做的饭菜。母亲是个地道的会过日子的女能人,什么都不想落在别人的后面,非常好强。她就像一台永不停息的发动机,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她白天下地干活挣工分,晚上还不顾一天的劳累,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给我们缝补衣服、做布鞋。小时侯我们最盼望的就是过年,过年除了能吃上母亲为我们准备的一顿丰盛的饭菜外,还能穿上母亲平时为我们缝制的新衣服和新鞋子,还有父亲从镇上为我们带回的副食糕点糖果等,就凭这,在同伴面前能炫耀好一阵子,我们在母亲的呵护下好幸福啊!
二
我还记得上高一时。当时的学校离家较远,有五六十里,我住在学校里。那个年月,学校生活不仅伙食差,而且吃不饱,我也正吃长饭的15岁年龄,当时没菜都可以吃1斤半,勤劳的母亲白天做完农活,晚上请姑婆(我们乡下攀的一个亲戚)陪她走五六十里来学校看望我给我送菜,一路那崎岖的山路,要穿过松林乱坟岗,伸手不见五指,高一脚低一脚的(全是牛脚坑),还不时传来野兽的咬叫声。听当地老百姓传,那条路经常有鬼出来,特别是迷魂鬼。真正有人被“鬼”迷过,有三个背男人背着锹、箢箕、扁担赶到三线水利上去做事,晚上十点从家里出发第二天早又走回家里来,家里人呆了,怎么回事,他们三人你看我我看你,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在那个山上转了一圈……。还有坛子鬼、披头散发的吊死鬼什么的,荒凉得不得了,一般男人晚上不敢从那里经过,走在那个路上你会毛骨悚然……
我母亲和姑婆走到我学校已是凌晨四点,母亲看天没亮,只好呆呆的站在我寝室门前等了几个小时,我在睡梦中听到有人轻声叫我,睁开眼睛看,母亲,她把在家里给我炒好的萝卜干、辣椒酱、热腾腾绿豆饼等递给我,我还未反应过来,母亲她们已匆匆忙忙走了,赶回家去出工、下湖田打猪草。同学们都用一种羡慕的目光看着我,你的母亲真好,吃着母亲亲手做的饼和酱菜,我心里有一种对母亲的感激,母亲在我心里是天底下最好的母亲。
后来儿女大了,有了第三代,母亲又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为儿女下刀山蹈火海她都心甘情愿。
1976年大侄儿出生,母亲到沙市照看大侄儿,母亲到沙市不久,我就病了,那次可能是我这一辈子发烧最长的一次,半月高烧不退,扁桃体发炎,脓肿,当时头都不能抬、转,一抬就会倒地,不能吃喝,连稀饭都不能吃,我怕掉课,天天坚持上学,老师对我挺好,看我病得不轻,把我送到医院打针,几针下来还是不退烧,医生说必须要开刀,父母亲不在身边怎么开刀?爸在很远的乡镇粮管所、母亲在沙市,请人搭信告知我爸和母亲,当时他们听到信后魂都吓得不在身上,我母亲从沙市马不停蹄步行六十多里连夜赶到我学校。母亲看到我,心疼地说,孩子烧成这样,怎么不早说呀,搞得不好会烧起肺炎来,引起并发症,我们就你一个独姑娘……母亲连忙把我带到医院检查,要求医生保守医治,不开刀,母亲来到我身边感觉病一下子好多了,我真感觉到没妈的孩子像颗草,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记得小时候,夏天热,在屋子里无法入睡。那时候根本没有电扇,就连电灯都是时亮不亮的,大人为了孩子休息好,想尽一些办法,不让孩子们受苦,把屋场打扫干净洒一点水,把自家的大门下下来,作铺乘凉。蚊帐一罩,让我们睡在里面,母亲总是坐在我们身边为我们不停打扇、讲故事、数星星。我不知道别人的童年是怎样的,但我的童年是甜蜜幸福的。
记得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年,母亲非常高兴,用那一双生满老茧的手拼命的挣钱,在烈日下洗石灰、捶砖渣、撕布巾,一分一角一元积赞,用110元钱给我买了一块上海女式手表,在那个年代戴表的人很少很少,当时我的工资只有18元一个月,110元简直是天文数字,母亲该付出了多少血汗。当母亲把手表放在我手上时,我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像做梦,眼泪直往下淌,几天几夜都睡不着。那时起,我发誓一定要孝顺母亲,只要我有,母亲就有,母亲要什么我都会给她买,我后来条件好了给母亲买了各种电器如电视机、冰箱,吃的穿的基本是我负责,每年春节我都会给母亲买新衣新鞋,还带母亲到北京、庐山、武汉三镇等地游玩,给母亲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我母亲回到老家后,和她的一些老姐妹们在一块拉家常时很幸福得意的夸我是她的宝,炫耀自己玩了大城市,去了首都。
母亲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妇女,没有文化,也讲不出深奥的道理,但她具有勤劳、善良、忠厚、贤惠的美德,为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母亲她操劳一生本应坐享晚年,但她一生为子女,甘愿清贫节俭度一生,不愿让儿女多操心,提着篮子做点所谓的小生意,到县城的各个学校门口、街上卖瓜子、小食品和小玩具赚钱养活自己。请人做了一个小推车,推着小车满街跑,风里、雨里、黑夜的叫卖,一分一角的赚,她舍不得吃、穿,基本一天只吃一餐饭,把钱攒下好让她的儿女们春节到她处过一个丰盛的大年。每次回家,每当我看到她弯着腰,背上像背的一个枕头——驼背,推着小推车的背影,心里很不是个滋味,酸痛酸痛的。我和哥哥弟弟劝母亲不要做什么小生意了,我们不是不给您钱。但她将我们给的钱不是拒收就是存下不用,她对我们说,我能动就不麻烦你们,你们好好的工作我不愿当你们的累赘。我的老母亲永远是我们生活和做人的楷模。
在我三十六岁、三十七岁那两年,人生像过坎儿,膀子摔断,阑尾炎动手术,每次一个电话都是母亲从老家赶来对我细心照顾,帮我洗澡、洗衣、买菜做饭,忙这忙那,使我很快好了起来。母亲爱儿女是无私的,可以用生命来呵护你……
我记得1990年我调到武汉工作,当时母亲内心很复杂,她很想女儿留在她身边有个照应(我从小没有离开过她),但她更关心女儿的人生前途,还担心女儿到一个新的地方工作适不适应……在我要快离开的那几天,母亲整天坐立不安,打嗝,睡不着,我问她怎么了,为什么您晚上不睡呀?她说没事……她把对我的不舍和担忧深藏在心底,装出满脸的平静和幸福来回忙碌着。90年的春节正月初三,三哥用大卡车帮忙把我全部家俱搬到了武汉,天寒地冻,在我离开家乡的那天,母亲慌神了,好像我永远不回来一样。母亲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都做给我吃,还把她亲自制做的各种酱菜、腊肉、香肠、熏干子都要我带上,满满当当的一袋子,现在回想起来真是特别的幸福。
三
母亲是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一日高血压中风,三月十一日晚,我母亲做完小生意回到家跌倒在地,强忍疼痛爬啊爬,站不起来,母亲的哭声被邻居听见,忙去帮忙叫我二哥。等二哥来,开始以为是缺乏营养,根本没想到她是高血压中风,第二天把她送到县人民医院打抢救针,但已经晚了,虽生命无虞,但已半边身子活动有障碍。我赶回老家,做女儿的也非常愧疚,连母亲有高血压病都不知道,从来没有给她量过血压。几天后就出院了,出院后的用药是我给她从武汉买了送回去,叫她怎么吃。还给她买了拐杖,后来又给她买了轮椅。母亲一生要强,什么事都自己做,从不愿求人,她每天一拐一瘸的拄着拐杖自己上街买菜做饭,不小心摔了一跤,头在冰箱上磕了一个大包。刚好那天我大侄儿从深圳回老家去看奶奶,大侄儿看到奶奶睡在地上拼命爬,连忙抱起婆婆大哭。大侄儿与婆婆感情很深,大侄儿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到四岁都是我母亲带到身边照看的。这一摔,她的语言功能开始不畅了,说话有点结结巴巴,我强烈要求她不要“逞能”了,请一个人来照护她,我母亲非常犟,在中风后的三年都是自己照看自己,毕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后来又摔了一跤,大约是再次中风,这下彻底不能说话了,失语了。不能说话的她自己打自己脸,捶自己的腿,心里烦躁。看着母亲这样,心在滴血,善良的母亲,你的命运里怎么有这么多磨难……
中风的第二年,我把母亲搀扶到县照像馆给她照了几张照片以防万一,我给母亲化了一点淡妆,颈子还给她系了一个蓝花小丝巾、穿着影楼的蓝色西服,挺精神的,母亲自认为这张照片照得挺不错。从我到武汉,每年都接母亲来我家住上1月,年年如此。她中风后也一样。虽然她后来不能说话了,但她心里是很明白的,总是记着每年要去女儿家小住一段时间,她心里天天期盼我接她,在挂历上做上记号。看到母亲的这些举动,心里总是发酸。
每年不管我的工作有多忙,也从来没有间断过、耽误过回去看望母亲,每年5—6次,尽量给她买一点好吃的,安慰母亲,和母亲多说话,她不能说话了,我给她讲话,引导她发出声,与我说话,她艰难地发出咦咦的声音,我连忙表扬她,说我听懂了她的话,她也笑了……我给她洗头、剪发、洗澡、掏耳朵、倒尿盆,每次回去都把母亲推到街上转一圈,让她看看街景,晒晒太阳。在福利院的7年里,我每次回去陪母亲睡,睡在她身边,她摸着我的腿、脚用嘴亲,其实我的母亲心里有好多话好多话想对女儿说,没有办法,只是呆呆地望着我,眼角流出泪花。一个人失语是多么的痛苦,这时的我,心被针刺一样疼痛,常人说母子连心啊!记得以前她身体好时我逢假过节回家,母亲总会带着她那慈祥的笑容在门口迎接我,我的乖女儿回来了……
2010年10月20日,我在从山东出差回来的路上,接到二哥发给我短信:母亲病危。我的心一下子像掉到了大海深处、慌乱的直跳。母亲啊,你要挺住,一定要等我回来……我回到武汉家,放下出差的行李,便与老公一起坐上了开往家乡的班车。坐在车里,望着窗外快速后退的风景,听着高速公路上不时会车时的鸣笛声。顿时感觉到这种情景是多么的熟悉啊!我每年接母亲来武汉一次,从家乡到武汉每次来来回回在路上都能遇到的情景,虽然母亲不能说话,但她眼、耳朵非常灵敏,我不时地给她说话,告诉她现在到什么地方了,路两旁是什么植物等等,她笑着不时点头……唉,一切的一切,事情好像是昨天。
经过近4个小时的车程,终于到了母亲住的福利院,进屋里,看着母亲9年来被中风偏瘫病魔的折磨,现在已瘦得像古尸,像一棵枯萎的老树,躺在床上,深闭着眼睛,心脏一起一伏在微微跳动。我叫喊着母亲,她眼睛微微挪动,好像听到了我的叫声,我们在她身旁说话好像她都能听懂,不时地有反应。吃过晚饭,二哥、三哥说,他们俩在福利院晚上陪母亲,要大家回家休息,我只好听从安排和老公两人到宾馆休息,到宾馆后怎么也睡不着,躺在床上,静静的回想着母亲过去的一点一滴。这一夜,多少年来往事涌上了心头,多少次泪水打湿了枕头。我们几姊妹静静地守候在母亲身边度过了艰难的两天,22日上午我还在母亲耳边给她开玩笑说话,请她坐起来吃饭,把身体养好后到武汉去玩,她还咿咿发出声来,这时我连忙录下母亲在世上发出的最后那微弱的声音,嗯嗯嗯……吐了几口长气,喉咙像被什么赌住了,咳了几声。她留恋这个世界,真的不想离开她的子女们……
下午我到街上想买点东西晚上吃,离开的时候我觉得母亲起码还能坚持几天,幻想她可能会好起来,以为她是赌气,绝食,我听服务员小王说,母亲前天早上还吃了一碗包面(农历九月十二,母亲86岁的生日),中午就不吃了,然后就昏睡……我脑子里总想母亲还不会走,不一会,大媳给我打电话说,母亲走了,我一下子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奔跑,似乎这个喧嚣世界突然间变得了如此的安静,所有的一切都凝固了……生死离别、肝胆欲裂,我跪在母亲的床前拉着母亲还有余温的手,看着母亲像似睡着那平静慈祥的面容,我悲痛欲绝,想放声痛哭,四周青烟缭绕(给母亲烧的断气纸钱),而母亲的世界变得沉寂了。大嫂说,不能哭,母亲的灵魂还在周围徘徊,你哭她舍不得走,她会痛苦的,我只有忍着;死亡把母亲变成神圣而庄严!在她的眼角闪过一点晶莹,那是生命的最后一滴泪。母亲静静地躺在那里,我为她揩干了眼角上最后一滴泪水。母亲显得那样平静而又安详,我没有害怕,与福利院小王、大嫂帮母亲换穿衣裳,擦洗身子。一边给她穿衣服,我一边对母亲说,母亲这是您身前自己去做的衣服,您喜欢的衣服,我给您买的真丝手帕放在了您的手上,现在衣服大了,九年病魔折磨您瘦得不像人了。母亲半边偏瘫,左边膀子不好穿衣,只有把母亲翻扑着。母亲很配合我们,把衣服都穿好了,然后把我给母亲买的盖身被给她盖上(老话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女儿的盖被要贴着她的身子,然后才能盖儿子给买的盖被)。我看着母亲安详的脸孔,给她说:您辛苦了,好好睡吧。您这辈子太累了,是要好好休息了。母亲那一辈子勤劳朴素,宽厚慈祥的身影依然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看到屋子里到处是母亲用过的物品,泪水止不住往下淌。我收拾了两件母亲身前穿过的衣服放在我包包里,准备带回武汉家,与我的衣服放在一起,看到衣服就像看到了母亲。母亲走后两个小时,按规矩要把烧的断气纸灰用布包包(枕头)和纸包上放在她的头下和装进裤子荷包里,这都是我帮母亲做的,搬动母亲的头、身子放断气灰时,感觉母亲的头和身子像一块冰石头。做这一切时我脑子里没有感觉母亲离开了我们,只是在沉睡而已。母亲,您走了几个月,但我总认为您还在福利院,下一次回家再去看您……
在盖棺的那一刹那,我意识到永远再也不能见到我的母亲了,想起母亲几十年的养育之恩,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撕裂疼痛,心脏好像要跳出胸口,这叫母女心灵感应吧。说真的,我现在只要一停来,母亲躺在棺木里的形象就浮现在我眼前,好像您在睡觉。
母亲入土的那天晚上,天空中的月亮特别圆大而明亮,就像白天,月亮旁边还有一颗闪闪发光的金星挂在空中,好像在为母亲照明指路,我抬头望月看到母亲站在月亮旁边在向我们招手说,孩子们来生再见!母亲葬在我们当年下放的乡下,姑婆的橘子林里,地势高,请阴阳先生看过的。母亲的坟动用了两颗优质品种橘子树,母亲的棺木油漆闪闪发亮,是母亲60多岁请人打的,那个木匠师傅用斧头砍下去第一块木材时,木材飞溅很远,师傅对我母亲说,您肯定长寿。果然母亲活过了86岁才驾鹤仙逝,也算是高寿了。
抬棺的八大金刚把“井”挖好后,阴阳先生下“井”用绿豆和米在“井”中间写上一个八卦字,然后写上:千子万孙;下写:幸福万年。阴阳先生说,要孝子孝孙在井里给母亲烧钱纸,要用钱纸把绿豆和米烧热,母亲的幺儿子和大孙子下去给烧,烟雾简直把人呛得不能呼吸,他们都说如果冥币没有烧透必须捡上来,不捡上来后人会长癞子的。母亲入土是十点整,按照乡下当地的丧俗仪式做过一遍后,接着一锹锹将冈上的泥土填进母亲的墓坑,一行行悲痛的泪水洒在母亲的坟上。冰冷的黄土把母亲阻隔到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黑暗的、冰冷的、没有人间烟火的世界。一挂响彻云霄的鞭,穿透时空、穿透我们的心。挥泪告别母亲,母亲在天上挥一挥手,天空洒下清冷的月光、露水,闪闪烁烁,银光点点……
母亲归土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杲”字,梦中我不认识这个字,整个晚上这个字反反复复占据了我的脑海,清早起来连忙打开电脑查,意思是高远、明亮,这时的我心才放下,菩萨不忍母亲在人间再遭受病痛的折魔,把母亲接引到祥云缭绕、百鸟啾鸣、姹紫嫣红的极乐世界去了。
这些天午休在办公室,整理着母亲生前的所有照片(扫描和传到QQ空间),想起与母亲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我期待着梦中能与她相遇,我多想能穿越时空,扑进她的怀里,向她倾诉我对她的思念之苦!我多希望有来世,我们还能做母女,让我好好补偿对她全部的爱!
此时,母亲离开我们已几年了,她静静地躺在那果实累累,面朝东方的橘子林里,前面是一大片金灿灿的稻谷,一千米处是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可以直达到母亲的老家常德澧县……我因工作出差苦于无法时常给母亲坟上上香、烧纸、叫饭,谨以此文洒泪寄托我对母亲的无尽哀思与怀念。我再也无法报答您的养育之恩了。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今生不会忘!
安息吧,亲爱的母亲!
责任编辑:田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