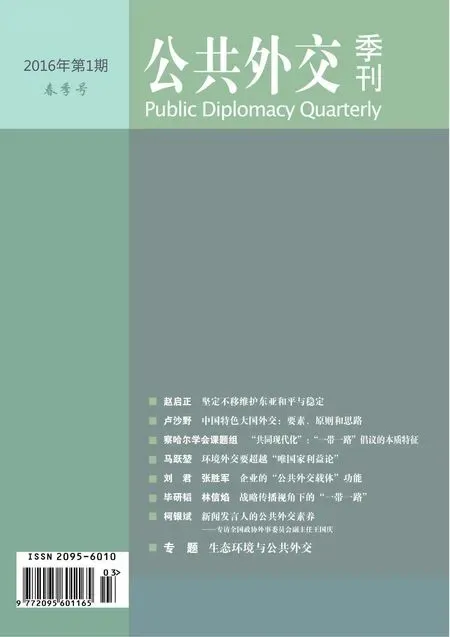刺破“铁幕”:冷战初期美国对苏东国家的“宗教外交”
贾付强
刺破“铁幕”:冷战初期美国对苏东国家的“宗教外交”
贾付强
冷战初期,为刺破“铁幕”,美国政府除动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外,还非常重视宗教在冷战中的作用,认为宗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冷战武器。为此,美国政府制定了“东正教支持项目”,积极利用各种宗教组织特别是东正教会开展对苏东国家的“宗教外交”。这清楚地表明美国外交“宗教性”的同时,也显示了美国“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度。
冷战初期,如何应对苏联在中东欧地区升起的“铁幕”,成为摆在美国政府面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乔治·凯南的“长电报”在详细分析苏联内部社会情况以及对外政策的基础上,认为苏联传统上的“不安全意识”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会促使其进行“对外扩张”。而且由于苏联在制定政策时“几乎”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美国不应“一厢情愿”地试图与苏联合作以改变其行为,而应对之进行长期地“遏制”。(The Chargé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69, pp.696-709)鉴于与苏联的冷战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的冷战,美国及其盟友除了应动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外,还应与苏东国家进行“文化冷战”。在把苏东国家及其影响囿于其目前地区的情况下,尽可能刺破(rip)“铁幕”,从内部点燃吞噬苏东国家的火焰。
美国对宗教在冷战中作用的认知
从历史的视角来说,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度”,但其在借助宗教开展外交活动方面却是“行家里手”。美国自建国始就常常借助宗教信念为其内外政策提供合法化的“神学”支持,把宗教逐渐变成一种“政治宗教”,使之“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美国政府通过宣扬“山巅之城”“上帝选民”“天定命运”“基督使者”等宗教理念,为美国的对外扩张行为提供道义支持。因此,在对苏东国家进行“遏制”与“分化”时,美国政府除希冀通过“马歇尔计划”使苏联与其卫星国之间的关系产生“裂痕”外,也没有忘记宗教这种“遗失的治国术”。
在杜鲁门总统以总统指令创建心理战略委员会,心理战略委员会主任戈登·格雷(Gordon Gray)就表示,心理战略委员会将成立一个由宗教领导人组成的专门小组,为美国政府在心理战工作中是否需要考虑基本的宗教诉求提供政策建议。(Memorandum to Joe Phillips, August 21, 1951,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简称DDRS)专门小组制定的宗教政策指南认为,宗教有助于唤醒世界各地珍惜道德与宗教自由的人们,使他们认识到需要反对极权主义对自由的侵犯。(Information Program Guidance on Special Series: Moral and Religious Factors in the USIE Program, June 22, 1951, DDRS)换句话说,宗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冷战武器,它有助于美国建立一个反对苏联及共产主义阵营的国际宗教联盟,并为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提供道德制高点与合法性的宗教说辞。对于宗教在美国推行冷战战略中的作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NSC129号文件的附件中也指出:“在那些宗教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有重要影响的地区,共产主义的无神论教条对宗教的憎恶会成为美国实现目标的一笔重要资产”。(Annex to NSC 129, April 7, 1952, DDRS)对此,杜鲁门总统也视美苏之间的冲突为“共产主义无神论与基督教之间最终的对决”,宣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否认上帝的存在并在力所能及之处消灭对上帝的信仰。(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Harry S. Truman, 1951, 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ce,1965, p.212)许多美国官员也开始利用《启示录》上的术语来渲染“苏联威胁论”,把苏联丑化为不但威胁西欧也威胁美国的“恶魔中心”,将美苏冷战描述为《圣经》中所说的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John B. Judis, The Chosen Nation: The Infuence of Religion on U.S. Foreign Policy, Policy Brief 37, 2005,pp.1-7)美国的一些宗教界人士也常推波助澜,宣扬冷战的“宗教性”。美国著名福音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在1949年洛杉矶的一个集会上就宣称:“世界已经分裂为两大阵营,其中一方是我们所看到的共产主义,其宣称反对上帝、反对圣经、反对所有宗教!”(Roy Palmer Domenico, For The Cause of Christ Here in Italy, Diplomatic History,Vol.29,Issue 4,September 2005, pp.625-654)
美国刺破“铁幕”的宗教手段
美国政府制定的“东正教支持项目”指出,虽然苏联在二战中及之后实施了“新宗教政策”,但苏联政府基本上仍对宗教持敌视的态度。因此,美国在实施对苏东国家的心理战时,应积极利用各种宗教团体特别是东正教会,通过援助把东正教会培植成反对共产主义的一种重要工具。为刺破“铁幕”,美国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维持铁幕背后东正教会神甫和信徒对东正教会的忠诚,并阻止东正教会成为苏联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府的一种工具。为此,通过适当的东正教渠道向铁幕背后的教会提供包括《圣经》在内的非政治性宗教文献;鼓励自由世界忠诚可靠的牧师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牧首的代表到铁幕之后与东正教会领导人进行交流,宣传基督教的普世精神;创办教会无线电广播节目,把东正教会的服务和音乐传递给铁幕背后的东正教徒;(Program for Support of the Orthodox Church, April 27, 1953, DDRS)利用美国之音重点攻击苏联政府对宗教的敌视以及俄罗斯人民所遭受的宗教迫害,批判斯大林“上帝”形象的虚假性;开展对东欧国家的文化与教育交流项目,在社会组织中宣扬宗教自由的价值。
第二,提升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牧首的威信,巩固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在
东正教世界的首席地位。为此,美国向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提供援助,以提升其在东正教世界中的地位;在自由世界的某些教会集会时揭发或破坏一些东正教会领导人对莫斯科牧首区的忠诚,使这些人名誉扫地;要求一些政府采取拒绝发放忠诚于莫斯科牧首区的教会领导人的签证,或者在其逝世时拒绝发放其继任者的签证的方式,使其忠诚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通过宣传机构的宣传,批判苏联政府的“傀儡”——莫斯科牧首区及其牧首。
第三,利用教会人士穿越“铁幕”。早在1945年底,美国著名的高级教士、佛罗里达主教约瑟夫·赫尔利(Joseph P. Hurley)就被梵蒂冈任命为驻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的罗马教廷大使,而赫尔利与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使节团的许多高级成员有密切的联系。鉴于英国国教会与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的良好关系,约克大主教赛瑞尔·加伯(Cyril F. Garbett)也在英国驻美国前大使哈利法克斯(Lord Halifax)的授命下拜访了铁托元帅,访问了塞尔维亚东正教会,并向塞尔维亚东正教会领导人传达了杜鲁门总统的一些“讯息”。之后,英国驻南斯拉夫大使查尔斯·皮克(Charles Peake)把约克大主教赛瑞尔·加伯的活动向前教廷大使和梵蒂冈国家宗教秘书处的美国首席代表赫尔利阁下作了通报。(Dianne Kirby, ed., Religion and the Cold War,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3, p.14)
第四,积极影响希腊东正教会主教的选举。在希腊东正教会主教达麦斯科诺斯·帕潘德里欧(Damaskinos Papandreou)于1949年5月20日突然逝世之后,泰勒向杜鲁门报告说,“不管从政治层面还是从宗教层面来说,其继任者的任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俄罗斯东正教会将努力争取一个同情共产主义和苏东集团的教会人士来担任主教。为影响希腊东正教会主教的选举,泰勒给监督选举进程的美国盟友、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牧首阿瑟纳戈拉斯一世写信,咨询有关秘密访问伊斯坦布尔和雅典的问题。同时,罗马教宗也已通过梵蒂冈与东正教会的秘密渠道直接向阿瑟纳戈拉斯一世转交了一封信,表达对主教选举的关注。经过“努力”,一位对美国比较有利的、名为斯皮里宗(Spyridion)的主教成为希腊东正教会的主教。之所以说对美国比较有利,是因为斯皮里宗与泰勒有着共同的看法,即俄罗斯东正教会“是苏联的一种武器,而不能被视为一种独立的宗教团体。”在斯皮里宗当选为希腊东正教会的主教后,泰勒立即前往土耳其与希腊,拜访了牧首阿瑟纳戈拉斯一世和新任希腊东正教会主教斯皮里宗。杜鲁门甚至还鼓励泰勒扩大他的旅程,“去刺破铁幕,同莫斯科牧首区牧首谈判。”(William Inboden,Relig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45-1960:the Soul of Containmen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41)因为如果苏联人民长期保持独立的宗教信仰的话,苏联政府的宗教压迫可能从内部点燃吞噬苏联的“燎原之火”。此外,美国还常向国外反对共产主义的东正教力量提供秘密的金融援助。
最后,美国还借助梵蒂冈反对与分化苏东集团。据估计,在1946年苏联西部人口的五分之三是基督徒:东正教徒、罗马天主教徒、新教徒或其他宗派的教徒。因此,杜鲁门派遣其私人代表泰勒访问梵蒂冈,讨论支持基督教并利用它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bulwark)”的想法。梵蒂冈当局对此也很感兴趣,并积极投身于反对苏东共产主义的“事业”中。为此,梵蒂冈号召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境内的天主教徒抵制本国政府对其的“诱惑”,并坚决反抗政府对宗教徒的迫害;同时,梵蒂冈于1949年7月1日颁布一项法令,威胁将以共产主义原因或给予共产主义支持的天主教徒开除教籍。在1952年,教宗庇护十二世还鼓励正在遭受宗教迫害的罗马尼亚人,让他们坚持对上帝的信仰,使他们相信最终的胜利将属于教会。在发给东方教会的通谕中,教宗庇护十二世谴责将上帝排除于信徒生活之外的做法。此外,教宗还向苏联人民伸出援助之手,为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感到遗憾,并预言共产主义毁灭不了俄罗斯的教会。(Dianne Kirby,ed.,Religion and the Cold War,pp.59-74)
对冷战初期美国“宗教外交”的反思
美国一份政府文件指出,“涉及到外交、军事关系、经济关系、国际法、国际交流、国际信息项目等生活进程的许多方面常得到大量的研究和发展,而宗教和宗教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却一直未给予充足的考虑。”(Proposals regarding U.S. relations with The rawada Buddhist countries, July 13,1956, DDRS)虽然学术研究未充分考虑宗教和宗教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但美国政府并未忽略宗教的外交功能。在冷战的整个岁月里,特别是在冷战初期,美国政府在反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常利用各种国内外宗教资源来赋予美国外交政策及行动一种宗教与道德层面上的“合法性”与“正义性”,以占领国际舆论场域的道德制高点。可以说,美国在整个冷战时期,不但对苏东集团开展了政治战、经济战、意识形态战,也对苏东集团开展了“宗教战”。对此,布莱恩·赫尔(Bryan J. Hehir)曾提醒人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宗教信念和考虑渗透于整个冷战时期的美国政治与政策中。”(Elliott Abrams, ed., The Infuence of Faith: Religious Groups and U.S. Foreign Policy,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eld, 2001, p.36)
美国政府常声称其奉行“政教分离”原则,但从冷战初期美国对苏东国家的“宗教外交”来看,宣称“宗教信仰自由”为宪法第一自由的、西方最基督教化的美国也并非完全奉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在冷战初期的美国外交实践中,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分离墙”既未阻止宗教及宗教团体介入美国外交事务,也未阻止美国政府利用宗教资源以实现其外交目标。美国政府在国际上试图建立反共宗教联盟,在铁幕背后秘密地资助牧师,对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布道广播和播放宗教节目,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祈祷和平的活动(明显地是反对共产主义),这都使宗教不可避免地沦为美国反对共产主义的一种工具。因此,可以说,“美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原则、为转移的,在宗教与政治之间,美国是政治放在首位的。”(董小川:《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页)
在战争问题、安全问题等“高级政治”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受到高度重视,经济问题、文化问题、宗教问题等“低级政治”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全球化时代,我国在批驳美国和西方国家利用宗教问题干涉我国内政,防止其身披宗教外衣对我国进行渗透和颠覆的同时,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也应充分重视宗教在对外交往中的作用,借助国内“多元共生”的宗教资源,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对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向外投射宗教影响力,以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与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贾付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