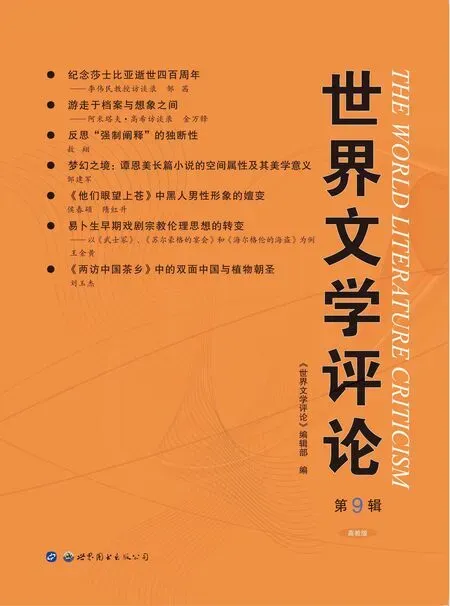纪念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
——李伟民教授访谈录
邹 茜
纪念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
——李伟民教授访谈录
邹 茜
李伟民,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莎士比亚研究所所长、《中国莎士比亚研究通讯》主编,国际莎学通讯委员会委员,重庆市社会科学专家库专家。主要从事莎士比亚和外国文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语境中的接受与流变”(项目批准号12XWW005),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外比较文论和批评的历史阶段与类型学研究”(项目批准号01EZW001)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重大课题“东方与西方:文学的交流和影响”(项目批准号01JAZJD750.11—44001);出版《光荣与梦想:莎士比亚在中国》、《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中西文化语境里的莎士比亚》、《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莎学知音思想探析与理论建设》等专著4 部;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100多篇,曾获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优秀成果奖,中国曹禺研究一等奖等奖项。在朱生豪、陈才宇译《莎士比亚全集》中撰写3.5万字“总序”;为《吴芳吉全集》撰写“总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主编的中国《莎士比亚悲剧研究》、中国《莎士比亚喜剧研究》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邹 茜:2016年时值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而且也是中国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和西班牙伟大的戏剧家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的年份,在世界各地都掀起了纪念这三位文化名人的一系列学术和纪念活动,可谓盛况空前。我注意到,您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莎学专著中都谈到莎学研究与中国文化、中国戏剧的互动问题,尤其是莎士比亚研究的现代性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学者们既熟悉,而又普遍没有进行过深入思考的话题。莎士比亚研究的生命力与其经典性和现代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忽视了对莎士比亚经典性、现代性的思考和研究,也就难以理解“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的莎士比亚剧作成为经典,至今仍然活跃于舞台,成为经典之中的经典的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目前在国内莎士比亚研究领域,您做出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有些研究论题其他学者很少涉猎,或虽有涉猎,但语焉不详,而您在这方面却颇多建树。我近年来也采访了一些以莎士比亚为研究方向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者或在读博士生,他们告诉我,您在莎学研究中卓有建树,在莎学研究中做了很多开风气之先的引领工作,是他们自己的莎学研究带来良多启示,他们甚至把您的文章下载后保存在专门的文件夹中,以便随时学习和研究。那么,我首先想问的是,李教授,你是什么时间开始研究莎士比亚的?为何对莎士比亚戏剧研究情有独钟呢?
李伟民:我大约是在1984年接触到莎士比亚研究的,算起来已有30年学习、欣赏莎作的经历了。我长期处于学术环境欠佳的境地,在互联网不发达的年代,查阅资料,了解学术信息都要比别人多付出好几倍的努力,只有积极主动地克服这一劣势,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做好研究工作。现在我的学术研究环境有所改善,我要借此机会感谢那些在学术上无私引领、扶持、支持、帮助过我的前辈、同行、学人和真诚的朋友。而且,有些朋友至今还在莎学研究中给我以支持、鼓励和督促,是他们的慷慨温暖着我的心,支持我一直能够走到今天。
文学研究是一项寂寞的事业,需要有长期做冷板凳的耐力、定力与坚韧精神,而且能够不断从自身的研究中寻找到纯粹的学术乐趣,否则很难坚持下去。学术耐力、定力对一个学者非常重要。西方莎学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学术积淀极为厚重,而且对莎作的研究业已成为西方文化、文学理论绕不开的言说对象,这客观上造成了研究的难度。而一个中国学者要涉足莎学研究这一领域,更会遇到难以数清的困难。不是有一句话吗?莎学研究是世界学术领域的奥林匹克运动,研究者需要和世界最顶级的莎学学者、文学、戏剧批评家、理论家同台竞技。即使是在翻译领域也是如此,很多已经功成名就的翻译家,最后都要通过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来证明自我,作为告别翻译舞台的最后一项重要工作。
我起初接触莎士比亚只是在文学史的学习中,领略到莎翁的伟大、莎作的迷人,相比于其他文学大家,对他的剧作多留心了一些。随着阅读的深入,感觉到莎士比亚与曹雪芹,莎翁剧作和《红楼梦》都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巨擘和不可逾越的高峰。在他们的文学世界里,蕴涵着丰富的人生感悟。我们只要略微联系一下当今的世界格局、战争、政治、经济和社会,以及各类政治人物走马灯似的人生起伏,就能够领略到莎士比亚对人生、人性的天才洞察。而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就是对这种天才描述作出当代阐释。基于对莎氏、曹雪芹《红楼梦》对人生的深刻剖析,我在1990年代撰写了《红学与莎学的东西互渐》一文,该文发表后引起了比较广泛地社会反响,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红楼梦研究》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这对一个初次涉足莎学与红学研究领域的年轻人来说是弥足珍贵的,也是一个巨大的精神鼓励,其后一发不可收拾。在一段时间里,我除了在吴宓、吴芳吉研究、宋代女词人朱淑真研究上有所斩获外,将学术精力较多地投入到对莎士比亚的研究中。
邹 茜:您长期从事莎学研究。已故莎学家孟宪强教授曾经说过:“在20世纪末10年间的中国莎坛上,李伟民先生所发表的莎学论文数量之多是无人能与之相比的,您以激情、勤奋、踏实以及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所凝结而成的莎学华章,为20世纪末的中国莎坛锦上添花”。实际上,在21世纪十多年的中国莎学研究领域,您也是中国莎学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凡是有志于研究莎士比亚的中国学者,您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李伟民:学术研究贵在耐得住寂寞,要有学术定力。学术定力和研究中的不断创新往往是一个杰出学者成功的关键因素。创新应该是学术研究的主旋律和永恒话题。文科大学、文科专业如何创新?莎学研究如何创新?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值得我们这一代学人深入思考。当前理工科大学,自然科学领域、应用工程技术领域创新不断,国家也把这些领域的创新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层面。而文科大学的创新则似乎还没有找准方向,或者不愿意寻找正确的方向。因为这里面掺杂了更多的人的因素。我们看到,很多文科大学或文科专业所理解的创新或所做的“创新工作”,就是在所设置的创新项目中设置几个“驾校报名点”;或者办几个咖啡厅,致使校园内咖啡厅林立,沦为赔钱的摆设;再或者宣称办几个“全球性”的所谓研究院和所谓“智库”,既没有科研支撑,也没有谁愿意向其咨询,纯粹沦为向政府要钱的工具。那么这样的所谓创新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说,这就是创新,那么街头林立的驾校报名点就都是创新的孵化基地了。文科大学应该重视的是学科建设,立足于学校几十年来形成的,现在比较突出的特色,在加以延伸的基础上,构建知识创新体系,以学科形成的特色锻造大学的灵魂,凝聚大学的精神,以文科大学的文化软实力自立于大学之林。学问与学科应该更重视学界内部的认同,强调真正以学术为标准,以科研为引领,以教学为基础,以学术为追求的同行间的认同,真学问是需要老老实实和认认真真去研究的。
邹 茜:您认为莎士比亚戏剧最伟大的成就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伟民:莎学研究尤其需要创新。莎士比亚戏剧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就体现在不断创新之中。我们先要从莎作的经典性谈起。莎士比亚戏剧的特色归纳起来是“同情、通俗、幽默、广博和深刻……文艺复兴的曙光,出现在他的一切的杰作中,通过他的作品所看到的田地,是那么的富丽与灿烂”。 莎士比亚剧作中蕴涵了人文主义思想,与中世纪教会神学观念不同,人文主义把人提高到与神相同的地位,提倡个性解放。莎士比亚通过其剧作透露了反对放纵情欲,希冀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思想。通过剧中人对自己的思想、行为和动机的自我剖析,反映了作者本人的伦理观;而莎士比亚的历史观和社会政治观则强调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效法自然、建立等级制秩序,重视历史发展中的现实因素,其中既包含了人对宿命的反抗,也描绘了人的自由意志的放纵如何扰乱神圣自然和社会秩序,阻碍或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因。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母题通过不同的主题反映了丰富的思想,具有不同的社会和哲学意义,其经典性正如其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真、善、美就是我的全部主题。
邹 茜:您认为莎剧对中国当代戏剧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李伟民:改革开放以来,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舞台上的不断演出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在一段时间,成为引领中国戏剧走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理论束缚的先行者。例如,中央戏剧学院徐晓钟先生导演的《马克白斯》确定演出的“形象种子”,“一个‘巨人’在鲜血的激流和漩涡中蹚涉并被卷没”与《培尔•金特》和《桑树坪记事》等戏剧一起被誉为中国“话剧探索走向成熟的标志”和在改革开放中显示出中国戏剧创作的光明前景,《马克白斯》概括了权位与鲜血之间的关系,暗示了人性与自身的非理性争斗并被其毁灭的人生悲剧,以及红桌布的舞台意象的著名处理,破除的生活幻觉强化了马克白斯的内心活动。由此,这部莎剧与上海戏剧学院的《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上海市昆剧团的《血手记》,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无事生非》,上海越剧院三团的《第十二夜》,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威尼斯商人》,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李尔王》,开启了中国舞台上中国人导演、表演莎剧的自由王国。这些莎剧演出在很长一段时间与中国舞台上其他影响很大的经典戏剧、探索戏剧甚至先锋戏剧一起构成了中国戏剧舞台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但是,莎士比亚戏剧又是很难演的,尽管,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舞台上演出的莎剧不少,但是与我们获得“国家舞台艺术精品”的戏剧作品相比,未来的中国莎剧演出仍有广阔的空间。
邹 茜:2016年是莎士比亚、汤显祖和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世界各地都举行了很多纪念和学术研讨活动,您能介绍一下这些活动和学术研讨会的情况吗?
李伟民:实际上,这些纪念和学术研讨活动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莎学家问鼎国际莎学论坛、世界莎士比亚大会和其他国家的莎士比亚戏剧节、学术活动以来,中国莎学研究逐渐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关注,自前任国际莎协主席菲利普·布罗克班克发出:“莎士比亚的春天在中国”的感慨以来,两任国际莎协主席吉尔·莱文森、彼得·霍尔布鲁克等专家相继来华参与莎学研讨、观看话剧、戏曲莎剧,惊奇于中国戏曲能以丰富的表现手段诠释莎剧,并对中国莎学所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2016年是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2016年是曹雪芹逝世253周年。2010年6月,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政府与英国斯特拉福德艾文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2011年4月,在中国遂昌汤显祖文化节期间举办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文化高峰论坛暨汤显祖和晚明文化学术研讨会”;2014年4月,“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遂昌隆重召开;2015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英时在伦敦演讲时提出:“中英两国可以共同纪念这两位文学巨匠,以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加深相互理解。”2016年4月,“2016遂昌汤显祖-莎士比亚文化的当代生命国际高峰学术论坛”隆重开幕。遂昌县通过举办文化节庆、重建遗存遗迹、创建纪念馆和网站、出版研究专著、排演戏剧、拍摄电影、发行昆曲和汤公邮票、“班春劝农”和“遂昌昆曲十番”成功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举措,推动汤显祖文化发展和繁荣。夏志清1970年就撰写了《汤显祖剧作中的时间和人的出境》,在北美,研究明代剧作家最多和最深入的是汤显祖。2002年白之翻译的《牡丹亭》,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史恺悌撰写“前言”。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出版了徐永明、陈靝沅主编的《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论著选译》,该书从主题学角度探讨了母题与民间故事之间的关系;由于研究者大多身处国外,注重借用西方文艺理论对汤显祖及其戏剧作出新的解读;利用挖掘的新材料进行梳理和分析;翻译研究成为重点。2010年,北京曹雪芹学会主办了首届曹雪芹文化艺术节,2012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举办了曹雪芹与红学文化为主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和第三届曹雪芹文化艺术节,2013年,恰值曹雪芹逝世250周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等单位举办了第四届曹雪芹文化艺术节。莎士比亚故居博物馆戴安娜·欧文、巴尔扎克博物馆伊夫·卡涅、托尔斯泰博物馆加莲娜·阿列克赛耶娃等,分别作了了《文化交流:莎士比亚搭建世界文化的桥梁》、《纪念馆为何能成为享誉世界的朝拜圣地——巴尔扎克纪念馆管理经验分享》、《托尔斯泰的精神传承:多功能文化机构—托尔斯泰庄园博物馆》报告,他们认为正是这些代表了民族文化的经典作家与作品“描绘了属于人类的价值、矛盾和真理”;“向世界剖析一位世界性的作家”;以此,来展示作家“真实的生命”。2015年10月,第六届曹雪芹文化艺术节纪念曹雪芹诞辰300周年纪念大会在曹雪芹故居所在地北京植物园召开。2016年8月,在英国举办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的世界莎学大会和学术研讨,中国有二十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盛会。显然,这一系列活动的举办,都是“在彰显经典当代意义的基础上”,“在对方的视角下重新观照自身的文化世界”,探讨经典作家、作品人文关怀的当代价值。毫无疑问,不断的学术研讨和纪念活动,已经成为当代人认识大师和经典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经典能够走向未来,建立民族文化身份,拥有现代精神的一张通行证。
邹 茜:和易卜生戏剧比起来,莎士比亚的戏剧有何独到之价值?
李伟民:我对易卜生戏剧了解不多,不过,我多年从事“外国文学史”与“西方戏剧”课程的教学,易卜生、莎士比亚和奥尼尔等西方戏剧家都是讲课的重点。我们知道,易卜生戏剧超越传统,在创作过程中,不断接受了古希腊悲剧诗人和莎士比亚戏剧的影响。自五四以来易卜生戏剧比莎士比亚戏剧对中国社会和文学的影响比莎士比亚更为迅速和深入,也更切合中国反帝反封建、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据我所知,华中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校的易卜生研究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华中师范大学素有易卜生研究传统,在王忠祥教授、邹建军教授的带领下,华中师范大学的易卜生研究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为易卜生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出版了《易卜生全集》、《易卜生文集》、《易卜生研究文集》、《易卜生戏剧选》、《易卜生戏剧精选》、《易卜生书信演讲集》、《易卜生诗剧研究》等学术专书,召开了一系列“易卜生学术研讨会”。中国每年发表的有关易卜生研究的论文几十篇,尽管在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易卜生研究论文在数量上不如莎学多,但是,也是外国文学研究和西方戏剧研究的重点。我在讲课过程中曾多次给学生放映过易卜生的《培尔·金特》,同学们表现出与看莎剧一样浓厚兴趣。我认为,不管是易卜生戏剧,还是莎剧在当代舞台上都面临着现代性的转型,这就更需要我们加深对易卜生的认识,以现代眼光深入阐释易卜生的当代价值。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应该把现代性的表现形式——现代主义二者区别开来。现代主义是现代西方的反叛性文学思潮,是现代西方名目繁多的反传统文学流派的总称,表现为现代西方人精神危机和艺术上的“先锋”、“前卫”特质。现代主义是一个历史现象或现代经典文本,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现代主义已经成为了过去。在艺术上,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动,与后期消费商业社会的出现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表现为现实朝着意象转化,而且融时间的碎片与永恒的现在之中。而具体到易卜生和莎氏的现代性。我认为,主要是要揭示易卜生、莎士比亚与现代文化乃至后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认识到易卜生、莎士比亚及其学术研究几百年里演进的轨迹,以及在新的时代易卜生、莎士比亚给人类社会所提供的精神资源。
邹 茜:易卜生、莎士比亚的现代性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呢?
李伟民:作为现代主义来说要么是后现代主义的对立面,要么就是后现代主义演进中永久保存的一种原型。后现代主义是对于封闭的抗拒,是旨在超越现代主义的一连串的尝试,是伴随着内容而出现的不加节制的形式,话语在叙事中有非常明显的作用,相对于原作来说,对过程更为重视,呈现为指涉性的断裂。我认为,莎士比亚与现代性的讨论将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开创了更为广泛、更加深入的理论视野,并且为我们的外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某些有益的经验。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易卜生、莎士比亚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一,易卜生、莎士比亚对人类情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乃至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描写的独特方式,以及对人类情感放在社会环境之中的深入描述,易卜生、莎士比亚作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的公共性,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仍然会以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某种方式,通过互文、拼贴、变形、挪移、重构、解构映射出来,构成了易卜生、莎士比亚传播的世界性;第二,作为一种文化范式和创作方法,易卜生、莎士比亚的普世性,已经成为各种戏剧风格、流派吸收他者导表演理论、经验的一张畅通无阻的介绍信,并且演绎出无数的易卜生、莎士比亚的副产品;第三,由于易卜生戏剧、莎剧的搬演已经日益成为戏剧工作者磨砺风格、体现创新、追求创意、实现深刻的磨刀石,所以作为经典的易卜生戏剧、莎作在审美上也就具有了某种标准性,人们常以是否成功地导演、表演过易卜生戏剧、莎剧作为自己戏剧艺术成功、成熟的标志,易卜生戏剧、莎作教学已经成为戏剧院校、中文与英文专业学士、硕士、博士学院派教学的必修课程;第四,文本和舞台改编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主要表现为,从形式与语境出发,拉开当代观众与易卜生、莎士比亚的距离;或者宣称遵循原著精神甚至细节的演出,希冀当下的观众能够重新回到易卜生、莎士比亚戏剧产生的时代;第五,全球化与跨文化中的易卜生、莎士比亚。现代主义成为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关键。后现代主义在强调“过程”中尤为注重游戏、行为、事件、娱乐、人工制品、语象的表演模式,而且实用色彩鲜明。因为元虚构的方式消解了个体的中心,主体与客体都是虚构的,我所拥有的个性化的本质,并不属于我,因为,本质的东西体现在主体与客体的交互作用中。后现代话语揭示了现代主义的许多中心观念都是站不住脚的,是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产物,但是,我们仍然应该看到后现代观念是现代主义观点和概念的自然延伸。当然,以上五点,既有世界易卜生、莎学研究的共同特点。
莎士比亚的现代性给我们的启示还在于,莎剧的未来在于非英语区的世界文化中的广泛传播,各种“异国莎士比亚”实验所提供的美学启示,以及对于人性的深刻理解往往会超越一般的英语莎剧的演出。在跨文化的改编和莎剧演出中,往往使我们能够具体看到莎士比亚不同身份,以及我们自己流变中的现代文化身份,对于“不土不洋的莎剧改编,在西方人看来感觉很酷,他们看到的是颇具后现代气息的莎剧改编。具体看看莎剧在中国舞台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包括话剧、京剧、昆曲、川剧、越剧、黄梅戏、歌剧、芭蕾舞剧、粤剧、沪剧、婺剧、豫剧、庐剧、徽剧、湘剧、丝弦戏、花灯戏、东江戏、二人转、潮剧、汉剧、吉剧、各家大戏、歌仔戏二十四个剧种排演过莎剧。这在外国戏剧改编为中国戏曲中可谓是绝无仅有的特殊例子。曹禺曾经说过,“莎士比亚的戏剧是诗、是哲学,是深刻的思想与人性的光辉;是仁爱,是幽默,是仇恨的深渊,是激情的巅峰。”即使是对戏曲改编莎剧持保留态度的王元化先生也认为“写意容许变形的表现手法,更侧重于神似,优秀的写意艺术本拙劣的写实艺术可以说是更真实的,因为前者在精神上更酷肖所表现的内容”。我们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演出莎士比亚戏剧,所有这些活动、创造,都在舞台上发出了他们独特的光彩,在莎士比亚与中国人民之间架起一座座美丽的桥梁。今天,从我们中国舞台上看,我们的莎剧改编和演出,早已摈弃了那种仿古式的莎剧演出,在莎剧的改编中充分利用中国戏曲的优势,创造出了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莎剧演出形式,即使是采用话剧形式改编莎剧,也是接中国地气的莎剧。
邹 茜:中国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有何特点,相比而言,您更喜欢朱生豪译本,还是梁实秋译本?
李伟民:我认为,中国的莎作翻译、莎剧舞台演出和莎士比亚研究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莎学的重要实践与理论基础,我们已经在这个基础上初步建构起中国莎学研究的理论体系。而且这种鲜明的中国特色正是我们的莎学赖以存在的基础和重要标志。如果我们的莎学研究只是跟在英美莎学后面亦步亦趋,失去了自我,那么还有什么价值呢?我们的莎学研究不同于西方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域的莎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同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莎学”和建构这一体系的任务也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而无论是彰显“有中国特色的莎学”,还是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莎学理论体系”本身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永远在路上,没有完成时。回顾我们以往取得的成绩,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在近二百年中国莎士比亚研究、演出、翻译这一莎学总体框架内,我们说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国家的莎学研究特色,甚至凝结着近代以来反对外族侵略,争取民族解放,为中国民族的文化建设争气的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和气节。但是中国特色的莎学又是在不断发展之中的,而就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而言,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莎学理论研究体系”,则还有待于“有中国特色莎学”这一宏大目标的进一步凝聚,以及莎学界同仁持续不懈地努力。
我们知道,威廉·莎士比亚的名字在19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代表。当时,泱泱神州大地正处于风雨飘摇之大变局中。我浩浩中华发生了有史以来波及最为广泛、影响极为深远的中西文化之间的大交融和剧烈碰撞。传统的民族文化、思想面临咄咄逼人,极端陌生之泰西文化、思想的猛烈撞击,东方古华夏被犹如排山倒海般的欧风美雨、仁智之辨,民主与科学、自由与革命,黄钟大吕、警世之钟所产生的巨响唤醒。夷语东渐,西学大张,异域文化如潮水般涌入我炎黄子孙世代栖居之家园。时代发展孕育着新旧更替,中西互融,文化价值观念之嬗变催生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域外文学名著的译介引发文艺在内容与形式上产生沧海桑田之感叹;欧美典籍之译介和文化交锋,打开、改变了人们禁锢已久的思想,开创了崭新的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而美善之所存,理趣之所蕴的莎士比亚作品传播就是经典输入中的一个杰出范例。
1978年,被“文化大革命”耽搁了15年之久的《莎士比亚全集》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套外国作家全集。《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为中国莎学走向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还拥有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虞尔昌译《莎士比亚全集》、方平译《新莎士比亚全集》、译林版《莎士比亚全集》、新世纪版《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手稿》、浙江工商大学版《朱生豪、陈才宇译莎士比亚全集》、《朱译莎士比亚戏剧31种》、朱生豪、苏福忠译《莎士比亚全集》、辜正坤主译,多人参与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以及曹未风、孙大雨、吴兴华、卞之琳、林同济、吕荧、张采真、林纾、邵挺、田汉、曹禺、屠岸、梁宗岱、林同济、杨烈、英若诚、阮珅、杨世彭、杨熙龄、李霁野、杨德豫、阮珅、孙法理、辜正坤、陈才宇、彭镜禧、绿原、黄国彬、王宏印、曹明伦等人的多种莎作译本。国内还有多位学者计划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前期,各种莎剧译本大量印行。至于说到是否对某位译者所译的莎作有所偏爱,我是这样理解的。作为一个莎学研究者,对所有的莎作译本和翻译者的风格都应该有所了解,通过比较、研究弄清译者的翻译风格和具体翻译中的特殊考虑。作为我来说,在阅读和研究中较多参考了朱生豪、梁实秋、方平等人的译作。当然为了学术研究的需要,也研究了一些在当代已经湮没不彰,甚至错讹很多的译本。早期莎学在中国的传播史,从林纾开始,对莎作的翻译、研究就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发生了联系。再到朱生豪、梁实秋、孙大雨均将翻译莎剧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联系起来,甚至与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抗日战争联系起来,并通过翻译莎作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气节。显然,这应该是莎士比亚在中国传播的现代性的题中之义。
中国接受、传播西方文化的历史表明,在所有的域外文学家戏剧家之中,莎士比亚是被中国人研究最多的外国作家。中国从五四前后到今天,总共出版莎学专著近百种,莎士比亚辞典六部,《莎士比亚全集》三种! 发表有关莎士比亚的文章二千多篇! 莎士比亚与中国文化的现代交集,自然也应该包括对中国莎学传播史的细致梳理。在这一点上,莎学研究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知道,作为西方经典的莎士比亚戏剧随着传教士的脚步被引入中国。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开始接触莎剧,但他们首先阅读的是莎剧英文简易读物。这些莎剧英文简易读物。对于学习者学习地道的英文,了解莎士比亚戏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把这些莎剧的简易读物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种,以中文注释的莎剧简易英文读物,主要以中文注释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为主;第二种,以中文注释莎士比亚戏剧的英语学习读物,而不是经过兰姆姐弟改写的读本;第三种为英汉对照本的莎剧简易读物;第四种为不加任何注释的兰姆姐弟的英文《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第五种,以文学阅读为目的由林纾和其他人翻译的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出版时也多以《莎氏乐府本事》来命名)。
兰姆姐弟合写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开始虽然是作为为本国青少年读物编写的,但是,流传到域外,尤其是在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人们认识莎士比亚戏剧时不可缺少的一本入门书。对于晚清和民国以来初习英文的中国学生来说,数量众多的英文注释本和汉英对照的《莎氏乐府本事》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初级英文学习教材。在中国最早翻译过来的不是整本的莎士比亚戏剧,而是普及性的《莎氏乐府本事》以及多种莎剧注释本和汉英对照本,这些书籍成为晚清和民国时代学习英文的学生必读的书籍之一,也是后来成为英语大师的许多著名学者的英文入门读物之一。在这些或者以文言文注释莎剧,或者以白话文注释莎剧;或者以文白夹杂的形式注释的《莎氏乐府本事》或单部莎剧中,我们亦可以观察到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以来,中国人使用语言的变化以及语言习惯的变化过程。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小学教科书一律使用白话文,白话文为国语的地位终于得到承认后,而谙熟英语的人士,在以汉语注释、翻译《莎氏乐府本事》等西方读物时,仍然采用了文言文或文白夹杂的形式,这说明人们使用语言的习惯也是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和适应的问题。在当下,今天的英语学习者也仍然把注释本莎剧作为学习英语的读物之一。这些以“莎氏乐府”之名出版的读物,在翻译实践上为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奠定了基础。从中国英语教育史的角度看,众多的以“莎氏乐府本事”命名的英文读物在中国的英语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并没有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对其研究相当薄弱,在中国莎学近二百年的研究史,我们一直忽略了对源头——《莎氏乐府》的研究,显然这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又如王国维的《莎士比传》堪称中国最早出版的莎士比亚传记。长期以来,王氏的这篇莎传在中国莎学研究中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在一些梳理中国莎学研究的论著中也没有注意到王国维的这篇莎传,缺乏对王国维这篇莎传的研究,显然,这是一个有待弥补的研究课题。尽管王国维在译介上的成就难以与他的再创相匹敌,但厘清其对莎士比亚的认知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自1836年莎士比亚被介绍入中国以来,Shakespeare有20多种译名。如天僇生极力推崇莎士比亚:“自十五、六世纪以来,若英之蒿来庵(今通译莎士比亚)……其所著曲本,上而王公,下而妇孺,无不人手一编。”但莎士比亚的名字此时并没有定型。王国维译介《莎士比传》正是处于莎士比亚在中国传播的前经典化时期。王国维对“戏剧家莎士比亚有很崇高的评价”。他在《文学与教育》中谈到:“至古今之大著述,苟其著述一日存,则其遗泽且及于千百世而未沫……英吉利之 狭斯丕尔也……皆其国人人之所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试问我国之大文学家,有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如英之狭斯丕尔。”王国维在《脱尔斯泰传》中“交友及论人第十二”提到“其论琐斯披亚也,曰:‘琐氏实艺术大家,然世人之崇拜之者通称扬其短处耳。’”由此可见,在Shakespeare还没有统一的译名之前,1904年出版的《静庵文集》和1907年第143、144号《教育世界》中王国维尚没有采用“莎士比”的译名。而“莎士比亚”这个中国通用至今的译名则是由梁启超1902年在《饮冰室诗话》中定下的。但是,紧接着,王国维在1907年10月出版的《教育世界》159号上在“英国文学专论”中刊登的《莎士比传》已经部分采用了“莎士比亚”这个译名。王国维在《教育世界》的“传记”栏中介绍了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西方名人的“嘉言懿行”,认为他们“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西洋的文学作品是有“警世”作用的。莎士比亚作品本身就包含了一切人类之精神。我们认为,即使是王国维的“戏曲研究也是在西方学术背景下进行的……对于王国维来说,戏曲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学术意识的产物……戏曲的定义也是以西方戏剧形态为重要参照的。”这自然包括王氏对莎士比亚及其戏剧的认知。莎士比亚戏剧的意义,在王国维看来无疑是属于真戏剧的范畴,这种真戏剧是“真演故事的,所演的若不是具体的故事,而仅仅是貌为故事之形,那就不是真戏剧。”所以才具有“警世”的意义。在现代戏剧的观念之下,无论是戏剧还是戏曲,戏剧也有“真戏剧”,戏曲也有“真戏曲”之区分,舞台表演既要“符合戏剧人物的性格,也要符合戏剧环境的写意追求。”王国维的这篇《莎士比传》,可谓得风气之先的重要莎研文章,相比于这一时期,同时代一些粗线条的介绍莎士比亚的文章,王国维在勾勒传主生平的同时,对其作品也进行了肯綮的评析。王国维的这篇《莎士比传》在中国莎学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其对莎士比亚的介绍已经使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了解了莎士比亚作品在文学与戏剧上的经典性,也纠正了林纾等人把莎剧剧本理解为小说的错讹。
邹 茜:我认为,我们中国的莎学显然应该由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莎学研究所组成。
李伟民:你说得非常正确!台湾、香港、澳门莎学也是中国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台湾开始莎士比亚研究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这时从事莎作翻译和评论的主要是从大陆去台的学者、教授,其中以梁实秋和虞尔昌为代表。1957年4月,台北世界书局出版了朱生豪和虞尔昌合译的5卷本《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这本全集包括朱生豪翻译的27个剧本和虞尔昌翻译的10个历史剧。每个历史剧均附有译者写的“本事”。全书附有“莎士比亚评论”和“莎士比亚年谱”。1961年,台北世界书局又出版了虞尔昌译的中英文对照编排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梁实秋除了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以外,还著有《永恒的剧场——莎士比亚》。1964年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时,梁实秋主持编写了《莎士比亚四百年诞辰纪念集》,由台湾中华书局出版。1989年台湾高雄师大召开了“第一届中美莎士比亚研讨会”。仅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译本,台湾就出版了不下7个译本。台湾莎学研究不局限于莎士比亚的语言、意象、结构、版本等文本范畴,而是从剧场演出、影视改编、戏剧观念、女性主义、性别研究、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领域出发,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莎士比亚。近年来,台湾的莎学活动较为活跃,而且与大陆的莎学学者之间的交流也比较频繁。大陆举办莎士比亚戏剧节、莎学研讨会也有台湾莎学家如朱立民、彭镜禧、姜龙昭、王淑华、林璄南、简南妮等受到邀请前来观摩、参与研讨。台湾大学彭镜禧翻译了《哈姆雷》、《威尼斯商人》等多部莎剧,他多次来大陆参加莎士比亚学术研讨会、讲授莎士比亚。
邹 茜:李教授,谢谢您!全球化与跨文化的莎士比亚,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织的莎士比亚的出现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世界范围内的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与研究,正处于全面超越以往莎学研究经验和理论的过程中,为文化、文学、艺术批评带来了更为丰富的话题,也能让我们从更多地角度解读、认识莎士比亚的经典价值。
邹茜,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主要研究比较文学与东方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