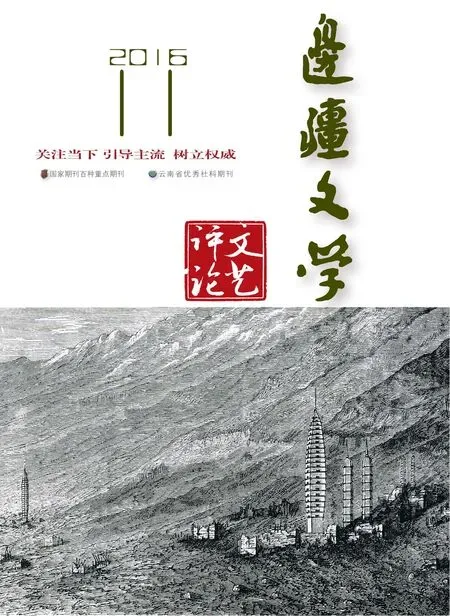《昭苏太河传》:富有艺术创新的优秀创制
◎姜 超
《昭苏太河传》:富有艺术创新的优秀创制
◎姜 超
不经意间,酣畅淋漓地读完了长篇小说《昭苏太河传》的第一部《大溪流碧》。这是一部有较强艺术特质的小说,是深接地气、通达天气、葆有底气、灌注生气的不凡创制。带着强烈的探究心理,我试图进一步从作者的只言片语中管中窥豹,从一叶见如来,从二位作者的文字切片中探查DNA的秘谛,以期贴近有着写作雄心的作者心理世界。如吴海中在前言所说,《昭苏太河传》有“深沉绵渺的三阙乐容——《大溪流碧》《月乱星摇》和《冰瀑银窗》组合在一起,这一条母亲河就有了她终身的契书。”
一、叙事兼代言的诗体故事
在经验愈发贫乏、贬值的年代,小说的意义在于勘探内心,探究存在。“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小说家画出存在地图,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的可能性……”[1]是的,在复杂的生活面前,小说已经比不过现实的精彩。好的小说应当为存在作证,探入当代国人的精神图景当中去,而不是在灵魂之外漫游。让经验走向存在,这是小说意义的旨归。这部长篇小说思索深邃兼有苦痛,唤起记忆又叩问过往。它有着结实辽阔的艺术想象力,仿佛极乐世界的七宝行树,奏响百千种美乐,皆是法音宣流的外化。王安忆说:“小说的想象力必须遵守生活的纪律,推到多远就看你的想象力的能量。”[2]想象力是作家的命脉。小说家的使命,就是让经验插上想象的翅膀,文字如恒星般闪亮。吴海中、张赤驱策着想象力,为读者提供了一场美学盛宴。
奈保尔曾说:“长篇小说是一种用滥了的形式,非常草率随意。人人都在写长篇小说,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于以往的长篇小说的无意识的不高明的抄袭。而真正的书是那些流传下来的,不是抄袭。我要说我宁愿读那些具有独创性的书。”若从《大溪流碧》的成色借以全观《昭苏太河传》,无疑是形式新颖独异的长篇小说。也许,很多人固执地认为只是借用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手法,而断然否定小说的艺术成就。汪曾棋说:“追随时尚的作家,就会被时尚所抛弃。”这二位作者广泛借鉴欧风美雨,还贴近中国古典传统和民间资源,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纳各种思想资源,做到了洋为中用、移古润今。《昭苏太河传》堪称东北版的《繁花》,似乎在为读者减低叙事带来的心理负担,别有一番风味可供品茗。
曾有人将二人转称为“叙事兼代言的诗体故事”。《大溪流碧》深得二人转的神韵,叙述者的身份自由切换,视角随意切入。二人转的叙事与代言功能,实际上是以多维视角观察,与观众同喜共悲的互动中,以铺陈交叉缠绕的线索,在破除传统小说的叙事结构的同时,还彰显作者强大的控制小说局面的能力。二人转的角色自由跳进、跳出,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演出中,艺人根据现场情况,随时融入时代元素,经常达到事先不可知的良好状态。
由是观之,《大溪流碧》可谓汲取了二人转的精魄。小说多角度叙述、多侧面展开描写,两个后辈的回忆中扯出先人的血泪情仇。换言之,跳进跳出的人物叙事,刷新了读者的审美视野,革新了小说结构。
《大溪流碧》采用限知视角,小说在叙事层面上颇显智慧。它采用古典小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述策略,却择用第一人称讲述故事。这种形式,实在是一种小说可能性的开创之举。在篇章结构上,如作者所说,“以二人转的文体结构来落实我们的叙述张致”,试图“以独特的演绎方式发运出尚好的幽默来。它需要的故事规模是那么的轻巧,可它要转化出来的人伦真知是瑰丽而透着鬼魅的,总是那么让人无法拒绝”。二位作者多次商议,向熟悉的民间资源索要精神和艺术形式,“抽丝剥茧,织成一片彩色的云锦”。这足以显示作者的雄心了,将小说当作“云锦”来织。作为艺术品的云锦技艺惊艳绝伦,其图案就有散花、团花、满花、缠枝、折枝、串枝、锦群等名称,且操作者没有设计图纸,全凭心中所想,创制人间极品。《大溪流碧》的谋篇布局不输于云锦,作者的心血与智慧力透纸背,不知用了多少心思?
小说《大溪流碧》的精妙之处是延宕叙述。延宕叙述,就是退后延迟叙述,造成艺术上的留白效果。小说家就是那把故事讲好的人,故事讲出来是最低纲领,重点在“讲好”上。我觉得,会控制叙事节奏的小说家,更接近艺术的本质。从这部小说看,作者有意识放缓事件发展的速率,经营悬念效应,刺激读者阅读的欲望,以延宕的方式雕刻着阅读产生的满足感。就好像高明的说书人,能将一秒钟的斩杀局面,演绎成十分钟的精彩场景。小说的叙述视角不断转换,一会儿是小万子,一会儿是杏儿,好似散点透视,逐渐抖出故事的原委,逐渐雕琢下多余的石头,显出石头里本就存有的马。
这部小说的对话量较大,承担了原本叙述的功能。对话,或者东北方言给予了小说新形式、新生命的可能。一种活的文学应运而生,也顺便拯救僵死的文学叙事,更新了文学肌理。语言作为后天习得,附着的地方文化、价值判断、心理惯性等,如艺术的介入小说,会带来摧枯拉朽的破坏力,新建一个庞大的标识性极强的建筑。随便拎出一段,让我们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来体会作者的语言创造:
薛大他背着一个布褡裢进了门,褡裢和薛大照直到了杏树下,蹲在爸身前看着血肉模糊的爸。他对着爸的脊背说,文魁呀,你就这么走了么?你不能这么走,我等了这么些年,就想看着你拿回你们于家的富贵,你这么一走,便宜了李秧歌那个鬼东西。文魁呀,你要是条汉子,你就给我活过来,我巴望着你给你爹把仇报了。他正念叨着,刘大德凑过来说,薛大,你看了一辈子阴阳,也耍了一辈子神杆子,有能耐你把管家的魂魄喊回来。薛大仰起脸看了刘大德一眼,懒得和他过话,手拄着大腿站起身,照直进了屋子。我知道,薛大是来给我们家操办丧事的。
不知何时开始,当代小说兴起了不要引号而径直叙事的风潮,其成败得失暂不探讨。小说的各种创造,应以不破坏小说的美感和气韵为原则,否则就是哗众取宠。平心而论,吴海中、张赤的口语叙事,深得古代话本小说的精髓,洋溢着梳理之后的雅气,还不伤害口语叙事的气韵。“巴望”“念叨”“神杆子”等语词,明显是东北方言的引入。读到此处,我颇有点担心作者会缺乏节制,被东北方言汪洋恣肆、活泛逗哏的特质所熏染,而左右了小说的空间。欣喜的是,小说的语言一直与常见普通话、东北方言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间离中生成了独特的陌生化效果,熟悉的生活因之变得新鲜。
东北方言的特质是力道十足,不矫揉造作,不拐弯抹角,较少中性色彩的词语,直接表达爱恨情仇。《大溪流碧》呈现了这一点,小说人物的爱恨情仇,不掖着藏着,直爽任侠地表述出来。同样钩沉家族历史,其他地域的作家很容易写到各种算计、阴谋,而吴海中、张赤的这部小说则像异类,借用感性、滚烫的东北方言叙述,塞给读者更多可信的世俗经验和情感。这部小说颇似二人转演员的表演,不隔语、不隔心,一段百年悲欢往事裹挟着沸腾的情感。
木心说:“艺术是光明磊落的隐私。”二人转的文类特质,就是以笑谑为主,张扬着酒神的狂欢精神。美中不足的是,《昭苏太河传》的第一部《大溪流碧》号称“借势于二人转的灵影,是我们要再度感恩乡土的一个实证”,但写得庄重有余,色调过于苦涩,还没有达到狂欢的效果,希望作者在第二部创作时有所改进。
二、鲜活饱满的民间经验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昭苏太河传》以时间轴,以纷繁的线索和巧妙的叙事勾联,要全景式再现近百年的各色人等的生存和精神境遇,走的是一条危险而富有挑战性的道路。
《大溪流碧》从容还原东北生民的日常生活。这部小说不但视野宏阔,而且笔法精微,历史场景中的芸芸众生相统统摄入笔端,显示了作者超人卓绝的艺术才华。左拉在评价巴尔扎克和司汤达时说,“他们伟大,因为他们描绘了他们的时代,而不是因为他们杜撰了一些故事。”这部小说呈现了历史的肉身状态。小说因历史的旁证,信服力大为增强。小说的真实是在叙事中一步步建立起来的。小说里没有高大上的英雄,那些随处可见的小人物书写着大历史。作者较少为英雄人物树碑立传,而是塑造血肉丰满的小人物,展现民间世相丰饶复杂的生命景观。二位作者聚焦卑微的生命图景,在如蝼蚁般艰难生存的人群身上发现生命的顽韧。
小说出场人物多达十几位,都带着历史的体温,人物纷杂而不乱,各自呈现出可以辨识度较高的性格特征。据此,与当下多如牛毛的长篇小说而论,这部长篇无疑是成功的,因为作者没有放纵情节,制造没必要的过场人物。小说笔下的众生在繁复时段里依旧忙忙碌碌,有着饱满的生命状态。如小说对李家西跨院长工生活的描写,活脱脱再现了他们勤劳、粗鄙、隐忍等日常图景,亲切如昨,似是耄耋之辈为我们讲述的旧日往事。本雅明说:“经验”在现代生活中的贬值,导致“讲故事的艺术”的衰退,进而导致人们经验交流能力的下降,因此从远方归来的讲故事的人越来越少。吴海中、张赤的创作实践,则可见讲故事能力的复苏。
作者刻意搜寻金子般的底层故事,发掘了源自底层社会鲜活的感染力,读来使人热泪盈眶。作者笔下的人物不可避免地面迎的各种苦难,仿佛无处躲藏的箭矢,射向轮回中的众生。李家、于家、绪家几十年恩怨情仇,随处可见历史的苦难、苦难的历史。
《大溪流碧》深入探寻着人性,观看人性的善与恶如何纠缠并铺排出一段烟云往事。据伦理学简要所论,善是人“应当有”的品性,恶是人“不应当有”的品性。可是,古往今来善恶的标准莫衷一是。作者通过文学叙事,观照善恶,构筑了一个善恶不确定的世界。譬如一时糊涂铸成大错的李秧歌,肉身一直饱受良心谴责的拷打,乃至选择素朴的生活而求内心的暂时平衡;复仇前后的于文魁身上是否隐藏着另一半的因子;值得我们深思。小说人物在灭度前,能否脱胎换骨,迎来道德的飞升和精神的救赎?作者持续探问着善恶这一主题,残忍地不断追问下去。很多故事的走向不能一望即知,而作家的安排又极不“友善”,时常出人意料,让人读来觉得不适应,以至于产生心理上的眩昏感。比如,小万子堕入“梦坑”后,五十几年没有回归故土,个中究竟,作者没说,读者费思量也是注定的了。
批阅生死,无疑是这部书的重要要义之一。作者推开了东北民间的生死之门,展示了很多人物弃绝生命的痕迹,有壮美也有凄凉,真正是百味杂陈,描摹了人性的极致。作者笔下的死,不只是灵魂对肉体的离异。
《昭苏太河传》里各色人等均处于爱与痛的交响、罪恶与赎罪的交缠状态中,几乎无人可供倾诉。虽然故事发生年代那么久远,但与现实的勾连清晰可见。指出时代的精神症候,作家也不一定比哲学家、社会学家高明,他们的任务还是揭开伤疤,发现和开掘人性。至此,吴海中、张赤的长篇写作,借史喻今,已经摆脱了单一向度的主题展示,其写作渐趋含混、交融,呈现了时代的复杂性,也昭示了小说写作的难度。
泰戈尔说:“我发明了一种哲学,既能思辨又能歌咏。”《昭苏太河传》怎么看都是这句话的完美实践物,风流慷慨写下寒地黑土民众的欢欣与悲愁,郑重为时间纵深里的心灵加冕。
【注释】
[1] 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5页。
[2] 宋庄:《王安忆的世俗与诗意》,《博览群书》,2014年2期。
(作者系文学硕士,青年评论家,黑龙江绥化学院图书馆长)
责任编辑:万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