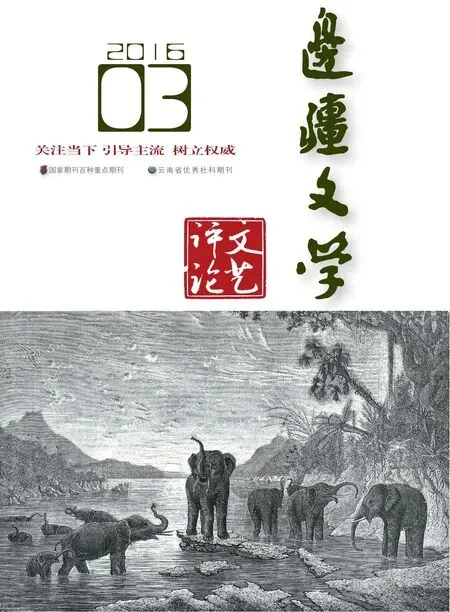时代的号角,艺苑的奇葩
——文化部2015年全国文艺评论研修班观剧有感
◎王红彬
时代的号角,艺苑的奇葩
——文化部2015年全国文艺评论研修班观剧有感
◎王红彬
艺苑评谭
主持人语:本期刊登的六篇艺术评论文章,作者们都以各自熟悉的艺术领域为依托,对某个艺术问题阐述自己的见解。其中,石小保认为被誉为“东南亚明珠”的傣剧,以其浓郁的地域民族特色,民族文化归属感、共鸣感,在德宏州以及邻邦缅甸拥有广大观众,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在我看来,傣剧的保护、继承、创新和发展,为云南地方戏剧建设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单丹华提到,为逐步解决新形势下农村少儿舞蹈培训师资匮乏问题,昆明市文化馆做出的种种努力,从一个侧面,进一步阐述了文化馆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红彬参加文化部在山东举办的2015年全国文艺评论培训班期间,看了不少戏。他着重对其中较有亮点的茂剧《红高粱》、吕剧《回家》作了评论。就茂剧《红高粱》而言,他认为该剧在形式上大胆创新、结构上富于变化,实属一出难得的现实主义的剧作。同时又对该剧女主角的选择、剧中对肉欲和血腥的过度关注与表达,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由此可见,戏剧评论家要善于发现戏剧作品的成败得失,为观众提供一种欣赏戏剧作品的角度和方法,共同提升戏剧鉴赏力。(胡耀池)
岁末之时,有幸参加文化部在山东举办的“2015年全国文艺评论研修班”,白天聆听来自戏剧界“大腕”们的教诲,晚上接受各种舞台戏剧的熏陶,尤其是山东本土吕剧、茂剧、梆子戏轮番轰炸,让人过足了戏瘾。两周的时间,在山东济南的历山剧院、百花剧院、山东剧院、梨园大戏院,先后观看了话剧《茶壶就是喝茶的》《孔子》、山东梆子《南下》《河都老店》、吕剧《兰桂飘香》、莱芜梆子《天唱》、柳子戏《张飞闯辕门》、柳琴戏《沂蒙魂》、吕剧《回家》、茂剧《红高粱》等地方戏。短短两周时间,却较为奢华地享用了一顿山东戏剧大餐。这些剧作,绝大多数是反映现实题材的扛鼎之作,既能彰显齐鲁大地的大气磅礴,也能看出剧作家们对时代脉搏的深厚把握。总体感觉,作为东部地区,山东的戏剧要比西部高出一个层次,其中不乏佳作,《回家》《张飞闯辕门》《孔子》《茶壶是用来喝茶的》《红高粱》等剧目,有着较高的艺术水准或鲜明的特点。这里,笔者就对其中的两部较有亮点的戏剧作一些较为深入的分析。
一、红的不是高粱,而是鲜血
在济南梨园大戏院观看的改编自莫言同名小说的茂腔现代戏《红高粱》,可以说是一出艺术的盛宴。该剧无论主题的设置、艺术形式的创新、舞台的布局、人物性格的塑造等等方面,都可圈可点,堪称一部小剧团上演的大戏。
作为一出传统戏剧,剧中有几处特别出彩的地方,属于创新之举。戏剧开篇,我们便看到一大片火红的高粱,在空空如也的舞台上矗立,紧接着,由莫言手书的“红高粱” 三个大字跳了出来,字是竖写的,出现在高粱地的上方,仿佛是由高粱丛燃烧而突然窜上去的一大团火苗。“高密大地,平坦辽阔,八月中秋,高粱似火。”唱词也是以八月的红高粱作为吟咏对象,似乎是为整出戏定的调子。其实,这样的“红”,不仅仅是高粱,在这部戏中,高密大地上的高粱是红的,女主角九儿出场穿的是红红的嫁衣,大地铺展的是无边无际的红,演员展现的是流动的立体的红,一种几近夸张的色彩,几乎完全覆盖了你的视觉,覆盖了整个世界。在这里。红是舞台的主色调,红既代表高密大地高粱的颜色,也是鲜血的颜色,它更是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关头的血性,这也是一场革命,因而,当舞台上红色涌动,血性涌动,我们的内心和情绪也在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戏剧整体的导演思想是成功的,舞台布景的设置是成功的,由此,它才能向观众准确传达出“红”的意义。这部戏的创新,还体现在两个地方——即戏剧场景表现的大胆。其一是“野合”一场戏,这是戏剧前半部分的一个小高潮。剧中,余占鳌还是使用他的那个招牌动作——一下就将九儿扛起来,进入高粱地。此时,高粱成熟,八月的高粱仿佛在燃烧,天地一片火红,前景后景,都是红红的高粱,而这一对干柴烈火的男女,就在这红红的高粱丛中遭遇,他们没有语言,语言便是燃烧的激情;他们没有动作,动作便是粗鲁的亲昵……九儿呈大字型,像一张巨大的煎饼摊开在地上,饕餮的食客就是迫不及待的余占鳌,随着他一件一件剥去自己的衣服,抑制不住的原始的野性也开始裸露出来,红色的欲望在血管里燃烧,铺天盖地,此时,观众的情绪也被点燃。如此直接和大胆的舞台呈现,在戏剧中是十分罕见的,这样的风格与小说原著一脉相承。剧院的同志介绍,该剧本最后是由莫言亲自敲定,怪不得能够保留这样的场景。下半场的另一个高潮出现在“剥皮”一场。鬼子来查红酒坊,这时,生性怯懦的罗汉抢过余占鳌腰间的手枪,吼道“大哥我情愿为你们挡枪子,也是让你们看看,我刘罗汉不是软蛋!不是孬种!”以此掩护九儿与余占鳌逃跑,最终余占鳌被日军抓住,严刑拷打之下仍未供出同伙,恼羞成怒的小日本于是找来杀驴的孙虎,让他剥了罗汉的皮。虽然孙虎一直叫着“我只杀过驴,可没干别的”,但在日军的刺刀威逼下,逃无可逃,最后还是不得不举刀上阵。危急关头,当日军撕开罗汉的上衣,露出赤裸的胸膛,观众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孙虎真的会活剥余占鳌吗?按照传统的中国戏剧美学原则,直接地、毫不含蓄的杀戮,不仅仅是少儿不宜,简直就是舞台不宜,但不呈现又似乎不足以说明日本鬼子的残暴和兽性,于是,孙虎举起了刀,剜下了罗汉身上的第一块皮肉,紧接着,在日本官兵病态的叫好声中左右开弓,干起了剥人皮的勾当,看得观众热血沸腾、血脉贲张,以致咬牙切齿,磨拳擦掌。老实说,像这样揭露日本鬼子的暴行,像这样直面血腥杀人的场面,在舞台上可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它不但颠覆了我们以往的戏剧常识,而且颠覆了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看完该剧,让人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好像重新回到了那一场七十多年前的惨烈战事。应该说,揭露暴行——作者这一目的达到了,但如此对戏剧传统的颠覆,也让很多人不能适应,无论是评论界还是观众中,都引发了剧烈的争议和讨论,对以往的戏剧美学原则,无疑也是一大挑战。
“人之异于禽兽者有理性、有智慧,他是知行并重的动物。”[1]然而,当一个人处于一种特殊的场景时,这种理性与智慧便瞬间解体。《红高粱》中“野合”和“剥皮”的两场戏,便属于这样的场景。“野合”一场戏,表现的是赤裸裸的性爱场面,这样的场面历来是戏剧禁忌,一般的戏剧都会选择回避,但这样一来,没有热烈的爱,哪来强烈的恨?下一场剥人皮无疑是血腥的,一般的戏剧更不会直接表现。从美感的角度来要求,毫无疑问,这样的表现与传统美学是强烈相悖的。“无论是模仿人物运动或是模仿线形运动……如果太强烈,使我们觉得它出于己体,都可以减少美感。”[2]当然,也许我们会说,如果没有这些血腥的描写,后面的逼上梁山,揭竿而起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于是,作者不回避,正面加以表现,并别出心裁地用一道又一道半圆形的高粱竿子围成屏障,加以屏蔽,再在高粱桔杆后面置一微微凸起的圆形舞台。这样,便使得视觉上的“不适感”稍稍减弱。由是,较好地化解了舞台布置与戏剧美感之间不可调和的严重冲突。
习近平同志在谈到创作应无愧于时代时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并指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创作要触及灵魂,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如何才能触及灵魂?如果我们的文学作品都是隔靴搔痒、欲言又止,那是不能打动人的,不能打动人的作品,又怎么能够触及灵魂呢?茂剧《红高粱》秉承了莫言小说敢于直面人生的传统,形式上大胆创新,结构上富于变化,实属一出难得的现实主义的剧作。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性,在我们肯定这出戏呈现出的诸多亮点的同时,败笔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女主角的选择,50岁的“半老徐娘”演绎20岁的“青春少女”,无疑是个无法回避的硬伤。她那臃肿的身形、沙哑的嗓音,无论是服装还是音响,都永远无法弥补。虽然,从表演的角度看,年龄不应该成为问题,但九儿是个十八九岁青春靓丽的女孩,一举手一投足,无不充满青春与活力,但剧中的女主角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究竟是人才匮乏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们无从知晓,但“戏因人而新”,不重视演员的二度创作,舞台的呈现便会功亏一篑。再次,对肉欲和血腥的过度关注与表达,也使得这部戏有一种“情色与血肉横飞”的感觉。我在想,如果一个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剧院中看到这个场面,将会何等地尴尬?也许,我们的戏剧也该有分级制度,在此之前,如何更好地把握这方面的分寸,就是编剧必修的功课。另外,莫言虽是小说大家,也许对家乡的茂剧背景并不陌生,但对舞台艺术不一定熟悉,这就引出了一个话题:小说如何改编为戏剧的问题。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莫言先生文学成就的意思,只是就这一部戏而言,如果有戏剧大家的深度介入,则由“小说”到“戏剧”的路会走得更稳。著名美学家、作家高尔泰在《莫言的高处与低处》一文中说:“高处和低处之间,是民俗、猎奇的盛大排档,丰乳肥臀,热气腾腾。你只要不嫌腥膻,可以吃得很撑,但没有营养。和那些自以为是在游泳,但不自觉地被潮流带着走的作家不同,他游走于商业和政治、时代潮流和官方意识形态之间,分寸掌握精到,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样的批评虽然令人耳热心跳,但细想不无道理。
二、情牵两岸写人生
这次艺术研修班通知10月11日至21日在山东举行,后来推迟了两天,到了山东才知道,这是因为主办方希望学员能看到23日晚公演的大型现代吕剧《回家》。我听了还诧异:什么样的一出戏值得主办方如此大动干戈?当然,由此也就对这场戏充满了期待。
这部戏可以说是“高大上”:占领了爱国爱家这样的“高度”;从大陆到台湾,从陆地到海洋,距离何其遥远,场面何其宏大;舞台采用了类似于电影场景的布景,旋转的舞台巧妙地将海峡两岸的空间加以转换,很上档次。《回家》根据“感动中国”2012年度十大人物——高秉涵的故事改编,讲述了山东籍台湾老兵函子及战友们对故土和亲人思念的强烈情感。由于回归家乡无望,战友们约定死后将骨灰运回故乡安葬。函子毅然承诺下送归战友骨灰的使命,年复一年捧归战友灵尘,先后背送回一百多个骨灰坛,一了战友心愿。说起《回家》的原型高秉涵,背后还有许多故事:他1936年出生于山东菏泽,1948年跟随国民党部队离开家乡赴台。两岸开放后,高秉涵开始奔波于大陆和台湾之间,义务帮助台湾老兵寻亲。20多年间,他抱回了百余位老兵的骨灰罐,帮他们完成了叶落归根的遗愿。这部戏的成功,首先得益于著名编剧刘桂成的认真采访和精心构思。他不但和作曲栾胜利赶赴台湾,与高老面对面交流,“高老当时70多岁了,但回想起年轻经历仍很激动,他告诉我,每临家门心生怯,每次到了老家门口都不敢靠近。”刘桂成在山东的研修班上给我们讲课时回忆,老人年少离家,有时候实在想家了就爬上附近的凤凰山,在山上望着家乡方向嚎啕大哭,那种真挚感情令人动容,这些都被他移植到了戏里。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两岸亲人不能相见,刘桂成说,他希望通过这部剧促进团结。正是这样一个站得高看得远的构思,决定了这部戏总体的思想高度。
“创作永远大于真实”,这是编剧刘桂成在给我们讲课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刘桂成在改编这部戏剧时,无疑用了许多心思。比如戏剧开场的一出戏,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情节”是,函子外出为母亲抓药被国民党抓丁,但为了营造戏剧冲突,改成了新婚路上被国民党兵拦截,并因为误信亲人被日本打死而从军。还有戏剧的结尾,当两鬓斑白,函子回到家乡,去寻他离家之前娶的妻子,妻子患了老年痴呆症,但却一天天叠着寄情心爱之人的“福万”,福万虽小,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居然装满了整个衣柜,函子打开衣柜门的瞬间,一柜子的福万倾斜而出,仿佛山崩地裂,山洪爆发,惊得函子一下子呆住了。场面十分震撼,也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福万倾泻而出的时候,观众的眼泪也倾泻而出。坐在我身旁的研修班的同学陈洁说,她哭湿了两张餐纸,另一位女同学小齐笑道:两张餐纸不算多,确实,我看前排的一个大娘,那简直才叫泪奔。这样的戏剧效果是编剧下了功夫营造出来。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情景是,二十多年过去,他的妻女其实已经改嫁,而且还有了子女。如果照着这个现实版的思路来写,戏剧的冲突也就平淡无奇。这就是艺术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的不同之处。如果剧作家只是忠实地记录生活,虽然那很真实,但却也就不可能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再现的想象’只是在记忆中复演旧经验,决不能产生艺术。艺术必须有‘创造的想象’”[3]《回家》中妻子二十年深情相守,并日复一日编织福万这个情节,就是艺术家想象出来的,这也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的含义吧?
如果你想知道戏剧的力量,看看这部戏就会明白。或许,正是吕剧《回家》的创作者深深懂得这一点,才营造出了十分感人的戏剧效果。剧场里,戏剧演完了,长时间的鼓掌之后,观众居然没有一个人离去。很长时间,观众还沉浸在戏剧的情景之中,为老兵函子的命运哀叹,为海峡两岸的亲人隔绝扼腕。我很长时间没看到这样感人的戏剧了。如果硬要挑这部戏的毛病的话,那也就是少了几分克制,如果创作者在感情刻画方面稍稍收敛一点,现收后放,先抑后扬,我想会有更大的爆发力。但这对于一部仅仅一个半小时的戏剧来说,应该算是鸡蛋里挑骨头了。
【注释】
[1] 宗白华著《艺境》,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第一版。
[2] 朱光潜著《文艺心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
[3] 朱光潜著《文艺心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
(作者单位: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胡耀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