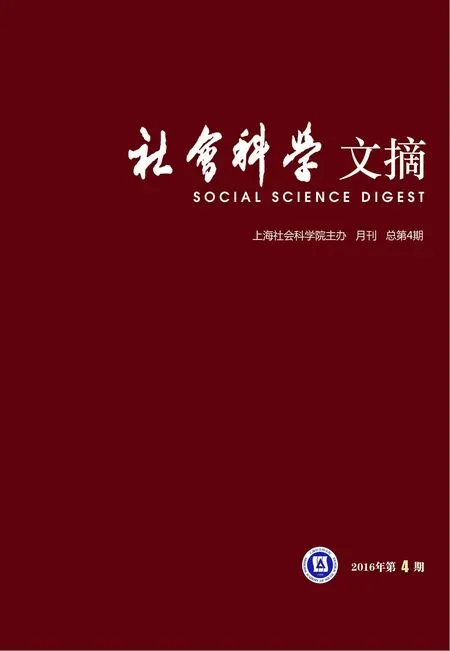革命与“革命叙事”
文/马勇
革命与“革命叙事”
文/马勇
在古代中国,“革命”似乎并不是一个“好词”。《周易》所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总觉得有强辩意思在。
直至孙中山出,“革命”渐成为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新词。这是孙中山的伟大贡献,也是后来国民党史观建构的基础。由此检视国民党主导编写的近代史,革命,包括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都与正统史学渐行渐远,清政府、满洲贵族承担了中国落后的原罪,孙中山、革命党成为救世主,晚清叙事逐渐脱离正统史观、王朝史观,叙述主线不再以统治者活动为主,革命者、造反者成为新历史叙事中的主角。
“革命叙事”之主旨
“革命叙事”与20世纪全球范围民族主义运动相吻合,因而迅即获得知识界认同,并将朦胧中的“革命叙事”体系化,填充丰富内容,至民族主义革命高潮,一个全新的近代中国历史叙事大致成型:
由1840年英人以炮火击破中国的门户,强行输入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中经英法联军之役、中法之役、中日之役、庚子联军之役、日俄之战、日德之战,一直到1925年“五卅运动”以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沙面、汉口、九江等处,对于中国民众的屠杀,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
这是李大钊1926年一篇文章的描述。他认为,这一条浩浩荡荡的民族革命运动史的洪流,时而显现,时而潜伏,时而迂回旋绕,蓄势不前,时而急转直下,一泻千里。它的趋势是非流注于胜利的归宿而不止。简明地说,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只在压迫中国民众的帝国主义完全消灭的时候,才有光荣的胜利的终结。
李大钊并不是专业历史研究者,他的看法只是一种天才般的猜测。近代中国的主题,就是怎样接纳不期而遇的“西方”,进而就是中国能否向西方学习,步入全球一致的发展轨道。回望19世纪全球史,整个东方实际上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作为先发的西方国家,他们来到东方固然不是传教士自诩的那样拯救人类,传播福音,而资本的输出、市场的开拓,才是那个时代的主题。但是,因而将这些活动一概归为帝国主义,李大钊的朋友胡适就很不赞成。胡适竭力反对革命的路,反对革命史观、“革命叙事”,主张以渐进的改良推动中国转型。
渐进改良或许也是一条可以选择的路,这是严复、康有为、章太炎以来知识人最期待的路。但20世纪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无法让中国循序渐进。期待往往落空,期待改良,却引来了革命,革命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主旋律。这是历史事实。
接续李大钊思考近代中国历史叙事的有华岗。华岗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兼具知识人情怀。华岗的一系列作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建构近代中国“革命叙事”的典范之作,回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走过的道路,一方面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承认帝国主义的进入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既为中国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为中国革命准备了无产阶级。
基于这样的理路,华岗那一代倾向“革命”的史学家,大致接受了共产国际、斯大林、布哈林对中国革命的分析,以为伴随着西方势力东来,中国由封建社会渐渐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何干之、李达、瞿秋白、张闻天、吕振羽等,都有比较细致的论述。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话语环境中,近代中国几乎所有事件、人物,都有了很不一样的含义。比如,1898年发生的变法与政变,原本只是中国资产阶级要求权利分享的和平变革、改良主义,与革命毫无关系,但在“革命叙事”者笔下,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改革领导者没有群众基础,没有革命意识,只是幻想、祈求点滴改良,因而注定失败。
“革命叙事”之定型
20世纪30年代,“革命叙事”还属草创阶段。各方面知识人对这个叙事充满怀疑,胡适说:“革命论的文字,也曾看过不少,但终觉其太缺乏历史事实的根据。”梁漱溟不认同胡适对“革命叙事”的责难,但对胡适“反对今之所为革命,完全同意”。他也认为“革命叙事”过于“轻率浅薄”,“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并不足以解释近代以来的中国问题。
“反对就是兴趣的表示,就是注意的表示”,草创期的“革命叙事”能赢得学界大佬反对,而且还有那么多的认同者、追随者,足以显示“革命叙事”的生命力,意味着具有修正、完善,逐渐定型的前景。
使“革命叙事”最终定型并一直深刻影响到今天的,有很多因素很多人,毛泽东等中共高层的理论思考是一个方面,延安、重庆知识界的讨论也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范文澜、胡绳,他们两人将这个模式渐次用于近代史实证研究、具体表述上,用事实证明了“革命叙事”的效用。
范文澜为章太炎再传弟子,具有非同寻常的学术基础,1940年初抵延安,正值整风运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因此契机,毛泽东建议范文澜编写一本适合一般干部阅读的中国历史读本。
毛泽东的建议为范文澜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用武之地。1941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出版第一卷,他计划用三卷篇幅重写远古至当代中国历史。按照计划,第三卷为鸦片战争至义和团时期的历史,后将第三卷单独出版,定名为《中国近代史》。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充分吸收了学术界研究成果,尤其是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但其主要观点,与蒋廷黻存在巨大差异。
与蒋廷黻的看法很不一样,范文澜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饱受侵略的苦难,中国由此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境地。痛定思痛,回顾往事,范文澜以为鸦片战争就是英国资本主义强国殖民扩张的产物,英国殖民者利用资本主义先进技术,驾驶着新式运输工具,带着可怕的杀人武器,还有那精美且廉价的纺织品,前往远东开辟市场。他们不允许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闭关自守,不允许中国孤立于资本主义世界之外。
范文澜赞扬林则徐的抵抗,推许林则徐是“中国封建文化优良部分的代表者”,是清代晚期维新运动思想先驱,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个评价与蒋廷黻的看法正好相反。蒋廷黻说林则徐不肯牺牲个人清誉与时人奋斗,是一个在道德上有亏欠的“伪善者”。而范文澜认为林则徐相信民心可用,因而愿意抵抗,愿意将英国势力拒之门外。
对于蒋廷黻称许的穆彰阿、琦善等外交家,范文澜始终不愿认同,以为这些人的妥协就是投降,就是卖国,就是与外国勾结。在范文澜看来,假如不是穆彰阿、琦善等人妥协主义影响,中国就不会在鸦片战争中失败。所以,范文澜一直以为穆彰阿、琦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投降派阻碍了中国的进步。
与范文澜稍有不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所要着重说明的,“是帝国主义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幻想曾怎样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等”。
胡绳认为:“为了说明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作者当然不需要在写作时丝毫离开历史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露历史事实中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题。”这是作者的自信,也是那个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最普遍的看法。
范文澜、胡绳的研究,将“革命叙事”定型化、经典化,必须承认在1949年之后,“革命叙事”取得了压倒一切叙事模式的绝对优势。这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后果——那就是一个多元的历史理解渐行渐远。
其实,从大历史叙事说,革命与改良相对而存在,都是人类历史上不绝如缕的事件。但社会进步主要凭借改良,也就是中国老话说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人们通过适度保守、适度变革,推动社会进步。但有些时候,革命又不得不发生,没有革命的推动,旧势力不愿自动退出,旧体制无法改良。革命,是一种非常手段,又是社会进步过程中不得已的手段。因而,革命与改良在历史上往往交替发生。一个理想状态,大约像冯友兰曾经期待的那样,大致维持革命与改良的适度紧张与平衡,而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我有时强调这一面,有时强调另一面。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欣赏我促进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道理,既接受赞扬,也接受谴责。”(《冯友兰学术论著自选集》)
“革命叙事”是一个伟大创造,居功甚伟。但一定要谨记“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以及其他一切叙事模式一样,都是为了“说话方便”,并不代表历史本身,更不是一切历史。一个多元开放的历史叙事,依然需要学界同仁不懈努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摘自《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