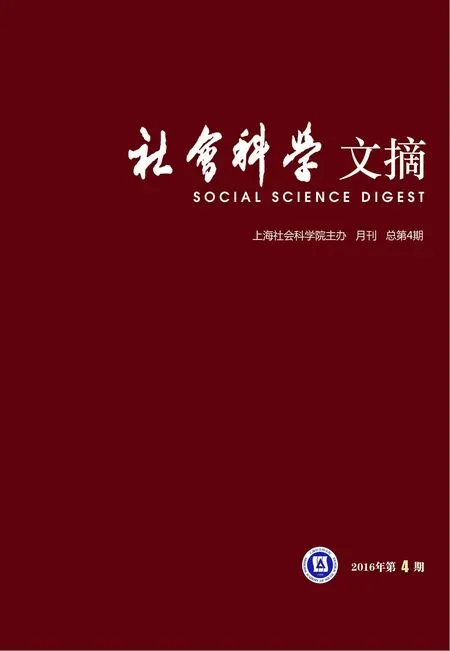嵌入理论视角下智库行政化现象研究
文/傅广宛 杨宝强
嵌入理论视角下智库行政化现象研究
文/傅广宛 杨宝强
问题提出
决策咨询在我国古已有之,并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逐渐从个体发展到群体,最终成为政治体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在制度设计上,秦汉的“博士组织”、唐宋的“谏官制度”、明朝的“内阁制度”、清朝的“幕府”等均具有完善的决策咨询功能。但本文所述智库仅指改革开放后专门从事政策研究与咨询的、相对稳定与独立运作的机构。本文聚焦其行政化现象,即受行政生态影响智库在运行逻辑上与政府存在重叠,并在组织行为上与政府趋同而表现出明显的行政化现象。
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主体的多元分化客观上给“后全能型政府”的政策制定带来了挑战;而智库因其理性的抉择过程、专业的知识技能等弥补了政府的理性不足,为其提供了有力的“外脑”支持,并得到迅速发展。《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的出台更为智库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与系统参考。但客观存在的制度惯性却给智库发展带来了阻力,致使智库虽有独立倾向但依然难以摆脱制度规定的隶属关系。吴月(2013)分析社团行政化现象时亦指出政府在减少财政压力与职能让渡上对社团放手与控制的矛盾心理。薛澜、朱旭峰(2009)在分析思想库的社会职能时也认为“中国思想库大多具有政府背景,所以很难把独立性作为其主要特征”。王锡锌、章永乐(2003)在分析专家知识运用时也认为“由于行政权力的扩张,致使政策制定过程中行政痕迹明显,专家参与政策制定的效果并不明显”,并在专家咨询制度悖论中指出,目前专家论证多是“形式化论证”,是为政府决策的合理性“背书”,专业性与科学性令人怀疑。另外,由于智库专业化发展需要自身的专业化过程,而这些过程的独立性需求和专业权威的形成与政府权威体制逻辑的整齐划一性并不兼容,咨询机构的专业性往往难以被纳入政府治理逻辑的框架内。故此,咨询专家在参与政府决策时不得不放弃或变通专业观念来论证咨询问题,智库亦不得不付出成本去经营与
政府的关系,或寻求组织价值实现,或寻求庇护,在决策中的专业优势并未得到体现,反而遭受行政化嵌入。但学界对此却鲜有诠释,虽有学者在智库存在问题的论述中触及到政府行为的分析,但仅止步于对体制弊端的论说与批判,对智库行政化及其衍生问题则缺乏解释性探讨。鉴于此,我们拟从嵌入理论视角来探讨智库行政化现象的发生机制并对其衍生问题进行分析。
政治嵌入、文化嵌入:智库行政化现象的分析框架
“嵌入”概念最早形成于卡尔·波兰尼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解读。他认为“对经济制度的理解不能脱离该制度形成的社会历史环境,运用抽象化的经济人假设和概念化的供求规律对经济现象解读是形式主义的,只有实质主义的经济研究方法才能在研究经济体系中得到有益成果”。他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中将这一概念引入对经济理论的分析,指出对经济问题的解读不应忽视社会网络的影响。格兰诺维特从嵌入视角对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认知缺陷进行了批判,指出“两学科在研究维度上的社会化不足与过度社会化,忽略了行动者之间的网络与相互作用从而导致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弱解释力”。在分析社会结构基础上,又将嵌入细化为“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两类。而祖金与迪马乔在“嵌入两分法”的基础上,又将嵌入分为文化嵌入、认知嵌入、结构嵌入与政治性嵌入四类,拓展了嵌入的范围与深度。目前,学界多以政府先验嵌入为前提而直接论述嵌入后的影响,已有文献也多是论述社会组织行政化、高校行政化、司法机构行政化现象,从嵌入视角对智库政化现象的研究则相对匮乏。鉴于嵌入内涵的拓展与应用,本文尝试将智库行政化现象纳入其分析框架内,以“政治嵌入”和“文化嵌入”为支点来探讨行政变量对智库的内嵌与影响。
智库行政化现象的产生源于我国高度集中的行政体制与官员考核机制。“压力型体制”下行政手段的选取成为各项任务完成的关键,同样这一手段在对智库的管理上也多有体现。我国智库多属官方,具有行政级别,客观上为政治与文化嵌入提供了便利。经济社会学认为,政治嵌入是政府的经济制度及政策与其他社会组织、阶层在权力博弈与分配过程中形成的。而对智库的政治嵌入则主要体现在政府制度与政策对智库的规制与影响,而智库的发展与运行亦渐趋体现出准政府特征,并由此引致行政化现象的产生。嵌入方式多以正式的制度规范对智库进行管理,通过正式的政策制定对智库的登记注册、运行、人员构成、承接项目、资金来源等进行监管与控制。但在智库地位与参与决策权限方面则多以政府号召和部门文件为主,缺少相应的法律支持,进而导致智库地位弱势与话语缺失。弱势的地位更易造成智库在资金获取上的困难,在资源获取压力的驱动下,智库往往会“理性”地选择向政府靠拢,在运行逻辑与咨询理念上也逐渐与政府趋同。为获取更多后续支持,智库在咨询建议的给予方面往往会或明或暗地进行迎合与诠释,伴随“政治嵌入”的不断深入,智库行政化现象亦更加凸显。
“文化嵌入”指群体共享的价值观念与集体理解在塑造嵌入对象的战略与目标中的作用与影响,而具体到政府对智库的文化嵌入则是政府的官僚化文化对智库的嵌入与主导。囿于我国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规定,智库必须要挂靠在某一政府部门之下。但智库地位的弱势也为挂靠部门的文化嵌入提供了契机。对智库的运作与管理,政府往往通过指派官员或者职能相近的工作人员到智库任职来实现。管理方式也更强调运行逻辑受层级关系的影响与制约。官僚化意识亦不可避免地嵌入到智库运行中,“指标化管理”已属常态。官员的智库任职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强政府在智库内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但智库的准政府特征亦逐渐使其失去客观中立表达政策建议的权力。“文化嵌入”虽能为智库的发展提供一定的人脉关系,但从长远看,官僚化思维并不利于各种思想的碰撞与融合,高质量的政策建议亦难形成。
嵌入依赖:智库的功能“锁定”
政治与文化嵌入为智库在资源获取方面提供了便利,但嵌入的同时也造成了智库“发育不健全”与功能弱化,逐渐形成对嵌入的依赖,引致行政化与各种衍生问题。
政治嵌入依赖是嵌入主体将正式的制度规范与相关的政策设想在受嵌对象内部进行复制和巩固,使其对这一结构产生认同与信赖,并不断强化这种认同,而使智库内更优制度难以发展。智库受生存与发展动力驱使,维持并依赖这种嵌入将是“理性”的选择,而脱嵌于这种关系将面临许多未知成本。文化嵌入依赖的重心在于受嵌对象,行动者一旦嵌入这一关系网络,便很难摆脱其影响,而是“理性”地不断强化和拓展这种关系,并巩固自我在这一关系中的认同。对嵌入主体的依赖不但造成智库自有特征的弱化,更引致组织功能在两者交互发展过程中的“锁定”。
首先,因组织目标和任务不同,智库与政府在职能设置上应有本质区别。但反观现实,智库除承担本职咨询功能外,还附带承担政府其它部门的秘书工作、宣传工作以及其他事务性工作等。先验存在的资源存量掌控多寡,迫使智库的工作重心不得不以政府需求为导向,智库资源的政府挤占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其咨询功能,机构职能的行政化或成常态。另外,“职责异化”也引致智库走向了另一轨道,职责安排的行政取向使其与政府职能更显趋同,甚至于在咨询建议的提出上也明显倾向于领导意图。
其次,作为独立运行的组织机构,智库有其自有的运行机制,但体制制约和嵌入使其在运行过程中也呈现了明显的科层化、官僚化特征。组织层级的政府趋同也造成了智库内复杂的人事关系,智库由于受体制与官僚化领导方式的制约而表现出明显的因人设事,导致效率低下。政府分流、退休人员的智库承接更导致机构内管理方式的行政化与懒散化,衙门作风、官僚主义也影响了智库的运行并引致组织内部人员的官僚习气。
再次,政府对智库的“借用”,一是因为其知识存量的丰裕与专业化,二是因为现代公共政策对政策结果的科学化有强烈需求。但由于官僚文化的主导以及智库对此的依赖等也致使其咨询质量难以提高,咨询过程中的官僚化现象严重,咨询建议的专业性亦失去了公信力。在行政指令压力下,智库往往以行政任务为重心,致使其工作重心本末倒置;对具体调研往往敷衍塞责,各种指标考核充斥其中,而对咨询课题往往难以给出高质量的应答,客观上也造成了公众对智库专业机构的非专业认识。
多维选择:智库“脱嵌”的逻辑进路
智库行政化不但造成其自有特征的弱化与组织功能“锁定”,更直接阻碍了组织创新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构建。因此,压力型体制下智库的多维选择或许是“脱嵌”于政治与文化嵌入的理想进路。
(一)从控制到协作:政府与智库优劣势的动态均衡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的出台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制定了时间表,规划了路线图。“政智”协作将是未来我国政府与智库关系的主要特征。主体间的自有优势与劣势将是两者协作的根基。优势是组织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与其它组织合作的资本。智库的弱势地位阻碍了其发展,而专业化的优势则保障了其生存。强大的资源汲取与动员能力是政府的自有优势,而理性不足与缺失则是其难以克服的障碍。由于两者共处同一体制,价值观念基本相同,这一基础既能使两者的利益实现整合,亦能拓展更广范围的协作。政府的优势嵌入为智库运作提供了支持,并在人力资源、资金支持、运行指导方面为智库的初成长提供“拐杖”。智库则以自身优势为政策制定、执行以及日常管理与运作等提供专业化指导。优势互嵌基础上形成的行事准则与规范也将形成二者共同遵循的文化,并为更广范围的协作创造条件、降低成本。优势虽是协作的关键,但劣势却是创新的源泉。劣势虽有碍自我发展,但却为其他主体嵌入提供了契机。优势虽可以提高双方的认知与信息共享,但也容易造成非正式组织的存在而引致组织运行的低效。而智库弱势的存在也为其能实现自身优势提供强大动力,使其逐步完善与政府的合作以实现两组织的有机融合。鉴于优势与劣势在两组织中的客观存在与独特作用,一个有机融合的协作组织优势与劣势均必不可少,并应在二者间保持动态的均衡。
(二)从分散到集中:智库与政府关系的法制规范
组织关系的随意性和无制度规约是造成智库行政化与独立精神缺失的关键。决策过程的人为主导势必使决策者的主观思维嵌入其中,决策者的理性无知也往往导致决策科学性的弱化。而决策过程中严格的法律规定则能为决策中的科学方法提供表达机会。因此,法制无论在政府决策抑或智库发展过程中均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经验表明,在没有法律和制度规约的条件下,合作中的强者往往有压迫弱者的欲望,并有将其纳入自己管理之下的意图。因此,智库与政府关系的法制规范将是二者长远协作的保障。
立法保护在国外已成为维护智库地位、职能与运行机制的共识。美国的《联邦咨询委员会法》明确了决策过程中的专家咨询为法定程序,并规定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中必须要由咨询组织出具咨询报告,并有第三方组织对咨询报告进行审核监督。日本的《国家行政组织法》也规定各层级行政组织设立协议会和审议会等咨询组织,以确保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我国目前尚未就智库的运行逻辑和管理方式等方面做具体的法律规定,对咨询制度的研究也多以规范性文件和会议为支撑。缺乏强制性的法律做后盾,不但造成智库行政化,也直接导致了政府决策咨询的形式化。因此,唯有法律保障才能避免智库沦为行政部门的附属。
(三)从边缘到中心:专家地位的再确定
政府要求政策制定科学化与专业化,但如何保证决策科学与专业?智库专家地位独立与话语权确立无疑是关键,但压力型体制下专家地位缺失、智库行政化现象亦是客观存在的。王锡锌(2007)从制度设计方面指出“政府的制度设计既没考虑专家角色的独立和对专家角色滥用的抑制,也没注意专家知识对决策结果的有效影响机制,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专家‘角色空洞’与知识滥用”。而专家地位的再确立将是应对该问题的有效进路。
首先在于对专家地位与话语权的保障。我们认为除制定相关法律外,智库专家构成的优化与竞争机制的形成亦不可或缺。不同类型的决策需要不同学科的专家,而同一决策亦需要不同类型的专家。因此,多学科背景的专家参与决策不但可防止决策结果的学科倾向性亦可抑制专家角色的非中立与保障各自的话语权。
其次,智库间竞争市场的形成不但有利于科学思想的出现,更有利于“咨询超市”的出现,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多备选方案,而倾向性明显的咨询建议将在开放的政策市场上面临严峻挑战。
再次,由于政策制定的过程性,专家咨询不能仅停留在政策方案的科学论证上,对方案的不可行性分析、政策执行的事中指导、事后追踪等方面也要有专家参与。因此,政府无涉保密条例的信息应向专家公开,以确保家对决策信息的全面把握,更要赋予专家决策执行过程中的追踪调查权以保障决策后的执行有效。
结论
决策咨询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关键环节,现有文献已多有论述,但对智库行政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问题学界研究还相对不足。本文以嵌入埋论为指导,试图解释该现象的发生机制并期望发掘智库与政府之间的深层密码,为嵌入与受嵌提供更好的现实依据。从嵌入主体与受嵌对象的分析中可以出:首先,智库在草创时期政府的适度嵌入不但带来资金上的支持,而且对智库结构和运行逻辑的形成也具有借鉴意义;其次,制度惯性与官僚文化的客观存在也造成智库行政化现象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再次,智库行政化现象的产生不但使官僚化缺陷更为显性,同时这一缺陷也恶化了智库的发展空间。
(傅广宛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宝强系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13级博士研究生;摘自《理论与改革》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