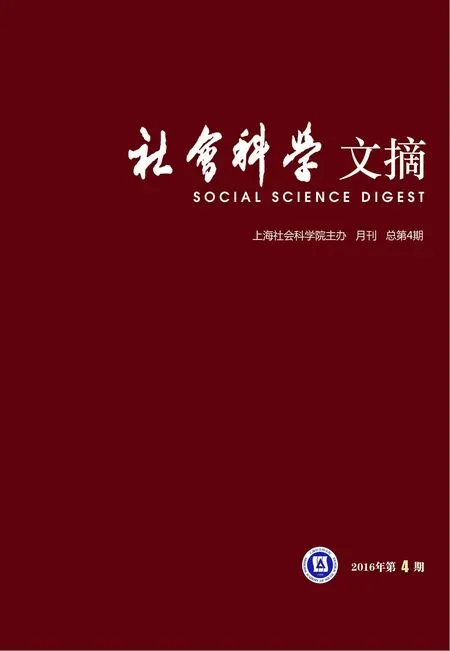对战争的伦理约束
文/何怀宏
对战争的伦理约束
文/何怀宏
我们惯用的对战争的道德评价一般多采用“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术语,即从战争的性质着眼,但我以为笼统地说“正义战争”或“非正义战争”有产生歧义的可能,即不易落到实处,不易具体和明确地评判、衡量与检验,甚至有可能为发动不当战争提供借口。为此,我尝试先对战争伦理进行一些分类,直接和明确地提出一种“对战争的伦理约束”,这种约束贯穿于从开战、作战乃至到战后的全过程,要求政治家和所有相关人不仅考虑参与战争的动机、意图和信念;也考虑战争的行为、过程和手段;乃至考虑战争结束之后的相对直接和比较长远的后果。在这一过程中,我也会讨论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对战争的伦理约束,以及这种伦理约束何以能够成立。
战争伦理的分类
对战争的分类我们可以分成两个方向来进行,一是形式的分类,借助于西方中世纪哲学家和法学家提出的分类框架,可以将战争伦理主要分成两类:一类是战争权利的伦理,或者说开战伦理;一类是战争行为的伦理,或者说作战伦理。沃尔泽在他近年出版的《论战争》中提出,还可以再增加一个战后伦理或者说战争责任的伦理。这是一个有用的涉及形式范畴的分类。
还有一种分类则是具有实质性观点和立场的分类——将战争伦理或对战争的道德态度分成以下三种:一是现实主义;二是和平主义;三是正义战争论。有些学者或再加上一种:军国主义。
我现在想尝试一个新的分类,即将有关战争伦理的观点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将“现实主义”直接称之为“非道德主义”;第二类是将“和平主义”更贴切地称之为“绝对和平主义”;第三类是将“正义战争论”改称为“伦理约束论”。至于“军国主义”,也可将其归于一种“非道德主义”。
在流行的分类中,一般也是把“现实主义”视之为在战争中的非道德主义,即认为战争就是战争,战争与道德无关,战争中的任何暴行都是可能的,也是可以的,甚至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发动战争也是可以的。“现实主义者”认为这就是人类的本性,就是权力的本性,战争的本性,政治权力必然要扩张自己,必然要争个你死我活,面对残酷的战争没有道德存在的余地。
但是,我虽然认为这种观点的确对现实的人性和权力相争的一面有清醒的认识,但将之概括为“现实主义”却不甚贴切。“现实主义”还有更广阔的内涵。上述观点适合于被称之为“极端的现实主义”或者这个领域内的“非道德主义”。首先,许多被认为是、甚至就自称是国际政治领域内的“现实主义者”的人,并不否认在权力和战争的领域内仍然有道德的存在,并不否认对战争仍然必需有伦理的约束。比如著名的现实主义者摩根索所提出的“政治现实主义六原则”中就有两条涉及到道德,他说政治现实主义深知政治行动的道德意义,只是认为普遍道德原则不可能以其抽象的普遍公式应用于各国的行动,但又认为普遍道德原则必然渗透到具体时间地点的情况中。
同样是著名的现实主义者、甚至是带来了20世纪美国战争伦理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向的爱德华·卡尔也认为,说政治人只追求权力,就像说经济人只追求利润一样,只能是一种虚假的论断。政治行动的基础必须是道德和权力的协调平衡。他认为,以为先追求权力,然后道德自会接踵而来,这只是一种幻想;而以为先坚持道德,然后权力自会接踵而来——这同样是一种幻想。两种幻想同样是危险的。当然,这些现实主义者在权力与道德的关系中更为强调权力而非道德,但的确还不是一种完全否认道德意义的非道德主义者。
其次,我想无论持哪种观点,我们都必须先有一种现实感,必须对人性和权力的本性有一种清醒的认识,这尤其是对绝对和平主义的一个必要调节。谈到“和平主义”,也有一个容易导致误解的问题就是,以为持其他战争观点者不想追求和平。而一般被用来举证为“和平主义”的观点,其实常常是一种比较绝对的和平主义。比如托尔斯泰的和平主义,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抵抗,反对一切的战争,期望可以通过所有人一致的精神抵抗和感化能够最后解决问题。但这看来是对人性估计过高,对现实过于乐观了。像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反抗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其面对的其实还是和平时期中相当讲究规则和法治的对手,若面对战争中直接就要杀戮的暴虐的敌人,看来是很难奏效的。而持其他的直接肯定战争伦理观的人们,比如“正义战争论”者或“伦理约束论”者,他们期望的目的也可以是说为了和平。甚至非道德主义者也不反对和平,只是希望一种能给他们带来较大利益的和平。乃至一些军国主义者,也还是会打着“和平”的旗帜作为幌子。
最后谈到“正义战争论”或“伦理约束论”,这实际是“极端现实主义”和“绝对和平主义”之间的中道,即它有一定的现实感,不是一概反对暴力和战争;但也认为应当,也是能够对战争加以必要的道德评价和伦理约束的。但我更倾向于使用“伦理约束论”而非“正义战争论”的概念来表述这一观点,其理由主要是担心“正义战争论”的说法容易造成误解,甚至容易给战争开方便之门。茨维格曾经如此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说:“那是无知的一代人的战争,恰恰是各国人民一味相信自己一方事业的正义性,成了战争的最大危险。”判断一场战争是否正义也是不容易的,它还涉及到战争的目的和意图,而真实目的和意图总是容易被掩饰的。总之,对战争性质是否正义的判断有可能会面临相当复杂的情况,而主张对战争的伦理约束则是相当明确的。它涉及所有各方的所有行为而非意图。它更像是一种普遍客观的边际约束,即附着于所有的行为,可用来判断所有的行为。
此外,我这里还想引用18世纪一位瑞士法哲学家瓦特尔的观点来说明一下我想用这一改称来强调什么。他在1758年出版的《万国法》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所有的交战国都认为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那么他们之间谁是法官呢?他的回答是:因为没有法官,所以要制定调节战争的规则。这种规则,他称之为“国家之间的志愿性法律”。
然而,战争的本性是要尽量摆脱约束的。但现实的战争都可能存在约束。对战争的约束主要有三种,一是来自双方力量的不足,这种力量的不足会约束战争的扩大和发展;二是来自经常是作为战争决策者的政治家,如果这些政治家是有理性的,我们也可以说这种约束是来自理性;而第三种约束则可以说是来自道德,或者说来自战争决策者和参与者的道德良知、社会的道德舆论。的确,在战争中,这方面的约束看起来是相当微弱的,但这也正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总之,仅仅“正义战争”的道德评价术语是不很明确的,不易落实的,而且容易产生歧义,甚至带来危险。相比之下,将一种“伦理约束论”结合于我们前面谈到的“开战伦理”“作战伦理”和“战后伦理”的三个方面,则可以将问题细化和明确化:即首先要严格考察介入一场战争的理由,应该说这种理由除了保护生命之外几乎不可辩护——由于考虑到战争的原始本性就是杀生,战争一定会带来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那么,除非它能够直接保护和减少这种损失,那就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一定要介入战争。其次,即便是为了止杀而不得不介入的战争,也还要考虑作战伦理即手段的伦理,这方面应该是有明确的国际法可循的,比如不可屠杀平民,不可杀害俘虏,等等。最后,还应考虑战争之后的结果——如果它并不能够带来稳定的和平,反而使战后的国家或地区继续有各种暴力的肆虐,甚至造成比战前还要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那么,这样的战争也是全然不可取的,而在战争之前或之初决策者就应该充分地考虑这种结果,承担起自己的道德责任。
战争伦理何以能够成立?
探讨战争伦理的确还有一个困难的问题就是,战争伦理何以能够成立,或者说,为什么战争应当接受某些基本的道德约束,其理由或根据何在?这是一个需要回答非道德主义的挑战的问题。
我们在此从沃尔泽的论证开始。沃尔泽提出了一个“战争的道德现实”的概念,他认为即使在战争中,绝大多数人还是想合乎道德地或看起来合乎道德地行动。我们之所以如此因为“我们的争论和判断经过长时间的重复之后形成了一种现实,我想称之为战争的道德现实——也即,道德语言所描述的或必须使用道德语言才能说出的全部经验”。并且,他相信“我们对道德词汇有十分普遍和稳定一致的理解,因而共同的判断是可能的”。
但是,这种“十分普遍和稳定一致的理解”到底包含什么内容,沃尔泽谨慎地语焉不详。他在后来的《论战争》一书中倒是谈到:“为什么发动战争是错误的?我们都知道答案。因为战争要死人,而且常常死伤众多。”也就是说,战争的恶就在于它的杀人,甚至是以残忍的方式不分对象地杀任何人。而我们可以从中引申出来的一个正面的原则看来就是保存生命。
于是,如果说在“正义战争论”方面我们可以考虑比沃尔泽的观点更谨慎地退后一步,在论证战争伦理的可成立性方面我们或许可以比沃尔泽更前进一步,即直接提出保存生命的原则作为给战争加以伦理约束的理由和根据。在这方面,我想先重新诉诸近代经典。
尽管格老修斯也主张正义战争的理论,但他是比较明确地将保存生命的原则视作是正义的基本标准的。他认为自然法是正当理性的命令,甚至上帝自己也不能对它加以任何改变。而按照自然法的规则,如果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全我们的生命和身体完整,那么这战争就是正当的,而如此理解战争的话,正义的战争也就主要是一种保卫自己和同胞的生命的自卫战争。但是,他也指出,这一原则是要建立在公平的理念基础上的,即不是单方面地强调一方的生命而是各方的生命,要区分攻击与自卫。
我们在格老修斯的论证中,可以发现一种诉诸普遍性的论据。他推崇古希腊赫西俄德的一句话:凡是在许多国家中普遍流行的任何看法都必定有某种共同的基础。这种普遍性或许可称之为是一种诉诸经验的普遍性。而康德的“可普遍化原理”则可以说是诉诸一种形式或逻辑的普遍性。即几乎所有人都希望生而不是希望死,如果你不想自己无端被杀,那么,你也就不应该这样杀死别人。如果允许非保护自己生命的杀人成为一条普遍法则,即人人都可随意杀死并未威胁到自己生命的人,那么,最后就是人类毁灭,进而取消杀人本身。
关于生命原则的内容,我认为基本的保存生命的规范原则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是对生命的直接保障,即不杀害生命,不压制生命,使生命有安全感;第二是满足生命的需求,供养生命,使生命能够维持下去。而从作为普遍价值的生命原则来说,第一层含义是人的生命本身是宝贵的。所谓“本身是宝贵的”,就是说,它不是作为手段和工具的宝贵,而是作为“自在自为的目的”的珍贵。这就引申出它的第二层含义,既然生命是本身宝贵,那么任何一个享有生命的人,任何一个活着的人,所有的人,他们的生命都是同等宝贵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应当受到尊重和珍视的。第三层含义就是,保存生命、尊重生命这样一个原则,在次序上是最优先的,优先于所有其他的道德原则。
应用到作为政治单位,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战争上来,则可以说,生命原则主要是强调其第一方面即对生命的直接保障,即不杀害无辜者的生命。在诉诸战争的时候首先要考虑这是否是为了保全生命的目的,并的确能达到减少生命损失的结果;在战争进行的时候则考虑区分对象,包括不以极端残忍和侮辱的方式杀害哪怕是对方的军事人员。至于第二方面即保障生命的基本物质需求方面,则主要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公民的责任,但是,在战争中也要考虑通过对一个城市或地区的长期围困和封锁使对方居民大量死亡是否符合伦理的问题。就像罗尔斯所言,在正义原则中直接地提出保障基本权利胜过试图间接地达到这一效果。
战争与伦理都是古老的现象,但广义的战争无疑比伦理还要古老。因为它还可以追溯到动物界,而伦理只是随着人类的意识、理性产生才出现,是特属于人的现象。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战争伦理是人性对动物性的一种约束,道德理性对原始攻击冲动的一种约束。战争的原始本性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搏斗和相杀,而且是一种大规模的、成建制的群体搏斗和相杀,至于它光荣或伟大与否,乃至正义与否,则是第二位的属性。战争不仅难以在人类生活中绝迹,甚至有时造成好的结果,但它归根结底并不是人类的光荣。
问题还在于,战争常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或者说,某种合力会使本来没有战争意愿的人们和国家却卷入了战争,甚至是狂热地投入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个范例。它是一场本来所有方都不想真正打的战争,最后却打得无比惨烈和持久。所以,对战争的性质和逻辑应该有一种自觉意识,对战争的伦理约束更应该有一种自觉意识,这样才能比较好地防患于未然。
《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国家再大再强,也不能好战,好战必有灾殃,甚至国家危亡。同时,忘战也是不可以的,这不仅指一个国家要强固与本国相称的国防,还应该指同时还要讨论和研究战争及战争伦理,以保证只涉入正义的或者说自卫的战争,且在卷入战争之后也总是正当地进行战争,并随时争取和平的机会,担负好战争的“善后”。而在聚集反战和正义战争的力量方面,学者和知识分子还有一种特别的责任。即他们不仅应该深入地研究战争伦理,而且应该努力去影响社会的舆论。
茨维格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战前各国的巨大经济和科技成就普遍地使人们陷入盲目的乐观,人们也不了解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他们看来,战争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奇遇。这样,由于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和防范,当大战突然降临的时候,无论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意大利、俄国、比利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就都顺从地为“战争宣传”服务,而不是与之斗争。敌对双方的所有国家的群众几乎都一度陷入亢奋的状态,于是,大战的车轮就开始毫不留情地碾过无数生命的血肉之躯了。
所以,为了保存生命,预防战争,在和平的时期就应该保有对战争、尤其是约束战争的伦理的深入研究和广泛传播。就像政治权力必须约束和驯化一样,对战争这一暴烈的权力更应该时刻保持警惕,仔细研究和实践如何约束和驯化战争,尤其是约束那种将对人类生命造成最大危险的战争形式——总体战的战争形式。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摘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