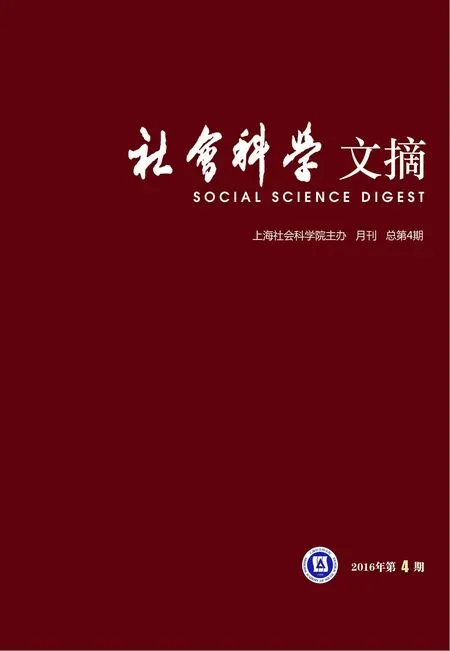中国人口学的理论重建
文/穆光宗
中国人口学的理论重建
文/穆光宗
破除“中国人口太多”的迷雾
对中国人口问题,各界始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中国人口太多”。当人们感受到人口拥堵的时候,就会同声感叹:人口太多。这是事实,但这与人口总量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因为我们也会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感受到人口太少——例如夜深人静的街市、穷乡僻壤的边地。“人口拥堵”只是人口集聚所带来的暂时性人口压力,是会转化和消散的。
放眼全球,中国固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人口第一”就等于“人口太多”吗?虽然很多人的潜意识中有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形成了某种根深蒂固的“集体自觉”和“国民意识”,但认真分析,却发现问题并不简单。直言之,这种看法是似是而非的。
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人口的“社会养育力”很低,难以负担这么庞大的“人口存量”,也恐惧“人口增量”的冲击,但这是体制和制度的问题,与其说是增长性人口问题,不如说是制度性人口问题。一方面社会福利是政府计划分配的,人口增长对体制内公共福利计划分配产生了压力;另一方面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由于缺乏自由,人口的正能量如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生产性没有得到有效释放。
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口很多,总量很大,但没有证据说中国人口“太多”,更不能以此作为理由倒推回去,作为强制性出生控制的理由。人口养育力至少有四个概念:自然养育力、社会养育力、制度养育力和家庭养育力。自然养育力是资源环境潜在的养育能力,具有很大的弹性。社会养育力是指在一定的科技水平下社会总体的养育能力。制度养育力考虑了福利分配保障制度,不同的人口处在不同的福利制度安排中,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养育能力。家庭养育力是家庭的供养能力、抚养能力和赡养能力。人口养育力是分层分类亦是动态可变的,生态系统越是复杂,其养育力越是深不可测。对于一个地理广袤的大国来说,无论是自然养育力、社会养育力还是制度养育力,都具有极大的张力和弹性,随着自然、社会和制度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理论上并不存在某个静态确凿的人口极限值,所以宏观意义上人口控制的必要性是不成立的。只有单位最小的家庭养育力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各个家庭所感知、预见和掌控,也正因为家庭养育条件的差别化,所以家庭决策的自主性和多样性必须得到尊重,绝不能“一刀切”和“齐步走”,这是家庭生育计划之所以在全球通行的原因。
退一万步讲,即便我们认同中国人口多了,我们也要分析是“存量”还是“分量”问题,是“流量”还是“增量”问题。从人口学角度看,人口的存量问题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源开发来解决,人口分量问题可以结合男女老幼分人口的不同社会诉求采取不同的解决对策,人口流量问题可以通过有序的人口流动迁徙、合理的人口分布来解决人口过多集聚带来的人口拥挤现象,人口增量问题可以通过家庭计划、优生优育等来解决。
人均指标的误导
“人均”指标最简单,也最误人。13亿中国人口是13亿中国人民的数量表达,他们是有生命的,有尊严的,也是有权利的。当我们将“人口”简单化为数字、理解成分母的时候,就已经远离了人权的高贵,进入了人数的误区。
“人均”指标意味着人口的零增长和负增长是值得欢迎的,人口的任何正增长都缺乏正面的价值。正是在“人均”指标理论的指引下,中国人口变成了“负人口”,人口出生变成了“负价值”。由此就产生了“少生就是一切”“生育率越低越好”“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导向和做法。
“人均”指标理论是本末倒置、极端片面的。用这种可笑的理论指导中国人口工作的实践风险太大,结果是长时期里错误地左右了中国人口发展的方向,这就是人口的萎缩弱化、生态失衡和结构坍塌。
人口红利理论证明了社会财富其实是人口力量的积极转化,当我们将财富与人口建立起联系时,就看到了人类人口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在人们的印象中资源是外生的,是自外于人口存在于世的,例如,水、大气、森林、矿产、生物等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一切自然资源。财富是资源的转化,包括我们的一切生活用品和资产,这种转化的源泉既来自自然资源,也来自人力资源。
考察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必须考虑人口的社会属性,也就是说,要区分“数字人口”(或“公民人口”)和“权属人口”。在这块国土上,很多资源都是有产权和归属的,不属于全体的“公民人口”,而是属于小部分的“权属人口”,虽然同是公民,与国土资源的关系却可能完全不同。区分这两类人口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数量关系,归根结底是权属关系——有权利才有归属,继而才有拥有、享有的问题。忽视权利和归属,是说不清人口与资源的实质性联系的。这样,选择什么样的人口做“分母”、什么样的资源做“分子”,然后分析和看待分子与分母关系的变化,我们就心中有数了。人口的人类行为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既有负面的破坏性行为,也有正面的保护性行为,还有中立的过境性行为。
人口总量是最简单的抽象,掩盖了人口分量的种种差别。总人口是分人口或者说亚人口(subpopulation)之和,没有分人口,就没有总人口。问题是在一个人口总体中,分人口的角色、地位和作用是很不同的。例如,我们将“青少年人口”定义为“潜力人口”,将“青壮年人口”定义为“实力人口”,将“老年人口”定义为“余力人口”。一切有爱心、有能力、有作为的人口都是国家的“希望人口”,都能给社会带来可喜的人口红利。主导一个社会发展的人口力量来自上述的三个“分人口”,他们的数量、素质、结构、关系和行为都会产生不同的人口力量。
总人口终究是“表象性人口”或者是“数字性人口”,带有不同社会标识的分人口才是“功能性人口”,才是实际发挥作用的人口。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个事实,总人口因为过度抽象,成了“同质性人口”,而分人口加上了社会标识,所以就成了“异质性人口”。分人口问题远在总人口问题之上。人口总量的压力主要体现在同质性需求和行为上,如对食物需求的压力、对住房需求的压力、对排泄需求的压力以及对交通需求的压力。
如果说中国人口太多,那么从分人口的角度看,到底是青少年人口多了,还是青壮年人口多了,还是老年人口多了?我们能够找到答案吗?从总量看人口不免流于表象。如果说总人口过剩,那到底是总人口中的“谁”过剩了?是你、是我还是他?质言之,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中国人口太多”都是一个伪命题,是不成立的。
然而,回望过去的35年,中国采取了自绝后路的、慢性自杀式的严厉控制人口的战略,就是基于“中国人口太多”的错误认识和“人均”理论的错误引导,在静态养育力的理论假设之上,将臆想中的人口存量的压力怪罪于其实在微观角度看已经很低的出生人口增量,不断丧失大国崛起最必要的年轻人口的战略储备。
古人云:“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中国人口问题却绝非“一锅汤”那么简单。中国人口是否太多从总量上是无法得出结论的,“中国人口太多”是基于我国人口总量大、资源相对紧缺而言的。但人们并没有找到客观的标准。“适度人口”的概念是有用的,但千人千面,并没有达成共识,操作性更是存在问题,只是“看上去很美”。
从人口分量问题来看,也是相对的关系,与特定历史阶段的体制环境和制度安排有很强的联系。历史地看,我国的人口问题是“体制性人口问题”或者是“制度性人口问题”,要解决人口问题,归根结底是要考虑制度创新,引入社会正义,倡导和谐发展。即便是高生育率问题,也可以通过宣传和利导得以妥善解决,根本无需通过强制的手段、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去降低生育率。
“人口问题的本质”和“人口发展的本质”
为何说“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经济社会的发展包括合理的制度创新是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本文对“人口”的三个基本看法是,人口的性质是“人力资源”,人口的能量是“人力资本”,人口的出路是“人力开发”。
首先,人口表面是“数”,实质是“人”。人乃天地之秀。人本主义人口学强调人的主体性、社会性和创造性。也就是说,人口问题的出路在于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所以需要赋权自由和保障人权。人口不仅是“资源”——不同于自然资源,它是能动的具有创造性的资源,而且是“财富”——人是幸福的源泉,人多人气旺,人多力量大,这是积极人口观的两个立足点。
其次,人口的力量和能量在于“欲望”和“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有自然形成的天赋,也有后天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包括智慧资本、知识资本、技能资本和道德资本。遗传和环境共同形成了智慧资本,同质人口有“成长”过程,社会人口有“发展”过程。
再次,人口是压力还是动力,取决于“人力开发”。人力得以开发,就是人口红利;反之,就是人口负担。
人口问题具有相对性和变异性。万物处在流变之中,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人口问题。我们判断人口问题,必须有“坐标意识”,将变化的人口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中来考量。人口的多少、数量的适应性并不是靠自身特征来说明,而是凭社会条件来解释的。人口也不会固定在某个环境中,而是在不同的环境中流变。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口没有节制的增长的确给人民和政府带来了很多的困扰。曾几何时,人口增长的压力主要来自高生育率;普通家庭的养育压力很大,吃不饱饭,上不起学,做父母的很辛苦;一个年轻型人口的国家则感受到了就业的压力。于是,人口成了问题的“替罪羊”。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并非很多夫妇希望养育平均4~5个孩子,而是因为缺乏避孕节育的知识、手段和方法,才导致了很多“意外怀孕”和“非意愿的生育”。中国需要人口友好型的制度和体制环境。质言之,不是发展水平过低、养育能力过低才导致出生人口成为负担,而是消极的人口观和限制公民自由和缺乏权利保障的制度安排将人口变成了问题。
进一步地,“人口发展的本质是平衡问题”,我们需要引入“人口生态”概念来理解和把握人口的结构、社会关系和功能作用。再具体点,男女老幼构成了人口生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人口生态的多样性、平衡性和进化性为前提。人口问题大致可分三类:
其一,人类发展问题,包括人心人欲、人类行为问题。或者说人的发展问题,涉及人的权利和保护——投资、化育和素质养成(道德、健康等)以及机会和选择等问题。需要正确理解以人为本,不是人类高于一切,而是生态重于人类。人本的含义是在尊重生态文明的前提下重视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人力资本的投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人的发展不足、人的发展畸形、人的发展片面、人的发展失败以及“人能否守其德”、“人能否尽其才”才是人口问题的内核所在。这是基于人口的主体性原理得出的结论。
其二,人口结构问题。人口生态问题表现为带有不同标识但有内在联系的亚人口之间关系失衡甚至断裂的问题。例如,性别比例失调导致大量适婚男性找不到对象从而衍生出很多问题,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外出导致“留守父母”的赡养脱离从而衍生出老难所养、老难所依、老难所乐等问题,等等。人口结构问题表现在一类分人口需要另一类分人口支持的时候却遭遇“人口失助”的尴尬。大城市老龄化程度高,依赖性人口比重高,对扶助人口有长期性需求,但北京等地已经出现“年轻人口短缺问题”和老年人口“失助风险”。老龄化城市存在着年轻人口供给短板的潜在风险。
其三,人口与发展问题,就是广义的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中国已经出现“人力短缺”问题,突出如2004年以来出现的“民工荒”。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可以说是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所带来的,也可以说是长期的超低生育率的恶果,当然也与供求关系所产生的结构性错位有关,应该理解为多因一果比较合适。年轻人口是国家的最大资产,我国却面临数量减少、结构脆化、健康流失和责任缺失等多方面的挑战。201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200~300万已经拉开“年轻人口亏损”的序幕。生育独子化的危害太大太深太广,长达35年的一胎化固化了人口发展的错误方向。“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说明了驱动高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力量是以人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发展,是高抚养成本下生育约束力的作用,也是追求个人自由生育抗拒力的影响。计划生育有不同的面相和做法,需要反思的是强制计生的“合理性”——无论是一胎化还是二孩化。我赞同政府支持下的“自主生育”和“家庭计划”,避孕节育其实是工业化时代以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强制计生肇始于计划经济,最初计划生育就是在计划经济年代提出并实践的,但问题的症结却是“权力的傲慢”,是政府的“公权力过于强大”而公民的“私权利过于弱小”。
占里的遥望:回归人口发展的原点
占里,这是一个因古老神奇的“换花草”而闻名的侗族山寨,地处贵州从江县。山寨的每家每户都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多少年来,人口一直零增长,人均收入却高于其他村寨。占里有朴素的节育思想和神奇的节育制度。这是一个掌握了生育秘密的古寨。奥秘在“换花草”,神秘的药草可以改变胎儿的性别。据说药材只有两根,药师掌门人传女不传男。药师给即将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妇女是煮好的不同药水,生了男孩的给的是怀女胎的药水,反之生了女孩的给的是怀男胎的药水。神奇的是,居然家家如愿以偿。几百年前寨老们立下寨规,每家只能生两个孩子,同时不能有两个儿子,否则逐出山寨。通过寨老、寨规、药师共同创立的适度生育文化,占里的人口生生不息地繁衍到了今天,不仅实现了人口自身的长期均衡发展,而且与资源环境保持了长久的平衡关系。
几百年来生育计划为什么能够成功?是因为在近乎封闭的人口系统中,守住了生育的底线——平均必需生育两个孩子,同时维护了生育的公平——不仅性别平衡,而且家家平等。
贵州占里社会人口调控的意义在于通过特殊的医药技术实现了适度生育的社会理想。智慧的侗族先贤通过完美的“两胎计划”实现了长久的社会和谐——人口变动与资源环境的平衡,以及人口自身的平衡发展——人口的更替平衡、性别平衡和代际平衡。虽然这个案例无法复制,但它的实践却说明了人口生态平衡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口发展规律,而维护更替水平生育率是实现人口内部均衡发展的必然要求。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摘自《江淮论坛》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