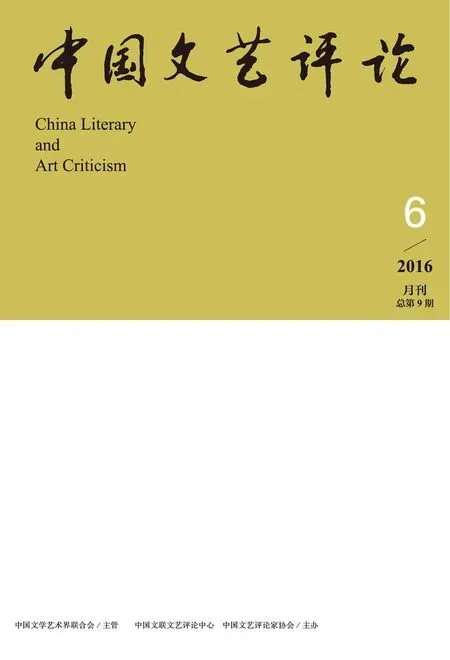戏曲文学的剧场性
王长安
戏曲文学的剧场性
王长安
中国京剧创造了演员时代,创造了“四功五法”,创造了几近完美的中国戏剧表演体制,把传统的写意美学发挥到了极致,但最大的短板在于戏曲文学不给力。其实,对于戏剧而言,表演更多属于技术层面,是一种工具,一种散碎和自为状态,须有文学进行整合、梳理并赋予新意。对中国京剧那么一门精致、完美、高峰属性的舞台艺术样式而言,断不该仅红火百余年就风光难续的。这其中,有意无意的戏曲文学意识的淡化或者说戏曲文学的边缘化正是其病痛所在。即便只从剧场性出发,戏曲文学的艺术地位也应得到足够重视。戏曲文学对于戏曲的剧场性应该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一、道德评价:为弱者代言
剧场是大众的课堂,更是大众的公堂。千百年来,中国普通百姓基本就是从这里获得做人做事的道理和一般社会知识,形成自己的人格构架。但是,仅有“课堂”是不够的,百姓们还需要在剧场中共同体验一种惩恶扬善的快感,验证自己的道德判断,以坚定他们为善、向善的决心和信心。戏曲演出一触及这样的命题就会获得强烈的剧场性。这也是中国戏曲自有可见的戏曲文学作品以来贯穿始终且久演不衰的题材领域。无论是《永乐大典戏文三种》,还是南戏四大本之“荆、刘、拜、杀”;也无论是肇始于元杂剧的包拯系列,还是泛滥于包括京剧在内的花部地方戏的“负心汉”“不孝子”“恶媳妇”“刁婆婆”系列,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戏曲文学对大众评判欲望的积极满足。也正由此,中国戏曲从一开始就与观众建立了同呼吸共命运的观演关系,成为真正意义上为大众的戏剧。
我至今不能忘怀当年传统戏解禁,庐剧《秦香莲》在合肥连演三个月,不仅市民半夜排队买票,郊县的农民也开着拖拉机潮水般地涌来看戏的盛况。这里不排除有对传统戏解禁的欢呼和拥戴,但我以为更多的则是长期以来未能宣泄的对是非善恶的评判欲望的喷涌与释放。人们更多的不是要欣赏唱腔、观看表演,而是争取对一种社会现象的无声发言,表达他们的情感取向。有一次演出中,竟有观众当场高呼“向包公学习”的口号,可见人们对法治、对公平、对善恶公判的渴望。相比之下,弱者更需要公平和秩序,普通百姓更渴望法制和正义,因为只有法制与正义能给他们安全和保障,只有公平和秩序能给他们机会和利益。通常在人满为患的拥挤混乱场合,呼喊“不要加塞”最多的都是老弱妇幼和力不如人的弱者。因为拥挤和加塞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他们,所以他们也就比身强力壮者更需要秩序。此时如果有人出头管理,或者惩罚了加塞者,他们就会倍感欣慰。戏曲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建设者,戏曲文学若能关顾社会大众扬善抑恶的心理需求,为弱者代言,把当今大众普遍关注的问题,通过戏曲文学予以适当反映,或许可以促进问题的解决,而戏曲的剧场性就会大大增强。
二、情感天地:为人性作证
剧场是情感张扬的天地,也是验证和托付情感的场所。中国老百姓常以“哭”来评价一出戏的好坏。是否哭,哭到什么程度,往往成为戏之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常言说,人不伤心不掉泪。哭是心灵接受逆向触动的结果。一旦遭遇这种触动,心灵受到炙灼,纵是泪不轻弹的铁男儿也要泪滴千行。这是人性,是善良与同情的本能。
高明在《琵琶记》开场词中说:“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其意是要求戏曲文学应当不止于“乐人”,而要攀登“动人”之境。如何“动人”?徐渭认为“无他,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传之亦弥远”。由此可见,高明所说的“动人难”,难就难在“摹情弥真”上。戏曲文学要写出人的真情实感诚非易事。高明为此作了努力,他收获了成功。按照徐渭的说法,《琵琶记》的“《食糠》《尝药》《筑坟》《写真》诸作,从人心流出……最不可到”。所以,这出戏打动了观众,满足了观众的人性需求,成为南戏的代表作且流传至今。徐渭由此也告诉我们,只要写出了真情实感(摹情弥真),“动人”也是不难做到的。
优秀的戏曲文学大都十分注重“摹情弥真”,在情感上做足功夫。《牡丹亭》“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西厢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真情”;《赵氏孤儿》“慷慨赴死”的侠情;《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悲情”;《天仙配》“天上人间心一条”的“纯情”;《梁祝》“化蝶”的“诗情”;《徽州女人》“等待”的痴情以及《挑山女人》“艰难挑山”的“苦情”;《白蛇传》“为爱而付出”的“柔情”等,都是既写出了人物的独特情感,又代表了观众审美的共同经验,表达了作家对大众情感取向的认知与尊重。从而,使观众人性中向往情感美好的愿望得到宣泄;爱美、向善、慈悲、温柔的本能得到验证。不仅如此,在戏曲文学中,即便是塑造“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那般铁血情感、钢肠傲骨,也是大众人性构架中的一个固有组成部分,同样是观众所需要和期待的。只不过戏曲审美更多的是要追求“怜悯与同情”,过于强悍刚烈的情感类型容易拒斥观众的同情欲。正所谓“不知心大小,容得许多怜”。当今的戏曲文学之所以乏善可陈,症结就在只说理,不说情;只讲表达,不讲感动;只走场面,不走内心;天马行空,不接地气;不是无情,便是矫情……面对这样的戏曲文学,表演再好也无力回天。舞台应是情感的天地,而非说教的讲台,更不是作家玩自我的包厢。宇宙中永恒的东西是可贵的精神,我们应当努力在舞台上构建情的天地。
三、智慧沙龙:给大脑加餐
看戏是一个领略智慧的过程。戏曲文学应当包含足够的智慧以给受众的大脑加餐,这也是戏曲剧场性的重要来源之一。
就戏曲文学而言,其智慧表达主要有三个层面,分别为体现在结构中的情节智慧、体现在角色上的人物智慧和体现在文辞上的语言智慧。当然,这些均需由作家智慧来完成。
先说情节智慧。我们常说戏要“抓人”,要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这实际上是对观众看戏经验的挑战。让观众不容易发现剧情走向,更想象不出接下来的情节是什么。情节中深埋着发现智慧的奇谲和快感。元杂剧《灰阑记》,在亲子鉴定尚无科学手段的情况下,让包拯把有争议的孩子置于灰阑之中,任由一真一假两位“母亲”去争夺。并且言明,谁把孩子夺到手,孩子就归谁。结果,真母亲因害怕孩子在争夺中受伤而不忍出手,假母亲毫无忌惮,成为赢家。岂料,这正中包拯圈套。包拯借此判断出谁才是孩子的真正母亲!使观众解颐、折服,油生敬意。这一智慧的情节使剧情发生陡转,一场严重的危机顷刻化为乌有。观众由此获得观剧的快感,增强了演出的吸附力。
再说人物智慧。情节智慧虽是戏曲文学结构的重要桥段,但其往往与人物智慧密不可分。因为情节是性格成长的历史,是人物行为的现实状态。所以,要想使冲突更具特色,人物更具亲和力和可辨识性,戏曲文学应当努力显现人物智慧。黄梅戏《女驸马》中,女扮男装、考取状元的冯素珍被误招驸马入了洞房,在与倍感委屈的公主对话中,她智慧地坦陈利弊,即“一对红妆怎配婚”和“公主倘若杀了我,岂不成了未亡人?”逻辑严密,遂令公主陷入“杀也杀不得,留也留不得”的两难之境。只好完全由冯素珍占据主动,听凭她的安排,依她的“道理”行事。最终导演了一幕既解了自己的危机,又救了身陷囹圄的夫君,还顾了皇家嫁女的体面的各得其所的大喜剧。人物的智慧,最大限度地获得了观众的认可、钦敬,提升了看戏的快感。
最后是语言智慧。它不仅体现为修辞造句的机巧、别致,而且表现在作家借人物之口说出“人人心中都有,个个笔下皆无”的格言警语。尽管作家智慧渗透在戏曲文学创作的各方面,但这些格言警语是提升戏曲的文学等级、实现剧场认同的重要表征。例如,一部《沙家浜》最引人兴味的是阿庆嫂与刁德一、胡传魁周旋的那段三人对唱。阿庆嫂的通篇唱词显现着极高的语言智慧,令刁德一节节败退,不得不为其“说出话来滴水不漏”的智慧而折服。那一句“人一走茶就凉”成为超越剧情的经典,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知世界。此外,如《窦娥冤》“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西厢记》“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红灯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智取威虎山》“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唐知县审诰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等,都是既能照亮作品,又能照亮世界、照亮人生,与观众和鸣共振的智慧语言。
还有一种语言智慧则体现为作家的学识涵养,亦是提升观众观剧热情的重要元素,使观众借此进入某种知识领域。如黄梅戏《夫妻观灯》,当夫妻看到“周朝灯”“三国灯”时,妻子便解说道:“周文王去访贤,无稽带路在河边。姜子牙坐车辇,臣坐车君背辇。愿保周朝八百年。”“驾坐西川刘备灯,默想荆州关公灯,喝断壩桥张飞灯,怀抱阿斗子龙灯,神机妙算孔明灯。”这些无疑是在给大众普及历史知识,为大脑加餐,使观众在看戏中获得收益。此外还有饱含高超修辞技巧的唱词和语言,如《西厢记》“碧云天、黄花地”,《牡丹亭》“袅晴丝吹来闲庭院”等,也都彰显着作家的语言智慧,撩起观众的学习欲,放大了观剧效果,增强了剧场的号召力,使作品成为文学经典。
四、时尚橱窗:给生活示范
戏曲文学还应是世风前沿、时尚的橱窗。作家应有超常的敏感,把握时代的脉搏,得风气之先。戏曲文学虽不是新闻,但一定要新鲜或者新奇。当今戏曲演出之不受待见,于文学上的不足就是缺少新奇。总是老生活、老人物、老思想,“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至今仍是戏曲舞台的主体。
戏曲要获得剧场性,就必须追随时代,引领时尚,哪怕是古代题材也要包含当代元素,以期首先在文学层面实现戏曲与时代以及观众审美需求的同步。古人在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优孟”的装扮表演解决的是当时的现实问题;“踏摇娘”表达的是普遍存在的女性苦难;南戏“祖杰传奇”更是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司法弊端;《西厢记》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作为婚姻通行法则的时代,发出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祈祷;黄梅戏传统小戏《打烟灯》《恨小脚》直接配合了清末民初禁烟和天足运动;《天仙配》则很好地配合了我国第一部《婚姻法》的颁布,打出了自由恋爱、自主婚嫁的时尚大旗,并且还弘扬了不羡门第财富、只爱勤劳善良的时尚择偶观,影响了几代人。这些都是戏曲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对生活的追随,挺在了时代的前沿。从而赢得了演出内容的新鲜和思想品格的时尚。因为说的是眼前事、身边事,所以才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观众的审美热情。通过关注社会,赢得了社会关注,延展了剧场性。
舞台上的褒奖弘扬,成为观众在生活中尤其是面对新生活、新变革效仿学习的榜样。舞台上的批评贬抑,也会让观众警惕自己和身边发生的类似行为,从而为转变观念、移风易俗、改良社会提供帮助。
五、快乐超市:为心灵减压
俗话说,要想欢,上戏班。观众看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寻求精神愉悦,排遣身心压力。为此,戏曲文学还应努力营造喜悦情境。这也是为什么由传统戏沉淀下来的折子戏多为喜剧片段的原因所在。这并不是要求戏曲作家都去写喜剧,而是要求作家的创作要有快乐意识。就戏曲文学来说,至少可做三方面的考虑。
其一,即使写悲剧也要有喜剧桥段。这不仅是“对比”“衬托”的需要,更是审美快乐的要求。众所周知,黄梅戏《天仙配》是一出爱情悲剧,但其“路遇”一场,就是不折不扣的喜剧段落。观众对这出戏的喜欢,多半是由这场戏奠定的。
其二,即使是沉重话题也要写得轻松。李渔说:“凡读传奇而有令人费解,或初阅不见其佳,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绝妙好词”。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痛说革命家史》本来是一个李玉和被捕,李奶奶向李铁梅说出家庭由来真相的悲愤话题,既名“痛说”,可见其悲痛之主调。然而,面对这样沉重的话题,编剧适时推出了“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的“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的话题表达方式,并借此对“家史”做了传奇性包装,遂使接下来的“痛说”稀释了“痛”感,浓化了兴味,获得了“轻松”。这一场戏也随之成为观众爱看、演员爱演的经典性段落。
其三,即使是正面角色也要有丑角气质。梨园有句老话,叫“唱戏要唱丑,走遍天下有朋友”,说的就是丑角的亲和力。“丑”因为能在舞台上给观众带来欢乐,提升剧场性,因此也更受大众的喜爱。一些影响广泛的剧目,如《徐九经升官记》《唐知县审诰命》等本就以丑角为主人公的戏,其“人气”自不待言。戏曲文学为着剧场性的最大化,应当尽可能为“丑”提供足够的展示空间。即便某些作品中没有或不能直接安排丑行,也应努力使正面角色带有丑角气质。如梁山伯本是小生、正生,但在“十八相送”时,那“呆头鹅”的表现就有丑角意味,令观众直呼过瘾。这里所说的丑角气质其实就是人物的亲和性,从而满足观众追寻愉悦,获得减压的心理需求。依李渔的说法:“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科浑乃看戏之人参汤也。”
王长安:安徽省戏剧家协会主席,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研究员
(责任编辑:陶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