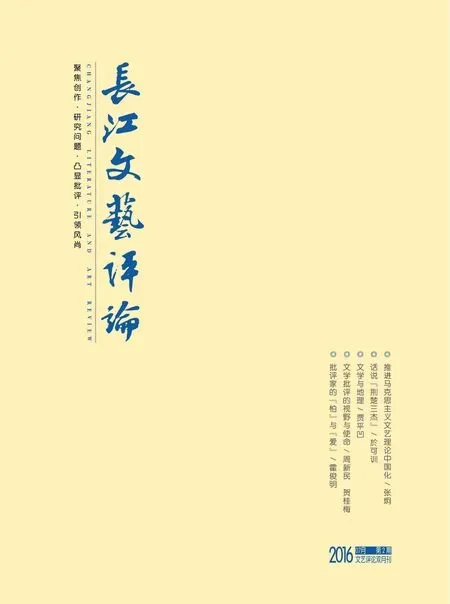奶奶的故事和文学的可能(创作谈)
◎ 曹军庆
奶奶的故事和文学的可能(创作谈)
◎ 曹军庆
我在写我父亲的一篇小文里提到过我奶奶。我奶奶缠足,三寸金莲,她还吸烟,笑起来嘴里的牙齿不是太整齐。但她是个洁净的女人,她的头发纹丝不乱,坐在小凳上双膝并得严丝合缝。我奶奶一边吸烟,一边讲故事。奶奶的故事永远是善与恶,所有故事的结局也永远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在我已经不再记得奶奶讲过的故事了,只记得故事里的两个坏人一个叫王恩,一个叫付义。后来我才明白奶奶是将忘恩负义这个词语拆分成了两个人名,他们几乎出现在奶奶所有的故事里,但是从来没有什么好下场。奶奶可能是我遇到过的第一位作家,虽然她不认得字,但我仍然要这么说。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奶奶在我幼小心灵里播下的种子,要到很久以后才会发芽。
我说的是1978年,这个普通的年份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因为恢复高考,整个国家高涨着喜悦昂扬的情绪。在普遍乐观类似于全民打了鸡血一样亢奋的状态下,没有人会注意到武汉师范学院孝感分院的工作人员所犯下的一个小小的失误。他们在《孝感报》发布招生公告时,漏掉了中文系这一项。这一小小失误带来的结果是没有一个考生知道武汉师范学院孝感分院还要招中文系的学生,因此也就没有一个考生填写这一志愿。这一年我十六岁,我也参加了高考。尽管我的分数比录取分数线高出了十七分,但是高考录取差不多已经结束了,我也没能领到通知书。我那个在村里做支书的舅舅估计我上不了大学,考虑到我的身子又比较单薄也做不了农活,于是他便安排我到村里的小学做了民办老师。我听从了舅舅的安排,到镇里去参加教育站主办的暑期培训。但是我父亲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他觉得一个农民的儿子能考出这种成绩却又不被录取,实在不公平。他把家里所有的鸡蛋归在一只布口袋里,拎着鸡蛋进城去了。我父亲进了县城,后来据说他还去了孝感。他分别去了地区和县两级教育局,面见负责招生的领导,向他们陈述了他的理由和请求。到了我父亲的晚年,他仍然会经常回忆这些细节,他为他的勇气而感到骄傲。当我站在讲台上给村里小学生上课的时候,突然收到了一封通知书,我被武汉师范学院孝感分院录取了。上学之后,我们被告知,虽然我们都是理科考生,但是因为我们的语文成绩都比较好,又加上招生人员的工作失误,所以我们都被调剂到了中文系。
于是我上了大学,并且还进了中文系。我走进了学校图书馆,我在那些书里面一下子看到了我奶奶的影子。现在我也是个写作者,回头看去,冥冥中我和我奶奶之间似乎有着扯不清的关系。我也已经写了好多年,写作的时间越长,我对我奶奶越有敬意。我突然发现我奶奶一生都在讲着同一个故事,那就是善恶终有报。与其说奶奶在讲故事,不如说那是某种信念,有关人类童年和个体童年所坚信的那种带有根基性的信念。能一直那样讲故事的人一定是幸福的人,因为她比听故事的人更相信她所讲的那些故事。
但是故事还有另外的讲法,这正是让我苦恼的地方,我不得不经常讲着和奶奶不太一样的故事。我曾经试图相信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揭示这世界的真相。作家有能力也有责任通过虚构来抵达真实,即使不能抵达至少也要接近这世界的本质。在很多年以前,这可能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想法,你要亲口说出来,说出真相,你不能撒谎。这是一个作家所应该做的事情。这想法的基础仍然是——你必须确信世界是可信的,或者说这世界是有真相的。你不能肤浅地照相式地复制世界的表层,你应该一层一层地剥开,深入进去,深入到世界的背面去。我相信这里面有深刻的怀疑精神,你甚至可以怀疑你亲眼看到的东西,你亲眼看到的那些东西也不是真的。这想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迷惑着我,并带给我安慰。即使是“零度”叙事,也会有一个叙事制高点。我在这里所说的制高点不是道德制高点,也不是思想制高点,而是一个巧妙的叙事切口。从这个入口进去,你所呈现的才是真实。所谓的叙事制高点所表达的是一种最高的叙事伦理,那就是真实性。
对真实的苛求,对真相的苦苦追寻,是一个作家的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这种职业和医生侦探比较相似。医生根据病人的蛛丝马迹去探寻疾病,去发现复杂的病理成因。侦探也要根据蛛丝马迹去还原作案现场和作案过程。他们是一样的,都需要直觉,需要将毫不相干的线索搭在一起的能力。在遥远的表面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之间——耐心地建立起隐秘的联系,可能会有意外发现。写作似乎也是如此,每个作家都有他偏僻秘密的路径。但是所有的写作又似乎都在证明:这个世界是不可能被穷尽的。正像已知的科学只能解释很小一部分世界一样,文学所能揭示的真相也极其有限。这实在是令人沮丧、绝望。当你发现你所试图揭示的真相其实是无法企及的,你对这世界的表达其实是言不及义的,老实说你还能做什么!这世界是没有真相的,如果这样说太过绝对的话,那么可以换一种说法,这世界有着多种真相。可以想象一下不同的时空关系。真相在某一个叙事结构里是真相,而在另一个叙事结构里则可能是另一种面貌。我们见识过很多伪造。伪造一段史实,伪造某些趣闻逸事,伪造民俗,伪造某一个早已毁损消失了的古迹。当我们伪造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伪造,可是当伪造完成之后一旦被保存下来,那种伪造出来的东西很有可能被当作真实传承下去。这样的事例当然不胜枚举,因此令我深感忧虑的地方恰恰在于——我经常会在深夜里扪心自问:我们的写作会不会沦为另一种形式的伪造?伪造与假托,有多少人在写着这样的文字?这种怀疑不是指证,甚至也不是内省。它其实更像是自我警醒,自我暗示。小时候我怕狗,我奶奶告诉我,当你碰到狗的时候你可以蹲在地上,狗以为你在捡石头,它反过来会因为害怕你而不敢靠近你。这一招很管用,每一次遇到狗我都会蹲到地上去。小时候我也怕路过坟地,尤其是夜间,在没有人没有光的夜晚路过坟地,会让我无比惊恐。我奶奶于是教给我另一招,她说你可以一边走路一边仰起头来嚎啕大哭。你如果哭着喊叫我不怕我不怕,效果可能会更好。我也这样做了,我觉得在我独自一人嚎啕大哭的时候,鬼魂正在远离我。蹲在地上假装捡石头也好,嚎啕大哭也好,对我是一种真实。可是关于狗和鬼魂,这世上一定还有另外的真实。现实因此是由多种可能性所构成的。
当我们相信作家无法穷尽这个世界的时候,实际上也为作家指出了另外一条出路:那就是作家可以建立他自己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他终于说出了这世界的只属于他的那种可能性。很多时候我们会指出某一个作家的片面性,或者指出他的局限性。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所谓片面性或局限性或许正是作家所拥有的特权,那是他的领地。每一个作家都必须沉溺于他自己所独有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里面,从而面对世界发言。不同的作家因此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那些异质的不同的声音汇聚到一起,才有可能更接近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文学的世界也因此才会更为丰富多彩。我相信我是有局限性的,我也受到了很多限制,我甚至都不知道限制我的那些东西到底是怎样的限制。比如天分,比如才华,这些先天性的限制有可能更为致命。你无法改变它们,而它们却可以决定你到底能够走多远。于是我所能做的便是安于我自己的局限,在我目所能及的范围内,在我所能掌控的地方,尽力去表达我对这世界的看法。我已经不再企求能够揭示真相了,有可能我只能说出一部分真相,或者只是我以为的那一部分真相。我不能伪造现实,这是最基本的标尺,也是最基本的良知。
在这篇文章里我多次提到了我奶奶,实际上很早以前我就已经默认了我和我奶奶之间心照不宣的关系。我奶奶是个讲故事的人,而我在那次鬼使神差的高考之后也变成了一个讲故事的人。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逻辑,但你说完全没有逻辑似乎也说不过去。我的写作动机往往会源于某一个记忆斑点,记忆是会有斑点的,越是久远的回忆越容易出现斑点。这种情况和水果上面的斑点很是相像。一只水果放久了,它的表皮上会出现斑点。当你拿起水果刀削去水果的皮,或者只是剜去那个斑点,你会发现——原来在水果的内部早已经溃烂了一大片。事实就是这样,你以为那是一只完好的水果,表面上细微的斑点无关紧要,但是它的里面早已毁坏。记忆的斑点往往只是一个线索,顺着那个线索剜下去,我能够发现很多溃烂。面对那些溃烂——当我觉得惊心动魄的时候,我才恍然明白:只有写作才是那把顺着斑点剜下去的水果刀。我在精神上和我的奶奶遥相呼应,但是我奶奶和我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我奶奶并不是我父亲的生母,生下我父亲的那个亲生奶奶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后来的这个我奶奶是我爷爷抢回来的一个女人。女人是可以抢回来的,而且还缠过足,这当然是另一个时代里的故事。也就是说因为讲故事,我所在的这个时代可以和我奶奶所在的那个时代相贯通。仔细想想,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
和那些实用的科学相比较,文学可能没有多少实际的用处。在你悲伤的时候,文学并不能安慰你,文学或许会让你更为悲伤。在你绝望的时候,文学让你更绝望。在你不知道如何选择的时候,文学会让你更迷惘。这么说文学似乎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文学的意义恰恰在于它的这种无意义。表面看来文学也是无用的,但是它的用处也恰恰在于它的无用。文学在更为深广的层面上,对人类的精神是一种补偿。我相信文学会一直陪伴着人类,一直陪伴到末日来临的那一天。文学——当然也可能是文学未来的变种,即使人类终将消亡,文学也有可能是人类最为温暖的临终关怀。所以文学不会死去,这个世界永远不会缺少讲故事的人。
曹军庆:《长江文艺·好小说》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