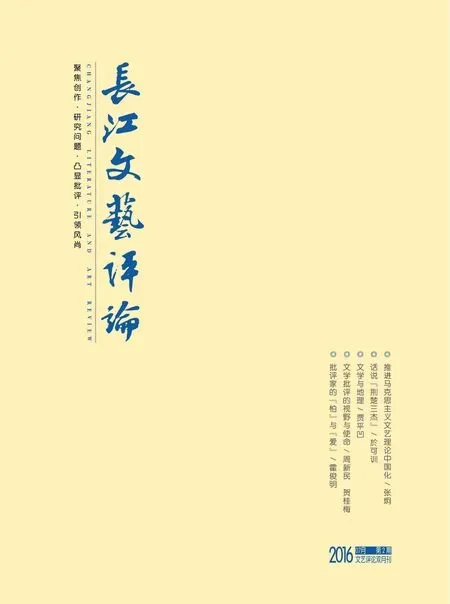故事·叙述与精神指向
——曹军庆论
◎ 刘川鄂 钱 刚
故事·叙述与精神指向
——曹军庆论
◎ 刘川鄂 钱 刚
曹军庆一直是创作势头强劲的湖北作家,广泛涉足长中短篇小说创作,产量大,质量高。从最初的乡村抒写到后来的县城叙事,风格有变,但都体现出很强的个人特色,是一个值得关注和论述的对象。
一、地域抒写的心灵胎记
曹军庆的小说带有强烈的地域标记,他曾经在一篇创作谈中谈到,自己“陷落”安陆。陷落一词,很好体现了这个地理空间对于作家本人的围困。弹丸之地构成个人文学地理学的叙事边界,而其叙事起点是一个更小的地方——烟灯村。在烟灯村里,曹军庆杜撰了大量灰蒙蒙的短中长篇故事,人物思想怪异,行为出格,背后又有着强烈的思想情感的逻辑动机。人们似乎都发了霉,人性霉斑处处可见。作者化为孤魂之地的野鬼,絮絮叨叨,诉尽败落飘零。《雨水》中的烟灯村一直在下雨,生与死,虚与幻的界限在雨中模糊,雨水让时间绵长暧昧,让人偏执癫狂,雨水绵延,欲望不绝。
就文学地理学而言,曹军庆的叙事其后跳离了烟灯村,来到安陆,摆脱单纯的乡村题材。他坚称安陆作为县级市的标本意义,表露出以此为据抒写世界的野心。不管这种表述是否周全,我们确实看到了作家对于县城题材的稔熟,叙述起来如鱼得水,声色俱佳。让人想起苏童对于香椿树街、莫言对于高密的自如抒写。这些地域作为作家的灵魂栖息地,积蓄了巨大的生命创造力。仿佛只有从此,他们的叙述才能有如鬼神附体,创作思路得以绵延。
县城叙事在曹军庆的笔下隐秘安详。它处江湖之远,又不属乡夫野老,没有复杂的时代讯息,人气好聚难散,人性故事代代流传、历久弥新,构成了曹军庆叙事的幽秘丛林。《和平之夜》的一段话很适合描述曹军庆的小说气质:“它在县城滋生着一种热烘烘类似于发酵过的气息,同时也滋生出秘密的向往。”县城在曹军庆笔下,安然盘踞,血脉奔突,粗俗、雅致、漫不经心和祥和都搅在一起,发酵出烂甜的气息。窗外正雨,曹军庆微醺般眯着眼,抚摸着县城地图,跟我们讲起无尽江湖往事:尴尬的村长、空落的空巢老人、无望的留守妇女、失衡青年、侠义妓女、困窘知识分子等各类失败尴尬者,市井气在这里得到审美升华,呈现出老港片的底色。
曹军庆迷恋县城的空间抒写,写来左右逢源,赫赫生辉。在这里,他找到了讲故事人的绝佳感觉:“每个县城都有一处中心广场,这个不容置疑。就像北京有天安门广场一样,县城当然也得有广场。广场在最为显赫繁华的地段。周边环绕着商铺,各类品牌服装店,美容厅和洗脚城。中间立着高大的灯柱。液晶电视不停地播放着药品和酒类广告,然后在晚上七点准时转播新闻联播。从外面看广场完全是敞开着的,开放而不密闭。它适合群殴,群体械斗,适合火并。也适合人群从各个方位围观。”(《和平之夜》)城市广场被曹军庆的想象与描述包围,叙述饶有趣味。各种关于广场的片段像蒙太奇的剪接一般,瞬息万变,城市广场变成打开的睡莲,成为欣赏人们喜怒哀乐的秀场,昭示人生无常之流变的公共空间。
空间的抽象存在是静止的,当空间作为依托,开始跟其间流变的人事展开对话时,我们就能看到空间本身包含的巨大张力。空间刻画体现了生命质感的沉淀,只有当生命质感浸透到物,浸透到空间,变得无所不在,随时能在叙述中显现时,才能说明作家与周遭环境已融为一体,其写作才能神明相助。
故事也必须从这里的空间起始,开始流脓流血,开始人间烟火,火遍人间。这时候,曹军庆变成了小说的霸主,任意扭动着叙述的魔方,至于他人所说的荒诞也好,魔幻现实主义也好,只是他写作快感结束后贴的寄生标签而已。他最近在一篇访谈中讲到,好小说标准有三个,一是好的故事,二是好的叙述,三是好的精神指向。在其小说中,我们看到曹军庆的野心在于将三者兼顾。他的小说被指认继承了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气质,但相比前辈,他没有那种大时代的焦虑心理,整体上没有流于语言游戏,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进行小说创作,以好故事、好技巧来深入表达对于现实的关注和感受。
二、精彩故事的杜撰者
关于故事,曹军庆的故事情节大致分为两种走向,一种是日常化的“弱情节”故事,一种是非常态的强情节故事,后者经常是极端情境的小说。几乎无事的小说在曹军庆的写作生涯中,处于后阶段。以小说《和平之夜》为例,曹军庆的叙述犹如精巧短片,通过各种人的叙述视角,大张旗鼓的铺垫立马发生的黑帮火并故事。这种处理方式是高明的,一方面保证了火并故事的传奇性和可读性,另一方面,这些故事是间接叙事者的口头传闻,无法在小说中的现实层面得到证实,小说中各类叙事者的生活,也即小说主线索展现的故事却平淡无奇,出乎读者意料。这种对比形成了故事的良好张力,也因此形成了中学生林之前的无限想象。就在故事紧锣密鼓铺垫,似乎掀起高潮时,却等来了一个无比平安的夜晚。我们渴望的传奇与血腥,英雄与荷尔蒙兑现成了等待的虚空,让人失落无比。这一设置构成三重落差,一是情节落差,二是中学生林之前的心理落差,三是读者的期待落差。顺便说一句,曹军庆小说人物经常有着好玩的名字,《和平之夜》中,一个老大叫刘从来,另一个叫魏之后的名字,注定了他们两个人的故事会不断膨胀发酵,横贯以后,还关联之前。他们是故事的主心骨,却又在故事里不知所踪,保持着神秘的底色。
类似手法还在《时光证言》这部小说里得到体现,四位女性叙述者在名为时光酒吧的地点展开罗生门般的故事追溯,她们与男性的过去式的故事跌宕起伏,叙述者之间的故事却相对平静,构成了巨大反差,最终生活的荒诞和难以持续的体面在曹军庆笔下被慢慢托出,四位叙事者成为一群无处藏身的狼狈之人。
而第二类的“强情节”在曹军庆的笔下比比皆是。曹军庆偏好这一类题材,这类小说不仅观赏性强,且在某种程度上方便揭示出人性深度和情境悖谬。以小说《越狱》为例,主人公林霄汉是“一个恶魔似的男人”,干的是砍砍杀杀的营生,偏偏爱上了宫小玲。宫小玲怀上他的孩子后,他被判了十七年零五个月牢狱。为了早日出狱见小玲和儿子,他拼命表现,一次次被减刑。离出狱的日子只有六天时,他越狱被狱警打死。“谁都知道这种时候他没必要越狱。我想不明白。人很容易发疯。要么,大哥没有疯。他的脑子是清醒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大哥就是自己不想活了。他在找死。他要找到一个理由让自己死掉”。原来,这个理由是:宫小玲为了生存,与武湖生成了家,其乐融融。林霄汉不忍拆散宫小玲现在的幸福之家,这个杀人魔王以越狱的方式找死,每一次减刑的努力变得滑稽可笑,而找死的方式突现了人性光亮的一面,陡转式情节带来了奇效。
在《煤球往事》中,男主人公早上醒来在一个不明不白的房间,忘了自己是谁,接到不明不白的电话,见到不明不白的人,甚至和一个不明不白的女人争吵、和解和睡觉,他依稀想逃离此地,却又不知为何回来,形成了一个意义混乱空白的死循环。这部小说情节离奇,故事荒诞,却又多么像我们很多人的一生,活得不明不白,死得不明不白。等着他人给自己命名和身份确认,但他人的确认又带给我们更大的混乱。
三、博采众家的叙述者
曹军庆习惯将自己的小说称为现实主义小说,但其叙述技法远非现实主义可以囊括。也许更准确的表述是,他在叙述上博采众长,不拘一格,可大致分为先锋和传统经典两类叙述技巧。古语有云:坐看云起云落。看曹军庆的小说也是这样,他经常将情节藏在云山雾海,要坐下来耐着性子,待云落后才能窥得全貌。他的很多故事叙述有意碎片化,原有叙述线索常常被横插进来的其他线索打断,各类叙事线索有意杂糅,枝生蔓长,甚至于主角是谁都变得模糊起来,这种方式强化了叙事难度,也突出了叙述的本身。这一点跟八十年代先锋小说有着相近之处。曹军庆非常迷恋叙述的快感,喜欢在这种有意设置的叙述险境中冒险,左奔右突,蜻蜓点水的前进,最后却又能够力挽狂澜,线索纷而不乱,故事意蕴百川归海,显出大格局大气候。
《月亮的颜色》的主角应该是胡立宇和肖明霞,故事主线因他们而始,因他们而终。但在叙述中,两位的主角地位岌岌可危,各种人物掺杂进来,他人一次次占据了叙述的中央舞台,演绎和讲述他们的个人史。随着小说的复杂叙事,一些传统中的配角在某个具体阶段,成为阶段性的主人公,如作为老师形象的吴勇福,作为医生形象的廖玉雪。个人史在这个庞大复杂的叙事体系中,变成了“多米诺效应”的爆发前奏,最终看似偶然的杀人事件有着多线索的、曲折漫长的酝酿史。让人深感这个故事的高潮的分量和合理性。而小说中的人物肖、王、胡、邬和廖都是有着心理疾患的人,可能需要耗尽一生去救赎。曹军庆对他们性心理的刻画异常精确出彩,他们是一群灰色的人物,有着无法填补的缺憾,曾不顾一切地奉献与求索,最终陷入自卑与无能的窘境的可怜人。在这篇出色的小说里,可以清晰看到人生因道德困境和情欲挣扎一步步走向异变的过程。曹军庆叙述节奏的把控,对于心理的深入分析和精准描写,让人赞叹。
小说叙述过程中,曹军庆有意模糊小说的真假界限,使真假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让读者失去判断。这既是感觉和玄虚的卖弄,也是对于这个世界认识的深入反映。《云端之上》写了一个宅男的故事。焦之叶大学毕业后自闭家中,大门不出,不理世事。却在网络上扮演不同男性角色娶妻生子,自如地生活在众多女性中间。一个现实世界中的废物,却是虚拟世界的骄子。作品敏锐而犀利地揭示了信息化时代的人性困境,令人警醒。也触发读者反思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缺失,引人深思。“他生活在不同妻子那里,因此他要准备一套又一套谎言和借口。谎言一旦成立,就变成事实了。有一个事实就会有另一个事实。当所有的谎言都变成事实的时候,你就明白了,所有的事实其实都是谎言。焦之叶把时间花在这上头,他相信他找到了活着的意义。”焦之叶的生存是一种虚拟状态,他一方面玩着撒谎游戏,一方面也分不清现实和虚拟,死在了自己建构的封闭心灵空间中。
《和平之夜》中,王老板的叙述真假莫辨,叙述者的口吻也是真假莫辨,像是俄罗斯套娃,一层层揭示叙述的不可靠。《风水宝地》中的真假关系更为复杂。“我”去柳林村写作,明明见过了小果妈,但是毛支书指出小果妈早就死了,“我”看到的小果妈是幻觉。可是到了结尾才发现,原来“毛支书”也早就死了,“我”看到的毛支书也是幻觉。这部小说写得很鬼气,透露出对于自我意识和感觉的充分不信任,对真实性的深刻怀疑。
除明显可见的先锋小说技巧外,曹军庆还娴熟运用了经典叙述技巧来加强他的故事性。最典型的手法是秘密设置、悬念和转折,形成其小说的鲜明标志。作为一个设置悬念的高手,他往往在波澜不惊的故事叙述中,向读者抖出各种秘密,勾吊读者的胃口,撑爆读者眼球。在我们认为已经了解一个小说人物时,冷不丁抖出包袱来,使人物的认可有了更深的层次感,更富冲击力。不到最后一刻,曹军庆不会停止揭秘。他的悬念经常从头分布到尾,这一点很像典型的商业剧本。在《时光证言》中:“何佳薇没结婚,但是她住外面。刚才那男人发来短信,说他一会过来。他是何思凡从前的下属,现在正往上走,如鱼得水。当然他有老婆,早结过婚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何佳薇是他爱的港湾,今夜他将停泊这里。”我们都以为故事结束了,作者却向我们揭示了何佳薇是情妇的秘密,对前面的叙述构成了反讽。
丝丝入扣、严密合缝的转折是一种高难度的技巧,马克·吐温、欧·亨利和斯蒂芬·茨威格是这方面的杰出大师。在当代中国小说家中,曹军庆是熟练而出色的运用着转折技巧者之一,因而他的小说颇有“奇崛”之风。悬念和转折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曹氏特色的结尾艺术。这种处理方式会让人想起早期的戏剧家丁西林,算不算曹军庆对于前辈的艺术借鉴留着待考。在《和平之夜》中:“它们拼贴到一起,意思是这样的:王老板说,昨夜里黑帮的人来找过他了,给他下了最后通牒。逼着他交保护费。不光逼着他交,还逼着他代收保护费。这附近一块住户的保护费以后都由他王老板代收。如若不从,便要灭他全家。为了证明他说的话,王老板带着人一拨一拨地去看他门上扎着的刀子。刀子扎得那么深,谁也拔不下来。王老板指着它说,‘它是黑帮留下的信物!’林之前转过头来,目瞪口呆地看着那把刀子。”
结尾时,情节陡转后戛然而止,好似说书人的惊堂木:且听下回分解。使人雌雄莫辨,形成开放式结局。叙述已然停笔,气脉却未终止,它的魂灵穿墙而出,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悬念和转折的手法在电影中被大量使用,是电影艺术得以成立的重要技法。就这点而言,曹军庆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比较接近电影剧本。而且他的某些小说中,场景相对简单固定,大量对白习惯性使用,跟舞台剧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房子的女人》最近被改编成舞台剧绝非偶然,是曹军庆善于借鉴各艺术门类,精心创造的结果。
四、生存困境的观察者
曹军庆长期在基层从事教育、文化方面的工作,有丰厚的底层生活经验,但他并不满足于“真实生活+平实感想”的基层作家模式,他所要“发现”的是生活之上的生存,是表相背后的真相,是常态生存中的反常。他小说有着强烈的现实指涉,这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他的很多故事材料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新闻,比如《我们的来历》中做了副局长的小姐,《有没有一只着了火的鸟儿》中身捆炸药包的讨薪民工,都是现实中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二是具有人间情怀的曹军庆理所当然地异常关注现实,是人类生存状况的解剖者。他正视生存窘况,领悟存在的巨大荒诞,格外专注人的生、死、疏离和交流,传达出对人类境遇的同情理解,鞭策读者于无意义处寻找出意义。在这些小说中,绝大多数是逃避者、失败者、尴尬者和困顿者,幼稚无辜的受害者,理想主义的殉葬品,很难看到幸福者和圆满者,他们最终完成的不过是具有悲剧色彩的灰色人生。由于有着现实的底子,写起来格外逼真。对于这些官员、农民和乡镇知识分子形象,曹军庆没有流于猎奇和刻板描写,而是深入挖掘人性畸变和精神崩塌,写出他们肮脏、猥琐和不择手段的同时,也对其报以人性的理解,使其构成曹军庆笔下真实精细和多层次的立体人物形象。
曹军庆对于死亡故事非常痴迷。死亡在其笔下,既是肉身的消亡,也是精神的隐喻和道具。甚至叙述手法也粘连着死亡。他的很多故事直接以死亡开头,死亡一开始就成其小说基调。在《雨水》中,死亡成了美学和诡异的叙述工具。《我们曾经山盟海誓》以死亡开始,以死亡结束,死亡仿佛开幕式和定音锤,贯穿了这部小说生命的全部。《云端之上》这部极端情境小说里,幽闭症的男主人公焦之叶漠不关心现实中的任何人,只是对顺乎自己想象的虚构世界报以感情。他对于死亡的态度犹如局外人一般,最终在结尾无足轻重的死,化为鸿毛一片,而在此之前,其亲人已相继过世,整个世界落了个白茫茫一片。焦之叶的死亡,既是肉身的,也是自身困境的终极解决之道,是走投无路,价值归零的隐喻符号。
他的广受好评的短篇小说《什么时候去武汉》写了一个复仇主题的故事。“我”和刘不宗,“无论在谁眼里,我们都是要好的朋友。我们的友谊持续了十几年。……我没有理由恨他。可是,当我在某一天夜里突然意识到他早就是我的仇人时,我着实吓了一跳。而且,我还发现这一仇恨根深蒂固,与日俱增。”作者对人物关系有意设定荒诞底色,为了报复刘不宗,我决定去勾引他的老婆,而他老婆马上接受了我的勾引,一起梳理篡改个人记忆史,为偷情建立合法性。但其接受的真实理由是意识到老公刘不宗的背叛,所以宁可篡改记忆,达到一不接受老公偷情事实,二要报复老公偷情的目的。可是两人约好的武汉偷情之旅却屡屡被偶然事件阻断,怎么也去不了近在咫尺的武汉,宣告了这种报复的无望、无聊和无意义。
曹军庆喜好描述男性的复仇故事,他注重挖掘复仇双方的心理状态,表现复仇的快感或者恐惧,以便更深入地拷问灵魂、撕裂人性。《地下室》的复仇者费向南的报复对象刘四五在小说开篇就死去了,“我唯一的目标,就是他。他活着,我的生命才有意义”。在得知刘四五死后,费向南迅速崩溃,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兽皮》的郭顺昌拿到宝物后把同伙丁石轩封死在石穴中,后来又一直觉得丁石轩没有死,会随时来找他报仇,陷入了良心的石窟,恐惧的石窟,一辈子逃不出来。复仇就成了自作自受的心理报应。这两种复仇形式中的双方需要相互依存对峙,充满了张力。
而《背面》中的肖雅丽,一个孤身女人,极富同情心。邻家出了什么不幸的事,肖雅丽必定在场,帮着人家痛哭流涕。肖雅丽是悲伤的,但悲伤却使肖雅丽容光焕发,食欲大增。肖雅丽果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吗?“我就是想,因为有了不幸,你才能替人分享他们的苦难,并且去安抚对方。你始终在做这些事情,你做得很好。可是,一旦没有不幸,你也就无从做起了。这才是你的悲哀。”也就是说,肖雅丽是在别人的痛苦中、在施舍同情中获得了一种满足,他人的痛苦冲淡了自己的不幸,因而获得了一种精神的平衡。这当然是一种病态的满足,然而这种病态却展现了一种更真切的人性。
曹军庆的小说很多时候趣味和灰暗并存,阅读时会带来一种压抑感,不仅源于现实的不可测与吊诡,同样也源于人心的幽暗和阴毒。他的每部小说都设有灰色人物,有的甚至面目模糊,他们经常陶醉于自我叙述,在吐出巨大的故事场域时,却像在喃喃自语。这种揭示的深度和强情节使小说爆发出巨大冲击力。同时,在他的笔下,人物经常变得不知所踪,一种孤独感在小说的空间弥漫。是逃遁,是消散,还是无意的隐瞒?读罢令人颇感沧桑感。
五、个性语言的创造者
诗人出身的小说家曹军庆十分讲究小说语言。他在每篇作品中都十分注意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越狱》几乎通篇都是对话,是武湖生和宫小玲二人关于相识经历的回忆和当下处境的应对。由于生活在魔王林霄汉的阴影下,两个人的对谈,依赖中带着恐惧,关切中带着无奈。《冬泳的人》的女主角刘金月痛说丈夫:“从来也不摸一摸我那里。他要么像畜生一样发泄一通,要么根本就不理我。你说说,还有这样做丈夫的吗?”刘金月因患乳腺癌失去双乳也失去了女人味,又对冬泳队队友李永刚抱有好感,直白地数落丈夫时带着悲愤。
当下小说好用间接引语,不大像传统小说那样特别在意个性化人物语言,而且由于现代人在教育、信息交流的模式化,人的表达趋同化倾向严重,因此小说表现人物表达个性的难度更大。当下小说似乎更注重叙述语言,曹军庆的功力更在于此。有评论者引用这样的妙句:“他转过头来,左边的脸和右边的脸一样疲惫。”(《地下室》)这是精神崩溃者的慢转身动作的传神之笔。“在这所房子里,如果吴桂芝是一只狗,那么管家就是仅有的一块骨头。他们迟早会走到一起:不管是狗叼起了骨头,还是骨头碰到了狗。”(《烟灯草》)用“狗”和“骨头”比喻不那么光明磊落的男女之情,也是曹军庆贴切、别致的独创。
他的叙述语言有一种特殊的曹式韵味、曹式气场:旁观、冷峻、简洁、奇妙。如《冬泳的人》写女主人公:
退休教师刘金月罹患乳腺癌,双乳被切。一个女人没有乳房了,就是这样。不是没长过。是被切掉了。医生。手术刀。那是个年迈的医生。在武汉的一家大医院里。刘金月还记得他严厉而混浊的眼睛。他的脸和手上,都长满了老人斑。而他的眼球,则混浊得就像是假的。看上去他总像是要流泪,却又流不出来。正是他切去了刘金月的乳房。他说好多女人都被他切掉了。还有一些女人在等着他切。这不是他想做的。
仔细体悟这段人物描写,就能看出曹军庆的描写特点和语言功力。短段落、短句式,多用句号,节奏快捷、信息丰富,有情感冲击力、还有冷幽默。
《盲人按摩店》写盲人高医生和小玉在按摩店偷情,肖医生不动声色去捉奸,作者不动声色描述肖医生怎么上楼、怎么让淫妇扇奸夫的耳光以侮辱他的尊严、怎么逼走了小玉。
小玉走后,肖医生没有再为难高医生,她不说什么。这么做,其实是肖医生想让他更为自责和内疚。她的目的达到了,高医生从此再也抬不起头来。
无论事件怎么轰轰烈烈、怎么奇形怪状,但都在作者意料之中,都已被作者过滤了一遍。作者的语言越节制,事件越有张力、人物性格越有非如此不可的逻辑力量、越显出真相的残酷。
丰富意象的经营也显现出曹军庆小说语言的魅力。镜子、游戏和迷宫等隐喻意象在他作品中多次出现,他们既是作品中的道具,又是增强故事内涵的手段。《兽皮》里白龙镇上的郭宅是一个巨大的圆盘建筑,一个迷宫。“也许在某一个点上,这一圈很容易和另一个圈串在一起。明明走在一个方向上,一不小心又去了相反的方向。而在另一个点上,类似的错误再次重犯。”有关复仇和被复仇的人生就在迷宫中反复上演,“丁石轩在和我捉迷藏。这些事情,不过是我们游戏中的一部分”。臆想的或是真实的,作者有意模糊它们的边缘,既使故事更有弹性,又使作品具有超故事的回味。《回家》里,“你”遭遇妻子离家的那一刻,“你对着镜子惨笑。在幻觉中,你的牙齿一颗一颗地脱落。它们像金属颗粒一样在地板上弹跳蹦哒。你张大了嘴巴,它们一颗不剩。红色的牙龈,舌苔。你摸了摸脸,让自己恢复过来。那些地板上的牙齿重又跳起来,回到它们各自的位置上。”人在镜子里看到现在的“我”,还看到了过去的“我”,时光流逝如一部默片在镜子里快速地放映。一种强烈的视觉印象冲击着读者,激发了一种新鲜的阅读快感。
曹军庆的“个人探险”,是在灰暗的生活背景下,描绘一幅幅幽暗的人性画卷,他解剖了日常道德情感中残酷的真实,温情面纱下的血腥,文明外衣下的兽性和非理性邪恶及反常态状态下的人性温情。曹军庆的人性解剖刀,冷峻、犀利、别致、力透纸背。
当然,篇篇玩高难度技巧,有时不得不警惕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顾此失彼。在顾及叙述快感时,有可能削弱故事的可读性和严密性;如果内容淡薄,就会沦为故弄玄虚和猎奇夸耀,这其中的平衡需要好好拿捏。此外,曹军庆的长篇小说在结构把握方面可以更合理一点,某些短篇的爆发力、故事性及节奏感尚可进一步考量。曹军庆的写作兼顾社会内容、故事情节和叙述本身,是一种非常消耗写作内力的写作,也是一种非常有难度的写作。考验读者的耐力,也检验评论家的内功。他取得的成就高于他应得的赞誉,也许与此相关。
(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重大项目“湖北当代小说与文明湖北建设”阶段性成果)
刘川鄂: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钱 刚:湖北大学文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