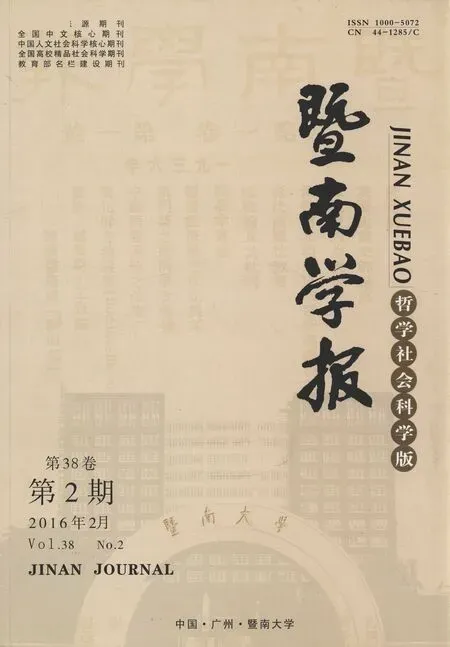闻驴鸣:中国中古时期的友谊、礼仪与社会常规
[美]陈威著,武泽渊译,卞东波校(.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亚洲语言与文化系,加利福尼亚 洛杉矶 90095;.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俄亥俄 哥仑布 40;.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00)
闻驴鸣:中国中古时期的友谊、礼仪与社会常规
[美]陈威1著,武泽渊2译,卞东波3校
(1.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亚洲语言与文化系,加利福尼亚 洛杉矶 90095;
2.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俄亥俄 哥仑布 43210;3.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在中国中古时期,学驴鸣似乎是一种名士风度的表现,但其背后实际上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当时的士人将闻驴鸣当作一种“知音”的表现。《世说新语·伤逝篇》记载了两则关于驴鸣的逸事,其引起的不同反应,正与中古时期复杂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有关。
[关键词]驴鸣;友谊;礼仪;社会常规;知音
[校者简介] 卞东波(1978—),男,江苏南京人,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海外汉学研究。
南京大学文科规划项目《中国古典文学的新视镜:新世纪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之再研究与译介》;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韩国学振兴规划办KSPS)项目《海外韩国学教科研重点基地》(批准号:AKS - 2013 - OLU -2250003)。
在许多传统中国文学作品中,对声音的表现常用于文学描写和引发某种场景的背景音。溪水潺潺,风过林间,聆听这些声音,文学主体会发现自己进入一种幻想之境或神明清发的瞬间。这些声音似乎是偶然的,但却是一种必要的细节,这些细节可以形塑某种给定场景的表象经验;没有这些声音,这一场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完整的。而且在文化想象中,听觉的呈现不但被赋予意义,而且自身也传达信息,或作为时序的标识,或作为自然音乐性的表征,或暗示着主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共鸣。而另一些声音既作为听觉背景,也是突出的前景,成为它们自身的文学主题(literary topoi)。这些声音可能成为文本场景(textual scene)的焦点,传递文化的回响,并在意义上蕴含着更多的复杂性。
本文关注的是一种特定的,甚至可以说是特别的声音:驴叫声(“驴鸣”“驴声”或“驴嘶”)。①当然,“bray”是对驴鸣标准的英语译法。汉语里的“鸣”一词更近于“cry”或者“call”,而“声”一词表示一般意义上一种声音的产生。“嘶”是在与动物鸣叫声有关词语中最有马类特色的。我使用“bray”一词以区别于牛哞、马嘶等其他声音,尽管原始文本的用词并不那么统一。在中国传统的文本或图像表现中,驴是常见的坐骑和负重的牲畜。②参见Peter C. Sturman,“The Donkey Rider as Icon:Li Cheng and Early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Artibus Asiae,Vol. 55,No. 1/2,1995,pp. 43 -97.不过,中国传统论述中鲜见关于中古时期驴鸣的研究。传统类书也没有将“驴鸣”列为类目,这一时期也极少有对这种声音的描绘。然而每当出现驴鸣时,我们总能惊讶地发现它与友谊、丧葬、礼仪等主题相关。本文将审视整个早期中古时代的驴鸣,在2世纪到5世纪的小说、正史、宗教文本和论辩文中追寻驴鸣的主题性回响。在这些关于驴鸣的文本中,并没有强大的因果关系或意图明确的典故来构建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但整体来看,这些例子重建了符号学范畴下驴鸣在这一时期可能的喻指。
为了说明为什么会有人对于这样一个话题展开学术研究,我将以《世说新语》中一则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作为开头——这也许是中国文学中最广为人知的关于驴鸣的例子——在这个故事中,诗人王粲(177—217)死后,他的朋友前来吊谒他: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①刘义庆编,杨勇注:《世说新语校笺》第十七门第一则,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36页。另见马瑞志(Richard B. Mather)英译的《世说新语》第二版(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2),第346页。
这是《世说新语》中“伤逝”一门的开篇,它呈现出的是一个相当怪异的场景。王粲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他们是一群汉末时依附于曹氏父子的文坛精英。在简短的《三国志·魏志·王粲传》中并没有关于王粲好驴鸣的记载,尽管这并不令人意外,毕竟正史倾向于记载传主的事功。②陈寿(233—297)著、裴松之(372—451)注:《三国志》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97—599页。因此,其本传提及王粲“貌侵而体弱”,因为这与他事业受挫有直接关系,但对驴鸣的喜好则不然,那只是个人的癖好。③见《三国志》卷二十一,第598页。这则逸事明确提到世子曹丕(187—226)带领其他的吊谒者齐作驴鸣以纪念他们去世的朋友,尽管这里并没有说明驴鸣在中古中国的文化大背景下表征着什么。④王粲去世时曹丕尚未称帝。但是他以魏文帝的身份出现,符合《世说新语》用功业上所达到的最高级别来称呼人物身份的倾向。换言之,假如王粲能够听见曹丕等人模仿的驴鸣声,他能够听出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再考察同时期其他有关驴鸣的文本。4世纪成书的《拾遗记》中的一则逸事似乎能作为时代更早驴鸣的例子,尽管驴鸣在这里只是生动的细节而非聚焦的主题。这则逸事讲述的是汉灵帝(168—189年在位)和他荒淫的行径,其叙述以关于“裸游馆”的游乐达到高潮:
帝盛夏避暑于裸游馆,长夜饮宴。帝嗟曰:“使万岁如此,则上仙也。”宫人年二七已上,三六以下,皆靓妆,解其上衣,惟着内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献茵墀香,⑤可能是“茵陈”,点燃它是因其有芳香的特性。煮以为汤,宫人以之浴浣毕,使以余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使内竖为驴鸣。于馆北又作鸡鸣堂,多畜鸡,每醉迷于天晓,内侍竞作鸡鸣,以乱真声也。乃以炬烛投于殿前,帝乃惊悟。及董卓破京师,散其美人,焚其宫馆。⑥见范晔(398—445):《后汉书》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70页;《三国志》卷六,第176页。至魏咸熙中,先所投烛处,夕夕有光如星。后人以为神光,于此地立小屋,名曰“余光祠”,以祈福。至魏明末,稍扫除矣。⑦王嘉(活动于4世纪末)撰,萧绮(活动于6世纪)录,齐治平注:《拾遗记》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4—145页。
此处对年轻宦官作驴鸣一笔带过,这本身看似无足轻重,但考虑到灵帝时期宦官揽政的历史语境,它将皇帝的荒淫与朝廷的政治腐败联系了起来。⑧关于灵帝统治与宦官问题,见B. J. Mansvelt Beck,“The Fall of Han”,载杜希德(Denis Twitchett)、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总编,杜希德、鲁惟一主编:《剑桥中国史》第一卷《秦汉史卷》(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1,The Ch’in and Han Empires,221 B. C. - A. D. 22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第317—376页。当皇帝沉溺于与宫女的淫乐之时,宦官的学驴鸣也许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皇帝兽行的最佳伴奏。而当驴鸣加上鸡鸣,以及宦官模仿鸡鸣仍无法将皇帝唤醒这些细节时,皇帝的纵欲无度又进一步变为荒唐可笑。与其他关于昏君的故事不同,在这则关于灵帝醉酒纵欲的叙述中我们找不到任何风流雅韵,显然也没有任何可以成为后世诗歌素材的东西。这则逸事的结尾直接跳到军阀董卓破京师,喻示着皇帝的自我纵欲是如何导致皇朝覆灭的。最终,皇帝曾经享乐的旧址变成了鬼火闪烁的凶宅,继而变为神祠:随着“神光”的逐渐黯淡,关于皇室堕落的记忆逐渐为祈福所替代。
如果说驴鸣在《拾遗记》中唤起的问题是政治失败,那么在早期佛经《骂意经》中我们发现的则是更加形而上学的问题。这部佛经的作者相传是东汉时安息国僧人兼翻译家安世高(活动于2世纪)。①见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5年版,T732:17. 530a -34c。该经难以系年,因为早期佛经在流传过程中往往假借著名翻译家之名。尽管现存最早的佛经目录,僧佑(445—518)的《出三藏记集》在编纂之时,确实在流传于5世纪末6世纪初的作者不详的经籍中著录了这部佛经,但并没有将这部佛经归在安世高名下。②见僧佑:《出三藏记集》,《大正藏》,T2145:55. 28A。在隋代目录《历代三宝纪》中,《骂意经》被认为是安世高所作,见《大正藏》,T2034:49. 51b。成书于730年的《开元释教录》和后世的传记都认为安世高是作者,见《大正藏》,T2154:55. 616c。另见陈士强:《大藏经总目提要》卷三《经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38—440页。
《骂意经》大致写的是业力与轮回,包括诸如“鱼鳖无声者,前世断人语头故”这样的论述。但就在同一章,该经继续说:
好捶人,后世作驴。所以长耳者,好挽人耳;畜生好抟人耳。或故世征卒。何以故?一卒传余卒皆作声,一驴鸣余驴亦鸣。③见《骂意经》,《大正藏》,T732:17. 532b -32c。
这里几乎没写什么转世为驴的好处,甚至更没写它对于一个人前世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什么。《骂意经》给出了两种转世为驴的可能,第一种比较明白,是典型的因果报应的铁律,似乎以讽刺性的命运反转为乐。即习惯性他人之耳将导致来生一种与之相应的“诗意”命运(poetic fate):转世为一种长耳动物(长耳大概更容易遭受虐待)。第二种不涉及对他人的施暴或虐待,却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复杂。在这里,重点不是驴这种动物本身的意蕴,而是对驴之所以嘶鸣的解释,其业因可追溯到不加思考地带领部卒征战赴死的兵士。虽然这不能算是对征卒(或者对驴)的公正描述,但该经阐述的是,战斗中的士兵教条性地传令无异于驴从众而鸣的愚蠢习惯。
以上两个例子都没有在任何方面论及驴鸣的审美性质,但相关的论述在《驳顾道士〈夷夏论〉》一文中得以提出。这篇文章是僧人惠通(活动于5世纪)对道士顾欢(420—483或428—491)的辩驳。顾欢的原文认为释迦牟尼不过是老子的化身,因而佛道同源。该文继而批判佛教作为外来宗教无法与中国传统思想兼容。④见萧子显(489—537):《南齐书》卷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31—932页;以及李延寿:《南史》卷七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75—1877页。关于这篇短文的讨论和部分翻译,见Walter Liebenthal,“Chinese Buddhism during the 4thand 5thCenturies”,Monumenta Nipponica,Vol. 11,No. 1,1995,pp. 44 -83。另见Livia Kohn,Laughing at the Tao:Debates among Buddhists and Taoists in Medieval Chin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p. 161—169.在驳文中,惠通这样开始:
余端夏有隙,亡事忽景,披顾生之论。昭如发蒙,⑤“发蒙”一词见于“蒙”卦的卦辞,见《周易正义》,1. 8b,载阮元(1764—1849)编:《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页。见辨异同之原,明是非之趣。辞丰义显,文华情奥。每研读忘倦,慰若萱草。⑥萱草据说有忘忧的功效。例如,嵇康(223—262)《养生论》说:“萱草忘忧。”见《文选》卷五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89页。真所谓洪笔之君子,有怀之作也。然则察其指归,疑笑良多。譬犹盲子采珠,怀赤菽而反,以为获宝。聋宾听乐,闻驴鸣而悦,用为知音。⑦见僧佑:《弘明集》,《大正藏》,T2102:52. 45c。
惠通指责顾欢既盲且聋,因此以菽为珠,以驴鸣为乐。而且更糟的是,由于无法辨别事物的真相,顾欢以为自己洞察到了宗教真理,而事实上却没有辨异同或明是非的能力。因此,道士顾欢的丰辞和华文仅能掩饰其肤浅的见识,除了表面的吸引力之外别无价值。
惠通所用的“知音”一词源于伯牙与锺子期的典故。又见于《吕氏春秋》的记载,伯牙善于鼓琴,每当他弹奏时,锺子期总能听出他的朋友心里在想什么。锺子期死后,伯牙断其琴弦,不再弹奏,因为他觉得世上再也没有人能理解他的音乐了。①见吕不韦(?—前265)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44—745。另一个版本,尽管结尾不同,可见于杨伯峻:《列子集释》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8页。如果伯牙被视为完美琴家的典范,那么锺子期则代表了完美的听众,其鉴赏力与理解力显示出他是一个理想的评论家。在早期中古时代,知音的主题进一步发展,既和音乐审美也和文学审美相联系,最著名的是《文心雕龙》中《知音》一篇。②刘勰(约465—522)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四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5—1864页。虽然惠通针对驴鸣而引用“知音”一词有点讽刺,但知音的观念对于理解驴鸣至关重要,因为能作知音的人不仅仅是富有辨别力的鉴赏家,更兼有知己与知人的含义。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我们才能再回到曹丕与他在王粲葬礼上所作的驴鸣。也许王粲喜爱驴鸣的原因现已不得而知,但曹丕在王粲葬礼上作驴鸣的原因现在却能被理解为,暗示着他是王粲的知音。曹丕对王粲喜好的准确理解得到了其他吊谒者的认同,并随之齐作驴鸣。这次不寻常的集体吊谒由曹丕引导,其中的意蕴可谓不寻常。曹丕并非只是王粲的朋友:作为曹魏集团的重要一员,他也是王粲的赞助者(patron)。另外,在公元217年王粲去世的这一年,他刚刚被立为世子。在这场葬礼的最后,曹丕实际上扮演着三重角色——评论者、朋友和赞助者——以此来作为王粲最好的听众。
虽然《世说新语》常被认为是为反礼教的行为提供典型,但其记载的人物既不简单地否定既有的行为规范,也不(都)反对儒家的思想与实践。③关于这一点,参见侯思孟在阮籍的例子中关于“反礼教”的讨论,见其Poetry and Politics:The Life and Works of Juan Chi,A. D. 210 -26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p. 73 -87.至于曹丕,他在葬礼上不寻常的行为严格说来并不是反礼法(anti-ritualistic),而是反常规(counter-conventional)。当曹丕率领葬礼上的众客齐作驴鸣,并暂时地将他们整合为一个群体时,他是在用一种不同的声音来取代仪式性的哭丧,尽管二者在程序上是一致的。不同于缺乏个人色彩的、仪式性的惯常哭号,驴鸣是独献给王粲的,因为他似乎很喜爱这种声音。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侯思孟(Donald Holzman)关于魏晋名士所谓的“自我的回归,对独立个体兴趣的勃兴,以自身为评判尺度,而不是作为儒家礼教驱动下的邦国机器的一个零件”④见侯思孟,“Les Sept Sages de la Forêt des Bambous et la société de leur temps”,T’oung Pao,Vol. 44,No. 4/5,1956,pp. 336 -340.。曹丕和他的同僚不是以一种异于他人的吊谒方式,而是以一种对王粲本人具有独特性、个性化意义的方式去吊祭他。
王粲与曹丕的这则逸事引出了一个有关礼仪之概念的关键问题。那就是,虽然礼仪能为日常生活或特殊场合提供行为规范,但礼法的本质却可能与真情实感的表达相悖。驴鸣在礼仪上是不合适的——或者至少是不属于礼法的——但曹丕认为它是对王粲最好的送别。曹丕行为的适当性为其他宾客所认同,他们成为赞同的观众,并影响到文本之外的读者反应。然而,这种叙事并没有给出一个更普适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样一种不协调的声音能够适合一场仪式庄重的葬礼。这是《世说新语》的典型特色,倾向于使用间接的暗示而非繁冗的考释来表达。在《后汉书》的一则逸事中,我们确能找到一种对不合正统礼法服丧的解释——同样与驴鸣有关。这则逸事与《世说新语》中的那则在主题上非常相似。下文见于隐士戴良(活动于2世纪)的本传:
良少诞节,母憙驴鸣,良常学之以娱乐焉。及母卒,兄伯鸾居庐啜粥,非礼不行,良独食肉饮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毁容。或问良曰:“子之居丧,礼乎?”良曰:“然。礼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礼之论!夫‘食旨不甘’,故致毁容之实。⑤见有关这则引文的讨论,从《论语》17. 21起的后几页。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论者不能夺之。①《后汉书》卷八十三,第2722—2773页。文青云(Aat Vervoorn)在与此相关的论述中错误地解读为,戴良母亲作驴鸣是为了提醒她的儿子不可傲慢。见文青云:《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Men of the Cliffs and Caves: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remetic Tradition to the End of the Han Dynasty,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0),第298页注109。很遗憾,张磊夫(Rafe de Crespigny)亦持文青云之说,见其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Later Han to the Three Kingdoms,A. D. 23 - 220,Leiden:Brill,2007,p. 106.
这里喜爱驴鸣的是戴良的母亲,而他的儿子模仿驴鸣是为了取悦她。②戴良经常模仿驴鸣以取悦他年老的母亲让人想起道家传奇人物老莱子(活动于前6世纪末—前5世纪)模范的孝行故事。老莱子虽然年事已高,仍然身着彩衣,模仿婴儿的行为以取悦双亲。见欧阳询(557—641):《艺文类聚》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69页。她死后,戴良的哥哥——此处只提到他字伯鸾——以礼法所规范的方式服丧,而年轻时就不循常规的戴良在其母死后仍然不循常规。虽然母亲爱听驴鸣并没有使戴良在服丧期间模仿驴鸣,但这件事却作为铺垫引出了戴良与那位质疑其行为正当性的质询者之间的辩论。
尽管这个有趣的小插曲没有收录在《世说新语》中,但是戴良的这番回答却回应了逸事编纂者所关心的一个中心问题:重要的并不是礼仪的外在形式,而是礼仪所要真正表达的东西,即它的情感内容。戴良引用《论语》中孔子与其学生宰予(生于公元前522年,在文中以“宰我”出现)之间关于合理的居丧行为的对话,支持了这一观点。宰予对孔子抱怨说三年的服丧期太长,因为这期间被耽搁的礼、乐、农之事都是十分必要的。宰予提议服丧一年就足够了。孔子问宰予一年期满后食稻衣锦是否能“安”,宰予答曰能“安”。孔子于是说道: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③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36页。
在这里孔子解释了居丧三整年背后的原因,这并不是简单地照搬并遵守既定的行为规范,而是哀痛之情的真诚流露。从这段话的上下文中,我们能明显看出孔子并不是提倡居丧者在食旨闻乐的同时不甘不乐,他的意思是说,即使居丧者那样做也不会感到任何愉悦。戴良所做的其实是用断章取义的方法有意曲解孔子的言论:他饮酒食肉而不遵守任何居丧礼节,却因为任何事都无法使其愉悦而致形容憔悴。戴良所理解的是,如果一个人在为父母丁忧时感到悲痛,那么重要的只是表达他的悲痛,而不是表达的方式。至于礼仪,假如一个人遵循礼法却无动于衷,则无异于不存在礼法。
现在看来,虽然戴良对反常规的服丧方式的辩护或许能为曹丕的驴鸣提供正当理由,但它并不能为所有在葬礼上作驴鸣的行为辩护。礼仪活动只有在被一个群体认可为礼仪活动的时候才是成功的或者“妥当的”(借用哲学家J. L.奥斯汀[J. L. Austin]的术语)。④奥斯汀认为这种他称为“践言性的”(performative)言语行为不能被认为是正确或错误的,而只有“妥当”或“不妥当”,也就是说,成功或不成功。见其J. O. Urmson and Marina Sbisá,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2nded.,Cambri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 12 -24.并且,如果一种尝试性的礼仪活动失败了,就会带来群体某种与之相应的失败。这种情况见于《世说新语》中仅有的另一则描写葬礼中驴鸣的逸事——同样见于《伤逝篇》,作为该门的第三则逸事,几乎紧接着曹丕的那则。这一次,故事围绕着王济(活动于3世纪)的葬礼展开,文学家孙楚(卒于293年)前来吊谒。孙楚如今最为人所知的大概是他是著名诗人孙绰(314—371)的祖父,尽管他本人也是优秀的作家。⑤孙楚的《为石仲容与孙皓》见载于《文选》,并被转录于其《晋书》本传中。然而,这两个版本存在显著差异。见《文选》卷四十三,第1931—1938页;和《晋书》卷五十六,第1540—1542页。虽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官居要职,孙楚踏上仕途却相当晚,在他年过四十之后。王济出生于著名的太原王氏,娶了晋武帝(司马炎,265—290年在位)的女儿。最后要注意的是,王济生前曾是孙楚的赞助者。这则逸事写道:
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①《世说新语校笺》第十七门第三则,第637—638页;以及马瑞志《世说新语》英译本,第346—347页。马瑞志也翻译了见于稍早的《语林》中这则逸事的版本。关于这个故事的另一种讨论,见梅家玲:《世说新语的语言与叙事》,台北:里仁书局2004年版,第214页。
与第一则逸事相似,我们看见了一个暂时性群体的形成,这个群体围绕着对已故友人的共同记忆结合而成。但是,当孙楚模仿驴鸣的时候,那个原本因他们比较惯常的恸哭而结合成整体的吊谒者们此刻在笑声中解体了,从而形成了一个不同的群体——一个破坏吊谒与纪念严肃场合的群体。
孙楚失败而曹丕成功的原因与此二人不同的地位、个性,以及他们与死者之间的关系有关。毕竟曹丕是曹氏集团的世子和当时最主要的文人赞助者。一种合理的解释是,王粲葬礼上的吊谒者们不能不服从曹丕作驴鸣的提议。相反,不论孙楚曾与王济关系多么密切,他毕竟只是一个幕僚,其他的宾客也可能嫉妒孙楚与王济之间的密切关系,不愿认同象征着二人亲密友谊的驴鸣。
而这失败的驴鸣也与孙楚的个性有关,正如这则逸事开头所写的。孙楚被描述为一个恃才傲物的人。事实上,孙楚唯一敬重的人就是王济,而王济也是唯一赏识孙楚才华的人。换句话说,孙楚从不推服他人,相应地也不被他人认可。他的驴鸣不是为吊谒王济的名士群体所准备的,而是仅为王济一人。并且,因为能够欣赏他的“知音”已死,所以他所学的驴鸣也只能被误解了。讽刺的是,假如孙楚想要重新演绎伯牙的故事,他应当发誓再也不作驴鸣。那样孙楚才能完全实现琴师的角色,以他最后的绝响证明锺子期的知音是独一无二的。
伯牙和锺子期的故事在《世说新语》中两则关于驴鸣的逸事里都呈现为隐含的主题,因为这两个故事本质上反映的都是有才之士与识才之人、依附者与赞助者之间的关系。只有赞助者才能发现士人身上蕴藏的能力并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提拔他们。没有赞助者作为知音,依附者就像琴师无法获得听众。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孙楚的赞助者死后,他发现自己缺少一个能懂得并欣赏他人才华的人。正如孙楚将发现的,如果在没有知音的情况下难以证明一个人的才华,那么同样难以让人理解驴鸣就不只是粗鄙之音了。很多东西决定于人们的预设,一旦一个人开头就错了,他就可能被引入自我错误的棘丛。
在《世说新语》关于王济葬礼的叙述中,以孙楚的话作结,他斥责了那些愚蠢的宾客,他们不能理解他对他恩主的最后致意。但是,愚蠢的究竟是宾客还是孙楚自己,也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驴鸣的历史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声音,一种既被喜爱也被嘲笑的声音。这则逸事暗示孙楚与王济之间关系的方式显示出这种模棱两可深入到孙楚自身个性的层面,并将问题复杂化了:孙楚自己是否真的掌控着他的行为。的确,这则逸事的开头说明孙楚抱有获得赏识的私念,这使得在这场葬礼上不可能形成暂时性的群体。也就是说,王济葬礼上众客的笑声不仅嘲笑了孙楚非正统的吊谒方式,更重要的是,消解了群体吊谒的可能性——事实上变为了群体性的嘲弄。相反,曹丕等人齐作驴鸣也许是非正统的,但被群体理解为一种真诚的吊谒行为,从而得到拥护。第二则关于驴鸣的逸事从而变成第一则逸事的反讽版本,引发了观者不恰当的反应,笑声既藐视了约定俗成的葬礼行为规范,也藐视了葬礼本身蕴含的意义。然而,那些嘲笑孙楚并破坏了这一严肃场合的名士们也许给出了一种恰当的回应——正如惠通驳斥顾欢时所言的——指斥一个错把驴鸣当作音乐并期望驴鸣能获得知音的人。
作为结论,我将再讨论一个例子,一首创作于上述文本几百年之后的诗,它或许能被看作是中古时期关于驴鸣话语的后续。这首诗是大诗人苏轼(1037—1101)所作的《和子由渑池怀旧》,是与其弟苏辙唱和的诗。在诗中,苏轼构造了一幅无常的、时光飘移,以及流逝的景象,最后以我们已经熟悉的驴鸣结束: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①冯应榴(1741—1801):《苏轼诗集合注》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0 -91页。我参考了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翻译,见宇文所安编译: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Beginnings to 1911,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96,P. 678.
人生苦短,一个人可能留下曾经存在的痕迹,但那常常真的只是痕迹而已。前四行精心构造了雪泥鸿爪的比喻,作为对开头“人生何似”这一问题的回答。然后,苏轼从诗歌意象与哲学沉思的畛域转到当下的渑池(在今河南省),这是他和他的弟弟曾经到访过的地方,他们借宿于一座寺院,并题诗于墙壁。如今故地重游,已是物是人非:曾经留宿他们的老僧已经去世,埋葬老僧骨灰的新塔刚刚建好,他与苏辙曾经题诗的墙壁已经毁坏,字迹不复可见。
诗的结尾亦悲亦喜,苏轼唤起他弟弟去回忆一个仅仅存留在兄弟二人记忆中的场景。他们漫长而艰辛的旅程是一段无法仅仅用文字与铺陈来完全表达的经历,却在蹇驴的嘶鸣中被唤起,苏轼也用这种声音结束了全诗。除了苏轼和苏辙,蹇驴嘶鸣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对于苏氏昆仲,这驴鸣声将兄弟二人关于渑池的共同记忆具象化。苏轼从所有关于驴鸣的荒唐和庸俗话语中,将其升华为一种崇高的时刻,因为正是在对驴鸣的回忆中,兄弟俩知道失去了什么,留下了什么,使得他们成为彼此的知音。
[责任编辑 闫月珍 责任校对 李晶晶]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研究》(批准号:12WWC014);
[作者简介]陈 威(Jack W. Chen),男,美国华裔学者,哈佛大学博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与文化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中古文学研究。 武泽渊(1991—),女,江苏南京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收稿日期]2015 -12 -15
[中图分类号]I206.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072(2016)02 -0011 -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