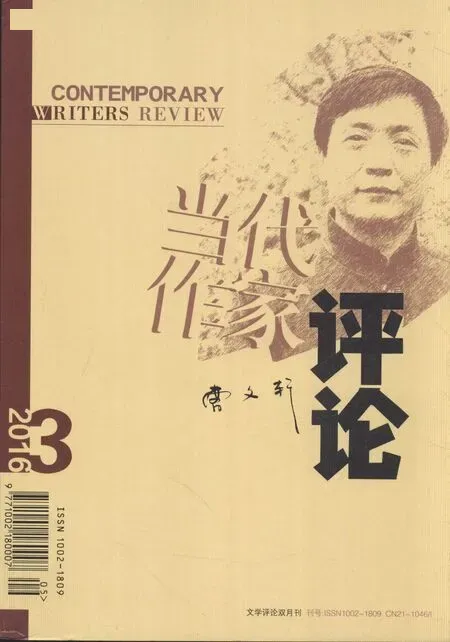近十年诗歌事件解读兼论余秀华的诗歌
肖 辉 黄晓东
诗歌研究
近十年诗歌事件解读兼论余秀华的诗歌
肖辉黄晓东
二○一五年夏天,我再次路过距离南京大学后门不远处的先锋书店。这间书店开在地下室,很不起眼。走进书店,摆在最显眼处的是余秀华的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和诗选《摇摇晃晃的人间》,我立马买了下来。其时余秀华已经走红大半年,在今天这个自媒体的时代,她俨然既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被媒体追逐的娱乐圈里人。直到今天“余秀华热”还没有褪尽,二○一六年初,门户网站还在登出有关她的八卦新闻,是关于她的婚姻近况的。余秀华的走红,算是跟新诗有关的又一个“诗歌事件”,甚至“文化事件”,距离二○○六年诗人赵丽华的“梨花体”诗歌事件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这十年间,出现了很多跟新诗有关的“事件”。跟这些“事件”有关的所谓“新诗体”也层出不穷,诸如“羊羔体”、“咆哮体”、“乌青体”、“歌颂体”等等,不一而足。而其间在网络上因为诗歌事件引发的“口水战”也异常激烈和混乱,例如诗人沈浩波的“下半身写作”在激战中就被重新翻出来,作为被攻击的靶子,一时间真可谓热闹非凡。十年间,新诗事件轮番登场,直到出了个余秀华和她的“成名作”《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因此我们不禁要思忖:为何“出事”的总是新诗?新诗人为何总是“走红”?“余秀华热”与此前的诗歌事件有何不同?余秀华的诗歌又到底该如何评价?
一、新诗为何总是“走红”?
今天很多人都觉得白话诗的门槛很低,不像写作旧体诗那样,还要考虑押韵、平仄、对仗等老规矩。不仅如此,旧体诗有时为了写出好的字句,还要去“苦吟”,为了一个字可能要“捻断数茎须”,偶得佳句还可能要“一吟双泪流”。相形之下,白话诗似乎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可言,只要不是文盲,谁都能读得懂,因此也就谁都可以评论两句,甚至可以写两句。正因为“门槛低”,新诗更容易受到网民和大众的关注,大众也自认为有能力来关注。我想这也许就是历次诗歌事件几乎都能“全民关注”和“全民参与”的重要原因。那么我们再试问,白话小说和散文也通俗易懂,为什么大众不去关注小说或者散文呢?今天它们阅读起来的难度也并不大。可是围观诗人余秀华的人仿佛比关注小说家莫言的人还要多,莫言那可是中国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其中的原因在于白话诗一般也就寥寥数行,短小精悍,很适合在今天的媒体,尤其是自媒体上登载和转发。试想,如果你把莫言的长篇小说《蛙》放到微信圈,在这个全民娱乐化和时间碎片化的时代,可能就没有几个人会耐心地去把这个长篇看完。看不完,自然,网民大众也就没有“资格”和兴趣去评论小说或散文了。因此篇幅短小导致的“易读性”也是白话诗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这算是新诗在文体上占了“优势”,所以才经常“出事”,也容易“走红”。
其次,阅读载体和“批评”方式的改变是新诗受到“关注”的另一个原因。如今随着阅读载体的变化不再是纸质文本的一家独大了。文字呈现的载体还有手机和电脑。而且电脑阅读甚至已经逐渐让位给了手机阅读。所以“低头族”才应运而生,随处可见。不仅如此,大众在阅读的同时,还可以随时随地对网络文本进行评论。读者、评论者之间还可以随时随地地进行互动。阅读方式的改变,也最终导致了评论的方式发生了实质性改变。而短小精悍的新诗,在网络上被传播和被评论的速度和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了。例如“梨花体”就是在博客和网络上迅速引起关注和围观的,这在纸质媒体的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两种媒体之间,在文本阅读、评论的时间和空间上都不具有可比性。网络文本呈现的这种迅疾性和共时性独具优势,同时也导致了文学评论能及时跟进。而且网络具有的虚拟性和娱乐性等特征同样开始显现。例如二○○六年“梨花体”诗歌事件时,当时在网络上就出现了万人仿写“梨花体”的现象。随后赵丽华被封为“梨花教主”,相关网站和讨论的虚拟平台也随之建立。不仅如此,就网络评论而言,在媒体的引导和推波助澜之下,网络名人和“大V”的效应也很独特。“梨花体”事件时,韩寒作为当时年轻人的“文化领袖”、网络名人,率先在网络上用博客文章开始了对“梨花体”尤其是白话诗的冷嘲热讽。作为论敌的沈浩波也加入其中,沈浩波的“下半身写作”也因此被韩寒翻了出来,“算了旧账”,尤其是他那首“代表作”《一把好乳》,被骂成是“诲淫诲盗”之作。而沈浩波则骂韩寒“别装处男”。当然,在此期间,很多真正触及“事件”本质和新诗本质的问题也被忽明忽暗地提了出来。例如韩寒说“白话诗没有存在的理由”,“因为有现代歌词就够了”,“白话诗只是分行的散文”,等等。韩寒的评论在此次论战中值得思考,因为他开始谈到了问题的本质。新诗自诞生以来就有正反两面观点,其中反面观点就是质疑新诗存在的“合法性”。
当然,网络时代的文学事件也有其独特之处。其特点是把有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无限放大,使其成为舆论的焦点,甚至借此来哗众取宠。下面一一来看。“羊羔体”诗歌也即纪委书记车延高的诗歌,也曾经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它和“梨花体”诗歌事件一样,网络时代的娱乐化倾向和噱头还是伴随其中。例如在热议“梨花体”诗歌之时,网民突出了赵丽华本人的头衔——“国家级诗人”和“鲁迅文学奖评委”,而同时又把人们的眼光引向了她的几首自娱自乐的打油诗,网络舆论的导向无外乎可以总结为“这个‘国家级女诗人’,‘鲁奖评委’居然写出了如此垃圾的诗,大家快来看啊!我们来骂她吧!”。然后网友的一片骂声也就如期而至,更多的围观、恶搞所产生的巨大网络效应也就势不可挡了。在“羊羔体”事件中,舆论的导向同样突出了诗人的“官员身份”,而不是其“诗人身份”。言下之意:“官员写的这么差的诗居然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大家快来看啊!我们一起来骂吧!’”而赵丽华真正的代表作自然不会是那首引起“热骂”的“馅饼诗”;同样,车延高的代表作也不是那两首引起热议的写女人的诗《徐帆》和《刘亦菲》。当然在“羊羔体”引起热议的背后,是人们对于当下文学评奖制度的关注和质疑,其中包括文学和“权力”的关系等问题,这才是论战背后的本质所在。至于“乌青体”事件,则是人们对于无内涵的“口水诗”极度失望的表达。但是网络舆论把大众的目光引向了对这种“无意义”的口水诗的过分关注。就像有人在地上吐了唾沫,于是有人被喊来围观和议论,然后越来越多凑热闹的人陆续围了上来。
还有,“咆哮体诗歌”是以标点符号和叹词的重复为特征的,这带有网络时代的用语特征。对它的仿写也是网民和大众内心的一种生活情绪的宣泄,某种程度上具有后现代的特征。而“歌颂体”则涉及到新诗写作与现实和政治的关系这一问题。至于被重新翻出来并引起热议的沈浩波的“下半身写作”,或者我们称为“身体写作”的诗,其本质是:在稍早或者当下这个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包括写作和表达环境——之下,男性诗人对其内心隐秘的,甚至在公众看来有些“委琐的”、“淫亵”的(对女性的)性心理的直白大胆的表达和书写。而且据我推测,诗人本人对外界评论以及自身写作所持的态度有一种“我就是流氓,我怕谁?”的意味。诗人甚至将自己的写作视为先锋的和独树一帜的,因为没有或者很少有男性诗人会如此直白大胆地公开在诗中描写、袒露男性如此隐秘潜在的性心理。当然,这种书写在传统道德观念之中,有一种侮辱女性的味道,很容易成为公众和女权主义者批评和攻击的对象。
二、我的阅读史:“余秀华热”与众不同吗?
最早知道余秀华,是有人在微信圈里贴出了她那首“成名作”——《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微信圈里有人对这首诗很是称赞,转发的频率也很高。百度了一下才知道,大家谈论的诗人余秀华,被贴上了“脑瘫诗人”的标签。我的第一感觉是,脑瘫的人能写出来被人称赞的诗?还引起了这么大的轰动?是不是余秀华把“睡你”一词直接写进诗里,所以被人称为“脑瘫”,其实是说她“脑残”?继续了解后,才得知她确实是个残疾诗人。于是又认真阅读了网上贴出来的她当时颇受关注的其他几首诗,有《在打谷场上赶鸡》《我爱你》和《一包麦子》等,感觉写得都不错。我没有对余秀华诗歌在网络上的“舆情”做太多调查。但我至少没有看到像以往的诗歌事件那样,网民曾经的“骂声”、恶搞、论战,这次都没看到。网络上出现的更多是正面的评价。在第一次阅读《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次又是个“炒作”的事件,因为我感觉“睡你”这个显得有些过于粗俗、口语化,而且涉及到“性”的词语,居然公开地出现在诗句的标题上并贯穿诗篇始终,是很突兀的。特别是“睡你与被你睡是差不多的,无非是两具肉体的撞击”这样的句子,更是显得过于直白赤裸。但是对此网上却貌似并没有什么批评之语。我对古代祖先们的“艳词”了解得不多,但据我推测,即使“艳词”中涉及到“性”的,恐怕至少也要含蓄一点,委婉一点。于是我不得不感慨时代的巨变,时代对于“性”的态度的巨变,时代对于诗歌中“性书写”的态度的巨变。
到此,也还需要指出,余秀华的走红还是具有自媒体时代的特征,其中也包含“炒作”、“噱头”、“起哄”等因素,这可能是不知不觉的,但也是若隐若现的。因为绝大多数非专业读者和网民对余秀华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脑瘫的女诗人写了一首好玩的“睡你”的诗,我们都来看看!于是网民大众都来围观。但是真正有耐心和素养来对余秀华诗歌做整体阅读,并对她诗歌风格作总体把握和评价的,肯定是很少的人。但是,有了最初的“围观”,才能有之后的“走红”。这是网络时代的特点,也是优势。因此余秀华的走红与前几次的诗歌事件相比,有相同之处,不同之处是少了负面评价。因为,相对于“睡你”那首诗而言,她剩下来的诗,网民则更是无法“起哄”的,它们与此前网民“起哄”的“诗歌”之间有着“质”的不同。另外专业阅读对余秀华的认可,对抑制网民的“起哄”,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当然,那些“网络名人”和“网络大V”们,更不会起哄,他们都具有读懂现代诗的素养,他们纵使选择沉默,也不会去冒“贻笑大方”的风险。
我对余秀华最初的阅读体验还有两点:在《我爱你》这首诗中,诗人写道:“……我会寄你一本关于植物的书,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稗子那提心吊胆的春天。”诗中写到了“稗子”,我想今天的年轻人和城市人恐怕没几个知道稗子这种杂草,也就不会知道诗人把残疾的自己比喻成稗子,她是在提心吊胆地活着的。所以读者如果不知道“稗子”为何物,就很难体会到诗人那种心境,很难领会只有将“稗子”和诗人的“多余人”心态相结合,诗歌才能产生的那种悲悯的意蕴。这里说的是阅读障碍。最初阅读的还有诗歌《一包麦子》。诗歌通过一个“扛麦子”的细节,来表现亲情和父爱。去年父亲还能把一包麦子扛上肩膀,但是今年不行了,“他骂骂咧咧,说去年都能举到肩上,过了一年就不行了?”其实余秀华很多的文本都是通过生活的细节和鲜活的农村生活场景,来表达对生活和人生的一种切身的感受和感悟,这样也能很容易地引起诗人和阅读者之间的共鸣,也最终赢得了读者的心,这应该就是所谓的越真实越动人,越真切越动人。当然,至于不了解农村生活的年轻读者是否能产生共鸣,这也是我担心的。
三、余秀华是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
余秀华走红以后我一直关注专业批评对她的评价。给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沈浩波,还有一个是沈睿。沈浩波的评论文章叫《冷看大众狂欢下的“诗人”》,刊登在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的《文学报》上。文章中沈浩波对余秀华的诗歌有一个总体的评价,他认为:“……无论是从其诗歌的整体水平看,还是审视其中的局部的语言、内在情感与精神,都没有太多可观之处。再客观一点说,余秀华的诗歌已经进入了专业的诗歌写作状态,语言基础也不错,具备写出好作品的能力,但对诗歌本身的浸淫还不深,对诗歌的理解也还比较浅。”不仅如此,沈浩波还认为余秀华“把苦难煲成了鸡汤”,但是“大众必会持续喜欢,热泪涟涟”。沈浩波的文章中也有具体的文本分析。他认为在《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中“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无非是这花朵虚拟出的春天,让我们误以为生命被重新打开”,这几句“是很本质的诗歌描写”,“是非常个人化的体验和洞察,具备本质的诗意”。而后面写到的“火山、枯河、政治犯、流民、麋鹿、丹顶鹤……”则过于宏大、空洞,也很媚俗。沈浩波对上述这首诗所做的具体的文本分析,我是基本赞同的。因为读完余秀华的两本诗集,就会发现她最能打动读者的还是那些通过具体的、细节化的乡村生活来叙述个人生活体验,表达个人真切的人生感受的诗歌。至于沈浩波对余秀华的总体评价我觉得相对客观,虽然他没有过多地褒奖或使用溢美之词。
学者沈睿是余秀华诗集的编者之一。她对余秀华诗歌的评价从她两篇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来。一篇是《这个让我彻夜不眠的诗人》,一篇是《余秀华的诗歌有何力度》(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和二月十二日的《文学报》)。在后一篇文章中,她对余诗也有总体的评价:“余秀华的诗歌呈现出她的语言天才,她的语言和想象力,有一种自然的横空出世,不是做出来的诗歌,是天上掉下来流星雨般闪亮的语言,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她是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沈文还从语言和想象力方面来着手,以文本《栀子花开》为例,对余诗特色做了大篇幅的分析和解读。
沈睿在文章中把余秀华比喻成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我翻阅了几本汉译的狄金森诗选,觉得至少在文本上两位女诗人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因为两位诗人毕竟生活于两种文化之中又相隔了几个世纪。余秀华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她生活在中国农村,由于自幼残疾,她的内心对生活有太多独有的个人体验和感悟,但是她却又能用自己的笔朴素、真切、清晰而又灵动地将其传达出来。她的文字中浸淫着的也是浓厚的中国本土文化,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各种中国式的情感,包括“夫妻”、“父母”和“男女”。这也就应了那句话,越是本土的才越是世界的。至于余秀华和当代中国其他女诗人及其群体的区别,很是赞同《诗刊》编辑刘年的一段话,说得形象而又生动:“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广西师大版余秀华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之“代序”)。
回望过去十年,从“梨花体”开始,新诗在网络上好像一直在丢分,一直被起哄,被喝倒彩,嘘声一片。余秀华的出现为新诗扳回了一局。余秀华的成功我想在于由于种种原因,她能沉下心来,真实地书写和记录她在那摇摇晃晃的人间的真切感受,书写她的所思所想,包括她的抗争,她的幻想。仅仅在这一点上,我想她和已经过世的作家史铁生倒是有几分相像。因为在浮躁的氛围之下,沉下心来,除净火气,也是写出好作品的必要条件。我这里谈的仅仅局限于近十年的诗歌事件和余秀华。希望新诗在未来能够一路走好,不再出事,真正走红。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民国以来的新诗教育研究”(15YJA75101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李桂玲)
肖辉,铜陵学院文艺系教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黄晓东,铜陵学院文艺系教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