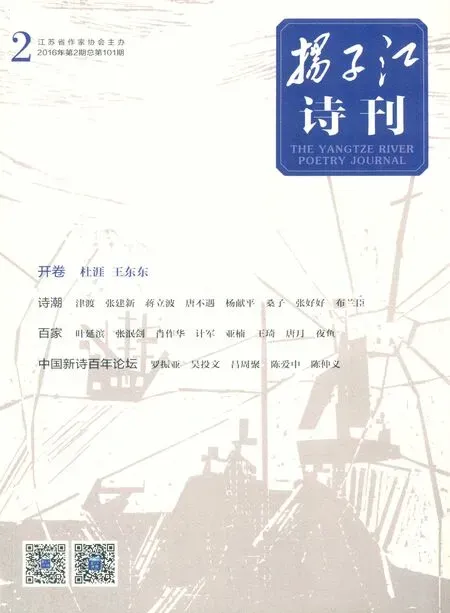马迟迟的诗
马迟迟
马迟迟的诗
马迟迟
马迟迟,1989年生,湖南隆回人。
永恒的节日
下雨或者阴天的时候
他常常坐在庭院的一棵树下
那时,火车在高压线下开过
她从厨房出来,猫蹲在花园的一角
他们的小院临近一条古老的河
四月寂静的郊区,鲜有人迹
他们周围居住着几家等待拆迁的农户
偶尔有邻人捎来鱼和新鲜的蔬菜
她总是笑,眼里有数不尽的云
他已经很少外出,有时朋友过来看他
他们会坐在午后干枯的葡萄藤架下
讨论里索斯、济慈或者茨维塔耶娃
鸽群通常是四点钟的时候飞过河流
而更远处的河中,轮船于巨大的日照下
闪耀着灰白的光。在他们搬过来后的五月
他已经清理掉院子里枯败的花草、器物
她换下好看的裙子,暮色纤弱又苍翠
房子的后面是一座没有名字的矮山
山上长满了灌木与高阔的树
夏天深起来时,一些鸟雀便成群地来到
他和他的情人常常在上面出现
绕过坑洼的小路,虫蛾唧唧
六月,他们的谈话日渐疏少
(而事实上,他们通常都很少说话)
每天早上,他独自一人去往河边
头顶上空,天际寥廓、晦暗
他们互相道,晚安和再见,彬彬有礼
后来,那个女人的大部分时间
都用来研习厨艺,或者养猫
偶尔在院子里栽种爬山虎、月季
和牵牛花。她们争执又和好
长日复短日,时间像轰炸机般驰过七月
他的病情逐渐好转,开始写作
八月的时候,很多个夜晚都被雨声灌满
她坐在树下他常坐的位置,在月亮下弄出
微亮的水声。他仍在写一些不为人知的诗
没有人想到他们会生活在一起
他们养起了鹅,买来农具与饲料
在院子里圈起篱笆,栽种蔬菜
他们知道再过几月,这里的事物都会长大
像度过美好的时光。后来
他们又收养了一只狗,每周一
他就会带着他的情人绕过院子西面的
一道竹林与细密的菜畦
去往城市的中央。哦,再后来
他们之中谁也没有意识到
日子会像这样晃闪着,平凡地过去
冬天就要来了,她对他说:
就这样吧,像永恒的节日
虚度时光
秋天进入九月,下旬,铁路桥下
水波平静,轮船在夕照中驶向远方
刚刚他给朋友,写去回信,信中提及
佩索阿与卡夫卡。小区外,高压线
麻雀站成阵列,那种孤独,他看到
梧桐树与樟树,早餐店、杂货铺还有
菜市场,一辆准点的火车,它的轰鸣
充斥耳膜。寂静,是从厨房,水龙头
流下的水线开始的,他想到他的
敌人与友人,他的原罪,在抵抗和潦草的
一生中,充满虚无,哦,虚无
一种心灵的分身术,让他的持续写作
变得毫无意义,一整日
他斜躺在这张暗红色沙发上,思考
而她的腿一直搭在他的身体上,在离他左手
三公分远的距离,一张旧报纸被一只打翻的
茶杯溢湿。她穿短裙,她的内衣,扔在
沙发的一角,而她的另一只脚靠在
茶几上,茶几上摆放着,泡面、零食、啤酒
和遥控器。墙上的电视机还未关
晚风经过书房,纱幔曳地,他给她念
《死亡赋格曲》里面的诗节,长发盖住的
双乳,她用右手轻蹭他的腿,用左手
支撑下巴,注视他,仰望那种声音
磁的旋律,肩胛骨与臀的弧线
像下午三点,叶的细细反光,他们谈到爱
和前女友。她说着,他从地板上拾起
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本,他死去前女友送的
名为《双重人格》的书。而此刻
蹲在墙角的猫,突然发出诡异的叫声
黑天鹅
这天,父亲说的黑天鹅在水面浮现
这只黑天鹅,在一个早上
仿佛人类此刻还未醒觉,四野静寂
我看到上帝创造出的一个颜色
在混沌中接近闪电
那是黑色的闪电,孤绝、阴翳
在河流的邈远之境,时间的空洞里面
这就是父亲说的那只黑天鹅吗?
十二件乐器
它漆黑的脖颈摆动
好像拨动世界的某一个音节
它浮在水面,观照黑的反影
那红的唇,来自一朵火焰
颔首与昂首,就是地球的低分音与高分音
这只黑天鹅,父亲说的
它在祖辈的传说中并未消失
此刻,黑天鹅扑腾起夜的羽翼
在水上奔跑起来,珠花四溅
哗哗哗,音乐在光华中波涌
自由、决绝、反叛的乐章
让这个正确的时辰,变得壮烈而哀戚
哦,黑天鹅终究会飞入雾霭更深的远山
飞走吧,黑天鹅,飞走吧
让我更清晰一些,接近父亲的真理
一个突然寂静的雨天
一个雨天
我在柜台整理旧书
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我蓦然从厨房转入卧室整理旧书
找不出缘由
我一本一本将它们从书柜里面拿出来
又一本一本放归原处
这一系列的动作
让我感觉到一种缓慢的愉悦
这是一种进入到急遽极致的缓慢
在卧室外面,雨声越来越大
听不到声音,我顷刻间清晰起来
一种骤然的寂静,我蹲下来
想到一些很远的细节
这是老友赠我的四本书籍
米 沃什《晚期诗四十八首》、布罗茨基《诗四十一首》、塞林格《九故事》
以及二十月的《双行星与小卷兽》
我幡然悔悟还没有读过它们
而后天,我却要把它们一一送还
因为一个事件,这时候的雨声
从寂静又复归浩大。我看向窗外
神经质般的用衣袖擦拭书上的灰尘
我好想把它们都擦拭干净
复归朋友送我时的模样
可这是朋友送我的
而我现在为什么都要送还?
我还没有认真读过其中的一页
或许命运原本就是一个辽阔而带有神秘的修辞
在四本书里面,我以为占有了它们
在无数平常的时刻,我那些下意识的念头里面
而这里面带有世界它所有的发生
——那些后来的幸和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