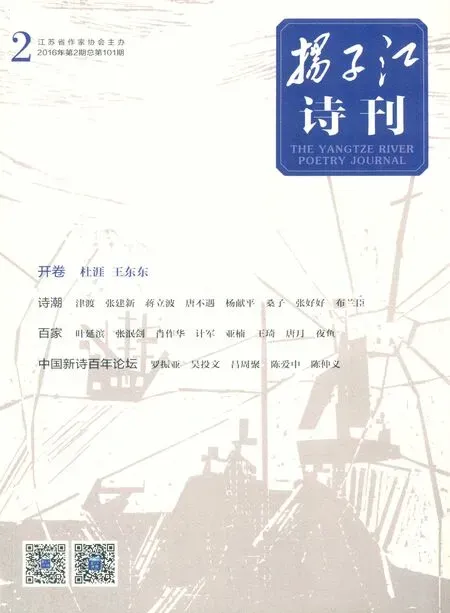津渡的诗
津 渡
津渡的诗
津 渡
社火饭
五十棵玉米秸秆走进火堆之后
我们遇见了自己的祖父
在溪流对岸,眺望乡间小路、麦地
他手里紧握的牛缰变成了一尾
鱼,一封书信
那些在火堆里冒烟的土豆,多像溪水中的卵石
我们埋头吃着社火饭,黝黑的面容照亮
而下巴骨喀嚓作响,一会儿就吃光了祖父
凉亭桥
梦中,上升得很快
我从云层里丢下了衣裳
欢娱过后
雨把枝上的梨花悉数打碎
醒来后,发现醉卧在袍子里
既没有姓氏,也没有名字
古老的拱桥上
风火轮转得飞快
亭子,亭子也不是我的
它有底座,有顶盖
四壁,是风做的墙,四条腿
永远奔走在石礎之上
但是每个人都回到了自身
假山,池塘,或是一根桑条
只有一只摇摇摆摆的小鹅是我的
心里明亮的事物
论白云
年轻时赞美她
像爱着少女,狂热地爱她。
又在床单的梦境里
像是突然失去了撞针,留下
羞于表白的记忆。
正如垂柳只顾着低头
溪水中有一个她
而风筝,总是在挣扎,幻想着
从上面去看一看她。
中年后我们被一场大雨淋湿。
如今隔着门槛看她
她离我们不远,也不近
还给我指缝间的一绺白发。
我也曾越过神庙的檐角眺望她
她垂下额头,一语不发。
当缥缈的势必成为永恒
该告别的告别,要说的也不会太多。
谁想过狮子的颈上会发生雪崩
留恋她,怀想她
极度的狂欢之后,痛苦地埋葬她。
登高阳山
是在秋天
乘醉到达山顶。
一缕跳起来的云,在交谈中变淡、消失。
因为哀伤,龙葵的果实
愈发鲜艳。
然而我记起过往的岁月,就在枝条
弯折的淤瘢之中。
天色愈晚,我们的狗
在膝下转圈、呜咽,仿佛脖子上
缠着无形的绳子。
河水一如既往地平缓,但是蕴藏暴力
等着将我们冲入大海。
关于马鲛鱼的一个童话
厨师从烟囱里望出去,只有一圈云
接着,天色暗下来,铺在马鲛鱼幽蓝的背上
一盆净水,厨师手指上的十块鳞片游动了起来
刀子,迟疑地
向着掀开的两片波浪中插下去
鱼 腹剖开后,厨师走进去,找到了铁锚、船桨、三角帆
和巨大的桅杆,然而船长
坐在鱼鳔的交接处抽烟,样子很阴郁
水手们正朝着一个方向使力,拖拉鲜红的鳃耙
从一根直肠,缓慢地摸到胃
厨师冷静地,摸到了老祖母的放大镜
咸鱼铺子
只有咸鱼们知道,冬天有多么寒冷。
咸鱼们在竹竿上排好队,咬紧了生铁钩子
咸鱼们互相问候,挤紧。
走进来的人低着头,说:咸鱼
走出去的人低着头,也说:咸鱼
咸鱼们眼眶深凹,嵌着窗外的乌云。
开始下雪了,像盐粒一样簌簌地落下。
有人往灶膛里扔咸鱼,用咸鱼取火
有人用柴禾串起咸鱼,在炉子上烧烤。
有一只炊壶里装满了水,咻咻地
喘着粗气,而店老板有事没事
会打开咸鱼皮夹,翻检里面的纸钞和硬币。
有人用旧报纸包走有文化的咸鱼
有人小心翼翼,用竹篮提着水
带走了一条性感的咸鱼
有人替咸鱼翻了翻身,就放下了。
有人穿着双咸鱼的鞋子,吧哒吧哒
跳过了门前的臭水沟。
天色渐渐黯淡下去,天气更加阴冷
红灯区里的红灯,红得滴血。
咸鱼们松开口,放掉了生铁钩子。
咸鱼们溜到了大街上,咸鱼们
像件深色的外套,伏在人们肩上。
咸鱼们伏在屋脊上,一声不吭……
而在最宽阔、最阴冷的海面上
最大的一头咸鱼甩掉了身上的鳞片
咸鱼彻夜难眠,身下的脓汁和血污粘成一片。
这可不关店老板的事。
绮园惊梦
这危险的游戏
又让湖水上涨了三尺。
穿过桥洞的锦鲤
悬浮在桥面之上,谈起了米皮
盐齑菜,妇人和天气。
时间一度静止。
湖边,南方所有的树木
皂荚、花楸、黄榉,杜英与香樟
从它们的管子里
不约而同,对着泻湖
吐出了香涎与汁液。
事实上,一切都尚未发生
湖水已被我生生裁掉。
掉在条石上的,只有摔碎了的
热的,流淌的光线。
盐,并没有分解,树,仍然
在季节里活动
并且如期地拜访津渡先生。
只是一把反向的锁
至今沉睡在湖心
三只空酒瓶,也没有把它砸开。
滚铁环的小孩
滚铁环的小孩推动铁钩子
铁环,从遥远的地方
推过来:大队、小卖部、洋灰马路
别扭的河湾
一阵阵雨,冲走河滩的树阴……
嚯嚯作响
他已推上我的脚背
胫骨、胯骨,我的脊梁
他推上我的后颈
我等着他歇下来,一些东西
却在快速地塌陷
一转眼已是多年
他在我中年的耳廓上推动
他沿着破碎的眼眶推
他向我眼窝深处推,在我大脑深处
他终于停了下来:
一只黑圈,一个瘦小的黑影
祖母的忌日
祖母从神龛上走下来
轻易地穿过了我们。
她轻手轻脚,参观每个房间
并且扶正了蛋糕上的樱桃。
像她生前一样
我们拥有幸福的生活。
一把香菜,平静地搁在碗口
未关严的龙头淌着水滴。
不仅仅是这些。
下个星期,中秋节来临
我们会集体去一趟动物园
父亲将抱紧最小的孙子。
而我们呆到很晚,在草坪上
玩扑克牌捉强盗的游戏。
直到节日的焰火点燃,一瞬间
看见整个家族,狂欢的血。
今天,大人们脸色落寞
孩子们挤在一旁吃喝,满嘴奶油。
祖母和胡桃树握完手
不说拜拜,回到了光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