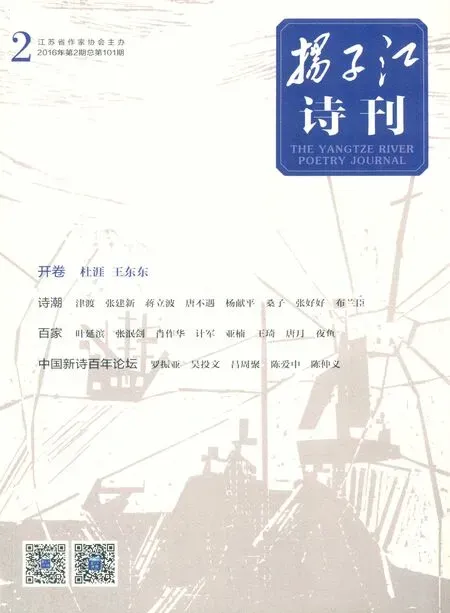王辰龙的诗
王辰龙
王辰龙的诗
王辰龙
王辰龙,1988年生于辽宁沈阳,现居北京。
影子:马铁虎
你痴迷急速上升的事物。他骑车下班,你
仍追赶竹蜻蜓的落点,直到她推开厨房
第二扇门,去阳台探出声音找你,骂你上楼。
南窗也已系上冰锁,年关近了,另一个下午
绕到化工厂小区的北面,一次次点燃窜天猴
灰色的短尾:最高的那只,误撞药厂宿舍的
屋檐,五层楼,我屏住呼吸……是年的五月,
劳动公园筑好鬼城,在伪地府的出口
我听见你体内的火药肾上腺般地呼啸:
不够……还不够。余下碎银两,我们就奔往
凌霄飞车飞过夏秋与寒假,你却抵达他
某夜的切齿:“永别了,工厂。”继而,他竟
向她和你作四年的暂别。“大北监狱,大北,
监狱。”起哄着挤作一团,他们踢沙土,你
紧跟她,不曾怒目不曾打过来,只是消失于
六单元的暗影之中。他终究回家;你一直在
却没再归来。“下来玩呀,马虎!”我听见我
一跑出五单元便喊,略去你名字里散发
黑硬光泽的部分,它像十余年前的流星,
划过此刻京畿突兀的晴夜:有人正在城北
隔着十一月的狭渊为烟火鼓掌。我想起你。
影子:姐
风发出了响动,我们的耳朵是挂铃般的
眼睛稍稍张开,它们透过温暖的幕纱,
摇向一边,看蹑手蹑脚的流动如何平息。
你总先于我,离开午睡的袒护,如竹蜻蜓,
出入于暑假的下午。小身子已滑过了十个
春天,你以柔软去迷恋糖果,你正爱得发痴
却单把糖衣留下,双目纤美如丽人手,将斑斓
喜看,你抚平塑料彩虹的褶皱。而那些炮弹,
都打给了我,我不归地发胖,并将跃向某一种
未来和八月末:被秋老虎紧盯,流汗。你则会
瘦 如水果硬糖,一裹上花花裙衫,就去小城探望
改 嫁多年的母亲。好时光如今想起都留在夏天了:
呆日头扒着工人村的建筑,五层楼曝露着红砖
从 四面围拢花圃,野草正紧。我们无法掘出深坑
用 以掩埋他对她说出的狠话、她对他施加的咒骂。
就 找一片铁凉亭边的松土,挖妥了小而深的窠臼,
你 落稳本周最爱的糖纸,你覆上汽水瓶底或碎窗的
一 角。俯身赏玩,回土,踩实……可你不曾在冬天
再 找回它们,即便当年的雨季没有过膝。很多次,
你沮丧极了,不甘心,泪水顺雪原的反光飞入
繁 星的行列。而我,陪你一起等待,等冷锋过境。
影子:姥
伏天里的厌食者消瘦依旧,她步入腊月,总是走得太快,却未尝溅动声息,往后也不曾亮起声控灯,久久封冻楼道的昏暗,直到一把明锁弹开门后的微光。紧跟她你踅过公用的长走廊邻人们堆出的旧物又多出几件,它们轮廓上的手温正退向你有关疼痛的记忆:是独自回家的坏时辰,走廊愈发狭长,得小心绕过雕花木箱闪避卸去了后轮的废车,赢取啪叽的那个夏夜它们碰碎过你的欢喜佛。三楼高的苏联式民居这惊觉之前的魔方大厦,你终究还是无法把它扭转为玩具柜台上的六面兽,一个她许诺中的礼物,它忽暗忽明在停电的冬夜;而卡车碾响阴着脏雪的后街,擦亮梦魇的余震,你看她正用点燃波心的手势熄灭磷火,等待他们的晚归
影子:爷
叫卖更近了,如爬山虎,它攀附
工人村新楼的外墙,尖梢漫出
打糕的诱惑,绿得刚刚好,足以
佯狂成一声钟,响彻你的瞌睡。
把左手从往事里探出,你练习醒来
唤我,一边摸索与喜悦对称的零钱。
而我正在模糊的大雪中走不出来:
肇工街,雪,拥挤多时,我五岁
站了起来,惊喜于被棉花接住;妈
扶起摩托,惊讶于我不喊疼,还乐;
往卫工街继续走,走入另一片白色
听你躺卧酒精气味的暖围,笑谈如何
被司命小仙的血栓箭狠狠命中……
跑回三楼卧室,八月的阳光蝉衣
都来不及抖落,就与你咀嚼此刻
我们最大的福。我后悔,我忘了
向那好游商去讨一个回答。星期一
他还会来吗?甜海的潮汐出入南窗……
这是石头流满你右半身的第六年的
某天下午。点了心的你拈起白纸
它缓缓鼓起蛙的姿态,你教我按
它的臀,蛙便跳出半指之远。你
继而依次拈起八张纸,恍若扯动
大小不一的八个扁木偶:前仆后继
它们在瑜伽中折起身子,成为
塔的局部……我真后悔,祖父,我
忘了问你那可以站立的纸塔顶端是否
藏有时光灵骨,能给二十五一剂醍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