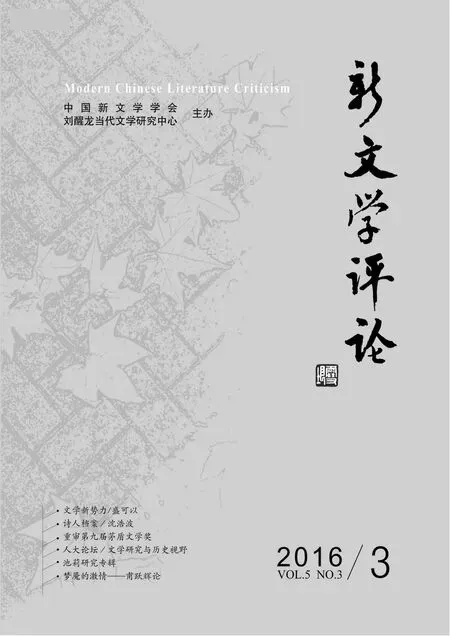盛可以小说的价值观念探询
——以长篇小说为中心
◆ 何 雯
盛可以小说的价值观念探询
——以长篇小说为中心
◆ 何 雯
李敬泽曾评价道:“盛可以的小说有一种粗暴的力量。她几乎是凶猛地扑向事物的本质,在这个动作中,她省略了一切华丽的细致的表现性的因素,省略了一切使事物变得柔软的因素,她由此与同时代的写作划清了界限,但她也在界限之外获得了新的力量,那就是,她更直接地、不抱任何幻想地呈现了我们混乱的经验和黑暗的灵魂。”①确实,盛可以整个的创作都洋溢着冷峻犀利的叙述风格。可以说,她是毫不留情地将生活与人性的本质剖开,呈现给读者,并通过各色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来阐释她对于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念的理解。
一、 现代观:精神失落、 道德失范的经济时代
盛可以长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大多以改革开放后为时代背景。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以飞快的速度向前推进,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自愿或非自愿,都被卷入了这场时代洪流之中。
这场巨变的最大表现是城市的猛然崛起,尤其是在南方。而城市建设与发展带来的经济诱惑,对于依附于土地却看不到出路的农村人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于是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其中包括数量庞大的女性劳动者。然而,对于这群怀揣着美好幻想的外来者而言,广东(包括其他地区、大城市)不是寻梦的天堂,而是现实的炼狱。这首先表现在生存压力上。来自农村的受教育水平较低的打工者一般只能进入建筑、制造、餐饮等对雇员知识、能力要求不高的行业,这些工作同时也有着工作时间长、强度大、报酬低、稳定性差,甚至存在安全隐患的缺陷。和在农村一样,他们还是用劳动和血汗换取生活,身体依旧是他们交换价值的筹码。而对于女性而言,这种身体的交换来得更加残酷。从发廊到酒店到夜总会,有姿色的女性总是被打上暧昧的标签,以取悦男性来获得金钱或稳定的生活。而在其他场域,这种交换也司空见惯。《北妹》中,村长就以职权之便,要求那些想办暂住证的女性向他奉上处女身。而当地男人常把猎艳北妹当作娱乐,有妻有子的坤仔就哄骗了李思江,与她同居,最后闹得她怀孕打胎。在工厂里,潜规则也已经成为普通女员工摆脱繁重劳动求得上位的必要手段。这群无一技之长的外来者只能以自己仅有的资源去谋求生存,处境十分艰难。然而,即使他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城市中也还是处在边缘地位的。他们还要面对可怕的收容制度。该制度的本意是遣送外来无业人员回乡,是一种社会救助,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却被扭曲成了警方创收的手段,他们通过抓捕和保释来获取经济利益。被抓的人面临的不仅是财产的损失,还有生命威胁,有很大比例的人就曾不明不白地死于收容救治站。《野蛮生长》中的六子就是这样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对于外来打工者,城市在经济建设的考量下是接受他们的,但同时在政策上,尤其是户籍管理制度,又是排斥他们的,将他们视作次等公民。这些人在城市中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他们作为城市建设的有功者,却享受不到应有的待遇和荣耀。盛可以对此有这样的感叹:“领导们逢年过节上演给红包送温暖的感人节目,在镜头前亲民如子,工人无法讨回自己的血汗,在没有镜头的地方声泪俱下。这个千疮百孔的城市,始终保持一个现代化都市的繁荣表象,各项指标排名全国前几位,像一个生意兴旺的漂亮妓女,内心流毒。”②在她看来,城市的罪恶来自粉饰太平,底层劳动者的痛苦被遮蔽,上层的丑恶嘴脸被掩盖。处在中间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则充满了消费时代的享乐气息,他们丧失了理想信仰,沉溺于情欲,追寻感官刺激而无积极向上的精神求索。整个现代城市的构成,在盛可以的眼中,就像表面精美的建筑,内里空洞无物,下面还埋葬着难以计数的尸体。
与城市相比,乡村尽管相对闭塞,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变化却更为显著。在以土地为生存手段的传统农村,社会结构是稳定的,乡村文化是自然的,但现代化的推进使得农村大量劳动力资源流向城市,乡村的封闭性被打破,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在面对现代化新风气新观念尤其是对物欲的无限制追求时,传统的乡社精神节节败退。换言之,在现代化浪潮中,乡村经济条件提升了,而精神内在却也衰颓了。对此,盛可以做了自己的展示。在《道德颂》里,盛可以通过女主人公旨邑,描述了她的故乡——一个湘北古镇的改变:“经济似乎好起来,部分旧木楼消失了,代之以洋楼小景。河里的水污染太重,不能饮用,游泳也不行了,政府将它包给个体户养鱼(一年到头往里撒肥料),改变了全镇人的生活趣味。年轻人都在吸毒,和抽烟一样普遍,毒瘾上来,趁黑到乡下偷鸡摸狗,打家劫舍,弄得村民们天黑闭户,每家养好几条狗。派出所的伙计们认钱不认人,行贿者能拿出上百万的人民币上下疏通。一个纯朴的小镇都变成这样了,其他自不待说。”③除了表现现代文明对乡村文明的冲击,盛可以也批判了乡民身上的某些劣根性。这首先表现在这些人的“看客”行为上。他们兴奋地围观新鲜事物,津津有味地观赏残酷场景,却对不公的现象不置一词。《野蛮生长》中的大哥李顺秋和其他几人在“严打”时期无辜被抓。在开审判大会时,村民们都去围观,那种盛况,“只有端午节才这么热闹”。人们还跟着游街示众的车子,去行刑地看枪决的场面,见证杀戮。盛可以借李顺秋之口表达了对这种陋习的憎恨:“你们都沉默,沉默就是帮凶。”作为集体沉默的一分子,人们意识不到自己的袖手旁观就是对施害的放纵,这种无意识的犯罪才更可怕。其次,表现在对他人私生活的关注与干涉上。在乡村,个人隐私基本不存在保密性,一有风吹草动,便会尽人皆知。而消息的受众往往又不满足于知晓,还会透露给其他人或者在当事者面前表达自己的看法。李顺秋的妻子因病出走,女儿失踪,他只好回到乡下家中。村里人还总是乐于在痛苦的他面前展示他们廉价的怜悯,提醒他作为一个失败者的事实。而谣言的制造与传播则更具有攻击性。在《北妹》中,钱小红就被春树嫂子污蔑在广东从事不正经的工作,大家还四处传播,使她名声败坏。另外,乡民们对死者不敬,对死亡不尊重。在《野蛮生长》中,爷爷将死的时候,“围观者嘻嘻哈哈,谈论我爷爷的荒唐事,场面喜洋洋的”。而大舅出殡的场景更是荒诞、血腥。为省钱,舅妈买了便宜的棺材,结果开裂了,只好重新钉合,而大舅又是高大的身材,结果棺木都染上了他的血。在乡村,死亡只与死者和至亲有关,旁人也不过是“看客”。当它来临时,没有肃静的场面,没有庄重的体面,有的只是与俗事纠缠的难堪。对于这些沿袭下来不曾改变的乡村文化的缺点的批判,盛可以在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现代性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渗透是方方面面的。不论是对新生的城市文明的构建还是对传统的乡村文明的冲击与改造,现代性都展现了它强大的影响力。而对于现代性带来的弊端,盛可以在她的小说中表现了明显的批判倾向。一是批判经济迅速发展,而精神世界却极度贫瘠的窘境。金钱至上的新准则,已经蚕食了传统的公序良俗,使人堕入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做出有悖道德、有违常情的事。在这个时代,个人外在的社会性得到加强,但是内心更具封闭性。精神失落、道德失范的大时代,人们实在难以寻到生命的诗意和生活的意趣。二是批判社会对底层人民更加深重的压迫。在城市,无学历、无能力的人只能做着最苦最累的工作,领最少的薪水,忍受来自各方的欺辱践踏。在乡村,没钱没势的人只能成为欺凌的对象,就像《野蛮生长》中的李春天拿不出两万块的超生费,怀孕七八个月还要被强行打胎结扎,而村干部乡干部的亲戚则可以躲过惩罚。三是批判混乱的男女关系。在现代都市,爱情、性和婚姻统统都被肢解了。结婚离婚如同儿戏,出轨、插足、同时交往多个对象已成常态,钱(权)色交易亦不稀奇。就像《水乳》里描述的那样:“商场里过日子的男女,满提着生活五味及日常用品,女的手臂懒懒地插在男的臂弯里,很难说是否貌合神离。女人在美容院把脸面整理得干干净净,说不准她取悦的对象。某些娱乐场所里挥霍钞票的男人,谁知道他是哪个女人的丈夫。”④在盛可以的笔下,婚姻的神圣性不复存在,它表面光鲜,内里却破败不堪。以道德来约束的两性关系已突破了传统的规则,发展成了自由的甚至混乱的交往现象。
二、 伦理观:对传统伦理的消解
“伦理”二字,最早见于《礼记·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在中国,伦理这个概念主要是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说的,其实质就是客观的人伦之理,即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理、原则和规范。”⑤所以,相较于“道德”而言,它更侧重于人所具有的社会身份带来的行为要求。但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我们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更有新的伦理观念在滋生、蔓延。
家庭关系是传统伦理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由父母和孩子构成的原生家庭中,理想的状态应该是父母关心子女,子女孝顺父母。这样一个良好的双方互动关系,在盛可以笔下,基本没有出现过。她的小说多是描写女性背井离乡,在大城市工作的经历,家庭或者说父母往往是缺席的。《水乳》中女主人公左依娜的父母只出现了一次,那是她登记结婚后,郑重地写信(而非打电话)告知双亲。她为自己仓促的婚姻恐慌不已,渴望来自亲人的关心,但得到的反应却令她别扭,因为他们不但没有责怪她的草率,还高兴于她在深圳安定下来。《无爱一身轻》中朱妙的父亲和哥哥们只出现在一次插曲般的回忆中。《道德颂》中曾写到旨邑回老家过春节的情节,但关于其家人的描述也仅是几笔带过。这些于都市中奋斗的年轻女性,在小说中,仿佛已经脱离了为人子女的角色,她们的原生身份是模糊的。在《火宅》中,女主人公球球虽然因母亲的冷淡而感到痛苦,但她还是孝顺的,为了生病的母亲奔走。可惜这只是感情的错位,母亲对于这个捡来的孩子并没有付出真心。在《野蛮生长》中,父亲则是一个专制的、暴戾的家庭独裁者,母亲及四个孩子甚至祖父都生活在他的管制下。姐姐李春天对父亲更是恨得咬牙切齿,诅咒父亲死掉,甚至以嫁人为手段逃离。所以,在盛可以的小说中,家庭和父母往往是缺失的,即使涉及,也不曾有父慈子孝的温情。这应该与作者的自身经历有关。她的父亲重男轻女,且脾气暴躁。为了摆脱这种家庭暴力,姐姐匆匆嫁人,而她则早早独立,外出闯荡了。这些过往,在她的创作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在由夫妻二人组建的新生家庭中,双方应当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忠诚于彼此。但在盛可以笔下,婚姻关系总是存在各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婚内出轨了。这些人有的是为了逃离令人窒息的婚姻,有的是为了满足身体欲望,有的是为了报复配偶的出轨,不管怎样,在婚内做出这种行为,就是对配偶的不忠,对婚姻的失信。
除了家庭伦理,两性伦理也是传统伦理的重要内容。在长期的男权社会中,女性较之男性是弱势的,是被统治的,于是在双方关系中,世俗和道德对男性是非常宽容的,而对女性则是极其苛刻的。这集中体现在“贞”上。“贞”,本指品行、操守,针对女性而言时,是指对女性性心理和性行为的道德要求。在中国古代,要求女性不得失身不得改嫁。这种对女性单方面的性禁锢否认了女性的基本需求,是非人道的。盛可以抨击了“贞”这个枷锁对于女性的伤害。如《火宅》中的球球,被黑妹泄露她打胎的消息后,镇上人都传她的谣言,她成了众人口中的破鞋,而她夜晚出门寻找县长的举动也被污蔑为偷情。对她有好感的男人也都因此远离了她。而在现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贞”这个陈旧教条对于女性的桎梏却还没有完全消失。盛可以塑造了一系列意识到问题并发出试探性反抗的女性形象,她们通过“性”来反抗传统规范加诸女性身上的枷锁。这些女性享受爱情,甚至享受情欲。《北妹》中的钱小红常常和看上眼的男人发生关系,《野蛮生长》中的李小寒在大学期间交往了四个男朋友,《无爱一身轻》中的朱妙和《道德颂》中的旨邑则都与中年已婚男性交往,《水乳》中处在婚姻里的左依娜也是先后与两个男人发生了婚外情。盛可以完全消解了“贞”对于女性的心理束缚,她笔下的女人大多遵从自身情感的本能驱动,而不以道德来绑架自己的欲望。但可惜的是,现实情况使得这种反抗往往都是以失败收场。
除了亲人、配偶、恋人,朋友是与我们关系最亲密的人。按照传统伦理原则,做朋友要交心,要相互认可,相互帮助,相互支持,有共同话题,能推心置腹。但是在现代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纯粹的友谊寥寥无几。在盛可以的小说中,女性之间似乎就很少有真正的坚固的朋友之情。除了《北妹》中钱小红和李思江的共患难以外,其他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及其女性朋友之间都难看到相依相伴的真情,往往还因为男人而存在隔阂。《水乳》中,左依娜和苏曼同时与吉姆郎格(即朱涵文)保持关系,虽然彼此都不知情;《火宅》中,傅寒与球球交往之前曾和程晓蝶有过过往,抛弃了球球之后又与程在一起;《无爱一身轻》中,与朱妙有过一夜情的张超成了龙悦的前夫,后来又将和朱妙结婚;《道德颂》中,谢不周和秦半两两个与旨邑有暧昧关系的男人都被原碧勾引到手。不管有意无意,女性友情因为男人而变得异常复杂与尴尬。而女性之间关于男人而引发的相互倾轧更是触目惊心。《火宅》中的黑妹暗恋厉红旗,但是厉却和球球走到了一起,嫉妒的黑妹捅出了球球曾经堕胎的事情,不仅使得两人分手,也彻底败坏了球球的名声。在《道德颂》里,原碧一直不喜欢旨邑自视甚高的姿态,嫉恨她在异性面前的受欢迎程度,于是处心积虑地勾引了与旨邑交往过密的两个男性,甚至要求旨邑做她和秦半两婚礼的伴娘。这是发生在朋友之间的背叛与报复。而那些没有交情的女性之间的相互打压,更是常见。在《北妹》中,老板娘因为丈夫对钱小红的垂涎,就诬陷她卖淫,将她赶出发廊,还有黄杏和大辫子姑娘为了一个男人的垂青而勾心斗角。本该惺惺相惜、互相扶持的底层女性,却为了私利私情互下狠手,实在是令人哀叹。
在这急速变化的商业时代,伦理关系的社会稳定性崩坏,有着血脉亲缘的家人分隔两地,自行选择的配偶、恋人、朋友,往往又因利益和欲望而关系紧张。在盛可以的小说中,人类自私的本性在这个追求物质的社会中愈加彰显,传统伦理维护的人际和谐与温情大多被消解殆尽,现阶段的伦理道德犹如立在深渊旁边,摇摇欲坠。
三、 婚恋观:形而上的追求与 日常生活和解的不可能
有学者认为:“在盛可以的小说中对爱情的鄙弃既是对现代理性改造过的爱情理想的鄙弃,又是对失去了统摄力,把男女之间的关系仅仅视为赤裸裸的动物的性关系的无爱现实的失望。”⑥于是,我们发现,在盛可以笔下,现实导致的心理落差使得爱情无处安放,女性的爱情和婚姻往往都是悲剧,行文间仿佛可以感觉到张爱玲女士作品中的苍凉。分析文本,可以知道追求和失落构成了这些女性的情感轨迹。《北妹》中,钱小红先后遇到了很多男人,唯一让她有爱情感觉的就是警察朱大常,可惜的是他已有未婚妻,拒绝了她。《水乳》中,左依娜为了逃离磨人的婚姻两次出轨,但都没有得到好结果,最终还是回归婚姻。《火宅》中,球球在经历了初恋傅寒的欺骗后,厉红旗用真心拯救了她,却在约定提亲的日子不见踪影。《无爱一身轻》中,朱妙渴望结婚,但是方东树为了家庭和前途放弃了她,程小奇的欺骗与玩弄、许知元对她的猜忌和侮辱,更使她遍体鳞伤。《道德颂》中,旨邑追随有妇之夫水荆秋,也是遭到抛弃,而真心相待的谢不周则与她天人两隔。她们按照本心、本能去追求自己想要的感情。但可惜正如“白色野菊花”的隐喻——自由和死亡,她们的追求最终只能沦为对理性世界的投降。
在盛可以的观念里,爱情的本质是虚无的。它只可能短暂存在,并且与身体的欲望冲动是分不开的。叶开就曾评论道:“很显然,对于爱情,盛可以是冷酷的。她的冷酷,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冷酷。在这样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爱情的确是可疑的,只有肉体尚且可以触摸。”⑦爱情是自由的,但是这种无保障的自由会使人滑入一种虚无的境地,而婚姻的安全感则对从未体验过的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是一旦踏入婚姻,个人性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妻子、丈夫的家庭角色,花前月下的浪漫演变成茶米油盐的平常,这种稳定性又将使处在其中的人感到寡淡无味,甚至产生恐慌感、厌倦感。盛可以以《水乳》中女主人公对于结婚登记的直观感受表达了自己对此的看法。“往名字上按手印的时候,女人左依娜心里涌起一阵莫名其妙的恐惧,与结婚有关的温馨感觉一概没有。她看见自己的名字躺在血泊中,像一具赤裸的尸体。这个环节像判决、枪毙、死亡一样,充满血腥。”⑧在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模式下,困在其中的人想寻找突破,追求精神的刺激,于是发展出婚外恋情。《北妹》中一位中学老师就直言:“有婚姻才有外遇,有老婆才有外欲。”而这种不道德的婚外恋情,出于种种现实因素的限制,往往也不能攻破牢固的婚姻城堡,不论是左依娜的主动逃离,还是朱妙和旨邑的持续攻略。另外,在婚姻中,女性明显还是处于弱势地位。被当作配偶的所有物,丧失自由和个人权利,依旧是相当一部分已婚女性的生活常态。同样是出轨,男性往往能轻易获得妻子的宽恕从而维护婚姻,而女性则常常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或是像《水乳》中的袁西琳,丈夫坚决要求离婚并让她净身出户,或是像《无爱一身轻》中的林芳菲,丈夫理所当然地冷落她并发展婚外情,或是像《野蛮生长》中的李春天,丈夫以此为理由对她进行奚落侮辱。总之,这种男女双方的不平等,也是造成女性婚姻悲剧的元凶之一。
爱情是属灵的,是精神层面的,婚姻则是属物的,是与现实生活相捆绑的,有时甚至要与实际利益挂钩。《水乳》中左依娜的丈夫前进为了获得最后一批政府微利房和她结婚,《无爱一身轻》中方东树则为了得到林芳菲父亲的提拔重用而娶了她。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因为各种原因而结合的无爱男女。婚姻由此更是一件庸俗、乏味的事情。爱情是个人性的,而婚姻则更多的是社会性的。“社会日常性把爱情吸引向下,使之变得无害,建立婚姻家庭的社会建制,同时也否定了作为生命张力和神魂颠倒的爱情的权利。社会日常性否定爱情的自由,认为爱情的自由是不道德的。爱情主题一开始就是非社会化的。社会化的是家庭。”⑨确实,爱情本身不是结果,它不可避免地要滑向另一个阶段,结束或结婚,也就是死亡或者沦为日常。前者或是绚丽地死去,给人们留下美好的回忆,像钱小红对朱大常,旨邑对谢不周,刘一花对六子,李小寒对喻书中;或是残忍地被杀,留下伤痛,像吉姆郎格之于左依娜,傅寒之于球球,方东树之于朱妙,水荆秋之于旨邑。而后者,就如上所言,进入婚姻的内循环。所以,社会日常性没法容忍自由的非社会化的爱情,要么将之粉碎,要么构建婚姻的秩序,将人归于合法监管之下。至于婚外恋情,则不过是扰乱秩序的一场混乱,平静之后,“太阳照常升起,没有什么偏离日常之外”⑩。盛可以在解构了自由、爱情和婚姻之后,将一切都纳入自然的惯性中去。在日常生活与形而上的追求之间,她始终没有给出一种和解的可能。
四、 审美观:揭示黑暗又展现温情
盛可以本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说过:“我喜欢真多于美,喜欢观察阴影多于欣赏阳光。”这种观念投射在写作中,正如她自己描述的那样:“在我的小说中,我用一根银针准确地刺进生活的内部,以及人性的穴位,于是,真实的站立,虚假的瘫痪。因为,在虚假和伪善粉饰的人间,我不去审那样畸形的美。”对于她而言,揭示现实的黑暗和丑恶,远比描绘飘渺的光明与希望来得真诚、实在。不管是《北妹》中打工妹的艰难处境,《水乳》中都市女性的婚恋悲剧,《火宅》中小镇少女的成长疼痛,或是《无爱一身轻》与《道德颂》中婚外恋的惨烈结局,还是《野蛮生长》中的家族几代人的不同悲剧命运,统统呈现了作者的创作初衷。
在小说中,盛可以批判了这个经济时代的利益至上、精神失落、道德失范,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无辜民众的戕害,也批判了堕入庸俗甚至虚无的爱情和婚姻。但在一片晦暗混乱之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她笔下小人物所表现出来的坚韧和追求以及人性的温情。在《北妹》中,钱小红是一个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女孩,她和很多农村年轻人一样,怀揣着对大都市的向往和出人头地的期望,南下S城打工。在一路上,她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体验了打工者的艰辛痛苦,看到了有权有钱者的无耻做派,了解了关于这个城市的种种乱象。但在这个大染缸里,她坚守着自己的原则,不拿身体作为交换的条件。即使最后被身体拖累,即使最好的姐妹离开,她还是选择继续在这座城市里挣扎。在《火宅》中,球球的生母许文艺,虽然已经疯了,但还是一直关注球球,保护她,这种舐犊之情,在那个昏暗不明的小镇里更令我们动容。在《道德颂》中,谢不周对于旨邑的关怀照顾,超越了男女爱情,于破败不堪之中拯救了她,指引她开始平和的生活。在《野蛮生长》里,晕车的母亲坚持坐很久的汽车去探望服刑的儿子,李春天疯了还是记得给女儿买娃娃,还有六子在刘一花不同意交往的前提下仍背井离乡地守护着她,喻书中明知会招来祸事还是要坚决报道收容制度的黑暗和SARS事件。这些鲜丽的色彩虽不足以支撑我们对于现实的乐观态度,但作为这灰色社会和黯淡命运的点缀,却也能唤起我们对美好事物的感动与期待。正如盛可以说到留在有着灰蒙蒙天空的北京的原因:“我就是喜欢在这个充满雾霾的城市,等待那不常有的美丽天空,只要它一出现,它所赐予的幸福感就足以涤尽往昔的晦暗。”
在盛可以的文学审美建构中,她坚持独立、自由的品格,执著于对苦难和疼痛的犀利表达,整个作品呈现了悲观和虚无纠缠的复杂面貌。《北妹》是粗粝的、原生态的,以女主人公钱小红的辗转经历为线索,带出乡村到城市的社会现象,《水乳》、《无爱一身轻》等则从外部的描述转向人的情感挣扎,叙述也从大线条的勾勒转变为细腻的描摹。而到了《道德颂》,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哲学因素的增加,使得小说的思辨色彩提升。这与此前不加节制的率性书写相比,不仅是叙述方式和写作理念的改变,也折射出了作者生活态度的变迁,从愤世嫉俗的尖锐转变为自然无为的内敛。而到了《野蛮生长》,作者的创作更加理性化,以冷静旁观的姿态展现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生存史。虽然盛可以小说的审美风格在不断地调整、改变,但是她的审美期待与理想却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毫不掩饰地揭露以期得到关注,引起反省。
盛可以说,在乡村,“贫苦”和“诗意”并存,那么在现代生活中,两者也是共生的。她的笔尖,有着类似鲁迅先生的锋利,大量地描述了沉重的现实和幽暗的人性,其间表现出来的种种价值观念也体现了她对这个荒唐世界的冷酷认知,李修文评价她有“丝毫不惧怕凄绝命运的决心”。她以悲观的角度来剖析、呈现,但并不绝望。因为她认为“悲观是切入世界、认识世界最好的方式。当然悲观不是撒手等死,它赋予人冷静与内省的精神空间,能比乐观产生更大的价值与动力”。她的小说,真切地戳痛了我们的敏感神经,读来使人备感压抑,却可以使我们联想到现实,联想到自身。如果我们能开始反思甚至开始自我精神的重建,盛可以写作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吧。
注释:
①盛可以:《北妹》,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②盛可以:《无爱一身轻》,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③盛可以:《道德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④盛可以:《水乳》,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页。
⑤朱海林:《伦理关系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8页。
⑥徐仲佳:《无爱时代的困惑与思考——关于盛可以的写作》,《南方文坛》2003年第5期。
⑦叶开:《干掉爱情的三种方式——读盛可以长篇〈水乳〉》,http://gb.cri.cn/41/2004/02/17/381@69648.htm。
⑧盛可以:《水乳》,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
⑨盛可以:《道德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⑩盛可以:《野蛮生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8页。
暨南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