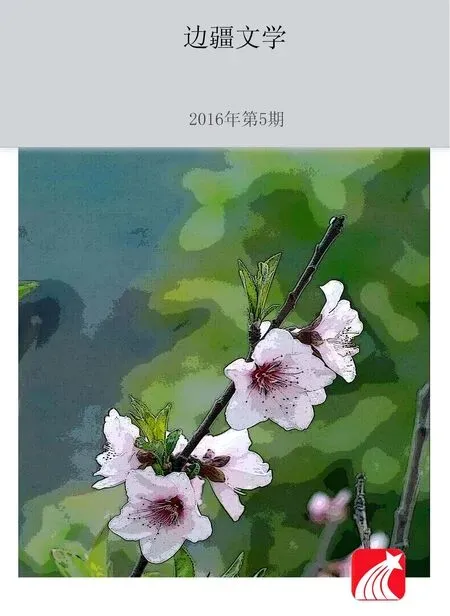张好好的布尔津
◎张晓琴
作家与作品
张好好的布尔津
◎张晓琴
主持人语:2015年,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医学奖,这是中国人首次获得的科学奖,是中国人为之骄傲的大事。我们虽不懂医学,但透过已提前出版的《屠呦呦传》,了解一些传主的生平事迹、成长经历、性格特点以及她是如何长期顽强拼搏,一心一意在投入科研,终于攻克难关,取得伟大的成就,是非常有价值有帮助的。《真实远比传奇更有力量》这篇评论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它总结出屠呦呦宁静的力量,提出“抓住‘宁静’这条主线,可以说是捕捉到了人物的灵魂,也是最打动读者的所在。”这一总结,对于当今身处异常喧嚣杂乱社会中的人们,包括所有的文艺评论工作者,也是具有启发作用的。(蔡毅)
我的布尔津,它是我的,就如同是我的爱人,与我血肉混为一体,我无法不罗唣地写到布尔津的哪怕是一枝艾蒿。
——张好好
初读张好好,时光倒流,尘世遥远,恍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遇到了萧红。那是2014年的夏天,我在《人民文学》杂志读到张好好的长篇小说《布尔津光谱》,被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应该再读读她的其他作品,可是,一时间找不到更多了。于是,通过《人民文学》杂志社的一个朋友联系到她,电话里,她的声音温暖,有布尔津阳光的味道。很快,收到了她的电子版作品,数量之大远超我的想象,除了诗和小说之外,竟然还有一本解读古诗的专著。我发现,张好好之于我,不仅仅是艺术魅力的吸引,更意味着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作家和其身后更为广阔的地域与文化的关联,作家如何以个人的方式实现这个时代的共同思考,如何呈现同代人成长的共同性与丰富性,作家在作品中又思考着怎样的现实问题。或许中国当代诸多作家也可以引出诸如此类的问题,但张好好的回答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张好好的魅力究竟何在?她以绵密酣畅的文笔与精致诗性的意象,间或复杂难言的乡愁,铸造了一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布尔津世界,这个世界是诗性的,散发着人性的温暖,尘世气息与哲学品质共存。张好好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又有在国内大都市生活的经历,她的写作中当然少不了都市生活,她的笔触细腻绵密,都市女性的存在与情感体验在《周末咖啡馆》、《幸福树》、《枝叶摇晃》、《软时光》、《静如天使》等大量作品中可以得见。然而,独特的成长经历让张好好对故乡、人生、存在等有了独特的思考
与体悟,她写布尔津世界的作品更具魅力。与那些许多一鸣惊人的作家不同,张好好的光芒是逐渐散发出来的。她2001年开始创作,潜力惊人又勇于创新:先后有诗集《布尔以津》、《喀纳斯》、《从前的年代》,长篇小说《布尔津的怀抱》,散文集《五块钱的月亮》、《最是暖老温贫》、《宅女的宅猫》,古诗研究随笔集《那么古老那么美》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问世。及至2014年,终以长篇小说《布尔津光谱》而绽放异彩,随后的长篇小说《禾木》更是一部难得的诗化小说。张好好的布尔津已经自成一格,她的写法亦是我行我素,而诗性则是讨论她的一个起点。
诗性的温暖的布尔津
“我敢说,/如果一片土地的冬如此地使你眷恋/它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乐土/冰封的/恰恰是希望,是来年大海深处溯流而上的问候/这问候自然年年地来,年年的我们/在这爱着的土地上,年年地站成直指蓝天的白杨”。这是张好好诗集《布尔以津》中《我爱的土地》一诗的句子。这首诗情感上与艾青的《我爱这土地》非常相似,一个人对故土最深挚的爱无非如此。在我看来,张好好首先是个诗人,诗歌是她存在的必然方式。诗集《布尔以津》、《喀纳斯》、《从前的年代》中都有大量布尔津故乡的诗:《月光下的小城》、《月亮河》、《童年》、《这是一片耐心的土地》、《多么标致的一条河》、《退回去》、《所以亲爱的河流》、《四条河流》、《我们的月份》……读过这些诗后,再读张好好的小说,就发现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诗性的布尔津。
是的,诗性,它是好小说必备的品质。中国现代文学以来,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这一脉以诗化小说而留名于世,废名自称“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1],张好好也是如此,她写诗的同时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她说:“在古诗中,人类精神的高贵,言语的高贵,都彰显着,保留着,我返身进入,无比荣幸与他们团团坐在一起对语。”沈从文说,“个人以为应当把诗放在第一位,小说放在末一位”[2]。张好好的创作与沈从文颇有相似之处,诗化的小说风格,同时写都市与故乡,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写故乡的部分。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现代文学上的高标,而张好好的布尔津正在引来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光。汪曾祺在和施叔青对话时曾经阐述过他的小说观,即“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3]。张承志也是诗化小说的坚定践行者,在他看来,“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诗。无论小说、散文、随笔、剧本,只要达到诗的境界就是上品。”[4]他对西部民族精神资源的挖掘不容忽视,而张好好小说中对民族精神资源的探索与张承志异曲同工。
如果说萧红的《呼兰河传》中的主人公是呼兰河小城的话,张好好的布尔津世界的真正主人公就是布尔津小城。布尔津是极负盛名的旅游地,也是中国最美的小城之一,张好好这样描述布尔津:
这里是阿尔泰山腹部的一块巨大开阔地,风总是浩浩荡荡,雪挥挥洒洒,河的涛声肆无忌惮,闯入我们的梦乡。丰沛的河水滋养着广袤的森林,白杨、白桦同野蔷薇等灌木相偎相依,黄色的蒲公英每年春天装扮草原,蓝色蜻蜓薄翼的翅膀弥漫整个夏天,白桦在秋天转红,冬天里大雪封山,人迹罕至。
额尔齐斯河就在他们的窗外。听河水流动的声音入睡,而且那水是活的,神采飞扬甚至略有跋扈的,盛着月亮的时候才温婉许多,傍晚会盛着绚烂的晚霞,白天里盛着柳树杨树榆树的树影……
这里,许多植物若生长便是大片的,一脉铺展开去,用视线和太阳起落的弧线勾画,也用一场浩浩荡荡的大风来丈量。它们饱满洁净、无限舒展,或艳丽或低沉的色泽,自然地焕发出来。麦子的金,葵花的乖顺,红柳燃烧的红,桦树的雪白,枣花的浓香,苹果花如翅的轻盈,灰灰草的“请你忘记我”的含混,蒲公英的童心,棕红色铃铛果在荆棘中若幼小的鼠,柳树尽向着天空昂扬生长。
布尔津的记忆是诗性的,也是温暖的。除了长篇《布尔津的怀抱》、《布尔津光谱》和《禾木》外,《发端》、《花朵》、《蝴蝶花》、《虫草疯长的夏天》、《黄雪莲》等中短篇小说也是布尔津世界的重要构成。《蝴蝶花》中,张好好说:“写它们的时候,我开始刻意寻找布尔津三十年前的气味的时候,我知道,那些记忆永远在那里了。它们构成了今天的我,这个叫张好好的女子。”张好好的作品中有“70后”一代人的成长记忆:《阿里山的姑娘》、毛阿敏、《草原之夜》、广播里路遥的《人生》、电视剧《一剪梅》、电影《牧马人》、大白兔奶糖、上海奶糖、一家人去照相馆照相,还有计划生育……
当然,长篇小说《布尔津光谱》和《禾木》是张好好布尔津世界中最重要的构成。《布尔津光谱》运用双重叙述视角,一重是作者,一重是爽冬的亡灵——一个未足月被引产的婴儿,他是个折翅的天使,但他有自己的使命:看着布尔津的众生、大地和天空,生存和死亡,离去与归来。小说中的亡灵叙述极少冰冷与残忍,反而多了许多温情。爽冬被海生用小毛毯裹好后埋在红柳崖,他并不孤单,家里的大灰猫一直尾随着他,他的三个姐姐也到红柳崖找过他,他第一次回家,姐姐爽春就看见了他。他对世界没有一点怨言,即使偶尔悲伤,也仍然坚信世界最后留下来的都是温暖和美好。他多么想钻到妈妈小凤仙的怀里,让她知道自己有多爱她,但是他无法实现这个愿望,他在悲伤中仍然由衷赞美小凤仙:她是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妈妈。小说中的海生、食堂里的董师傅也都一样,他们流泪的时候,嘴角那里却是微笑着的。
从小说的诗化程度来看,《禾木》比《布尔津光谱》更深。《禾木》由93节构成,是一首叙事抒情兼而有之的长诗。喀纳斯的蓝水、和布克赛尔大草原的绿,可爱如欧洲小城的布尔津小城,禾木山的神秘与温情,共同开拓了布尔津的新空间。作者以诗性的语言叙述父亲的人生与有关禾木的历史与当下,生存与信仰,小说中也有对于生态的破坏的痛心疾首。小说用第二人称叙述,这本身是有很大难度的,但是当张好好把对父亲与对故乡的情感融在其中之后,反而显现出一种难得的流畅与酣畅。父亲是布尔津世界中的重要人物,张好好在诗歌中曾经无比深情地怀念与赞美父亲:“他离去又回来,只为我在梦里哭出来/——咯出结节的痛”(《他说——给父亲》)。《绝别——写给父亲》、《金莲花地——献给父亲的爱情》、《我想念,你的大手》,都是献给父亲的诗。当然,小说中的父亲不能完全等同于生活中的父亲。《禾木》中父亲因为一个生活在禾木的叫娜仁花的图瓦女人十年滞留在禾木,还和她生了一个儿子,但是父亲不承认。多年后,“你”去禾木寻找这个图瓦女人和他们的儿子,这个儿子的名字叫巴特尔,就是勇敢的意思。“你”四处流浪,生活不易,但“你”把她们放在心里,对禾木那个弱小善良的图瓦女人和“你”的小姑姑一样充满爱意。
《禾木》把布尔津世界的温暖进一步深化成爱。“你只是为了等一个爱你的人出现。你全部的信仰就是这个。”小说第77、78、85、87四节是“你”爱他的理由。张好好的主人公往往成长过程中“家底殷实,但情感不快乐”,唯一的拯救途径是爱。“唯有爱,让那伤口愈合。——孩子长大,这是爱;遇见了呵护你懂你的人,这是爱;原谅一个人,把温暖公正的话语给这个人,也是爱。“你”说:“亲爱的图瓦女人,你们是天下草原的母亲,别就这么放弃了……留下来的只能是美和善。”小说快要结束时,张好好这样叙述:“所以你的父亲,用那端凝的微笑走入你的梦中。”爱成为张好好写作和面对世界的一种信仰。
民族的历史的布尔津
在和桫椤的对谈中,张好好这样描述自己在布尔津的生长环境:“我出生在布尔津,眼睛一睁开就看见了大河,牛羊,青草,鲜花,做木匠的父亲,做裁缝的母亲,美丽骄傲的小姐姐,还有邻居漂亮的哈萨克小伙伴,屋檐上行走的猫,院子里狂吠的狗。我们出生就坐在哈萨克老乡擀制的羊毛毡上。我们吃邻居哈萨克阿姨油炸的包尔萨克,吃馕坑烤制的金黄的馕。我们吃山上的牧民送下来的酥油奶酪和奶豆腐。逢年过节我们吃大锅炖的牛羊肉。我们知道清真的礼节。忌讳哈萨克老乡们忌讳的一切。我们和他们,从来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这是怎样的一种生命影响?!它意味着我们从小就没有一颗‘分别’的心。”布尔津生活着哈萨克人、图瓦人、蒙古族人、俄罗斯人,也有汉族人,这些民族的生存与信仰是张好好布尔津世界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布尔津光谱》中,爽夏和爽秋在阿娜尔家玩,阿娜尔教姐妹俩学哈萨克语,学习哈萨克人的礼节。她们还观察羊毛毡上盘绕的花,虽然姐妹俩看不出所以然来,但却感悟到那是哈萨克人的祖先在远古时候赞美天地说出的话。姐妹俩低头吃阿娜尔妈妈做的哈萨克饭菜,她们沉默不语,那意思是:这么好吃啊!我们家里做不出这个味道来。《禾木》中更有大量关于图瓦人和蒙古族人对自然的认识与生活的呈现。小说中的父亲是个汉族人,但在自己的汉族妻子面前没有尊严,就去了禾木山里,和一个叫娜仁花的图瓦女人生活,因为这个图瓦女人给了他宁馨。禾木,是带给父亲宁馨的地方。图瓦人远古的时候信仰萨满教,后来在统治者的更换,信仰佛教,但他们更是萨满教的子民。图瓦人有自己的语言,他们的小孩子都会说蒙古语、哈萨克语、汉语,有的还会说俄语。布尔津小城里也居住着俄罗斯民族,他们酿造了一种叫卡瓦斯的酒,张好好甚至以此为名写过诗:“乡愁坐在高高的河堤上吃沙枣,它递给我一杯叫卡瓦斯的甜酒,并将酿酒的秘方压在酒杯之下”(《卡瓦斯》)。卡瓦斯不仅仅是俄罗斯民族的酒,也成为布尔津多民族的文化象征之一。布尔津也时常能看到牧民下山时的情景:“牧民定期会从草原上,从山里来到小镇。他们穿着皮袄,戴着皮帽,骑在高大的马背上,赶来牛羊,搅起喧杂的动静。”“他们的马拴在店门口的白杨树边。马总是百无聊赖地站在那里等待。马尿的气味冲天,但那是青草的味道。我们从不会嫌弃和指责任何一匹随地大小便的马和牛。黄昏的时候,牧民骑着马离去,他们上了南边的额尔齐斯河大桥,或者去了北边的布尔津河大桥。他们的身影看着无比地寥落。长河落日的圆让他使劲一蹬脚,踢着马的结实肚皮,马加快了脚步,绝尘而去。”张好好也写出了布尔津各个民族生活的艰辛与不易:可爱的哈萨克姑娘阿娜尔小小年纪就去乌鲁木齐给人做了保姆;新娘子小凤仙剪掉了长发,开始捡破烂,小凤仙后来和男人一样去六道湾淘金;她和海生因为交不起计划生育罚款,怀孕五个月时忍痛去医院做手术。还有青木这样的年轻美丽女性的故事,都让人久久不能释怀。这些生存的艰难最终都被爱和信仰融化超越。
布尔津给了张好好向历史文化深处溯源的可能性。《布尔津光谱》中就有向布尔津历史深处探寻的清晰意向,最典型的是小说第10节,海生带着一家人,包括爽冬和大灰猫一起去六道湾探望淘金的小凤仙,那里的戚老汉喜欢讲古,“你听戚老汉在这夜色的额尔齐斯河边说着怎样一个玄妙的地方:用直线最短的理论,成吉思汗他们在古老羊皮的地图上把目光和手指一并地按压在了友谊峰上。翻过这座大山,一直地向西挺进,便是欧亚大陆相接之地。横扫欧洲大地,直指美洲,最后把世界用他的铁蹄踏遍。这样的野心如天空中突然出现的九个太阳,它们的熠熠之光可以把无数有水和葱绿树木的星球燃烧为死寂的黑洞。安营扎寨,在布尔津以北的喀纳斯湖畔。”
到《禾木》时,历史空间的探寻更加清晰深入。第34节“大汗”与第37节“孛儿只斤”是《禾木》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将布尔津的历史投向更古老的年代。“孛儿只斤。蒙古人黄金部落的姓氏,成吉思汗祖上的姓氏,最高贵的血统,神的儿子。山上的图瓦人说,喀纳斯的意思是‘大汗的水’;布尔津的意思是‘孛儿只斤部族的草原’。成吉思汗路过这里,大风刮着他,两条滔滔大河滚滚向西,森林遮天蔽野,草原因丰沛河水可以被保证世世代代丰美。于是他把自己的姓氏给了这里。”作者把叙述视角由历史拉回当下时,让二者获得了奇妙的关联:“那个善良的女人是图瓦人,是成吉思汗将士的后代”,“因为这个女人,你得以靠近一千年前的事情。”对这段历史的回溯让作者书写当代生活时忍不住如此想象:“推着勒勒车的你们,那策马翻飞的成吉思汗的部队,是不是很像?”
现代文明进程中,布尔津各个民族的生活开始改变,游牧民族也开始经商。张好好在表达对现代文明进程中游牧民族文明变化与消逝的担忧,但同时又清晰地感受到他们难以改变的信仰,她发现了他们的矛盾,也将这一矛盾通过细致的笔触呈现出来。旅游的人纷纷闯进布尔津,闯进喀纳斯和禾木图瓦人的家中,他们买走图瓦人的石头和手工艺品,但是他们和图瓦人没有什么话可说。图瓦人沉默,买卖结束后,图瓦人就回到了纯洁的信仰中。他们怕欲望的魔鬼拉扯他们坠入深渊,所以他们用安静抵抗、保守、维持最后的尊严。《禾木》第70节“味道”只引了图瓦族的五句古歌:
她家搬去了哪里?
那里可有青草?可有苦艾?
我心上人去的地方,离我多远,离我多近?
没有黑马,我的马鞍如何不断解冻?
如果没有我心上人,如何将我暗淡的心永远温暖?
这与张承志《黑骏马》蒙古族古歌《钢嘎·哈拉》多么相似!还是,它们原本就是同一首歌?图瓦古歌的调子和悲剧都已经此世难逢,它带给我们悲伤的刻骨感受,却不让我们的灵魂有彻底体验它的可能,因为其中的真正灵魂已被图瓦人隐蔽。张好好说:“遮蔽了。图瓦人的遮蔽是为了尊严。你们的遮蔽是因为你们掉入了‘享受’中。”她坚信:“如果你以遮蔽的心灵,走在‘一场生命’里,长生天就不给你‘爱’。”
哲学的生态的布尔津
张好好通过各种体式的作品进行哲学思考。有对人与恒河沙粒之命运的关联性思考:“搬入阳台搬入大街搬入熙攘中轻易走散的时局里,/我们牵住自己的手端坐于庄重的沙粒的命运”(《庄重的砂粒的命运》),有对人与时间空间的思索:“多年以后,哎!又是多年以后/众树长出天成的翅膀它们飞翔/你清洁的目光亲密挨着——我和夜”(《我们的夜》)。也有写给造物主的诗,比如《以者》:“他创造这一切——/他说,要有光,要有空气,要天地分开,要各从其类/于是相爱的人逢着,并不以为是奇迹/相同的人牵手,循着阳光他看得清楚”。这种哲学思考在小说中则通过多种方式呈现出来。最典型的是《布尔津光谱》中的大灰猫与爽冬的对话。
大灰猫是布尔津真正的哲学家,面对人性,它如此发表自己的感慨:“人哪,是最说不清楚的东西,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到底想要什么。”“这里的人……或者全世界的人,他们一心想要得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它不明白人类的欲望为什么那么多,它眼里的人类满脸忧愁,一旦看见了可以得到什么的希望,就雀跃欢欣。爽冬虽然未正式降生为人,却也在思考命运。他问大灰猫:命运是能阻拦的吗?不能。大灰猫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没有命运袭来,你怎能明白活着的滋味?当爽冬要开始他的新生命时,他说:没有命运的始终,如何知道活着的意义呢?当海生的三个女儿收养了一条小小的流浪狗时,海生表现出少有的冷漠,他不允许孩子们的善行,但是哈萨克人阿娜尔家却收养了它。大灰猫认为,他们人类就是这样,时而冷酷,时而善良。后来,海生把大灰猫装在提包里扔掉,但大灰猫奇迹般地回家了。大灰猫表现出超常的哲学气质,小说有这样一段:“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大灰猫说,《红楼梦》里这句话最讨人喜欢,贾宝玉披着红斗篷在大雪地里越走越淡,我就觉得那片雪地正是额尔齐斯河旁冬天的大戈壁。”这显然已经不只是猫的思考,而是作者的哲学观了。
张好好在她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强调自己对猫的喜爱,她收养过许多流浪猫。这一经历化为她小说中的人物经历。她作品中多有爱猫收养流浪猫的人物出现。她自称,《布尔津光谱》中的大灰猫完全真实地存在过。猫是我的生命长河里不离不弃陪伴我左右的小动物。从小就养猫爱猫。养护小动物有利于人类心性的正气的培养。可是有多少人类懂得这个道理呢……早夭的小男孩的灵魂因为有大灰猫成为好朋友,是一件多么值得慰藉的事情啊。光谱里的温暖,来自可爱的小生灵。光谱里的人物的温暖,来自他们清灵没有贪婪的欲望。
生与死也是张好好布尔津世界的一个哲学命题。布尔津有美丽的河流,但河水每年都要带走几个人。张好好作品中许多人的生命都被河水带走,这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多有相似,沈从文写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自称“檐溜,小小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莫不对于我有过极大的帮助,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5]。张好好写过许多有关布尔津河流的诗,其中最经典的是《四条河流》:“神的预言书上说/你们将携手共渡四条河流/最后抵达纯蓝墨水翻卷的太平洋……”布尔津的禾木河、喀纳斯河、布尔津河、额尔齐斯河,以及这些河流最终汇入的北冰洋都是张好好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意象,当死亡遭遇河流,它就成为另一种存在。
还有原乡与异乡。布尔津人往往是在原乡无法生存后来到这里的,这里是他们的异乡,所以他们在这里表现出强烈的回乡冲动。小凤仙的弟弟玉成千里迢迢到布尔津后却不习惯这里的一切,要回四川家乡去。更多的布尔津人想回却永远回不去了。海生的母亲去世后,小凤仙说,老家没人了,你们的爸爸再也回不去了。她知道自己和四川的关系也是邈远到隔绝的。老曲回到家乡后却不得意,给海生来信说布尔津的生活让他留恋。年轻一代更想离开布尔津,他们渴望外面的世界,钱小苹和三姐妹等都是如此。《布尔津光谱》中的爽冬最后也离开了,大灰猫问他要去哪里,他说,去你从前给我说过的晨雾和炊烟如牛奶的禾木。而海生也从喀纳斯骑马往禾木去,他来到禾木,看见一个胖胖的小婴孩坐在金莲花的花海里抬头冲他笑,就仿佛多年前他那早早就分离的儿子已投胎足月,正式来到世间。那么,《禾木》中父亲与图瓦女人生的弟弟巴图尔就是爽冬的另一世。
《布尔津光谱》的结束就是《禾木》的开始,它们都是张好好的布尔津的重要诗篇。不同之处在于,《禾木》表现出更加深厚的生态思想,之前的作品中,外面世界的因素已经开始进入布尔津,比如《蝴蝶花》中突然出现的飞机,《布尔津光谱》中开发廊的南方人,挖金子挖虫草破坏大山和河流的外地人。《禾木》中,布尔津的世界变得复杂而可怕,“风景被管理起来了,这奇妙的现代脚步,像个大脚巨兽,比黑熊更可怕,而且没有道理可讲的莽撞力量,撞击着山壁。”大自然就是蒙古族说的长生天,长生天保佑着草原上的众生。但外来者对大自然缺乏应有的尊重。人类猎杀野生黄羊,黄羊幼弱的目光未曾发出诅咒,但是恶的人泯灭了——那个恶的人死于擦拭手枪时走火。又一条河流在死亡,死亡的标志是河流里的野生游鱼无法正常繁殖生息,突然就成为空白。在这个意义上,额尔齐斯河已经死亡。所以,“你只常常厌倦人类。面对人类,有轻微的恶心,你这样形容。”
张好好在诗歌中同样表现出强烈的生态思想。“我不对生活撒谎,也不靠近他者制造的谎言……人类黑色的五指,剖肠刮肚/呻吟的长江在我的目力所及之处是一尾垂死的鱼/我不会因为人类予以我的巨大恩惠而放人类一马/光先于我的目光抵达事物的真相,它引领我,安静不说话/蹲踞如一尊猫。它永远在提醒我,绝不……那些谎言!”(《我不……》)“这世间的苦难非要人亲自制造/跋涉或观看。地气已破坏殆尽/当大坑被称为天坑/当天命疏离,一个一个的人/传奇里的湖光山色,英雄佳人/那样永长的天命,地气,人事/的唱合,为我们所沉醉的/它们就要消逝……在人类的余音里/在我偶然来到世间,又必会离开的/我们携手的时光里/对上古时代澄澈的天地之眼/表达谢意。还好/我们竟然做了送行人”(《对上古时代天地的澄澈之眼表达谢意》)。《禾木》第4节“中原”一开始就写中原大地某个地方在一个清晨发生了“地陷”,也就是天坑。天坑其实是人为的灾难。中原的今天让张好好无比担忧布尔津的明天。小说中一个明星穿着貂皮,媒体在赞美她的贵气,“你”极为愤怒:你想把她和新闻制造者一起灭了,她的贵气倡导人类加大步伐戕害生灵。“你”的愤怒就是张好好的愤怒,这是对生灵的爱与尊重,这与彼得·辛格与汤姆·雷根有关动物解放与权利的生态伦理思想完全一致,布尔津的生态主题由此彰显。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应该在两个层次上建构:第一层次,组织小说故事;第二层次,也就是上面的一个层次,发展各个主题。一个主题就是对存在的一种探询。这样一种探询实际上是对一些特别的词、一些主题词进行审视[6]。张好好的布尔津就是在故事之上发展她的主题,这些主题又是建立在一些根本性的词语上的:诗性与温暖,民族与历史,哲学与生态,这些词语在布尔津世界里被研究,被定义,再定义,并由此转化为存在的范畴。行笔至此,想起了张好好的一首诗,《春天里我们提着剑下山》:“天下万物/各归其主/春天里我们提着剑下山/花朵静立清寒中/在它们飘飘摇摇之时/世界是折叠的仙鹤……行走江湖/随身之物留不多矣/不过是一盏昆仑玉,两寸相思/你的唱腔是绕指柔,要看那第一朵花的模样/我的笔法是杀无赦,抱剑在怀中金鸡独立”。
提剑下山者自有行走天下之法,未必总以绝招致胜,但有一世界在心。布尔津大地赐予张好好灵感与勇气,所以张好好有写。
【注释】
[1] 废名:《废名小说选·序》,见冯健男编:《冯文炳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94页。
[2] 沈从文:《沈从文谈艺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2页。
[3] 汪曾祺,施叔青:《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上海文学》,1988年第4期。
[4] 张承志:《骑上激流之声》,见《绿风土》,作家出版社,1989年,第78页。
[5] 沈从文:《沈从文谈艺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7页。
[6] [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