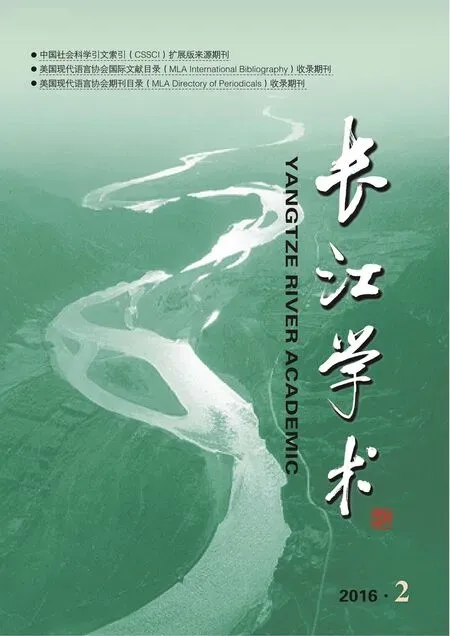沈从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国家意识与国家想象
严靖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沈从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国家意识与国家想象
严靖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1940年代的沈从文,通过小说《长河》和数量众多的政论文章,表达了自己独特而丰富的国家意识和国家想象。《长河》中诸多现代媒体和词汇作为外来事物涌入湘西,将湘西世界和中国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从而完成对新型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在此基础上,沈从文从文学者的立场,提出了自己的建国设想,一是以“抽象的观念”反对充满武力和短视的社会现实,二是以爱和美培养新的国民。这一想象显示了沈从文对文学功用观的新的认识,也体现了沈从文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的思考。沈从文的国家想象随着时局变化而最终破灭。
沈从文国家意识国家想象 《长河》
对于沈从文而言,1940年代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它不仅是文学者沈从文的最后一个写作阶段,也是知识分子沈从文最热心于社会和政治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沈从文,以文学作品和更多的非文学写作,表现出自己国家意识的转变,以及参与中国未来的建设想象的积极性。这些写作体现了沈从文对前期创作的某种超越,显示出其文学世界的丰富;同时也预示了他在1949年后与新型文化体制格格不入的命运。
一、“‘现代’二字已到湘西”:政治/中国意识对审美/地域意识的超越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几度返乡,亲眼目睹了湘西的种种巨变。他也一反过去的浪漫化写作,以纪实性手法呈现湘西这一历史景象。
这一变化在1934年的《湘西散记·序》中就已经为沈从文所预见。他不无担忧地写道:“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预感他们的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的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一种来自外部的巨大势能所摧毁。”①沈从文:《湘西散记·序》,《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0页。此时沈从文见到的湘西,不再是那种田园牧歌的世外桃源,而是一个在现代文明和现实政治双重冲击下的蛮荒而混乱之地。
这种“外部的巨大势能”很快就接踵而至:1935年,国民党军队势力抵达湘西;次年,湘西结束了多年的自治状态,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部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抗战期间,湖南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战场之一。敏感的沈从文将这一切融入了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长河》之中。《长河》诞生于抗战全面爆发后的1938年,最终出版却是1945年的事了②被迫南迁的沈从文在其兄沈岳林(云麓)家中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初稿,而后匆匆南下昆明。同年8月7日至11月19日在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副刊连载,未完。1942年,沈从文开始修改《长河》,预计篇幅是三十万字,最后得第一卷近十四万字。经过国民党当局的层层审查删改,最终于1945年出版时只得十一万字。遗憾的是,沈从文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完成原初的写作计划。。
《长河》的主题犹如它自身的命运一样充满遗憾和惋惜。虽然这部长篇制作在细处依然随处可见沈从文对湘西世界景致和人情的美好描写,但它更重要的意义却在于展现了时代哀愁和历史命运的并行。
《长河·题记》是沈从文作品序言中罕见的长篇幅。内云:
表面上看,事事物物自然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①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虽然这只是湘西一隅的事情,说不定它正和西南好些地方情形差不多。虽然这些现象的存在,对外战争一来都淹没了,可是和这类似的问题,也许会在别一处地方发生。②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金介甫认为《长河》是“沈从文写田园诗喜剧的最优秀作品……也是沈从文长篇中最富于历史意义的一种,是对湘西往昔生活方式的一曲挽歌”③〔美〕金介甫:《沈从文传》,符家钦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52—253页。。沈从文的写作在写湘西沉痛的变故时,加入了不少诙谐幽默,反而使得现实更显悲凉。金介甫所说的“历史意义”准确地指出了《长河》区别于沈从文其他作品的特别之处。以《长河》为标志的沈从文创作表明,到了四十年代,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崭新的沈从文,一个现代想象和国家想象的建构者,而并非人们习以为常认为的地域文化的迷恋者。面对现代性和民族国家问题,沈从文超越了其早期的那种纯粹的抵抗或嘲讽,而采取更为主动、更为成熟的姿态,更倾向于发展建设而非批判否定。
研究者发现,《长河》中,“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是频繁出现了报刊的字样,既有如《创造》、《解放》、《申报》、《中央日报》、天津《大公报》等一些现代报刊史上重要的报刊,也涉及到省报、沅陵县报等地方性报纸。……复现次数最多的是《申报》的字样,一共出现了十六次。④吴晓东:《〈长河〉中的传媒符码——沈从文的国家想象和现代想象》,《视界》2003年第12辑。”这些现代大众传媒符码在三四十年代湘西地区的公共舆论空间建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与之相对,湘西世界还有另外一个公共舆论空间,而且是占据更主导地位的空间,就是湘西大众口耳相递的传闻和道听途说的消息。它们构成了老中国更具普遍性的乡土口头传闻空间。两种舆论空间的互补和对立,是“现代”侵入湘西的必然体现。
老水手是“口头传闻舆论空间”中的代表。老水手对消息的汇集与传播具有典型模式。他穿梭于商会会长、橘子园主人与湘西普通民众之间,负责了大部分的“新闻”和“消息”的传递。而官道与河流,成为他传播资讯的最重要的渠道。“长河”沅水在这一时期的沈从文笔下不再是抒情的对象和叙事的环境,而是具有工具功能的交通和资讯的渠道。《申报》《大公报》一类的现代传媒,经由水与水手带到湘西,建构起一种新型的话语和舆论空间。这种话语建立在文字基础上而非口头流传上。它是静默的,但又具有别样的权威性和真实感。它的最大优势在于不以人的传播而变异。
通过报纸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湘西民众开启了空前的对外部世界的好奇,这个世界很快就落实为“中国”。在对外部世界进行想象和形塑的同时,这一地域性的群体也完成了由湘西人向中国人的转变。
另一个重要的渠道是官方的物质和精神双方面的建设对湘西的侵入。
物质层面,湘西地区的经济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抗战之后越来越得到重视。公路的不断延伸,加速了物产和信息的流通,也极大促进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的改观。
精神方面,主要体现在《长河》中的另一关键词——“新生活运动”。围绕“新生活运动”,乡土口头新闻与现代报纸新闻,展开了激烈的冲突和交锋。对现代中国的想象也都由此得以呈现。
由蒋介石亲自倡导、发起于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本来是蒋政权最重要的精神文明建设运动。它通过各种政治手段侵入了本来是自古山高皇帝远的湘西。作为新名词,给不明就里的湘西世界带来了空前的恐慌。它在小说中一共出现了五十次之多。
“新生活”一词在不同人群口中的频繁出现,固然显示了沈从文一贯的对“现代”话语的嘲讽和拒斥,但是它更显示了“外面的世界”的影响已经真正进入湘西,并对民众的生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
因此,形成悖论的是,当沈从文越是用其一贯的立场和语气来表示自己对现代事物的漠视和拒斥的时候,这一现象的真实存在就越得以彰显。作为一个真诚且对家乡有深厚感情的作家,沈从文的的确确开始重视政治意识和国家意识了。在一个大转折时代,乡土舆论空间对国家大事的态度如何,民间话语以怎样的方式对待官方话语,这是沈从文写作《长河》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事实上,并非所有人都持保守的态度或表现得慌乱不满。国民对于“国家”的情感还是不少见的:
长顺是个老《申报》读者,目击身经近二十年的变,虽不大相信官,可相信国家。对于官,永远怀着嫌恶敬畏之忱,对于国家,不免有了一点儿“信仰”。……他有种单纯而诚实的信念,相信国家“有了老总”,究竟好多了。国运和家运一样,一切事得慢慢来,慢慢的会好转的。①沈从文:《长河》,《沈从文全集》第1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
会长说:“亲家,树大就经得起攀摇。中国在进步,《申报》上说得好,国家慢慢的有了中心,什么事都容易办。要改良,会慢慢改良的!”②沈从文:《长河》,《沈从文全集》第1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长顺的想法在湘西民众中恐怕是有代表性的,中国的相当一部分老百姓也是这样,“不大相信官,可相信国家”。长顺、会长代表的湘西士绅和老水手这样的民众,都有这样一种相信“国家”的意识。通过对外来资讯的接受,他们自然地将自己和湘西想象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的确,《长河》中也存在沈从文一贯的站在“乡下人”的立场进行对“城里人”以及都市生活的嘲讽性想象:
女子中也有读书人,……还乡时便同时带来给乡下人无数新奇的传说,崭新的神话,比水手带来的完全不同。城里大学堂教书的,一个时刻拿的薪水,抵得过家中长工一年收入!花两块钱买一个小纸条,走进一个黑暗暗大厅子里去,冬暖夏凉。坐下来不多一会儿,就可看台上的影子戏,真刀真枪打仗杀人,一死几百几千,死去的都可活回来,坐在柜台边用小麦管子吃橘子水和牛奶!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全苏州到处都是水,人家全泡在水里。杭州有个西湖,大水塘子种荷花养鱼,四面山上全是庙宇,和尚尼姑都穿绸缎袍子,每早上敲木鱼铙钹,沿湖唱歌。③沈从文:《长河》,《沈从文全集》第1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0页。
……顶可笑的还是城里人把橘子当补药,价钱贵得和燕窝高丽参差不多,还是从外洋用船运回来的。橘子上印有洋字,用纸包了,纸上也有字,说明补什么,应当怎么吃。若买回来依照方法挤水吃,就补人;不依照方法,不算数。说来竟千真万确,自然更使得出橘子地方的人不觉好笑。④沈从文:《长河》,《沈从文全集》第1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然而,认真比较的话,这一口吻比起早期的沈从文小说或杂文,其嘲讽或者与“现代”“城里人”的对立对抗意识已经轻浅了许多。
与二三十年代的沈从文思想一致的是,“现代”在沈从文那里依然算不上一个好词。《长河》题记中表达了对“现代”冲击下的湘西的忧虑:“‘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⑤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现代”必须在中国语境中尤其是乡土语境中被检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上述话语也能说明沈从文开始正视“现代”了。在具体层面,沈从文还反思湘西文化的愚昧野蛮麻木,鼓励湘西人自信面对现代社会。抗战爆发后回到家乡的沈从文,特意召集并宴请当地的军政长官,力劝他们停止内斗,握手言和,群策群力地为抗战服务,为“国家”服务。
就这样,沈从文以《长河》为思考的起点,逐渐完成了政治/中国意识对审美/地域意识的超越。
我们不妨就此接着提出疑问,沈从文四十年代后期以后的精神状态,如焦虑孤独等,是否与其理想湘西世界的形象的崩溃有关,而不仅仅源自左翼力量的压迫?以往的研究者习惯的从政治力量直接干涉文学这一角度进行的解释是否过于单一?再者,其三十年代后期以来的小说,逐渐地不再完全倚仗湘西作为题材,艺术手法也慢慢转向了意识流等新的尝试和试验,是否也与此有关呢?
二、“依然是那个无量无形的观念”:以抽象观念建构新的国家
沈从文具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普遍存在的“感时忧国”情怀。这一点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前被极大地掩盖了。
写于1947年的《从现实出发》是沈从文心路历程的一个缩影。他坦承,自己年轻时到北京求学,为自己“寻找理想”,理想便是“读好书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①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页。。这一出发点与鲁迅“立人”为救国是相似的:“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②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页。该文表面上写自己,但无处不写“现实”,亲眼目睹亲身体验的现实中国。在三十年代的小说《若墨医生》中,沈从文就借若墨医生之口,宣称要“写一本《黄人之出路》”。感时忧国还体现在他直接对暴政表达不满的系列散文与小说中。如《丁玲女士被捕》《湘行散记·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新与旧》等。
如果说二三十年代的沈从文对政治的表达主要是侧面的间接的,对“政治”(当然也包括商业)持整体的排斥态度的话,那么四十年代的沈从文则主动将政治纳入自己的思考范畴,开始追寻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的道路。
他的立场首先是否定暴力、战争、武力。他说:“我看了三十五年内战,让我更坚信这个国家的得救,不能从这个战争方式得来。人民实在太累了,要的是休息,慢慢才能恢复元气。”③沈从文:《政治与文学》,《沈从文全集》第1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7页。他总结了20世纪前半夜中国的政治,表明自己对“政治高于一切”的中国现代历史的绝望。在他看来,国家遭遇的苦难与当局密不可分,一国的苦难并非某一单独原因造成,但近代中国的政治环境应该为国家悲剧担负主要责任:“国家所遭遇的困难虽有多端,而追求现实、迷信现实、依赖现实所作的政治空气和倾向,却应该负较多责任。当前国家不详的局势,亦即由此而形成,而延长,而扩大。”④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2页。
沈从文在四十年代写的政论文数量远多于文学作品,但是他所能提出的方案并非成体系的思考。不过他提出了“抽象的观念”这一独特的理念。
功利的“政治”“现实”是不可取的,只有“抽象的观念”才能改变国家,这是沈从文整个四十年代念兹在兹的:“凝固现实,分解现实,否定现实,并可以重造现实,唯一希望将依然是那个无量无形的观念!”⑤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2页。显然,他是偏向于从精神观念的角度解决国家混乱现实的:“不单纯诉诸武力与武器,另外尚可发明一种工具,至少与武力武器有平行功效的工具。这工具是抽象的观念,非具体的枪炮。”⑥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所谓“抽象”,与具象,也就是“现实”相对。这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是一种超越的思维。
沈从文对具体的政治体制谈得很少,这可能与他主动保持与国共两党的距离有关。但他对具体的西方政治文明基本是肯定的,虽然直接提及的并不多。比如他在《中国人的病》一文中有关这种态度:
合于“人权”的自私心扩张,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它实在是一切现代文明的种子。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能自由思索,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然比一个国家多数国民皆“蠢如鹿豕,愚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王恩赏神佛保佑过日子有用多了。①沈从文:《中国人的病》,《沈从文全集》第1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俗话说:“要得好须学好”。在工业技术方面,我们皆明白学祖宗不如学邻舍,其实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技术?……我们应明白一个“人”的权利,向社会争取这种权利,且拥护那些有勇气努力争取正当权利的国民行为。应明白一个“人”的义务是什么,对做人的义务发生热烈的兴味,勇于去担当义务。②沈从文:《中国人的病》,《沈从文全集》第1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因此,他绝不是站在田园牧歌的角度全盘否定现代文明的。
在三十年代京派海派对峙的时候,沈从文即发出过这种对暴力革命的强烈不认同:“你即或相信法国革命流血,那种热闹的历史场面还会搬到中国来重演一次,也一定同时还明白排演这历史以前的酝酿,排演之时的环境了。使中国进步,使人类进步,必需这样排演吗?能够这样排演吗?阳燧取火自然是一件事实,然而人类到今日,取火的简便方法多得很了。人类文明从另外一个方式就得不到吗?人类光明不是从理性更容易得到吗?”③沈从文:《给某作家》,《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页。此信是写给巴金的。沈从文毫不客气地批评巴金把冲动和否定当做青春朝气的思想。他明确否定激进的、代价太大的法国大革命在中国再现的必要,认为这种暴力革命不值得模仿,反而应该吸取其中的教训。四十年代的沈从文延续这一立场,认为不流血或少流血的理性道路才是中国人应该学习和探寻的道路。
沈从文与现实政治之隔膜可见一斑。他眼中,政治的本质是“只代表‘权力’,与知识结合即成为‘政术’”,所以他“在心理上历来便取个否定态度。只认为是一个压迫异己膨胀自我的法定名词”④沈从文:《政治无处不在》,《沈从文全集》第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这份带有“悔过”性质的检讨书写作时间已经是1949年12月25日。通过《政治无处不在》,沈从文才第一次“悟到”政治在现实生活的地位以及对历史的改变力量。而这恰恰说明沈从文文学生涯中一以贯之的反感现实政治的态度。
三、“实需要一种美和爱的新宗教”:想象新国民与对蔡元培传统的继承
民族国家的主体是国民。作为一位文学家,沈从文更能理解“人”之于国家、社会、世界的意义:“察明人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⑤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研究者认为:“从现代文化建构的历史线索来探视,沈从文作品中有关‘人的重造’、‘民族精神的重造’课题是鲁迅改造‘国民性’的艰苦宏大工程在走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延续,是现代文化构建过程中的必经途径。”⑥赵学勇:《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沈从文的思考和言行证明此言非虚。早在1935年,他就极其看重“新国民”之于“新国家”的意义:“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应当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各方面共同努力,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⑦沈从文:《中国人的病》,《沈从文全集》第1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云南看云集》中的《新废邮存底》,收集了沈从文答复各界人士的信,对象有“一个广东朋友”“一个大学生”“一个青年作家”“一个诗人”“一个中学教员”“一个军人”等。涵盖了不同阶层和职业的“国民”构成。尽管内容不尽相同,但相同的是沈从文总会在信中提及时局。在关注国家民族前途的基础上,去积极鼓励对方尽自己的努力去救国家。这些工农商学兵都能激起沈从文真诚而热切的期待,在他眼中他们都能够为新的国家贡献力量。
沈从文对理想国民的认识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他批判国民性对“现实”的功利追求。沈从文认为,当时国民普遍存在的过于世俗、功利、短视,是极为严重的问题:“多数优秀头脑都有成为人格上近视眼的可能,为抽象法币与具体法币弄得昏头昏脑,在一种找个人出路实际主义下混生活。”①沈从文:《给一个广东朋友》,《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页。沈从文坚信,因为世俗、现实、短视,所以会才会出现追求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时局。同时,热衷于眼前利益的人,也无法取得高尚勇敢的人格,无法过上庄严道德的生活。
其次,他认为国民普遍缺乏血性,应当从湘西文明中汲取精神养料。这一思想在《箱子岩》一文中表现得最为充分。文中叙述了湘西民众的赛龙舟的往事,通过对这一往事的追忆,歌颂了充满血性的龙舟精神。沈从文认为中华文化是老态龙钟而失去生机的,需要输入野蛮人的血液,以实现新生和复兴。这种近似于艾略特《荒原》的思想,实际上是沈从文二三十年代文明观的延续。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沈从文极为重视文学在构建家国理想中的根本性作用。沈从文对文学之改造人与社会的作用,具有很强的历史使命感:
我是个弄文学的人,照例得随同历史发展,学习认识这个社会有形制度和无形观念的变迁。三十年来虽明白社会重造和人的重造,文学永不至于失去其应有作用。爱与同情的抽象观念,尤其容易和身心健康品质优良的年青生命相结合,形成社会进步的基础。……文学或其他艺术,尤其是最容易与年青生命结合的音乐,此一时或彼一时,将依然能激发一些人做人的勇气和信心……②沈从文:《定和是个音乐迷》,《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
制度有形而观念无形,文艺的作用就是用爱与同情,去改造社会成员的身心,从而改造社会,完成对有形制度的潜移默化的改变。在此,沈从文呼应并延续了鲁迅一代五四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改造工程。只不过,沈从文是立足文学,坚持艺术本位,同时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与鲁迅介入政治的鲜明姿态不同,沈从文的方式更接近于指导和提供,更多的是从精神层面进入。
在沈从文看来,文学对国民精神的重塑而言,首先也是最直接的,是能提供“爱”与“美”的美好情感。《阿丽思中国游记·后序》他就说:“我除了存心走我一条从幻想中达到人与美与爱的接触的路,能使我到这世界上有气力寂寞的活下来,真没有别的什么了。”③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后序》,《沈从文全集》第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沈从文不断重复这一点:“爱”和“美”能激发国民对国家、人类、生命的热情。四十年代的沈从文发扬了这一对“爱与美”的观念,使其上升到“宗教”的层次:“我们实需要一种美和爱的新的宗教,来煽起更年青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为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感情。”④沈从文:《美与爱》,《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62页。沈从文从爱与美的角度培育新国民的思想,与1917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伊始时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呼吁遥相呼应,构成文艺改变国民性的思想传统的重要一环。
这段话以感伤兼以悲愤的语气歌颂了爱与美的“应当”:
我倒不大明白真和不真在文学上的区别,也不能分辩它在情感上的区别。文学艺术只有美和不美,不能说真和不真,道德的成见,更无从羼杂其间。精卫衔石,杜鹃啼血,情真事不真,并不妨事。……
……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是罪恶,总不能令人愉快。我们活到这个现代社会中,已经被官僚,政客,银行老板和伪君子,理发匠和成衣师傅,种族的自大与无止的贪私,共同弄得到处够丑陋!可是人生应当还有个较理想的标准,至少容许在文学和艺术上创造那个标准。…………美丽总使人忧愁,可是还受用。①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107页。此文最初发表于1943年1月和2月的《文学创作》第1卷第4期和第5期。1947年,作者将其收入拟交开明书店印行的《王谢子弟》集,对文章重做校订。《全集》所收为1947年8月校订版,与原文有一些出入。初刊文为:“我不大明白真和不真在文学上的区别,也不能分辨它在人我情感上的区别。文学艺术只有美或恶劣,道德的成见与商业价值无从掺杂其间。精卫衔石杜鹃啼血,事即不真实,却无妨于后人对于这种高尚情操的向往。……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美就是善的一种形式,文化的向上也就是追求善或美一种象征。竞争生存固十分庄严,理解生存则触着生命本来的种种,可能更明白庄严的意义。……美丽总令人忧愁,然而还受用。”1947年的这一改动,庶几能看出沈从文对时局的悲愤甚于抗战时体验的感受。
为了保持、延续和发扬民族素质和品德中健康、自然、优美、高尚、充满人性的因子,经由重塑国民而重建国家,沈从文有且只有一种方式,就是文学。沈从文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思想纳入历史的序列,即文学在晚清以来的民族国家想象中的社会功用:“文学当成为一个工具,达到‘社会重造’‘国家重造’的理想,应当是件办得到的事。这种试验从晚清既已开始,梁任公与吴稚晖,严几道与林琴南,都曾经为这种理想努力过。”②沈从文:《“文艺政策”检讨》,《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275页。
在一个非理性的“现实”时代,抽象的、观念的、理性的、唯美的文学迅速败下阵来。不过这种失败是暂时的。沈从文早已看出这一点。在《给一个作家》中他不无自信地说:“这个民族遭遇困难挣扎方式的得失,和从痛苦经验中如何将民族品德逐渐提高,全是需要文学来记录说明的!”③沈从文:《给一个作家》,《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页。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国家想象虽然落空了,但他所看重的文学的记忆意义却有特殊而恒久的价值。
沈从文四十年代对理想中国和新国民的想象,体现了他由远离政治到切入政治这一较为显著的改变。
他曾这样概括湘西人民悠久的、似乎亘古不变的生存状态:“这些人生活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担负,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④沈从文:《箱子岩》,《沈从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页。他也曾通过小说《菜园》,歌颂“林下风度”,以田园对抗政治,显示美的追求的自成一局。前期沈从文基本上是以抒写田园牧歌来歌颂自然人性,同时表达对政治的反感与疏远的态度。红色的三十年代,京派海派之争,虽然也滋生了《大小阮》《新与旧》,体现了沈从文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但他总体的风格和姿态没有改变。
促使沈从文思想观念乃至文学生命发生根本变化的动因是抗战。上文已提到,1937—1949年间,沈从文的政论文文章远多于文学作品,小说的创作更是几度停滞。其原因与其说是沈从文创造力的下降⑤参见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131页。,毋宁说是沈从文对文学的另一种观照和理解。从《长河》可以看出,一个新面貌的沈从文开始了他文学生命的另一个高度。这使我们联想到1926年后的鲁迅。只不过,同样是在文学生涯的后期写下数量多于小说的杂文或政论文,鲁迅更具体深入地介入社会现实,以一个革命文学家的身份深化了五四文学的社会革命特质;沈从文的政论文则无一例外地坚持文学本位,坚持文学对现实的改造而非被改造。
沈从文的新国家想象,并没有具体细致的方案,但有两个前提被他一再强调,一是反对武力,而依靠文化、美育和理性;二是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沈从文的新国民想象,也包含两个主要意思:一、国民培养重于国家建设;二、以美育培养国民性,反对崇尚短视的武力之争和党派利益。
无论是新国家还是新国民的想象,沈从文的独特之处在于重视文学的意义与作用。这与当时很多作家主动或被动对“文学无用论”或“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接受是迥异的。另一方面的意义在于,沈从文由对抗战文学引发的美学危机的关注(“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转进到借助文学手段来重铸国民品格(之前是普遍的“人性”,此时具体为国民),实际上存在一个由强调文学的超越性到重视文学的功用性的转变。规模空前的民族战争和随后的内战,促使沈从文急切希冀以文学的方式来重造人性和国民性,进而实现建国理想。不过,其中不变的是他对文学恒久性的自信,是对短视的暴力(非理性的政治形态)的反抗。沈从文仍然坚信“有情”、“人性”是永恒的,“事功”与“现实”是短暂的。
沈从文在四十年代尤其是四十年代后期的文字,表现了他对文学的未来,也对故乡和国家的前途的担忧。他努力将审美理想与政治理想相结合,将艺术本位和国家本位相统一,为理想国家的建构贡献文学者的力量。然而,在处处充满“现实”的四十年代,沈从文的孤独挣扎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他所自我期许的自梁任公与吴稚晖、严几道与林琴南而来的文学改造国家的试验,在四十年代遭遇了空前的挫折。
Shen Congwen’s Consciousness and Imagination of Nation in 1940s
Yan Ji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In 1940s, Shen Congwen expressed his consciousness and imagination of nation through the novel The Long River and numbers of articles on politics. In The Long River, Xiangxi was connected to the outside via modern media and rushing new words and so Shen constructed a new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n this basis, as a litterateur, Shen expressed his opinions on founding a new country: opposing the reality full of violence and narrowness with‘abstract concept’, and train the people with love and beauty. It showed Shen’s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and also the new think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Finally, Shen's imagination of nation was broken because of the changes in political situation.
Shen Congwen; Consciousness of Nation; Imagination of Nation; The Long River
责任编辑:於可训
严靖(1981—),男,福建连城人,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新诗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文学转折中的作家精神史研究(1937—1949)”(项目编号:15FZW 06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