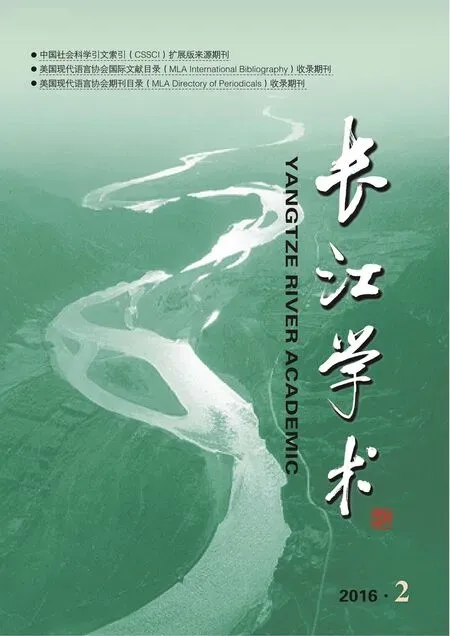文学研究中的断裂与连接
张荣翼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文学研究中的断裂与连接
张荣翼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文学研究中涉及到不同时代的各种不同的文学。在这一工作中就面临实际的文学现象之间的断裂和换一角度看显示出的部分连接。作为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文学研究中的断裂体现为三重,即语境的、文学活动之当事人的以及文化角度的;文学研究中的连接也体现为三方面,即现象中的、影响关系的和阐释角度之激活的。在文学研究中,通过三种重组即意义重组、秩序重组和价值关系重组,来对断裂与连接这对矛盾中的文学状况进行思考。断裂与连接实际上是文学研究所面对的文学的基本形貌。
文学研究断裂连接
文学研究是在学科规范的平台上进行的,否则就不能达成相互交流对话的效果,而作为学科在不同的具体研究之间达成沟通交流是学科得以存在、学术机构得以建立的基本条件。这样一种平台并不是要求所有的研究都持有同一话语,都表达同一意思,甚至也不要求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保持一致,但是也有一个基本的底线需要遵循,即要有一种学科的共同体的话语。关于共同体,科学哲学家库恩采用了“范式”(Paradigm)一词来说明,他解释道,通过范式,“是想说明科学实践中某些公认的事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事例——如某一特定的前后一贯的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所提供的模型。这就是一些历史学家以‘托密勒(或哥白尼)天文学’,‘亚里士多德(或牛顿)力学’,‘微粒(或波动)光学’等为例所描述的传统。”①〔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8页。这种传统的东西不是作为参与者共同认同的目标,而是要在这样的基点才有对话基础。“范式”的概念给出了一幅比较清晰的学科传承与学科变化的路线图。
这样来看,文学研究必须有传统的支撑;另一方面,文学作为一种充满了感性的表达,感性总是变动不拘的,而且随着各个学科的不断交融和碰撞,产生一些在边缘的新的学科和新的思想,它和过去的研究有明显的断裂感。连接和断裂的不同两端就在文学研究中并存,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必要在理论层次上清理文学研究的实际状况。这里,断裂与连接作为矛盾的两方面纠缠在一起,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文学研究中的三重断裂
文学研究的断裂是表明一个事实:文学研究所面对的文学和当初创作该文本时的状况已经不同,当文学研究来指称所面对的文学时,这种不同的文化语境状况可以使得同一文本显现出截然不同的意思,也有截然不同的语境中的价值。阿诺德·豪塞尔曾经说:“有一件事似乎是确实的,即不论是埃斯库罗斯还是塞万提斯,不论是莎士比亚还是乔托或拉斐尔,都不会同意我们对他们作品的解释。我们对过去文化成就所得到的一种理解,仅仅是把某种要点从它的起源中分裂出来,并放置在我们自己的世界观的范围内而得来的……”②〔法〕阿诺德·豪塞尔:《艺术史的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页。豪塞尔这种认识是文学研究领域中大家公认的事实。其实这里就有一个对话平台的问题,当批评家来评说它所选取的作品时,这一作品有一个作者,可是这一作品的意思却是由批评家来定调的。当后来的不同批评家来评说同一名著时,它们可能所说的并不是同一对象;或者反过来,当他们出现意见分歧时,也可能并没有真正意义的意见交锋,而是各自在阐述一套自己的意见。我们可以把这样境况称为学科中的“断裂”。
文学研究中的“断裂”可以有多种分类,也可能在不同的分类条件下有着不同的断裂状况。这里说的断裂应该是从研究者的角度所看到的状况,即研究者作为一个读者,他和作者意思之间的断裂,批评的语境和创作语境的断裂,以及当研究者看待作品所描写的社会时,他会以今天看待社会的眼光来打量作品的描写,这样就把前后不同时代的变化状况引入到了批评的视野,也造成一种断裂。
关于创作语境和批评语境的断裂,这是作者和批评家各自看待问题的角度差异所致。宋人尤袤《全唐诗话》记载,白居易在16岁时赶考,带了诗文谒见名士顾况,顾况看了名字“白居易”就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但当翻开诗卷,读到《赋得古原草送别》诗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句时,不禁连声赞赏说,“有才如此,居亦何难!”这里全诗共八句,为“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其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成为了唐诗中的名句。对此两句,《唐诗三百首》点评是比喻小人的无所不在,难以根绝。可是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就是从正面价值角度肯定小草顽强的生命力,中国有一部电影名为《野火春风斗古城》,其中的“野火”、“春风”就取喻于此,“野火”、“春风”作为对立的双方,那么孕育在民间的抗日力量就是“小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不可断绝。可是我们从原诗来看,一位16岁的少年诗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思想上的考虑,而就是对于草原景观的状物描绘;即使作者有所寄托也不可能把以上两种矛盾着的解释同时囊括,其中至少有一种释义脱离了作者创作的语境意义。
关于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断裂,在古今不同时代都有面对,而且也都可能有不同认识。孟子当年说知人论世,就是强调要尽可能地避免两者的断裂,他提出了以意逆志的批评主张,认为批评家要在作者的角度来体会作者的意思。在汉代儒学兴起之后,汉儒如果有什么新的想法都要在儒学的名义下才取得言说的合法性,于是假借对于先儒的阐释的名义来发表意见就成为几乎唯一的发表看法的途径,这里早先圣人和后来儒生的关系,就是一种师徒性质的关系,但是不同儒生可能对于早已作古了的老师的面目的描写并不一致。在西方从对《圣经》进行阐释基础上有了阐释学的思想,在文艺复兴的哲学认识论框架中,对于作为一种认识表达的阐释活动,发展出了哲学的阐释学。阐释学既是作为一种工具,探究阐释如何可能和如何进行,同时也是一种认识上的方法论。在方法论意义上,阐释就是意义的一种重建过程,重建意味着要承袭过去的一些东西,但也必然要新加入一些东西,完全的复制是不可能的。
这种断裂还可以从文化转型的角度来理解。新小说派的作家萨罗特曾说,“过去,读者和作者通过小说中的人物相互了解,并且从这个牢固的基础出发,一起共同致力于新的探索和发现。可是现在,由于他们对小说人物采取怀疑态度,彼此之间也不能取得信任,结果他们在这被破坏了的领域中相互对峙。”①〔法〕萨罗特:《怀疑的时代》,见《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页。所谓对峙就是作家的期待视野和读者的阅读感受呈现了不易协调的方面。相对说来,作家是比较敏感的,而且作家作为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对于文学的探索精神等方面比较积极,这样就造成往往是在读者面前,作家显得超前;而从作家看来,读者就是惰性比较强。双方的这种隔阂完全可能造成在文学接受领域的相互的不予理会,事实上在当代诗歌阅读中就已经发生了诗人和普通诗歌爱好者之间的龃龉。
关于文学阅读和创作语境的断裂,与在文学史上已经发生而且还会不断地发生。施莱尔马赫就认为:“我们必须想到,被写的东西常常是在不同于解释者生活时期和时代的另一时期和时代被写的;解释的首要任务不是按照现代思想去理解古代文本,而是要重新认识作者和他的听众之间的原始关系。”①洪汉鼎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55—56页。他所说的对于古代作品的认识,在文学批评领域的确往往是以今人的思想来理解古人,这样就造成同一作品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理解。《史记》有对一代豪杰项羽的生平描写,项羽人生的尾声是乌江自刎,司马迁站在同情项羽的立场把这一尾声写成了英雄绝唱,自此之后的文学表达就大体沿用了这一路径。唐代杜牧的咏史诗喜作翻案文章,他写的《题乌江亭》道,“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表达了项羽如果“包羞忍耻”也不失为大丈夫所为,而且在策略上也未必不能重振河山,在评价上有不同于《史记》的倾向。而且《史记》中写的《淮阴侯传》里面的韩信遭受“胯下之辱”,并不是在羞辱韩信的角度,而是在大丈夫能屈能伸的角度来写的,因此项羽所为实在不值得称道。再到后来宋代的李清照所写《夏日绝句》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则又回到了《史记》的立场。这里简单的是非不能派上用场,而是需要考虑各自的创作语境。
对于司马迁来说,他对项羽表达同情,其实也就是对作为项羽对手的刘邦的抨击,而司马迁在写作《史记》之前遭受汉武帝刘彻的宫刑,《史记》不只是他作为史官的本职工作,而且也是支撑他继续活下去的发愤之作。他不可能对刘彻直接表达不满,那么通过修史工作对刘彻的前辈发表微词也就是一种合理的也是可能的渠道。到了杜牧,他已经和各位当事人全然没有利害关系,他就可以从单纯事理的角度看问题。在韩信遭受“胯下之辱”也不失为大丈夫本色的情况下,项羽当时东渡乌江以待东山再起,或者就只是保全性命也是合理的。李清照写《夏日绝句》则是南宋屡遭金人劫掠,甚至有宋军听说金军将临就弃城而走。通过缅怀项羽功业,实际上是对当时出现抗敌勇将的一种呼吁!这里各自创作的语境是我们理解其作品的关键因素。各自的创作语境的断裂,使得我们在研究中必然有各自的具体分析。
二、文学研究中的连接
如果说在文学的实际过程中有着断裂的话,那么文学研究为了较好地贴近文学,除了也采用断裂的方式来分阶段地把握文学之外,还需要建立研究中的连接。
连接的具体状况可能呈现多样化,大体来说有以下三种典型的情景:在断裂现象中的连接,前后影响关系的连接,以及后代解释重新激活前代所造成的连接。
断裂中的连接是文学研究中的主要状况。《诗经》有些篇章如《硕鼠》,在传统的讲解中是孔子所说的诗歌的“兴观群怨”中的“怨”的表达,在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儒家礼仪中,它是达成社会和谐的一个步骤;而在当代的按照阶级斗争观念进行讲授的讲学中,这里的表达则是劳动人民对于作为统治者的剥削阶级的愤懑情绪的表达。应该说,在表达不满的意义上古今的不同表述有相通之处,但是儒家角度的“怨刺上政”和从阶级斗争观念出发来的反抗意识毕竟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今后的学者从宪政民主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的民意和行政部门的关系,那么则可以认为这首诗,是把社会的不满情绪通过诗歌的准仪式化手段加以表达,一来这样可以把破坏性的东西通过仪式方式相对地屏蔽,二来也是民意的宣泄渠道,三来行政部门其实是通过一种非常经济的手段获取了民众的真实想法,有助于在实际的政府管理中加以改进。在《硕鼠》诗歌的思想分析中都有民意的关注,但是各自参照的角度是可以完全不同的。由此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断裂的总框架下的有限连接。
前后影响关系的连接是另外一种状况。它涉及到前代影响后代和后代评价前代两方面的交互作用。前代影响后代是容易理解的,这在于在时间段看前代的作品和文学观念可能被后代接受,甚至就是不认同前代,在阅读的角度上也多少会有影响。反之,后代对前代的影响就有些不可理喻。在实质层面,后代当然不可能影响前代,不过后代拥有对于前代的阐释权力,前代的面貌是在后代阐释的基础上呈现的,所谓前代的影响力实际上也依靠对它的意义阐释才能够发挥效果。在后代关于前代的阐述中,事实的层面当然不能够编造,这是史学的最基本的原则,可是史实如何加以阐述,史实在历史叙述中如何作为叙述的元素发生作用,这的确是后代可能产生影响的方面。约翰·吉洛利对此提出,“文学的连续性对其伟大来说是实质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二流作家的作用就是保持这种连续性,提供一批子孙后代不一定阅读的作品,但所起的重要作用却是形成那些不断被阅读的作家之间的联系。”①〔美〕约翰·吉洛利:《意识形态与经典形式:新批评的经典》,见闫嘉主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在我们关于文学史的论述中,组织起一个由伟大作家领衔,然后由众多的比较优秀的作家参与,再有数不清的爱好者拥戴的文学作品的系列,这在历史线索中看来才有可理解的因素。其实这样的叙述是文学史的一种叙述,而文学史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写法。譬如作为一种后起的诗歌形式,“词”是“诗余”,基本上被定位为诗歌表达的余兴,即在“诗言志”的文化宗旨中,诗人的情感需要化身为一种社会化的情感才被看成是有价值的,所谓的“志”,其实是群体的、一般属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情感,这样个人的东西就被很大程度上被屏蔽。诗人的创作必须要有情感的参与,就是说他们的工作的一个方面就是诉说情感,可是在文化的总的格局中,个人情感没有多少发挥空间,因此他们是属于情感问题上受到压抑的。词的形式使得诗人有“诗余”的说法,这样才使得个人化的情感有了合法化的空间。那么作为词存在的“诗余”是怎样的“诗余”呢?词以各种词牌的形式出现,词牌使得它有明显的音乐亲缘,这样的话,词相当于唐代以后出现的新的乐府诗歌;另一方面,词又是有平仄等规定的,它的格律规范相对于较早出现的律诗、绝句来说大多是句式参差不齐,因此也被称为“长短句”,这样来看的话,词又是格律诗的后起之秀。把词看成是格律诗的后继者或乐府诗的后裔,这样两种看待本身都有道理,可是把它们作为诗歌发展的线索来理解时,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路径,对于诗歌的总体发展格局也就有不同理解,甚至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的性质等也会有不同看法。
至于后代解释重新激活前代所造成的连接,这本来是文学史常见的,却往往被忽略。这是因为,后代对于一切作品的解释,一般不是认为这种解释是对原先作品的新的深化或升华,而是认为代表了原作的精神,和原作一脉相承。这样来认识的话,各个不同时代的人和批评家,就都竞相争取这种代表权,如果新的研究观点和早先的认识产生了重大出入,那就可以说以前是把原作的真意遮蔽了或者曲解了,而现在的认识才是使得真意得到阐明。这种批评观有很大的副作用,一方面只是把自己立场的观点视为正宗,打压其他的不同意见,这从学术交流的角度看不利于思想交流和相互砥砺。另一方面,只是把文学研究看成对于文学的发现,这既是对研究成果的不够尊重,也不能起到鼓励研究领域创新的作用。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把不同的研究,不同的对于作品的读解,看成是在真理角度上的正误差异,这样就不能形成和文学史并列的一个文学研究史。对于实际的研究工作来说,也应该树立一个尊重以前时代人们思想的风气,这种风气的形成需要承认前人想法的合理性,在此情况下又得有自身的合理性,因此就不能在科学认识的真伪意义上来说明不同的见解,而需要在艺术的各师其心的角度来把握差异。当各种批评见解层出,新的见解遭遇到过去的作品时,使得早已完成了的创作可以散发出新的释义,这种新意奠基于旧有的作品架构,同时它又来自于新的时代的感触,这样的两方面的碰撞使得早先的作品可能焕发合乎后面时代的要求的东西,重新激活过去的作品。
也许历史过程就如福科所言是断裂的,不同历史时期之间有时不能通约。当我们看到中医药对于疾病和医治原理与西医不一致时,我们可能想到的是文化差异,其实我们所说的西医真实的境况是现代医学,它和中世纪欧洲的医学根本没有细菌病毒的知识时,对于疾病原因的解释归咎为邪气一类也是不能通约的。在所谓中医西医文化差异的背后,其实是科技观念冲击到传统之后的一个特例,几乎所有的传统观念都会因为不及现代科技的实用功能而被弃置,往往还会受到价值方面的贬黜。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同样依据阴阳学说作为理论根基的占星术(把天象看成人事的征兆)被斥为迷信,而传统医学则因为简便易行,而且现代医学的门槛不能随时普及到广大乡村等地区,于是被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内容而受到保护。这里占星术和医术之间本身并没有实质性的重大差异,而是在人们的看待中将其置入到了不同的框架中。
同样道理,文学研究中也可以造成后代阐释中才发生的连接。屈原当年因为楚王的不信任而失去官位,颠沛流离,最后殁于他乡。屈原的部分诗作中表达了对于自己遭际的不满情绪。我们从后来发生的历史事实看,屈原可能代表了对于楚国来说的正确的意见,可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是当政者的执政理念的差异,而在后代把屈原的作为解释为“爱国主义”,这种解读在中国近代以来积弱积贫的国家形势下,加上源自于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爱国主义的传入,于是就成为对于屈原的一种现代解读。在中国爆发了全面抗战之后,屈原形象迅速上升为国家的守卫者的符号意义,郭沫若在40年代撰写了五幕话剧《屈原》,就是这样一种现代解读的表达,在当时战时陪都重庆上演之后,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文学研究中的断裂和连接就相当于一枚硬币的两面,它总是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地纠缠在一起,在这样的过程中,文学研究其实就可以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它可以根据需要在断裂的与连接的某一面来加以言说,其中的断裂与连接的矛盾,为言说提供了话语的自由空间。因此也可以说,断裂与连接作为文学史的事实只是存在,而让它发挥意义的则是研究的意图,以及围绕该意图而采取的各种举措。
三、文学研究的重组功能
这样我们也就过渡到另外一个问题,即文学研究中面对文学事实的具体举措问题。这些举措因人因事可以有所不同,只能从大的类别方面来进行剖析。那么应该说在文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涉及到的是完全主观层面的,而我们的立足点则是考察文学事实的客观一面的状况,因此,真正需要考察的就是文学研究对于文学事实的重组问题了。这里重组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即意义的重组、秩序的重组和价值关系重组。
所谓意义重组,即同样的文学事实可能在不同的角度被解读,这种解读可能有批评者的主观提示,直接参与到对读者理解的引导,但是更主要的还是通过建构一种解读的方式、模式而体现出影响力。譬如我们阅读《史记》,其中有《淮阴侯列传》对韩信生平的描写,韩信少时的“胯下之辱”就极具震撼力。韩信为了励志而随身挎剑,可是被当地泼皮挑逗要进行决斗,否则的话就得胯下爬行;而韩信志存高远,不肯为了这样一个无聊的噱头而赌上性命,于是毅然接受了跨下的受辱。作者司马迁对于韩信的忍辱没有表示不屑,而是在大丈夫能屈能伸的角度对于人物行为进行描写。在《项羽本纪》中,被当成英雄人物来塑造的项羽,在人生最后的垓下之战一败涂地,在战败成为事实的情况下,项羽可以选择逃亡和自裁两种方案,而他在可能逃亡成功的条件下因为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选择了自裁的不归路。从司马迁遭受过最具有屈辱性的“宫刑”的经历来看,它有某种个人倾向完全可以理解,项羽和韩信都可以作为汉王朝开山之祖刘邦人格的一种对比。两种描写在作者司马迁那里是统一的,可是在后代没有个人恩怨的角度看来就不同了,所以唐代杜牧《题乌江亭》写“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对于项羽的自裁之举表达了异议,其实从韩信胯下之辱也不掩盖他大丈夫的本色的话,那么从受辱的角度看项羽也就应该逃逸,再图东山再起的机会。在杜牧这样一个阐释中,原先可能包含的汉王朝的兴起都是通过各种方式杀戮英雄才俊,甚至其中包含了一些下作手段的描写,转到了比较单纯地探讨历史兴亡的角度,对于在原先文本中的“壮举”表达了非议,这表面看来是对作者立意的商榷,实际上也是对事件所体现的意义进行了不同语境的重新组合。
秩序重组,则主要是涉及影响关系。在文学史历程中,同一时代不同作家、不同流派之间本身就可能发生碰撞,如果再加上历时意义的前后影响,则影响关系一方面是更为切实,另一方面则是显得错综复杂。秩序重组工作就是要梳理影响的线索,找到文学现象的源流。诸如中国传统小说历来有很强的“史”的因素,除了《史记》、《左传》等历史著作就包含了小说叙述因素之外,好些小说如《三国演义》等也是把历史叙述作为小说情节的基础。但是,历史叙述并不能概括全部小说的类型或者小说的全部因素,像《金瓶梅》、《荡寇志》是在小说《水浒传》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它作为先前小说的副文本,和写实的历史之间没有多少关联度。在这些梳理中,找到影响关系的蛛丝马迹可能并不困难,可是要得到实证性的分析和结论就绝非易事。
价值关系重组,其中关键在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需要对文学进行加重评判,这些评判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可能由早先的众说纷纭演变为大体一致。当然这一过程可能是各不相同的,李白在生前就享有了盛誉,而陶渊明则算生不逢时,在宋代才有了一流诗人的地位。在获得了佳作、巨著名分的作品中,也可能有把握程度的变化,《红楼梦》曾经被看成淫书,后来基本上把它理解为有更深寓意的作品,那么脱离淫书这样一种理解本身也就有价值认定上的变化。在价值关系方面,有时直接牵动的只是个别文本,但是所涉及的文本可能是某人所写,而这样的话就还会影响到相关的一系列其他文本。
意义重组、秩序重组和价值关系重组作为文学研究重组的集中表现,它们从几个不同层面体现了文学研究在认识文学时,可能就多少改变了文学的秩序和关系。这些方面在分析层次看可以分别论说,而在实际的文学关系中则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并且,这些方面还和更大范围的相关因素发生作用。笔者认为,在20世纪以来一个世纪的现代中国文论的建设过程中,经历了几个不同时期,“五四”时期强调启蒙,而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则强调救亡图存,延安时期开创的革命文论的传统则是强调党的思想作为革命思想的核心,对于整个文艺活动的指导作用,等等。如果只是着眼于这些不同时期自身状况,那么,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断裂的、缺乏连贯和系统发展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反之,从现代性的追求入手,我们就会看到不同时期实际上都是从不同侧面对现代性的追求的体认。所谓文学的断裂或者连接,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对象本身的性质所决定,而更重要的是在于从一种什么关系角度来看待和理解当时的文学。
这种矛盾的现象不只是文学史在后来的整理过程中会充分显露,而且就在文学史的当时都可能成为当事人的一种自觉。胡适在日记中记载,傅斯年对胡适说:“我们思想新信仰新,在思想方面完全西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然是传统的中国人。”①参见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5》,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04页。作为“五四”文学的主要发起人、参与者,他们自己就感受到了一种身份的矛盾。当他们要从事自觉的社会革命时,他们是义无反顾地要和旧的文学决裂,可是在他们进行具体的审美创造时,他们其实在骨子里面也是浸淫了他们所反对过的旧的文学的精神特质的。
在处理文学材料所面临的断裂时,文学研究往往可能采取一种“旁敲侧击”的方法。即每种不同角度的文学研究,可以有自己不同的文学审美坐标,它首先是要对所推崇的文学加以眷顾,进行细致的研讨,可是伟大的作品毕竟是凤毛麟角,于是在对伟大作品的研究叙述中就会形成一些空挡,在不同的伟大作品之间就有断裂。这时,把该研究视角看来并不突出,但是对于建构文学的连续性有意义的非杰作也纳入到研究范围就是一种学科建设中有价值的工作。因为,“文学的连续性对其伟大来说是实质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二流作家的作用就是保持这种连续性,提供一批子孙后代不一定阅读的作品,但所起的重要作用却是形成那些不断被阅读的作家之间的联系。”①〔美〕约翰·吉洛利:《意识形态与经典形式:新批评的经典》,见闫嘉主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举例来说,胡适早年所发表的《尝试集》,作为文学创作的审美意义其实很有限,它缺乏作为文学作品的关键性因素的审美情趣,可是《尝试集》是中国现代诗歌的开山之作。很大程度上这种新诗又是整个五四新文学的前驱,因此要研讨五四新文学创作的基本情况,就不能绕开胡适的《尝试集》,这里的“不能”,不是说它本身的审美重要性,而是它成为连接学科背景下的中国传统文学与借鉴西方的现代文学的一个桥梁,离开了这样一条线索,就难以把握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缘起和发展路径。
在文学研究对于文学事实的重组过程中,原先呈现为连续的过程可能就有了断裂的痕迹,而原先可能被认为是断裂的文学事件,可能换一个角度看,其实是连续过程的另外一种表现。这里关键的不是对象的事实存在,而是在观察时的问题架构如何搭建。
麦克卢汉曾预言:“总有一天,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将要发现,我们时代的广告是日常生活最丰富、最忠实的反映,它们对一切活动领域的反映超过了过去的一切时代。”②〔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9页。丹尼尔·贝尔则提出,“在当代社会,汽车、电影和无线电本是技术上的发明。而广告术、一次性丢弃商品和信用赊买才是社会学上的创新。”③〔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5—116页。麦克卢汉和丹尼尔·贝尔在此提到的问题,我们在康德和黑格尔的美学著作里不会找到一丝痕迹,事实上在此前不会把这些问题和美学思考联系起来,甚至在形式主义的文学观也是只就文学来说文学,也都不会涉及到广告等商品经济所研讨的领域,但是它却成为了当今对于文学、对于美学研究的“文化研究”题域的必修课。对于钟情于传统美学和文学研究的人来说,它显得有些另类,可是得承认,在今天的学术主流,“尽管文学理论可以从文化理论中区分出来,但它却不能脱离文化理论。”④〔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页。这里的“文化理论”或者“文化研究”,就需要考察包括广告在内的一些新的要素,这些要素在康德时代看来不仅不能作为理解文学的“要素”,而且它们是戕害艺术的体制化的元凶。因为在康德所理解的文艺活动的特殊性在于,人类已经越来越功利化,算计一个活动的利益的考量成为该活动是否得以实施的基本方面,而文艺的领域需要不计较物质的、经济的投入产出,它是一种爱好,甚至在一些艺术家差不多算是一种宗教层面的东西,因此,把在经济活动领域需用考量的方面纳入到艺术层面并不合适,在根本上讲,康德这种理解是有艺术活动的实际状况作为依据的。可是,在市场化条件下,包括文艺在内的人类活动,都可能被纳入到经济活动的范畴。且不说个体的作家有这样的行为,有些文艺活动譬如拍摄电影、电视剧,它需要众多人员参与,如果没有一种经济管理的链条则不能保证巨大投入之后能够回收一部分成本,而这里对成本的核算是生死攸关的,假如投入的巨资不能有足够回报,就不能有效地组织各项目的专业人员参与,从而也就不能达成创作目标。在这里康德的观点在他所处时代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涉及到了艺术的根本性的问题;而今天抛弃康德那种保守的见解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触及到文艺的现实!
结语
文学研究中处理的问题多种多样,它涉及到文学本身不同的方面,也涉及到采取不同的学科路径来接触文学,在这样一些不同情况存在着的状况下,以“文学研究”来作为整体的命名,就会造成作为整体的统一性和各自具有不同特性的差异性之间的冲突,表现出来也就是文学研究中存在着断裂与连接这样的矛盾的同时存在。这里断裂也好、连接也罢,都只是文学研究中所要面对的一些具体问题,而不能作为文学研究遭遇不能克服的困难的借口,也不能作为取得了某些成就之后炫耀的资本,它不过就是文学研究所要面对的问题,就相当于在农耕劳作中既可能有旱情,也可能会出现水涝,针对具体困难就要去积极克服。艾耶尔对哲学的一段总结在此看来很有回味价值,他说,“哲学的进步不在于任何古老问题的消失,也不在于那些有冲突的派别中一方或另一方的优势增长,而是在于提出各种问题的方式的变化,以及对解决问题的特点不断增长的一致性程度。”①〔法〕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对于文学的断裂和连接的各种问题,并没有孰高孰低的评价,而是在这种不同的境况下,我们看到的文学的不同侧面可能会给予我们不同的思考。应该认识到,文学是人所创造的,对文学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人的观照角度和方式。
Fracture and Connection in Literary Studies
Zhang Rongy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involves different kinds of literature in different times. Inevitably, it will be faced with the fracture of actual literature and the partial connection in some other aspects. As the two aspects of this contradiction, the fracture of literature research has three kinds: those of context, of the participants of literary activities, and of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connection of literature research is also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namely, those in phenomenon, those impact relationships and those activated by interpreting perspective. Literature study works on the literary status i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fracture and the connection through three kinds of reorganization, i.e., the reorganization of meaning, of order and of value relationship. In fact, fracture and connection are the basic appearance of literature in literary research.
Literature Study; Fracture; Connection
责任编辑:李建中
张荣翼(1956—)男,重庆市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