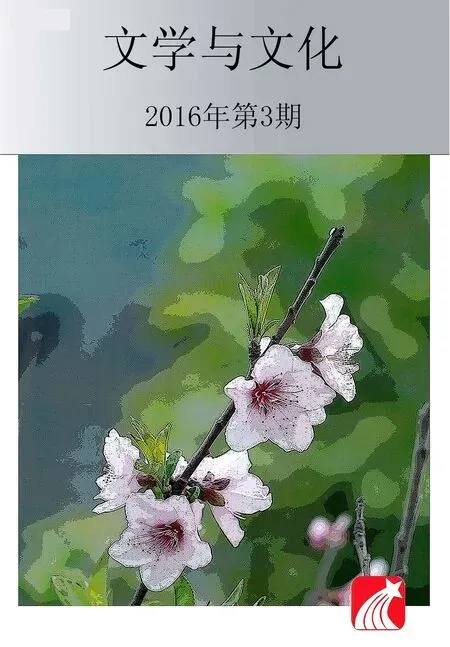当代诗中转喻接续性与意象产生的关系
简政珍
诗学与词学
当代诗中转喻接续性与意象产生的关系
简政珍
内容提要:雅克慎曾经在其著名的“语言双极”的论述中,谈到一般人在诗作的诗学探讨上,大都忽视转喻的功能。受到雅克慎如此的感叹与启发,本文拟以转喻的接续性探讨诗意象的产生。本文将探讨时间接续性中词语展延所产生的意象,意象叙述的环炼,空间接续性的意象,时间性与空间性交互活动的意象,随机接续性的意象,语意蔓延所延生的意象。雅克慎说:诗学运用上对于转喻的忽视,呼应了心理学接续失错的现象。本文算是对于雅氏如此感叹的一种尝试性响应。
雅克慎接续性意象环炼语意蔓延接续失错
主持人语:本栏目四篇文章均是围绕诗学关系问题展开的。简政珍的《当代诗中转喻接续性与意象产生的关系》,以对雅克慎关于诗学的语言两极被切割成单一模式观点的呼应,呈现出接续性转喻丰富的面相,宽阔的视野和专业的思维达成了良性互动;赵为娅、胡翠娥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意象主义在早期中国新诗中的理论旅行》,凸显从早期白话诗到格律诗派、现代诗派的流变过程中,美国意象主义在中国的渗透与变异现象,影响比较里牵涉着不同文化、文学“对话”的规律性因子;范丽娟的《女性的崛起与中英浪漫主义女性诗学构建》,力求在文化诗学的视域内把握女性作家崛起的背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和中国五四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共性与差异,平行透视中隐含着“一加一大于二”的启迪;谢模楷的《论楚辞对李群玉诗歌创作的影响》则以李群玉为中心,从语言、故事、风物和意蕴等维度,阐释晚唐诗歌和楚辞之间的联系,以及风貌表现与发生成因,紧扣文本的分析说服力强。而不论是纯粹的本体理论阐释,还是具体的诗学实践探讨,研究者们的学术指认都切合了中国新文学的引发模式实质或古典诗歌的内在精神,能够促进学界的进一步思考,而这便是文学研究的最大价值所在。(罗振亚)
雅克慎的接续性
雅克慎在其著名的《语言的双极:隐喻与转喻》(Two Aspects of Language:Metaphor and Metonymy)谈到:语言有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同一个词性的位置上(如主词)选择相似性的字词;接着,将前后不同词性(如主词与动词)的字词组合成更高阶的词语或是句子;因而,彼此能相互替代的相似性词语(similarity)是隐喻的思维,专注于先后词语的接续(contiguity)则是转喻的思维。我们若是将雅克慎如此的看法用于诗的意象讨论,则相似的意象互为隐喻,前后接续的意象互为转喻。
接续在雅克慎的论述中因为着重于先后的顺序,因而呈现时间性。但是雅氏在该文透过著名的心理实验也指出,转喻藉由“位置的相似性与语意的接续性相互组合、对比”①原文是:“combine and contrast the positional similarity with semantic contiguity.”本文所有外文的中译,都是本人权宜性的翻译。参见:Roman Jakobson,“Two Aspects of Language:Metaphor and Metonymy,”in European Literary Theory and Practice:From 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 to Structuralism,ed.Vernon W.Gras,New York:Dell Publishing Co.,1973,p.123.而产生,这样的说法已经有空间并置的暗示,如垃圾(litter)与茅草屋(hut)的关系。垃圾与茅草屋并不是时间性先后的接续,而是出现于同一空间的接续或是并置。之后,狄曼(Paul de Man)与吉内特(Genette)延伸雅克慎这方面的看法,更确认了接续性的空间特性。②狄曼与吉内特强调转喻促成隐喻,因为比喻是由空间比邻而造成。请参见:Gerard Genette,Figure III,Paris,Seuil,1972,pp.42-43,pp.55-58以及Paul de Man,Allegories of Reading,New Haven:Yale University,1979,pp.65-67.
时间接续的意象
词语的接续
由于雅克慎《语言的两极:隐喻与转喻》的“初衷”是语言的探讨,词语的接续或是组合的讨论可以看出这个论述的原貌;以语法的接续讨论现代诗,呈现的是诗作的叙述。正如上述,语言的完成是相似词语的选择后的组合,叙述必然要触及词语的选择才能进一步探讨词语的接续。试以孙维民《路径》的诗行为例:
那是分别以前了破晓
凉爽如在露珠之中
窗子快显一段晒衣绳
连接壁纸及扶桑③孙维民:《麒麟》,九歌出版社(台北),2002年,第35~36页。
第一行的“破晓”与“清晨”、“早晨”等等相似,选择“破晓”可能着重在“破”这个字的意涵,有改变、破坏、好的东西破灭消失等等的暗示,呼应前面的“那是分别以前了”,原来诗行是勾勒两人分手之前的记忆。既然是过去甜美的时光,想必身心“凉爽”。第二行“凉爽如在露珠之中”的“露珠”一者意象来自当下的情境,再者,它是与“露水”乃至“微风”④在雅克慎的论述里,相似与相对比都是隐喻的特性。孙维民这个诗行的开头是“凉爽”,“凉爽”的微风是自然的思维,因此也是选择时“相似或是相对比”的候选情境。的选择中脱颖而出,以“露珠”替代“微风”打破了思维的惯性反应,以“露珠”替代“露水”凸显了“珠”的珍贵而易碎的特质,暗示美好的时光已不在。
以接续的观点来说,“破晓”、“露珠”所铺陈的情境对照下一组意象:“一段晒衣绳/连接壁纸及扶桑。”选择“连接”,因为一者它将前两行与后两行的意象衔接,让两组意象表象不相关,却暗中接续;再者,它在第三、四行是主要动词,连接了共同的生活空间(房间)与共同培养的盆栽。连接的主词是晒衣绳——一条两人可以自在曝晒亵衣的绳子,一条两人过去亲密关系的牵系。
意象的接续
以诗的探讨来说,意象的接续更显得重要。意象接续,因而变成叙述的主导,有时意象牵引意象,有时意象环环相扣,变成意象的环炼。试以陈义芝〈出川前纪〉的诗行为例:
梦见弹三弦的瞎子穿黑衣来到门口
烟熏的黄牙似笑非笑强把
父亲的八字带走
叮叮琮琮,每一根弦绞紧在我心上①陈义芝:《不能遗忘的远方》,九歌出版社(台北),1993年,第176~177页。
诗中人梦见弹三弦的人带走“父亲的八字”,谈三弦穿着“黑衣”,满口“黄牙”,衣服与牙齿的意象接续成为一种不祥的化身。而他是“瞎子”和“黑衣”更加强“父亲”命运黑暗的感觉。牙齿熏黄,好似口中叙述的多半不吉利,一种熏染,一种难以刷洗的污垢。而“似笑非笑”更是内容诡谲,命运在言语的狎弄中,似有笑声,但也许皮笑肉不笑。
“瞎子”、“黑衣”、“黄牙”、“似笑非笑”、“八字”接续成叙述。对于谈三弦的人的描述,阅读的过程中,读者感受到一个意象牵引出下一个意象,而下一个意象又牵引出下下一个意象。意象是叙述的动态之旅,而非静态的整体的象征。由于是动态,父亲的命运在诗行的进行中也就定夺了。这时,黑衣黄牙的人不止弹三弦,他拿走了父亲的八字,似乎是死神的化身。
再以洛夫《莫斯科广场》的诗行为例,说明意象接续的另一种面向:
一不见马克斯的画像
二不见列宁的画像
三不见斯大林的画像
据说,他们全都排队刮胡子去了。
一位游客高举双手
大声说:我占据了莫斯科广场
照相机咔嚓一声
他立即被囚禁了黑房②洛夫:《雪落无声》,尔雅出版社(台北),1999年,第13~14页。
引文的第一节表面上是三个意象的并置,但因为这些画像已经“不见”,不在现场的空间,所以是诗中人意识里意象的接续状态。他看不到马克斯的画像,接着想到列宁的画像也不见了,接着又想到斯大林的画像也不见了。三个思维依序发生,有时间性的先后。因为是诗中人的意识状态,所以这一节的最后一行“他们全都排队刮胡子去了”是诗中人的臆测。这个臆测充满想象力。一者,三人外表共通的就是长了胡须。二者,“刮胡子”意味时不我予,当年脸上的胡子可能是威权的形象,现在胡子要被“刮”了。三者,“排队”与上面的三人依序排列相呼应,四者,“据说”更强化了上面的“画像”不是空间上的实存。
第二节更有意思。游客举双手说,他占据了广场。举双手的动作让人联想到当年共党专制时代,老百姓面对秘密警察,经常有的动作。读者从“占据”两个字,心中必然闪现第一节的三个想象的画像。想当年占据广场的是这三个画像以及画像的代表的威权。因此,经由“占据”,“我”与马克斯、列宁、斯大林相互成隐喻,只是我在现场,而后三者已经缺席。另一方面,“我”与这三者也是转喻,因为“我”接续这三者,“占据”才更能发挥语意的反讽效果。引文的最后两行接续了前面的叙述后,再次增加语言的浓密性与趣味性。举双手是为了照相,而照相实际上是影像“被囚禁了黑房”。这里的两组隐喻效果非凡。“他”和“影像”经由选择后①隐喻基于相似,词语最后的决定,是各个相似词选择后的结果。,前者变成主词。“黑房”既写实又暗喻。照相的影像必然进入黑房,而“黑房”则暗喻当年恐怖的时代,因此接续了马克斯,列宁,斯大林,占据、举双手文字的意涵。
空间接续的意象
接续的空间性有两种状况:一种是诗行的并置,另一种是诗中情境里意象的并置。诗行的并置使两个诗行的意象互成转喻,由于并置,诗行相互依托,不需要其他的文字作为比喻的说明,如白灵的《钓》:
水月是一轮沸腾的黄金
溪水忙了整夜收拢它怀中的财富
仍有些流金漂到下游去了
老者唇边停着一只萤火虫
钓丝垂进水中寻鱼儿的小嘴②白灵:《五行诗及其手稿》,秀威信息(台北),2010年,第172页。
第四行的意象是老者唇边停了一只萤火虫,第五行是钓丝在水中寻找「鱼的小嘴」,两个情境相似,相互并置,相互依托成为转喻。两行不仅是诗行的并置,也是情境的并置。并置的结果,让诗多了一些密度,人类垂钓自认理所当然,但人可能也是被垂钓的对象。萤火虫是钓饵,这个钓饵,随者前三行“黄金”、“财富”、“流金”,是一只会发亮的虫。由于萤火虫接续的是黄金等意象,它类似财富,是人类追求的对象,是人类欲望的钓饵,因而也类似鱼的命运,会因为吃了鱼饵后上钩。
诗行的并置,看起来比较明显,比较容易吸引读者的注意;而诗中情境的并置相对地比较隐约,读者需要更纤细的思维才能体会其中的“诗意”。试以杜十三的《桥》为例:
他把一句谎话吐在地上
变成一座桥
架在两岸之间
河水不相信
从桥底下走过③杜十三:《石头悲伤而成为玉》,思想生活屋(台北),2000年,第130页。
桥隐喻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管道,“两岸”暗示彼此相隔而无法沟通,可能意见相左、隔离对立。第一节没有写到“水”,因为“桥”的意象,水的影像已经呼之欲出。另一方面,水与桥在现场空间并置,本来水从桥下“走过”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由于第一节有“谎言”,逻辑的接续上,因为河流“不相信”这个谎言,所以不走桥上,而走桥下。用“走过”而不用“流过”一方面强调了水的意志力,另一方面也延伸呼应了桥的功能,因为“桥”是让人“走”的,走过去才能与对岸沟通。当然“对岸”指涉的对象可大可小,可以是任何一条河的两岸,也可以是当年互不往来的海峡两岸。
时间性与空间性交会的意象
有时,时间性的接续与空间性的接续交织,使诗的内涵更繁复隐约。试以
李进文《战争》的诗行为例说明:“十字架自梵谛冈的胸前起飞/多美的雪白战机,瞄准山下百姓/空投宝训。”①李进文:《不可能;可能》,尔雅出版社(台北),2002年,第100页。现场可能是战机飞过梵谛冈,战机与教堂并置,进而引发教堂上的十字架与战机的联想,因为外型的相似。既然十字架的意象与战机的意象结合,瞄准地面空投的就不是炸弹,而是富于教理的“宝训”。三个诗行是诗的接续,而在接续进行中,不时因为空间的并置,使原有的意象一再变形,融入别的意象。
再以李进文另一首《宁静开口说话了》,进一步讨论:
繁华的夜景啊
繁华的你
笔在听,而信纸说话
沙沙的回音拍打梦境
当一个人不再
面对一个人:
一行脚印流啊流,在远方
一个身体流进另一个身体②李进文:《不可能;可能》,第74页。
本诗的第一节是年老,“当一个人独自/面对一个人”。引文的第一节是全诗第二节的后半段,回忆过去“当一个人不再/面对一个人”。“不再面对”,因为一个在远方,两人只由藉由书信寄情思忆。你之所以“繁华”,是因为和“繁华的夜景”并置而造成语意的渲染。由于“你”的繁华,更衬显此地诗中人无助的孤寂。笔的“听”、信纸“说话”,接续成笔在纸上书写时“沙沙”的回音。“沙沙”又隐含海边沙滩潮水的意象,接着的“拍打梦境”“拍打”的动作进一步证实这是海边的情景。似乎是一个人读信,梦中出现对方在海边的身影。
接着的下一节(也是本诗的最后一节)第一行“流啊流”是“沙沙”海边意象的接续。但本诗最后结尾的两行却造成本诗最大逆转。第一行是上一节的延续,诗中人意识到的是对方在远方海边沙滩的脚印。但紧接的一行与其并置,却是诗中人在当下和另一个身体缱绻,而且身体的体液流进另一个人的身体。两行并置,句型相似,而且第二行的身体与第一行的脚印用的都是同一个“流”。别离有情的牵挂,但现实的当下情仍然有情或是欲的填补。这就是人生。
随机接续的意象
转喻因为接续,文字或是彼此的碰触,富于随机性。假如结构是一般诗学或是理论家经常要追逐统筹的目标,随机(chance)则是诗路在逻辑之外另辟蹊径。假如隐喻有语意相似的基础逻辑,接续可能只是语法的接续以及随机因缘所造就的叙述。试以朵思《百年阡陌》的诗行为例:
飘浮在天空底下五颜七彩的色泽
涉过风、涉过雨
历经骚动的节拍
建构红蓝板块的冲突
之后,岛屿浊水溪以南的壁虎
叫醒了戒严时期的幽静
绿色便进驻为地图上可以言诠的一个名词①朵思:《凝睇》,秀威信息(台北),2014年,第85页。
本节诗行影射台湾的政治情境,其中引文的意象如“风”、“雨”、“红”、“蓝”、“绿”等等大都可以找到逻辑的立足点,是隐喻的各种化身。但第五行的“壁虎”则迥然不同。某方面说,“浊水溪以南的壁虎会叫”是现实确切的现象,比隐喻的想象更有逻辑的立足点,但是在诗的意象叙述里,这里的出现的“真实现象”却是随机的,因为“壁虎”并没有任何政治意涵。它的“叫声”完全跟政治形势无关,是诗行把牠的叫声和“戒严时期的幽静”接续连结。壁虎会在诗行中出现,主要是“在浊水溪以南会叫”的机缘,假如有任何其他动物,也有这样的特性,也可能在这里成为关键性的意象。
接续与语意蔓延的意象
随机接续的进一步发挥,就是意象随缘,因而语意蔓延,成就现当代诗极精彩的思维。值得注意的是,意象随缘与许多随意拼贴极为不同。后者经常是文字游戏的代名词,而前者有丰厚的人生情境。这个情境显现文字与诗人活泼的创意,文字嬉戏展延语言的可能性,但终究不会坠入文字游戏的陷阱。再者,诗作在嬉戏的意象与语调中,似乎可以无止境的延伸,但在某一个阶段又有自觉而有暂时的封口,诗论家安德鲁斯(Bruce Andrews)说:“以嬉戏的语言作为行动暗示一种无止境的展延,一种本质上的开放。但是会在观照、体认与感觉趋于稳定的状况下在外形成封口。”②Bruce Andrews,“Poetry as Explanation,Poetry as Praxis,”The Politics of Poetic Form:Poetry and Public Policy,ed. Charles Berstein,New York:Roof Books,1990,p.29.本人在《台湾现代诗美学》中也引用了这一段话,请见简政珍:《台湾现代诗美学》,扬智出版社(台北),2004年,第223页。由于有这样的封口,诗作映现了人生的深沈。在当代所有汉语诗的创作中,洛夫在这方面的成就极为杰出,值得审视研究。试举他的两个诗例说明。第一首《橹声》的第二、三节(本诗共三节):
昨夜
船上的酒嗝
居然合折押韵
有点咀嚼唐诗的味道
清晨
听到李香君绣楼下
一阵阵刷马桶的声音
则纯属意外①洛夫:《背向大海》,尔雅出版社(台北),2007年,第76~77页。
这是洛夫独特的诗风,想象鲜活,幽默诙谐。第一节“酒嗝/居然合折押韵”,“居然”两字意味连诗中人也为如此的发现而惊喜。但事实上这是诗人写的诗句,感受最大惊喜的是读者。从“酒嗝”到“押韵”到“咀嚼唐诗”文字接续成古典氛围,既流畅又不时异峰突起。再细致品尝之,连第四行的“味道”都遥遥呼应第二行的“酒”。
第二节更出人意表。船过李香君的绣楼,听到“一阵阵刷马桶的声音”。诗中人说这“纯属意外”,正如上一节诗中人说酒嗝“居然押韵”,但感觉更大意外的是读者。诗从第一节古典的氛围中——坐船、饮酒、唐诗,一下子到现实鲜活却粗陋无比的“刷马桶”。以一般的诗作来说(不论是传统诗或是大部份的现当代的诗),这是大煞风景,古典的气氛一剎那间全部崩毁。但以现代诗来说,却是诗意另一波的扬帆远航。“刷马桶”是古典意象的接续以及语意的蔓延。也就是意象如此的转折,洛夫表象古典情境的铺成,成就的是极富于当代意识的现代诗。诗行提醒读者,在船中饮酒赋诗毕竟是现代的时空,而在江边生活,“刷马桶”是当下人生“日日的存在”(everydayness)。②海德格在《存有与时间》提到“日日的存在”这个词语。表面上这是时间的理念,但真正的重点是存在的方式,例如人如何经历沈闷,痛苦,如何面对当下。请见Martin Heidegger,Being and Time,trans.John Macquarrie&Edward Robinson,New 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62,p.422.诗表象的嬉戏,剎那间让读者面对人生的冷肃。
再以洛夫《顿悟》一诗说明:
慧能玩腻了钟磬木鱼
于是转过身子面壁
以头
撞墙
冬。
冬。
冬。
终于撞醒了春天
裂开的秃头上
一朵妖娆的玫瑰
含笑而出③洛夫:《背向大海》,第141~142页。
诗中人以戏谑的语调书写一个高僧的顿悟。修行人的诵经、敲打木鱼等动作,诗中人以“玩腻”来描述。如此的语调牵系了以下诗行的进行。“玩腻”也许意味每天例行的修行不得利,因而转头撞墙。撞墙的动作也许是修行者对自己的失望,也可能是想以比较激烈的动作寻求开悟。不论例行的修行也好,或是突发的撞墙也好,当事人都有相当的求道恳切度,但诗中人的叙述语调却是嬉戏揶揄。
第二节三个“冬”字是撞墙的声音,但不能用任何同音字如“东”、“咚”等取代,因为它所传达的不只是音,还有义。那是冬天,是修行陷入谷底的季节。
第三节的“春天”是“冬”的接续,是前面季节的翻转。撞墙的当下,春天来临,瞬间顿悟。心灵的开悟以肉体的头破血流为代价。但诗中人继续以戏谑的语调,将“头破血流”描述成“裂开的凸头上/一朵妖娆的玫瑰/含笑而出”。开花意味得道,但是开的不是莲花,是玫瑰,是人间传递情爱的花朵,妖娆含笑。一方面,选择玫瑰,当然与血的颜色有关,但另一方面,本诗结尾隐喻高僧得道,玫瑰意象的叙述语调却是得道的逆转;所谓顿悟,竟然沾染人间的习气。这是语意的蔓延,促成原初理念的消解。本诗具体而微印显了洛夫的诗风,文字意象活泼自在,想象飞舞奔腾,但诗作经常在关键处有一种逸轨逆转的观照。
小结
传统诗的创作以及一般的诗学的研究通常以隐喻为焦点。相似性与相异性是大部份诗人思维的主要依据。对于转喻接续性的意象,大部份的诗人不得其门而入,有些则在“不经心”中产生,诗人自己对如此的书写说不出所以然,有些含糊地将其归诸“超现实”,有些粗枝大叶将其误解成另类拼贴。对于接续性的奥秘,台湾大部份的诗评者几乎懵懂无知,对其专注探索的诗学当然少之又少。不仅中文诗的研究如此,国外的诗学研究也是如此。因而雅克慎感叹地说,诗学上,“语言本来确实的两极,在研究时,却经常以独断的策略,将其切割成单一的模式,这种状况,令人讶异的是,刚好与失语症中的接续失错的现象相对应”。①原文是:”The actual bipolarity has been artificially replaced in these studies by an amputated,unipolar scheme,which,strikingly enough,coincides with one of the two aphasic patterns,namely,the contiguity disorder.”Roman Jakobson,“Two Aspects of Language:Metaphor and Metonymy,”in European Literary Theory and Practice:From 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 to Structuralism,p.127.本文的讨论,某方面来说,是对雅克慎的感叹的一种回应。我们从洛夫、李进文等人的诗作中看到接续性转喻丰富的面向。接续所涵盖的时间性与空间性,时间性与空间性的互动,接续的随机性,随机性所促成的语意蔓延等等,都让当代诗跨越了传统或是一般诗作既有的门坎,让读者展望“现代诗”更辽阔的天地。
(简政珍,台湾亚洲大学外文系教授)
Relation Between M etonym ic Contiguity and Image-Creating in Contemporary Poetry
Jian Zhengzhen
Inspired by Jakobson’s remarkable idea aboutmetaphor and metonymy,the two poles that forms the basic linguistic articulation,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general ignorance of use ofmetonymy in poetry-writing and poetics.The contiguity aspect of metonymy enriches the poetry and poetics andtherefore creates imagery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similar aspect ofmetaphor.The contiguity asserts itself with temporal continuation ofwords and syntactical structure and therefore builds the linkage of images. Themetonymic contiguity also results from the juxtaposed lines and adjacent images in contexts,and it also enhances the interaction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elements of words and images.It imparts the elements of chance and semantic dispersion into image-making.In a way,this paper serves as a response to Jakobson's comment that the neglect ofmetonymy-use is an aphasia corresponding to the contiguity disorder.
Jakobson;Contiguity;Series of Images;Semantic Dispersion;Contiguity Disor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