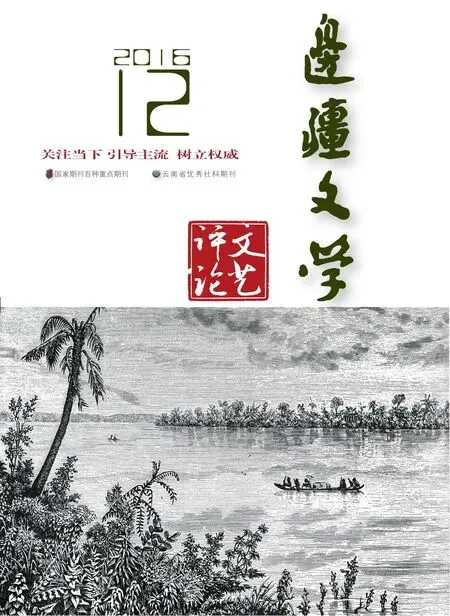两性永恒的困境
——重温《伤逝》
◎马 琼
两性永恒的困境
——重温《伤逝》
◎马 琼
经典重读
主持人语:《伤逝》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也是“最具鲁迅意味”的短篇力作。青年学者马琼的文章《两性永恒的困境——重温〈伤逝〉》,从“从‘女神’到‘女仆’”、“真的隔膜”、“如果子君能说话”三个层面对这一短篇经典进行了较有新意的分析。虽然研究《伤逝》的文章较多,但这篇文章独辟溪径,从两性困惑的层面探讨,认为“《伤逝》就是一部直面惨淡人生的小说,它深刻地揭示了男女两性永恒的困境,即使是在今天,它也没有丧失启示意义。”论文角度新颖,论述详实,值得一读。
《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是美国著名作家、美学家苏珊·桑塔格的短篇小说,作品发表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青年学者杨洁的文章,从哲学意义的高度,以文本细读的方法对这篇小说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立意高超,叙写有力,是一篇非常难得的好文章。(李骞)
鲁迅的小说《伤逝》,是一部“直面惨淡人生”的小说,它深刻地揭示了男女两性永恒的困境,即使是在今天,它也没有丧失启示意义。那么,《伤逝》展现了怎样的鲜血淋漓的真实呢?
一、从“女神”到“女仆”
《伤逝》中,作者笔触充满了柔情蜜意,爱情在他笔下,被表现得如此美好,如此令人沉醉。比如他写沉浸在热恋中的涓生,在焦躁的长久的等待中,学会了一样本领,就是能够在众多的足音中准确地分辨出,那属于子君特有的“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涓生陋室枯坐,久候心上人而不至,心心念念的都是伊人的倩影,什么书也读不下去:“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耳朵却分外地灵,仿佛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履声”。当佳人终于翩然来临,那一刻真是喜不自胜:“迎出去时,却已经走过紫藤棚下,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
此时的子君不啻是涓生心目中的“女神”,这也就难怪涓生在求爱时,虽然事先仔细地排演过,临时却身不由己地采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大概涓生潜意识里觉得,只有这样谦卑到极致的举动才足以打动伊人。而涓生之所以能如愿得到子君的允许,这戏剧性十足的西式求婚仪式可以说是功不可没。“求婚”这一幕对子君来说意义重大,充分满足了女人天性中对浪漫爱情的渴望,她脸上闪现的“没有见过,也没有再见的绯红”足以证明,而对涓生来说,这不过是“使我不愿再想的浅薄的电影的一闪。”子君不厌其烦地反复和涓生“相对温习”这记忆中最美好的一幕,陶醉于自我想象的恋情之中,涓生却明白这不过是浅薄可笑的演戏,让这出戏反复在眼前重演无异于一种折磨,
于是子君只能“两眼注视空中”“神色越加柔和,笑窝也深下去”地自修旧课了。子君不愧是个好学生,她掷地有声地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句话,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连涓生这位“启蒙者”也为之“震动”。而且子君的完美不仅表现在她的语言上,也体现在她的行动上,当两人在寻找住所的路上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涓生这位满脑子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也不免有些瑟缩,而子君却能够“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这就更令涓生惊佩不已。只有在爱情彻底幻灭之后涓生才恍然领悟,子君此时的“勇敢和无畏”不是因为思想上真正的自由和解放,而是因为爱,是爱给予了子君大无畏的勇气。
“女神”的光芒并没有焕发太久,爱情只有在没接触到现实以前才是美妙的。两人同居之后,子君的形象就迅速急转直下,一变而为“女仆”了。在涓生看来,婚后的子君,完全变成了一个庸俗的家庭主妇,再没有闲情雅致,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不爱花”:“我在庙会时买来的两盆小草花,四天不浇,枯死在壁角了”。对照涓生之前的回忆,子君到会馆访他时,是特意“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是否在由“女神”到“女仆”的过程中,子君连爱好都改变了?她饲养油鸡,逗弄“阿随”,在“川流不息”的“吃饭”中建立自己的功业,远离了“读书和散步”,“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自然也就让涓生远离了她。在会馆的时候,子君的形象是“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这种纤弱娴静的病态美符合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审美,同居之后的子君,“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不仅病态美一扫而空,而且“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女神”完全跌落尘埃了。在人物叙述者涓生对子君的形象做如此描述时,我们不难体会到他内心深处不小心被带出来的那份鄙薄与厌弃,而子君的悲剧也已经铸定。
二、真的隔膜
事实上,这段恋情从一开始就质量不高。仅仅经过三个星期的共同生活,涓生就发现:“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我们会发现,这一对恋人其实并不真正相爱,所以他们在互相了解之后,才会震惊地发现,对方其实是一个陌生人。
涓生说自己的爱是纯真热烈的,驱使涓生展开追求行动的心理动因,无疑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原始的情欲,有着“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的子君,实际上是涓生的欲望对象。一旦欲望得到实现,被弃的下场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了。小说中虽然只字不提涓生的亲人与家庭,但涓生独自一人客居异地的处境是非常清楚的。小说一开篇,人物叙述者涓生就交代:“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来解读,“逃出这寂静和空虚”不是爱情的派生物,反而是产生“爱情”的原因?正是因为能借此逃脱寂静和空虚,所以才爱子君?如果涓生不是偏居于一间“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苦等子君的来访,他的爱是否还会如此热烈?
从涓生与子君热恋时的相处模式来看,他们与其说是恋人,不如说是师生:“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涓生可以谈社会谈人生谈文学,而子君的反应却永远只是“微笑点头”,虽然这并不代表她真正听懂了涓生的话。涓生扮演的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启蒙者”的角色,两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等,也没有精神层面上的深入交流。事实上,涓生对子君的“爱”仅仅维持了三个星期,涓生的自白让读者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使是在他没有失业之前,他也早已心生厌倦。正因为昔日的爱已不可追,生活如同一潭死水般“凝固”,所以两人婚后唯一能做的,居然是怀念和回味在会馆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
三、如果子君能说话
《伤逝》的副标题是“涓生的手记”,小说以人物叙述者涓生的视角展开叙述,不论是热恋时的纯真美好还是决裂后的痛苦悔恨,一切都来自涓生的追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女主人公子君一直是被遮蔽的,读者对她的内心一无所知,只能凭借涓生的叙述来加以揣测,而涓生的讲述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呢?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涓生这个人物叙述者,实际上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他在自己的叙述中,有意无意地扭曲和隐藏了一些事实。如果沉默的子君能开口讲述,她的故事会是什么样子?子君在小说中
被抽离了内涵,成为一个空洞的符号,读者只能在涓生冠冕堂皇的言辞的缝隙中,在他自相矛盾的指控中,努力地去寻找真相,还原子君本来的面目。涓生在文本中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整个故事都是由他叙述出来的,这个视角无疑会影响到读者的思想和情感判断,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涓生的讲述中,颇多前后矛盾和含混不清之处,这使得他的“伤逝”疑点重重。
涓生对子君最强有力的指控就是认为她在婚前婚后判若两人,而这是他之所以不再爱她的重要原因。涓生最难忍受的是婚后生活成了“吃了筹钱,筹来吃饭”的循环,虽然他认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便是生活,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看似毫无意义的循环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子君并不仅仅只是在说“我是我自己的”这句话时才是勇敢的,她婚后也奋力承担了家务的重担,并非无法面对现实生活、只会要求涓生重温昔日誓言的柔弱女子。但涓生却对子君的操劳视而不见,他反感的是自己苦思冥想时子君催促吃饭的声音:“使她明白了我的作工不能受规定的吃饭的束缚,就费去五星期”。涓生不惜贬低子君的智商和情感反应,以便为自己的绝情开脱,因为读者不难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子君之所以招致厌弃完全是她咎由自取。就在向子君做出不能“催促吃饭”的规定之后,涓生很快又有了新的抱怨:“只是吃饭却依然给我苦恼。菜冷,是无妨的,然而竟不够;有时连饭也不够……”。“菜冷,是无妨的”和“我不吃,倒也罢了;却万不可这样的操劳”一样虚伪,涓生仅仅因此就心怀愤懑,他根本不关心子君究竟以什么食物果腹,就得出结论说自己在家中的位置“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难怪子君只能“不大愿意开口”了。
涓生将子君的父亲称做“儿女的债主”,说他有“烈日一般的严威”,我们会发现,涓生这位“夫主”的严威也非同一般。子君固然是勇敢地走出了父亲的家门,然而要在“夫主”的治下生活,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失业对涓生来说“不能算是一个打击”,“这在会馆里时,我就早已料到了”,他所痛心的只是“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面对“豫期的打击”,涓生却毫无准备,表现得手足无措。事实上,不能做到“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的人恰恰是涓生,他无力改变自己的生存困境,只能迁怒于子君,视她为多余的累赘,不仅“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愤怒于子君的“毫无感触”和“大嚼”,还暗示子君自己“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了她”。当涓生在“通俗图书馆里觅得了我的天堂”时,难以想象子君在冰冷的小屋里是置身于一个怎样的地狱!无力创造新生活的涓生只能将“新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分离”上,对自己昔日的恋人他已经丧失了起码的尊重和怜悯,只一味设想“她的死”,奇怪她“倒也并不怎样瘦损……”。涓生明明是嫌弃子君“只知道搥着一个人的衣角”,明明是害怕自己与子君“一同灭亡”,却在对子君下“驱逐令”时为自己辩护说:“人是不该虚伪的……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如果分手的结果真的是子君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的话,为什么涓生要反复“想到她的死”呢?
始终沉默的子君真的是依附型人格,完全没有自我吗?子君接受了涓生的启蒙,凭着爱的勇气毅然走出了家门,然而梦醒之后她仍然无路可走。子君在两人结合之时卖掉了自己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来“入股”,这证明了她是有着独立的精神人格的,但当时的社会并没有给她提供任何出路。当涓生的“新的生路”都不过是又重回到会馆那间破屋,“一切请托和书信,都是一无反响”时,子君又能如何呢?子君曾经“倾注着全力”去建设那个“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爱情成为了她的全部人生。然而悲哀的是,一旦她交出了自己的全部,她也就因此失去了对方的尊重。对于男性来说,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在生存面前,爱情变得不再重要。反过来说,如果子君不再依赖涓生生活,她也可能重新变得可爱。涓生离开了吉兆胡同,就又可以开始幻想子君“将要出乎意表地访我,像住在会馆时候似的”。小说结尾,涓生又回到会馆那间破屋,过去一年的悲欢恍如从未发生,从虚空又回到虚空,证明的是爱的虚无。
子君的时代已经远去,然而我们究竟进步了多少呢?女性在争取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道路上,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鲁迅在《伤逝》中揭示的是深刻的人性和两性永恒的困境,这使得这部经典在今天依然常读常新。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杨 林
——《古对今》教学活动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