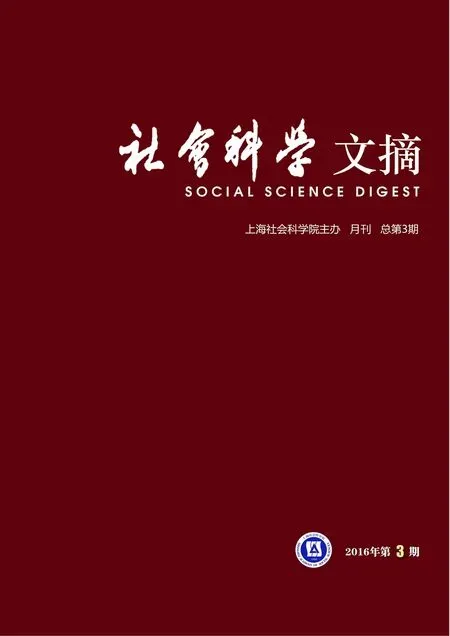《聊斋志异》研究三百年
——以方法论的线索与转向为中心
文/王昕
《聊斋志异》研究三百年
——以方法论的线索与转向为中心
文/王昕
《聊斋志异》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小说一流名著的阵营。名著的研究历来是古代小说研究的主体、推动中国小说学科发展的前沿。可以说,整个古代小说学科几乎就是围绕着名著的阐释和接受建立起来的。因此,小说研究的一些整体性的问题和现象也容易从具体的名著研究中显露出来。总体上,这些小说名著的研究可分三个时期:明清两代以评点为主的研究时期;近现代在小说学建立的框架内研究的时期;最近三十多年来的多样化研究阶段。《聊斋志异》研究和其他名著研究一样,近年来都呈现出某种难以推进的疲态:重复的题目、观点,雷同的视角和单一的论证方式等,让人感到在成果数量的累加、研究范围的平衍之外,殊少精彩的、原创性的推进。
《聊斋志异》研究现状并非偶然形成,从清代序跋、评点到现当代的研究,中间贯穿着是十几代学人自觉不自觉的研究方法论和批评立场。回顾这些方法论在不同时期的成就与表现,共同点与相异处,就可以对目前的现状由来、问题所在,有更清晰地认知与辨析。
清代评点传统与鉴赏式研究
《聊斋志异》研究史的发端是清代的序跋与评点。序跋、评点都是以介绍、推扬小说为目的,而它们在批评方法和立场上又开启了后来的鉴赏式批评。
通过近年的文献阅读,笔者对《聊斋志异》研究存在的问题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突出的印象有:视野不广,选题较为集中;主题归纳以偏概全,有笼统的道德化倾向;鉴赏式的研究过多,缺乏学理性分析和整体性研究。明清小说评点传统对目前研究现状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具体来说,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1)研究者的视野问题。作为一部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的作品有五百余篇之多。然而在众多的论文和上百部的专著里,人们反复赏析、引用、论述的篇目也只在五十篇左右,只占十分之一。这种篇目研究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名篇”鉴赏的连篇累牍和作品解读的类型化。(2)研究角度的固定化。研究者从丰富的文本中拣择出固定的主题或者解读路径。为突出这些个“要领”或“统摄”的意义,论述者不惜割裂作品。(3)鉴赏代替了深层次的阐释与研究。赏析是感性而主观的,只是初步的小说研究。它们之所以成为《聊斋》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还是受明清小说评点传统的影响。
与以上当代研究的问题相对应,明清小说评点的主要特点有三,即传播功能、主观式的评点和类型化的批评套路,这些都对《聊斋志异》研究方式和思路有着潜在的影响。(1)小说评点的主要目的是对普通大众传播文本,其功能在文本普及,不会有太高深的理论建树。这就决定了其理论性和系统性先天不足。(2)编创修改式的评点批评。明清评点者往往以居高临下、为王做主的态度看待文本。这种传统使得不同时代的研究者很难在同一文本或者理解框架中,形成建设性的对话与知识积累。(3)小说评点针对“事理”与“文理”的论文传统。其本质是按八股文的标准评小说。这种功利性很强的应试型文论,实是方凿圆枘、难以搔到痒处。
在文本赏析问题上,现代研究者还面临着比早期评点者更困难的局面。当代研究受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占据主流的功利主义文学批评贻害较深。主要表现是不重视文本内在的关联,有孤立地看待和解读文本的倾向。在现代研究者的文章中,很少能够读到与作者的心怀、意味互相映发的机趣文字。而浸淫在同样的文化氛围之中,清代评点家倒是能够领味其中意趣,文本内外构成有意味的对话。
因之,明清小说评点虽是非系统性、有文体针对性的一种理论,但评点者却是最接近原作文化语境的人,他们对小说纹理脉络的揭示为后来者提供了原始的视角。目前古代小说研究的某些框架和思维方式同古代的评点传统,具有根基上的相似性,是大家习焉不察却又无可否认的事实。
道德判断与政治伦理批评
《聊斋志异》研究具体而微地展示了古代小说研究方法与视野的演进。研究者倾向于使用道德判断、政治伦理等外在的意识形态标准判断文本价值。
《聊斋志异》研究对外部意识形态的变化过于敏感、亦步亦趋,直到近来才有些许的放松。无论是评点者还是现代研究者,他们在对作品内涵的认识上,都有某种用简单的道德评判代替对文学意蕴的整体把握的倾向。
这种受儒家“文以载道”价值观影响的批评范式,与古代小说产生于同样的思维路径和文化传统之中,有其深契的适用性和合理性,但它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从合理性来看,小说文本中道德教化立场与道德叙事确实是普遍存在的。虚构的小说人事,给了读者从阅读中认知和理解人生处境的模型。从作者到批评者俱擅长从故事和人物中引导出富有道德价值的人生经验。从局限性来看,意识形态批评也有难凑肌理之处,本质上是“利用文本”而非对文本进行审美的研究与阐释。它们的成果与弊端表明,外部的政治伦理立场对深入理解小说世界似乎难以着力。
以上是以《聊斋志异》研究史和方法论的传承为线索进行的大致梳理。传统文献考证本身依赖于材料和文献的新发现,在缺少新材料、新发现的情况下,研究自然也陷入了某种停滞。在缺少新材料、新文献的现状下,如何引入新的方法和视角,在现有的文献和文本基础上产生新论题和新视角,使研究工作持续、深入地展开是当务之急。
《聊斋志异》研究方法的转变
既然目前的研究困境主要是由研究者的视角和批评思维所导致的,传统的小说研究方法的转变就势在必行。古代小说学是相对稳定而保守的研究领域,可以预期的发展方向不是某种系统性的变化,而是方法与重心的重新组合与逐渐转向。新的研究模式应以蒲松龄和《聊斋志异》为主,选择、综合各种理论与方法,以避免理论操作文本的粗率。以下试从“志怪”题材、作家研究和文本解读几个方面,探讨文化研究可能给《聊斋志异》和蒲松龄研究带来的新的价值认识与阐释空间。
一、关于志怪。《聊斋志异》以花妖狐魅为志怪的形式和内容,是蒲松龄主动的选择。考察其所处文化与传统,可更清晰地发现他“雅爱搜神”行为的文学价值和意义。
文化研究可以在志怪小说的文本研究之外,引入民族志的研究视角。研究者如果能够进入到蒲松龄所在时代和地域的特殊群体文化中,就更能了解蒲松龄大量撰写“花妖狐魅”式志怪,不是可有可无的形式,而是有其独特的意义与动机。(1)蒲松龄所处的乡间社会,是他笔下的花妖狐魅滋生与传播的沃土。《聊斋志异》的志怪,其实是扩大了文学的表现范围。文化与风俗研究可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聊斋志异》之“志怪”的价值。(2)志怪语异是古代悠久而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在多维的文化视角审视下,志怪文本的多重意义和丰富的内涵可以立体地呈现出来,因而是一个空间广阔、具有多方面延展性的课题。
二、作者研究。文化研究注重个人的主观性,故能从更切近的视角把握作家的特质。精神分析、历史考证以及生活细节的还原,可以让我们更真实地观察与认识蒲松龄。
三、从通观的角度阐释作家作品。小说研究的通观角度就是用更有针对性的、具体的批评取代对作家作品的一般化的认识。只有在尽可能还原的作家生存境遇中,才能理解他的性格与内心,发现作品独一无二的价值。(1)伟大作家的凡常性。蒲松龄首先是一个擅长用文学手段表达个人体验的普通人,以常识性认识为参照,才能较真实地认知作家。(2)对作家作品原始语境的审视。历史的眼光可以还原作品的实际语境,避免抽象的、想当然的解读与评价。
通过勾勒300年间批评方法论的演进线索,我们可以看到,《聊斋志异》的十几代研究者大致沿着一条具有内在统一性和连续性的路径探索前行。这种统一性和连续性在以下两点上最为突出:批评者根据他所处时代较狭隘的意识形态来寻找作品所反映的历史现实并以之判定其价值;用鉴赏和赞誉代替理性的分析和批评。
文化研究作为方法论转向的一种可能性,其优点主要在整体性研究、批评意识和作品中心论三个方面。首先是综合各种文化因素的整体性研究。文化研究作为一项整体性研究,既可以将名著与二三流作品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现象纳入视野,又能拓展名著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在缺乏新材料、新发现的现状中,使研究工作能够有推进和展开的空间。其次,批判精神带来的活力。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可以挣脱狭窄化的专业评文方式,从更多样性的角度评价文本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再次,解决理论操作文本的问题。文化研究以作品为主,综合各种研究方法,恢复文本与作家的历史面貌,将作家、文本以及历史的复杂关系作一番重新的、更符合事实地描述与归纳,使之呈现更多样的意义与价值。
总之,文化研究作为综合研究手段,可以避免单一的研究方法带来的障蔽。同时,文化研究也非尽善之方。因为在本质上,它和“聊斋”研究的传统批评方法都属于意识形态批评,都着重探究文本的政治学和权利——文化关系。这既保证了《聊斋志异》研究方法论转向的稳定与可衔接性,又具有明显的局限。因而,“聊斋”研究方法论的转向,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如何使文化研究更适用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还有待学人们共同的努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摘自《文学遗产》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