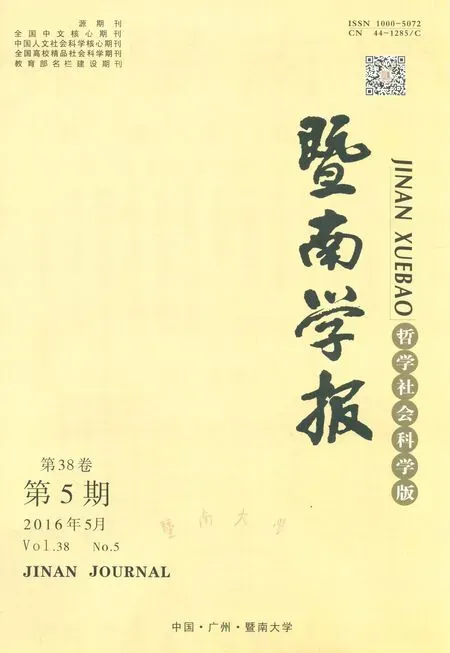国际合作中的制度选择:以软法为视角的分析
韩书立
(暨南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国际合作中的制度选择:以软法为视角的分析
韩书立
(暨南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制度结构的本质差异决定了不同的合作结果。在全球治理面临制度困境的情况下,“软法之治”的兴起,弥补了硬法在全球治理中的不足。一方面,国家为了避免高昂的缔约成本与主权成本,将软法作为实践中新的制度选择;另一方面,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选民权力分配,国内政治制度以及领导人的个人因素亦会对国际合作中的软法选择产生重大影响。
软法;国际合作;制度选择;全球治理
近年来,全球化朝着“更快、更廉价也更深入”①Thomas Friedman,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Farar Straus Giroux,1999,pp.7-8.的方向发展。国家的数量不断增加,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异、文化碰撞日益激烈。政府权力与国家主权被日益削弱,跨国组织(transnational organizations)与超国家组织(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s)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则不断提升。新的行为体,例如跨国公司、劳工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愈加活跃地参与到多边机构的决策中来。全球安全、国际经济、生态环境、人权保护以及跨国犯罪等问题领域的联系日益加深,以“规则之治”为核心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在纷繁复杂的新形势面前捉襟见肘,面临失灵的危险。②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全球治理的核心是机制治理,全球治理失灵(global governance failure)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的困境。③卢静:《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1期。全球治理在公平性与有效性上的不足致使全球治理陷入发展的泥潭。④赵骏:《全球治理视野下的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
然而软法理论凭借其独特的制度优势有效地回应了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为国际合作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选择。但是,软法理论至今仍处于型构阶段。⑤一般认为“软法”概念出自国际法院首位英国法官麦奈尔勋爵(Lord McNair)。参见A.J.P.Tammes,Soft Law,Essays o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In Honour of Judge Erades,1983,p.187.有学者认为施米托夫所谓的“新商人法”就是软法的早期雏形。参见何志鹏、孙璐:《国际软法何以可能:一个以环境为视角的展开》,载《当代法学》2012年第1期。软法现象虽然由来已久,但长期遭到学者有意识的回避。在当下的国际社会中,人们对国际法的效力尚且存在诸多争议,⑥韩书立:《走向平庸的国际法效力依据理论》,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9期。对软法的疑问则更是如此。软法当如何定义,软法是不是法,软法是否可以作为国际法的渊源,软法同国际关系领域中的非正式国际机制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亟须一个合理的答案。
一、国际制度中的软法问题
软法是相对于硬法的一个概念。①从制定主体与适用范围上进行区分,可以将软法分为国内软法与国际软法。国内软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政法方向,属于国内公法范畴,与国内社会规范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而国际软法的外延则相对宽泛许多,二者差异显著。参见刘颖:《论社会规范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郑毅:《论习惯法与软法的关系及转化》,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本文所述之软法概念皆指国际软法。“硬法是指精确的(或者能够通过裁定或公布细则而变得精确)并且代表法律解释与执行权力的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②Kenneth W.Abbot,Robert Kenhane,Andrew Moravcsik,Anne-Marie Alaughter,Duncan Snidal,“The Concept of Legaliz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3,2000,p.401.虽然在国际制度的实践中,软法的数量远多于硬法,但是,学界对软法的概念却众说纷纭。
对软法概念的把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从传统的定义法对软法进行解释。例如《欧洲法律杂志》主编弗朗西斯·斯奈德认为软法是“原则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legally binding force),但会产生实际效果(practical effects)的行为规则”③Francis.Snyder,“Soft Law and Institutional Practice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The Construction of Europe,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4,p.198.。这是目前国内外接受度较高的一种观点。此外,有学者认为软法是“没有中央权威加以创设、解释和执行的规则”④Andrew.T.Guzman,Timothy L.Meyer,“International Common Law:The Soft Law of International Tribunals”,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9,2009,p.518.。有学者认为软法是“条约之外包含原则、规范、标准或预期行为声明的国际文件”⑤D.Shelton,International Law and Relative Normativity in International Law,M.D.Evans,2003,p.166.。有学者认为“软法是在私人领域内确立和实施的混杂交织的行为规则”⑥Orly Lobel,“The Renew Deal The Fall of Regulation and the Rise of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Legal Thoughts”,Minnesota Law Review,Vol.89,2004.。有学者认为“软法是一种文件形式确定,但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却可能有某些间接法律影响的行为规则,它以产生或者可能产生实际效果为目标”⑦Linda Senden,“Soft Law,Self-Regulation and Co-Regulation in European Law:Where do We Meet?”,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Vol.9,2005,p.13.。可见,软法的概念有两种特征:其一,软法不能产生具有可执行力的权力义务关系;其二,软法能够实现一定的规则效果。
另一类以肯尼思·阿伯特的三要素说为代表。他受到哈特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理论的影响,认为国际关系法律化的概念包含三个要素,即义务(obligation)、精确性(precision)、授权(delegation)。其中义务是指,国家或其他行动者被某个规则或义务,或被一组规则或义务所约束。精确性是指规范的内容,即所要求的行为、授权和禁止行为被清晰的界定。授权是指第三方被授权执行、解释、适用的规则,甚至在必要时创造新规则。他认为:“一旦法律制度的安排在义务、精确性和授权三个维度中的一向或几向综合的维度上受到弱化时,‘软法’王国便出现了。”⑧肯尼思·W.阿伯特、邓肯·斯奈德尔著,胡晓琛译:《国际治理中的硬法与软法》,载杨雪冬、王浩主编:《全球治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95页。此种学说虽然为软法的概念研究提供了三种变量,较以往的传统定义法更为客观,但是,上述变量的弱化程度亦很难通过外部观察进行考量。
此外,还有的学者从后现代主义出发认为不必对软法进行定义。在其看来,任何一个给定的文本、符号或者信息都具有无限多层面的解释可能性。软法是20世纪中后期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传统彻底反抗的产物。后现代主义不可言说,不可表达、模糊性的特征,同样适用于软法。因此,定义软法是无力的,不必为此背上断言的沉重负担。⑨王申:《软法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及其启示》,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6期。
至于软法的法律属性则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从广义法的角度看,法律约束力不同于强制约束力①程迈:《软法概念的构造与功能》,载《金陵法律评论》2009年第1期。。“强制力保证”与“授权机构裁决”并非法律效力的核心。“一个法律制度之实效(即被遵守并产生规范效果)的首要保障必须是它能为社会所接受,强制性的制裁只能作为次要的和辅助性的保障。”②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4页。正如同秩序的真正生命力源自内部,软法虽然不具备强制属性,但是其仍然具有法律约束力,且来源于自身的内在理性。建构主义亦否认“强制性”的中心地位。“有效的制裁即实际的强制在法律中只具有有限作用,大多数规则在大部分情形中由于不同的原因而被自发地遵守。”③马克·范·胡克,孙国东译:《法律的沟通之维》,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7—49页。在建构主义视野下,“人类社会的结构主要决定于共享的观念而非物质结构。”④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1.法律的约束力出自“认同”。“不论是正式的国际条约和习惯法,还是非正式的国际软法,都属于集体期待一致遵守的社会规范。国际软法塑造了各国对于合规行为的预期并由此产生了一定的法律效果。”⑤夏春利:《论建构主义维度的国际软法研究及其方法论建构》,载《东南学术》2014年第2期。如果国际社会的行为体认可软法具有法律约束力,且认为对该文件的违反将产生不利的后果,那么软法即具有法律属性。从上述两类观点出发,软法亦法。从狭义角度看,“强制性”是法律所必备的形式要素。乔治奥·德尔·维奇奥认为,强制力与法律这两个概念在逻辑上是不可分的,“哪里没有强制力,哪里就没有法律”。⑥Philosophy of Law,transl.T.O.Martin(Washington,1953),p.169.汉斯·凯尔森甚至将法律描述为是“一种强制性制度”⑦Kelsen,The Pure Theory of Law,2nd edition,transl.M.Knight Berkeley,1967,pp.19-21.。笔者亦认为法律的约束力意味着该文件对国际社会行为体的行为施加了某种强制性的义务。如果拒绝履行,将会引发第二性的法律义务,即法律责任。没有强制性的法律规则是“一把不燃烧的火,一缕不发亮的光。”⑧鲁道夫·冯·耶林著,胡宝海译:《为权利而斗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软法的主张是重要和有影响的,但是由于软法不能在国际社会产生可执行的权力义务关系,因此其本身不构成法律规范⑨Malcolm N.Shaw,International Law(Sixth Ed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19.。
此外,软法亦不是国际法的渊源⑩有观点认为国际软法是国际法的“第三渊源”。参见Roberto Adorno,The Invaluable Role of Soft Law in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al Norms in Bioethics,Deutsche UNESCO Kommission,https:∥www.unesco.de/wissenschaft/bis-2009/invaluable-role-of-soft-law.html,2016年2月1日最后访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国际法的渊源主要包括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除此之外,司法判例以及各国权威公法学家的学说可以作为国际法渊源的次要表现形式,并没有列举软法。在实践中,由于国际法院将该条所规定的内容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且事实上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93条均为该规约的缔约国,联合国会员国的广泛性使得该规定成为人们对国际法渊源的普遍理解而具有极高的权威性⑪Malcolm N.Shaw,International Law(Sixth Ed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71.。但是,从严格意义上看,《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之规定仅仅是国际法院的裁判依据,并非所有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都必须依照该条所规定之国际法表现形式进行裁判。例如《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21条的内容就对此有所突破⑫《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21条规定,本法院应适用的法律依次为:首先,适用本规约、《犯罪要件》和本法院的《程序和证据规则》;其次,视情况适用可予适用的条约及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包括武装冲突国际法规确定的原则;当无法适用上述法律时,适用本法院从世界各法系的国内法,包括适用当时从通常对该犯罪行使管辖权的国家的国内法中得出的一般法律原则,但这些原则不得违反本规约、国际法和国际承认的规范和标准。本法院可以适用其以前的裁判所阐释的法律原则和规则。。并且,有学者认为《国际法院规约》中的部分条款,尤其是涉及法律援引的内容沿袭了1920年《常设国际法院规约》的制度安排,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缺乏对国际社会制度发展的回应⑬William R.Slomanson,Fundament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Law(4th edition),Thomson/West,2003,p.12.。软法的出现,恰好弥补了传统国际法渊源的不足。因此有学者主张,由于国际软法的当事方一旦对文件作出承诺,就受到“诚实信用”与“禁止反言”这些基本法律原则的约束,因此国际软法是未预见的新的国际法渊源①Christine Chinkin,Normative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in Commitment and Compliance,Dinah Shelton,Oxford 2000,p.31.。笔者认为,由于软法并非法律规范,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即使受到“诚实信用”与“禁止反言”这些基本法律原则的约束,仍然无法在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产生可执行的权利、义务,且内容的灵活性较大。把软法作为国际法的渊源将加剧国际法体系的碎片化,破坏现有国际法规范的稳定性,不利于国际司法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的实现。正如同善于恶的概念是确定的,法律的规定亦应当是确定的。大卫·休谟曾指出:“无疑权利、义务、所有权是不承认这种细微的渐变梯度的,一个人要么拥有完整的、全部的所有权,要么就根本没有;他要么完全负有某种行为的义务,要么就不负任何义务。”“生活中看来很平常的半权利和半义务的情况”一旦应用于法律,就成了“彻底的荒谬”②David Hume,Political Writing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Indianapolis,1994,pp.43,45.。软法虽然不是国际法的渊源,但是软法的先导立法作用,有利于新的国际条约的签订以及新的国际习惯的形成。以跨国银行业监管领域的软法性文件《巴塞尔协议Ⅲ》为例,虽然其出台时间不长,但是根据统计资料显示,除土耳其尚未公布将《巴塞尔协议Ⅲ》转化为境内立法的草案之外,巴塞尔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方均已出台国内立法草案,甚至最终立法文本。截至2014年11月,非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方中亦有89个国家或地区正在履行或已经履行了《巴塞尔协议Ⅲ》。③Implementation of Basel Standards:A Report to G20 Leaders 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BaselⅢ,November 2014,http:∥www.bis.org/ bcbs/《巴塞尔协议Ⅲ》虽然不是国际法的渊源,但是以该协议中的某些规则为内容的国际习惯正在形成,这些新的国际习惯就是国际法的渊源。
那么,软法与非正式国际机制又是怎样的关系呢?国际机制是广义国际法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一直以来机制亦缺乏一个足够精确的定义④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563页。。斯蒂芬·克拉斯纳从行为学的角度认为:“机制是一套隐含的或者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它将行为体对国际关系某一既定领域的预期汇于一点。”⑤Stephen D.Krasner,“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185.这一定义企图通过限定词“行为体的预期汇聚”(actors’expectations converge)将实践中不具有实效性的国际协议排除在外。但是,“行为体的预期汇聚”是一种难以从外部进行观察的主观现象。⑥刘宏松:《正式与非正式国际机制的概念辨析》,载《欧洲研究》2009年第3期。并且亦不能以某种机制的实效性缺失而否定其存在。因此有学者主张机制是“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中得到共同认可的管制性国际协议或安排。”⑦Abram Chayes and Antonia Chayes,The New Sovereignty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Agreement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转引自刘宏松:《正式与非正式国际机制的概念辨析》,载《欧洲研究》2009年第3期。这一定义将实践中的一些“死亡协议”(dead papers)重新纳入到机制的范围中来。机制可以分为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前者必须由国际组织或机构认可并监督实施;而后者则仅需参与者达成目标和相互利益一致的专门协议。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的区别在于成员国之间是否意图创设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如上文所述,软法与硬法的区别在于能否在国际社会建立可执行的权利义务关系。有学者认为:“‘软法机制’包括两种机制形态:一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非正式机制;二是机制规则不精确或缺乏执行条款,但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国际机制。而‘软法’机制以外的规则精确、执行条款明确的正式国际机制则是‘硬法’机制。”⑧刘宏松:《非正式国际机制的形式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笔者认为,从形式上看,软法、硬法与正式国际机制、非正式国际机制相对应。由于软法不是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软法不可能包含一部分机制规则不精确或缺乏执行的条款,但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国际机制。此类机制虽然在国际合作的实践中存在实效性的缺失,但仍然意图在成员国之间创造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依然是硬法。从另一角度看,硬法的实效性缺失亦是国际社会选择软法的动因之一。
二、软法在国际合作中的功能优势
软法虽然没有经过正式的立法程序,不能在成员国之间产生可执行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但是这种独特的制度特征却有着硬法所无可比拟的优势。
首先,软法有助于减少国际合作中的缔约成本,也即程序成本①相对而言,硬法的优势在于协约后成本低,或者说法律框架内的运行成本低。。国际条约的制定需要经过复杂的国内批准程序,特别是当国内的反对团体所占优势较大的情况下,国际条约的最终确立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软法的制定条件则相对宽松,在国家元首或者部门首脑同意或签署后即可生效。尤其是在应对危机局面时,由于软法创制程序简便,可以快速地达成协议,避免势态的升级甚至失控。
其次,软法有助于减少国际合作中的主权成本。硬法是一种义务程度高,精确性高,授权程度高的行为规范。在遇到纠纷时,硬法通常将权力授予第三方,以执行、解释和适用规则,甚至在条件允许时创造新的规则,这极大地限制了行为体的国际行为甚至主权。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领海、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的重新界定,给国家造成了高昂的主权成本②刘中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的负面效应分析》,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3期。。相反,软法内容模糊,缺乏授权,国家可以因此避免在相互间建立具有可执行力的权利、义务关系,合理减少主权成本的顾虑,促进合作。
再次,软法对不确定性的合理适应性可以应对不可预知的国际形势。国家的有限性无法预料制度设计的所有可能性后果。今天的盟友可能成为明天的敌人。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会改变原有的收益分配与激励结构。硬法的稳定性与精确性导致高昂的制度更新成本,造成前文所述的治理失灵③硬法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主要是将权力授予一个中央机构(法院或国际组织),以执行、解释和根据现实情况调整协议。这一方法虽然可以避免协议的空白与再协议的谈判成本,但是国家需要为此付出难以接受的主权成本。参见Kenneth W.Abbot,Duncan Snidal,“Hard Law and Soft Law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3,Summer 2000,pp.421-456.。软法则通过采用模糊、建议性的词汇,仅仅制定最低的基础性标准。各国可以通过重新谈判调整其承诺,例如弱化已有的硬法,或者在不具有约束力的行为规则上提高违约成本。在情势显著变化时,国家甚至可以选择退出机制。
此外,软法制定主体的广泛性能够更好地兼顾各方利益。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使得国家以外的行为体成为国际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国际行为体的多元化要求国际民主向协商民主的方向发展,采取开放协调机制④Orly Lobel,“The Renew Deal The Fall of Regulation and the Rise of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Legal Thoughts”,Minnesota Law Review,Vol.89,2004,p.386.,以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另一方面,受自由主义的影响,弱势行为体或个人普遍地对政府活动持怀疑态度。硬法的制定不免会引起人们消极的情绪与行为,阻碍合作的实现。协商民主的平等性与开放协调机制的广泛参与性,鼓励每一个国际行为体通过讨论与协商及建议的方式参与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最终的协议方案虽然不具有强制力和执行力,主要通过彼此的认同与支持而自我约束执行,但是,却形成了一种超越个体偏好的理性和善⑤哈贝马斯著,童世骏译:《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85-189页。。软法“通过劝服、学习和讨论促进成员国对共同的标准有一致的理解,达到规则的有效性。”⑥David M.Trubek,Louise G.Trubek,“Hard and Soft Law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Europe:The Role of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European Law Journal,No.11,2005,p.343.
最后,软法有助于提高国际合作的专业化程度。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问题的复杂程度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程度加剧。国际社会要求制定专业性更高的技术规范,将技术的操作流程与行业的监管标准通过技术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这种高度的技术性也意味着非政治性、非意识形态性。因此技术规范的制定主体通常并非国家而是跨国行业协会与研究机构等非政府组织。软法制定主体的多元化,能够更有效地将非政府组织甚至专家学者网罗到制度的制定中来。例如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ccountants)致力于国际审计与会计准则的制定。这些准则是推荐性的,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三、国际合作中软法选择的动因分析
国际机制由制度结构组成,制度结构的本质差异决定了不同的合作结果。基于以上功能优势的考虑,国际行为体在合作中有意识地选择软法。国家是主要的国际行为体。在全球公共问题的国际合作中,国家的行为呈现出以下几种特征:第一,国家以功利主义为活动原则,是理性的行为体。①利益驱动是国际合作的前提条件,是否存在中央集权机构并不对制度的设计与生产构成充分的障碍因素。参见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9页。第二,国家的理性是有限的。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和不完善,国家并不总是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国家存在理性的无知现象(rational ignorance)②赫伯特·西蒙著,杨烁等译:《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p.111-116.。第三,同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人一样,国家的行为存在机会主义倾向。最后,国家是多头政治(polyarchy)的行为体,国家的决策权是由不同偏好的行为体分享的③Robert Dahl,Modern Political Analysis,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84,pp.75-93.。通常情况下,国家希望通过以集体行动取代个体行动的方式,使个体在集体行动下的收益大于在单方面行动下的收益,最终实现国际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以上前提假设的基础上,本文从缔约成本、主权成本、国内政治三个方面对国际合作中软法选择的动因进行分析。
(一)缔约成本
避免高昂的缔约成本是国家选择软法的主要动机。美国的《扎布洛茨基法案》规定:“成员方有意于建立法律性约束关系的国际协议必须尽快送交国会。仅有政治或道德分量的,而无意于建立法律性约束关系的文件不属于此类协议。”国际条约从议定到最终批准需要经历一套复杂的程序。在议定阶段,出于较高的违约成本考虑,政府通常会谨慎地咨询各方意见。特别是当条约的制定没有获得广泛的国内支持时,审查批准的博弈使得国际条约的制定过程更加漫长而艰难。相反,软法的生效只需得到国家元首或者部门首脑的同意或签署。软法简便的制定程序在应对危机局面时可以快速地达成协议,有效地避免势态的升级甚至失控。
近些年来,在国际劳工权益保障领域,受高昂的国内批准成本影响,发达国家制定新条约的能力和兴趣有所下降。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为此备受压力。虽然遭到劳工代表的强烈反对,但是该组织仍然开始采纳实施一些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以减少各国的批准成本。④弗朗西斯·彭宁斯编,王锋译:《软法与硬法之间:国际社会保障标准对国内法的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1页。此外,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亦是缔约成本影响国际合作的又一例证。《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起初设想通过制定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的形式,促进世界经济贸易的合作。然而这一计划遭到了美国国内的强烈反对。1947年,成员国选择了相对软性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作为低成本的临时性的降低关税协议。该文件由框架性的规则构成,且设计了宽松的退出机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硬法更适宜新的经济环境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向世界贸易组织转化。
缔约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两个关键的独立变量的影响:主权成本与国内政治。当某一问题领域的主权成本相对较高或者国内政治对该问题存在严重分歧时,国际协议的议定与批准就会异常艰难。
(二)主权成本
主权成本对国际合作中制度选择的影响首先表现在问题领域的类型上。主权成本的大小受到问题领域敏感程度、同质性以及透明度的影响。当某一议题关涉“高政治”的国家安全领域时,行为体对问题领域的敏感程度是最高的。并且此时各方往往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甚至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成员国之间对信息公开的意愿亦比较消极。高风险下巨大的损害可能导致各国希望通过硬法的形式,提高合作的违约成本。然而在实践中出于应对意外风险的考虑,各国均不愿放弃对安全事务的自主权而选择义务度高、精确性高,但是低授权的制度形式,例如美国与苏联之间战略武器限制谈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SALT)所签订的一系列文件,双方精确规定了导弹的数量与种类,却未对授权做出安排。相反,在“低政治”的经济领域,主权成本则相对较低。尤其当成员国之间的认同度较高时,其对承诺可信度的需求较低。此时国家趋向于选择软法的形式加强国际合作。以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为例,其成员方为石油净出口国。由于在稳定油价维护石油利益上的目标一致性,成员方相互间具有很高的认同度①有观点认为,从法律特征上看,OPEC与卡特尔组织差别很大,它并没有操纵和控制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参见王智辉:《欧佩克对国际石油价格的影响分析》,载《东北亚论坛》2007年第1期,第32页。。在法律合作的形式上多为软法,并没有对成员国的违约行为规定严格的惩罚机制。相反,当相互间的认同程度较低时,对承诺可信度的要求则较高。此时国家趋向于选择硬法的形式加强国际合作。例如相对于石油净出口国,石油消费国对石油供给所导致的能源安全高度担忧,高昂的机会主义成本使得相互间的承诺可信度较低。于是,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所组成的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致力于通过硬法机制协调成员国之间的石油供给,以实现能源安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目标。
此外,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主权成本分析,在国际合作中选择硬法,往往会给国家带来高昂的不可预见的主权代价。通常情况下,硬法将权力授予超国家的第三方,以执行、解释和适用规则,甚至在必要情况下创造新的规则。国家通过条约对某一国际组织的授权将极大限制国家的国际行为甚至管理国内事务的能力。《罗马条约》第177条有关欧洲法院对成员国法院享有初步裁决权的规定即极大地限制了欧共体成员国的司法主权。该条规定当某一成员国的法院在适用欧共体法律审判本国案件时,如若对条约或者理事会、委员会所制定的条例、指令、决定等次一级立法或其他规范性文件产生疑问,则可以请求欧洲法院先行裁决,裁决的结果对成员国具有权威约束力②许睿、李风华、李允载:《欧盟法中的国家责任原则探析——从Francovich案和Factortame谈起》,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1期。。美国国会甚至明确指出,一旦国际条约包含限制授权给国内法院的规定,该条约不会被国内法自动执行③Frederick M.Abbot,“NAFTA and the Leg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A Case Stud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3,2000,pp.519-547.。
正是出于以上可能性的考虑国家不愿接受硬法的限制而选择软法。在国际反洗钱领域,国家既希望通过国际合作抵制此类跨国犯罪,又担心国内的合法贸易、监管政策与司法主权受到干预。为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通过建立金融行为专家小组的方式,出台一系列政策性建议。这些文件的内容虽然不具有强制执力,却可以兼顾各国间的偏好差异,协调管理行业间的监管,提供共同的标准④Beth A.Simmons,Soft Law Compliance:The Case of Money Laundering,in Commitment and Compliance:The Role of Non-binding Norms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edited by Dinah Shelt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a.。
(三)国内政治
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具有相互依赖性。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纯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国内(及跨国)行动的个人和团体是国际政治中的基本行为体。”⑤Andrew Moravcsik,“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1,No.4,1997,pp.513-553.甚至有学者认为“相对于担心其他国家的相对收益或者欺骗,合作努力的国内分配性后果对国家间合作影响更大。”①海伦·米尔纳著,曲博译:《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安德鲁·莫拉维斯克指出,仅从国际层面分析国家的对外行为虽然很吸引人,但是在现实的反常现象与有限的理论面前,这种分析方式就显得无能为力②Andrew Moravcsik,“Introduction:Integrating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in Peter B.Evans,Harold K.Jacobson,and Robert D.Putnam eds.,Double-Edged Diplomacy: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1-42.。这是因为国家并不是单一行为体而是多头政治(polyarchy)的行为体,国内行为体的相互关系较无政府状态与等级制更加复杂,更像是一个相互交织的网络。即使在非民主制国家内部,其国内政治亦很少呈现权力与决策权沿垂直等级自上而下流动的现象。有证据表明即便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政策’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亦是国内派系冲突消长的函数”。③Gavirel Ra’anan,International Policy Formation in the USSR,Hamden,Conn.:Archon,1983,p.8.在国际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尤其在宪政民主国内部,由于国内行为体从利益驱动出发追寻国家决策与自身偏好的一致性,输赢双方分化为对协议的制定持肯定态度或否定态度的不同集团,激烈的议会斗争常常导致国际谈判的失败。可以说,国家在国际合作中的制度选择往往是国内斗争的延续。因此,应当将国际层次与国内层次的分析相结合。从国内政治角度看,国际合作中的制度选择受到选民权力分配、国内政治制度以及领导人的个人因素三个方面的影响。
当反对制定国际制度的政治力量在国内政治博弈中的优势较大时,国家倾向于选择软法。国内社会的反对者拒绝某项国际制度的建立,往往是因为决策的制定将极大损害其自身利益。从反对者的角度看,最优的结局是不建立任何形式的规范,而次优的结局却是建立硬法规范。这是因为,首先,制定硬法的严格程序有利于国内社会团体通过立法阶段的辩论与批准程序更多地参与到造法过程中来,这将增加其影响制度建立的机会。其次,即使硬法生效后,国内的反对者亦可以通过正当程序对其提出审查与修正要求,以便自身的利益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相反,国家则倾向于选择软法的形式,将政治压力隔离在政策过程之外。④Kal Raustiala,From and Substance in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The American Journal Internations Law,2004,Vol.99,No.3,p.597.一方面,软法的立法程序简便,通过国家元首与部门首脑的同意或签署即可产生,避免了国内社会团体通过民主途径阻碍国际合作的实现。另一方面,软法可以避免产生具有可执行力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遵守协议的空间较大。在极端情况下,国家甚至可以选择退出机制,以减少协议对自身的束缚。此时软法是首要的妥协工具。
政策制定权在国内行为体间的分配取决于国内的政治制度。权力如何分享决定了谁的偏好将最终主导政策的制定。民主国家中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的制度关系对国际合作的制度选择亦产生重要影响。当某项议题采取硬法的形式将严重损害国内强势集团与社会团体的利益时,这些团体会向其立法部门施加影响力以阻碍硬法的建立。此时行政部门的决策者即政府就会选择软法以减少来自国内的制度阻力,同时最大程度地实现国际合作,亦可以规避强势的利益集团日后凭借硬法的严格程序对其进行审查与修正。以2009年《哥本哈根协议》(Copenhagen Accord)的签订为例。当时奥巴马政府正积极推进“绿色新政”,企图通过新能源产业振兴美国经济。但是国内的利益集团依然惧怕全球气候谈判对温室气体排放的限制会制约国内经济的发展。此时即使奥巴马政府的谈判代表在国际谈判中签署有关全球气候治理的多边条约,亦很难在国会获得批准而因此失去意义。最终美国政府选择了《哥本哈根协议》这样的软法性质的文件。
此外,领导人的个人因素亦是国内政治对国际合作制度选择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看,个人的偏好与政府的公共选择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政府官员出于获得连任机会或者筹集竞选资金等自身利益的考虑,通常会向其支持者承诺一定形式的回报。官员如果承诺以硬法的形式满足需求者的利益,这一承诺的可信度就是很高的,但是亦会为此支付高昂的政治成本。此时,精确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承诺,具有很大的制度优势。选择软法,一方面,竞选者满足了当下支持者利益需求,另一方面,未来的国际形势无法预知,在遇到激烈的利益分配冲突时,官员所领导的政府亦可将政治损失最小化。2009年年中之后奥巴马的民众支持率长时间在50%以内徘徊。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奥巴马所领导的民主党政府在民众中的支持度落后于共和党。一旦发生政府换届,奥巴马的绿色新政将前功尽弃。一方面,当时的民调显示有86%的国会议员反对向高碳排放企业加税;另一方面,国内民众则普遍赞成政府改变当时对《京都议定书》的立场,加入一项新的包含限制美国温室气体排放要求的国际条约。①《奥巴马气候变化政策含义:与振兴美国经济相联系》,载《中国新闻周刊》,http:∥www.cecc-china.org/detail/6398.html。因此出于巩固新政与继续连任的考虑,奥巴马政府在哥本哈根大会的谈判中选择签署软法性质的文件。
四、结 语
在国际合作的制度选择中,所要考虑的问题还有很多。一方面,软法的制度缺陷与功能优势同样明显。违约成本的降低使得国际社会对国家遵守承诺的信任度降低,国内政治干扰国家坚持自身政策的机会增多。灵活的内容与简便的生效程序为国家提供了逃避责任的机会。另一方面,“国际关系可以被看做向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发展的复杂而变化不定的各种趋势的混合。”②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81页。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合作中,制度的发挥需要不同的语境,每一项议题亦都有着不同的特征。缔约成本、主权成本与国内政治的变量分析需要与更为具体的实践相结合。例如,通常,经济领域的主权成本较低,国际制度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间认同的影响。但是从经济领域的内部看,主权成本则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多样性。国际运输与食品贸易的主权成本相对较低,金融监管领域的主权成本则相对较高。经贸领域的制度合作多采取硬法形式,金融监管领域则由于受到问题领域的敏感度及瞬息万变的金融形势的影响而多采取软法形式。同时,主权成本亦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对于那些幅员辽阔、政治集权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协议的主权成本较高。但是通过技术的革新,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比重下降,主权成本则会降低。
此外,当加入条约的获益高于主权成本时国家依然会选择参与到此类硬法机制中来。例如,《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中所设计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虽然改变了以往国家通过主权豁免规避纠纷的历史,将主权国家送致各种仲裁机构与跨国审判机构的被告席上直接面对精明的投资者。但是出于获益的考虑,许多国家仍然希望加入到该协定中去。可见,国际合作中制度选择的动因考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法律发展的中心不在立法、法理,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③埃利希著,叶名怡、袁震译:《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国际社会行为体的价值与利益呈现更加复杂的多样性,以往的以国家为中心的主权协调模式已很难适应国际社会快速发展的现实。软法虽然仍处于起步阶段,且许多理论上的争议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软法已不仅仅是通往硬法的过渡形态,国际社会行为体亦可以通过其独特的“契约”价值实现更多的合作目标。
[责任编辑 李晶晶 责任校对 王治国]
D9
A
1000-5072(2016)05-0120-09
2015-04-20
韩书立(1987—),男,江西九江人,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