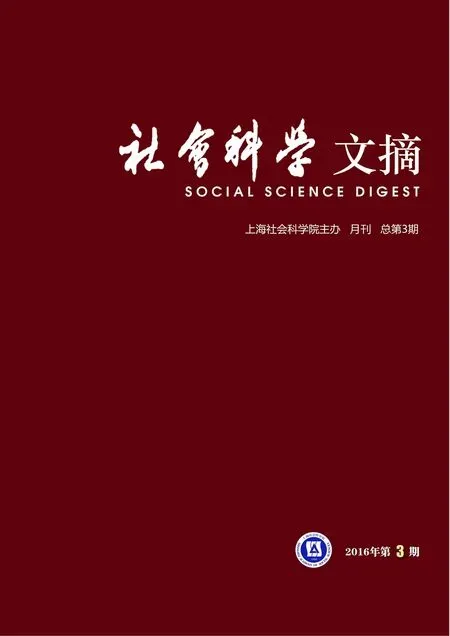“汉学主义”引发的理论之争
文/顾明栋
“汉学主义”引发的理论之争
文/顾明栋
“汉学主义”是一个关于汉学、中西研究和中国知识生产的理论,也是一个主要由国内外中国学者提出的文化批评理论。由于“汉学主义”理论的最初灵感来自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再加上早期的“汉学主义”实践基本遵循了后殖民的路径,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会以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为理论参照系对“汉学主义”予以审视,并据此对“汉学主义”理论的不足和有待改进之处作出批评,这些批评意见对“汉学主义”理论的完善和进一步发展具有不可多得的建设性作用,也引出了这样几个值得认真反思的理论问题:“汉学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不是后殖民主义?研究范式是不是二元对立的东方主义?“汉学主义”的提出者对东方主义的局限有没有自觉反思?“汉学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是什么关系?“汉学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术理论?究竟有没有不同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创意?汉学和中国知识生产应遵循怎样的范式?
“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的关系
毋庸讳言,“汉学主义”是汉学和中西研究领域受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启发而产生的一个概念范畴和批评理论,但“汉学主义”不是东方主义的翻版。像东方主义一词那样,“汉学主义”是一个含义多元而且容易令人混淆的概念。根据笔者对现存的理论和实践的观察和归纳,这一概念可能涉及8个方面:(1)一个从外部对中国和中国文明进行探索的知识系统;(2)一个由对待中国的意识形态所操控的一个知识处理系统;(3)是中国知识生产中的问题性;(4)是一种对汉学研究中的问题进行批判的理论;(5)一种由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分子共同创造的智性产品;(6)是中西研究中被异化了的知识和学术;(7)是中西研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转化为知性意识形态的产物;(8)是一种自觉反思、提倡尽可能客观公正地生产中国知识的批评理论。这8个方面可以归纳成两大类:“汉学主义”现象和“汉学主义”理论。
“汉学主义”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1)前期阶段,其发展深受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影响,重视对中西研究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批判和研究;(2)后期阶段,其发展扬弃了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力求超越政治意识形态批判,反思造成汉学主义现象的内在逻辑,强调政治和学术的分野,提倡尽可能客观公正的知识生产方式。汉学主义的理论基础不是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而是“文化无意识”和“知识的异化”。两个阶段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前者的批评实践和理论探索就没有后者对东方主义的超越。即使在当下,前期的意识形态批判路径仍然有着不可小觑的价值,而且国内外不少学者沿着这一路径继续不断地做出令人钦佩的成果。比如,2012年,西方学者丹尼尔·武科维奇就按照东方主义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发表了专著《中国与东方主义:西方的知识生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由路德里奇出版社出版,该书已有中文书评。
“汉学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东方主义的批评方法,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路径,不少“汉学主义”的批评研究也常采用。对这种以政治意识形态为理论导向的研究,不少学者颇有微词,认为其偏狭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路径正是“汉学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短处。我们必须承认,前期的“汉学主义”理论的确把西方汉学,特别是“广义汉学”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但这一观点在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说“汉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主要指的是 “广义汉学”。更重要的是,有学者之所以认为把“汉学”说成意识形态没有根据,是因为其所理解的意识形态是狭义的意识形态,即政治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可以说是现代理论中最复杂而又令人困惑的概念之一,其定义和涵义有好几种。我们通常使用和接触到的基本上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左翼思想家的思路而做出的政治性定义。马恩把“意识形态”简要地定义为“虚假意识”,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思想和制度等以看似正确其实是虚假的方式误导人民大众。因此,这种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是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的概念性基础之一。但人们常常忽略,意识形态的概念并不起源于马克思,也不仅限于政治和权力。雷蒙德·威廉斯在其对该词追根求源的研究中说,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特定群体或利益集团的一系列思想的看法与意识形态作为虚假意识的看法一样被广泛使用。如果我们把“汉学主义”理论所说的意识形态不是看成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掩盖社会现实真相的虚假意识和社会实践,而是视其为产生于汉学研究领域、并左右着学者们在生产中国知识时的一系列主张、信念、见解以及治学方法,以此评价西方汉学而将其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并不离谱。一切知识皆有意识形态,只是程度、性质、功能不同而已,广义汉学的政治意识形态成分多,而狭义汉学较少带有政治意识形态,但并不是没有政治意识形态,而是更多受制于知性意识形态(即治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等),这种意识形态同样不利于中国学术和知识的生产,这就是本人认为“汉学主义”可以在特定情况下被定义为“认识论的意识形态”的理由。本人在《汉学主义》一书中以不少案例表明知性意识形态是如何导致一些没有政治偏见的学者生产出歪曲中国文化和传统的知识。
“汉学主义”有没有走出东方主义?
批评“汉学主义”理论的一个观点就是,“汉学主义”并没有超出东方主义的范围,这一看法对于早期的“汉学主义”,特别是 “汉学研究的东方主义”来说比较贴切,但对于后期的“汉学主义”就格格不入了。在此仅从《学术月刊》2013年第4期的一篇文章中摘出有关“汉学主义”的理论基础的阐述以说明问题:
“汉学主义”理论的概念基础既非东方主义,亦非后殖民主义,而是由另外两个概念相结合而形成的概念性基础。其一是“文化无意识”,它包含一系列次无意识:“智性无意识”“学术无意识”“认识论无意识”“方法论无意识”“种族无意识”“政治无意识”“语言无意识”以及“诗性无意识”等。这诸多无意识组合而成的大范畴构成了“汉学主义”研究的概念性基础,它广泛涉及的所有问题,并将对“汉学主义”的认知与东方主义及后殖民主义区分开来。其二是“知识的异化”,就异化的知识而言,“汉学主义”可视为汉学和中西知识的异化形式。“文化无意识”和“知识的异化”这两大概念的结合构成了一个新的概念框架的理论核心。根据这一概念核心,人们可以用大量的个案分析对文化无意识进行理论探索,并可探讨“汉学主义”是如何演化成为中西方研究中的异化知识。总之,文化无意识是“汉学主义”之源泉、动力,而汉学和中西方研究的异化知识则是“汉学主义”之结果。
在理论层面,文化无意识和知识异化的结合构成了“汉学主义”的理论基础;在实践层面,造成“汉学主义”现象的是学者的文化无意识。因此可以说,文化无意识是造成汉学主义现象的动因、源泉,而“汉学主义”现象是汉学研究和中国研究受文化无意识支配而导致的知识异化。总而言之,“汉学主义”不仅要超越东方主义的二元对立范式,而且要摆脱后殖民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路径,这一点正是拙文《后殖民理论的缺憾与汉学主义的替代理论》的核心思想:“后殖民理论虽然提供了发人深省的新颖视角,但并不完全适用于跨文化研究、特别是中西研究中出现的种种现象。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国学界提出了“汉学主义”这一受东方主义启发、但又有别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的替代理论。对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的政治层面进行反思,可以了解后殖民理论在跨文化研究方面的不足,探讨意识形态和政治批评如何影响学术的客观、中立和公正性,也可了解“汉学主义理论”为何是一个可以弥补后殖民理论之不足、促进文化自觉和学术创新的替代理论。”这段话表明,笔者不仅看到了东方主义的不足,也看到了后殖民理论的缺憾。
“汉学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
除了东方主义,有人认为“汉学主义”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是后现代主义,而且,正因为如此,“汉学主义”有着后现代主义不可克服的哲学问题:“提出‘汉学主义’的学者不仅在知识上有不足,在跨文化理论的运用和分析上也有着明显不足”;他们的“观点其实并无任何新意,不过拾起了西方后现代史学的话语而已”。
遗憾的是,批评者由于对后现代理论的发展状况了解得不够全面,而且采用的基本上是二手甚至三手资料,因而似乎并没有认识到后现代理论的复杂性和微妙之处及其对当代学术的指导意义。
首先,并没有能准确把握后现代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哲学动因。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在哲学上是自康德把人类的理性推至极致以后的强力反弹,后现代的先驱尼采和后现代的哲学奠基理论家海德格尔都是对理性主义强调精神的超验作用而忽视感性的现实和具体人生的不满而另辟蹊径,倡导对当下的把握和体验感性的人生。批评者认识到后现代主义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反叛,但却简单地把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说成是福柯所代表的哲学:“福柯的哲学所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是对19世纪以来西方实证主义的解构”,显然没有看到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来自尼采和海德格尔。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批评者仅引用一位汉学家的话,就认可其局部判断可以涵盖后现代主义,进而说明“汉学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有问题。那位汉学家指出:“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认识论立场是客观现实并不存在。自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只有心灵的概念才是真正的存在……总之,心灵并非由现实存在决定,而是心灵决定了现实存在。”这显然并不是后现代主义的主流思想。那么,后现代主义的主流思想是什么呢?我们得从真正从事后现代研究、而且是公认的权威学者和思想家那里去获得。最早研究后现代主义而且是公认的权威是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他在那已成为后现代纲领性文献的《后现代状况:一份有关知识的报告》里指出,现代科学知识的权威性基于一种“元叙事”,又称 “宏大叙事”,即可以对所有事物进行解释的一种“叙事的叙事”。而在后现代,叙事已经产生危机, “宏大叙事”已经破产,甚至连自然科学的叙事也失去了往日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因此他把“后现代”简单定义为“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并指出因为叙事是传统知识的典型形式,后现代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还原知识作为一种“叙事”或“话语”的本来面目。列奥塔的书只有区区80余页,我找遍全书,也找不到所谓“客观现实并不存在”“只有心灵的概念才是真正的存在”之类的观点。我简要回顾后现代主义的核心理论旨在说明,所谓后现代强调“只有心灵的概念才是真正的存在”“心灵决定了现实存在”等言论不是后现代的核心思想,倒更像是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康德的“纯粹理性”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简而言之,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对用所谓科学、真理、普世、客观性等概念构建起来的宏大叙事的怀疑,而不是否认存在真理、历史事实和知识,后现代在还原了那些所谓“客观”真理和知识不过是“叙事”的本来面目以后,因而强调研究具体和局部知识的叙事,提醒人们更加注意知识产生的历史语境以及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文化逻辑的社会基础。
公平而言,解构主义理论由于集中关注语言、文本,而被人批评为有忽视历史的倾向。于是,新历史主义就应运而生了。新历史主义其实是对解构主义的偏颇之处的修正,但是,像许多学者那样,批评意见对后现代史学理论与解构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误读:“德里达提出文本之外别无它物,由此,历史全部化为文本,而文本都是语言的符号,真实的历史消失在语言符号之中。”误读错在什么地方?作为一种后现代理论,新历史主义者对解构主义是持批评态度的,他们批评解构主义对历史的关注不够,但并不是抛弃解构主义重视语言文本的做法,而是把语言文本与历史研究重新构思成一种能动的辩证关系,这一点反映在新历史主义的核心观点之中。新历史主义的首倡者斯蒂芬·格林布赖特引用一位新历史主义者的话把新历史主义的核心观点总结成一个简单明了的公式:新历史主义的“目的是同时捕捉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 这句会可以转换成另一种明白易懂的说法:“历史是文本的,文本是历史的。”误读只注意到“历史的文本性”,而没有注意到“文本的历史性。”因此,新历史主义并不是拒绝承认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而是强调这些历史事件在撰写历史著作时被有意无意地根据某种主观意识而编织成历史叙事的情况,实际上,这种理论思路不是否定历史真相,而是力求尽可能接近历史真相。
对后现代理论和“汉学主义”理论的误读可能不仅是因为信息不全,还有其哲学根源。这就是在哲学层面上虔信知识和真理的客观性:“汉学作为西方学科的一支,其知识的客观性是毋庸置疑的”;汉学“作为知识体系有着自身要求的客观性”,并认为有“无功利的纯粹学术活动”。对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潮流轻视历史,过分强调语言的作用,我也认为是剑走偏锋,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很不可取,但虔信知识和真理的客观性,在知识哲学的研究已高度深入的当下,似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仅相信学术和知识是相对中立的,因而具有相对的客观公正性。因此,本人在《汉学主义》一书中一再强调学术和知识的相对中立性,并把“汉学主义”的终极目标定位为“尽可能科学、客观、公正地生产有关中西文化的学术和知识”。在这一表述中,“尽可能”三字十分重要,因为这不仅认为没有所谓的“客观”知识,而且含有辩证的意思:虽然没有绝对客观的知识,但有相对客观的知识,而且通过不懈的研究,我们可以不断接近客观真理。
“汉学主义”的理论基础既不是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也不是后现代主义,而是借鉴了多种现代理论重新构思的新理论,即上文所说的“文化无意识”和“知识的异化”相结合的反思理论。后现代理论被一些学者推向极端,甚至走向诡辩和忽悠,这是不可取的,但后现代理论并没有走向穷途末路,而是深入到当代学术研究的方方面面,极大地影响着知识生产。当然,后现代理论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警示人们注意知识的主观叙事性,从而不轻易接受所谓科学、客观、公正但实质上是受制于某种意识形态而产生的“知识”或“真理”;另一方面,它也给了一些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人一种十分好用的知性工具,可以解构甚至曲解特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某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事业服务。也许,在“尽可能科学、客观、公正地生产有关中西文化的学术和知识”这一理念上,“汉学主义”理论可以和批评者们找到共同的认识论基础。我相信,有热心关注“汉学主义”发展的学者,“汉学主义”理论一定会得到进一步深化,并对汉学研究、跨文化研究和中国知识生产乃至学术范式的革新做出有益的贡献。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摘自《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