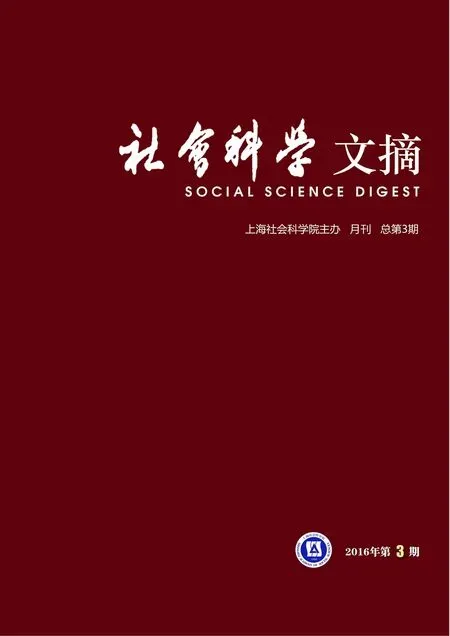社会学理论下的“民族电影”
文/[英]菲利普·施莱辛格 译/王继阳
社会学理论下的“民族电影”
文/[英]菲利普·施莱辛格 译/王继阳
民族与社会沟通
卡尔·W·多伊奇(Karl W. Deutsch)清晰地阐明了一个最明确和广泛的关于民族主义中沟通的角色的理论。在其第二版《民族主义与社会沟通》(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一书的引言中,多伊奇强调与当前争论有关的一个基本主题:他观察到民族国家是“处理事务的主要政治工具”,并强调,考虑到民族的弹性,超越民族的整合具有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多伊奇理论的主要命题是:“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本质——是个体之间沟通的互补性或者说是相对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就好比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只不过规模上更大罢了。”多伊奇认为“人”是民族形成的基础。反过来说,这与“民族国家地位”不同,即利用政权来追求一个群体的凝聚力及其身份认同的一致性。尽管没有清晰命名,这一理论蕴含这样一种理念——那就是“无国家的民族”(the nation without a state)——这一理念既作为一种分析范畴,又作为一种旨在现存的国家国际体系中重新定义民族自治权的政治目标,近年来变得日益显著。多伊奇认为,对国家权力的使用最终依赖于“相对协调和稳定的记忆、习惯和价值结构”,而这些反过来又“取决于社会从过去到现在及同时代之间的沟通能力”。
社会沟通理论包含聚集社会文化群体的方法,以及内聚力形式如何影响制度和社会文化互动。沟通的整合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生产出社会封闭。争论的核心就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强烈地被其社会性沟通互动结构所限制这一观点:“人们通过这种沟通效果和其成员获得的沟通能力的互补性而被从内部凝聚到了一起。”民族性因此具有沟通能力和归属感的客观功能。
高雅文化、想象的共同体与平庸民族主义
多伊奇关于社会沟通的潜在概念——如果不是他理论上的习语——充其量一半被认为紧密依托于最新的著作,如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著名的《民族和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以现代主义的视角对民族主义概念的原则进行了阐述。盖尔纳认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工业化不可避免的结果,伴随着复杂的劳动分工。工业社会所创建立的社会关系意味着,为了有效运转,人们原则上需要能够做任何事,这就需要“通用的培训”。这种实际知识的传递需要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化的教育体系,适用一种标准化的语言媒介。就是这一过程引发了不可避免的“政策和文化之间关系的深层调整”,即民族主义,“人类群体组织成为大规模的、集中教育的、文化同种的群体”盖尔纳的理论把工业化的解释模型与典型的多伊奇社会沟通概念联结起来。
盖尔纳认为,文化指的是“特定群体各种风格的行为和交往”,在当代世界中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呈现。对这种政治形态中的成员来说,“文化现在是必要的共享媒介”。文化的边界被民族文化所定义,传播着一种文明(教化)的“高雅文化”,是国家教育系统的关键介质。因此,民族文化被官方文化所广泛定义。这一理论较少关注民族内部的不同和冲突的来源,而更关注是什么让民族得以凝聚。因此,如同多伊奇的理论一样,盖尔纳主要关注民族文化如何被创造,而不是如何维系和复兴,他同样强调被民族国家保护的文化的独立性。因此,尽管多伊奇只是顺便被提及,但是作为盖尔纳的跳板来简略思考媒介在民族文化中角色,实际上他的影响比看起来要深远得多。
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相呼应,盖尔纳部分地认同媒介即讯息,但是这一准则考虑到“语言与风格”而被修改了。所谓“语言与风格”即常见的行为准则如何引领观众去意识和理解到,他们是某个集体(通过那些常见的行为准则所构造出的集体)中的一员。媒介因此承担起一个分类体系的功能:公众对民族空间的普遍认同便被认为是这种文化体系形式产生的影响之一。媒介是分界的标志物,与“盖在文化上的政治屋顶”密切相关,并使那种文化进入一个民族国家之中。
这种说法夸大了一点。“语言和风格”不仅仅是用于传播它们的媒介,它们与“内容”方面的问题也密切相关。这是文化产业所生产出来的基本要素,也是电影和电视业政策的核心问题。国家对于自身“民族”内容的态度通常在国际文化贸易中是非常重要的,并且经常体现在民族交流政策中。因此,盖尔纳对社会沟通理论的演绎,重现了多伊奇对沟通共同体内部因素的专注,而不去考虑引进外部的因素和思考外部因素会如何影响内部因素。它忽略了那些能在实质上决定特定民族身份的差异性。
内在论的观点也贯穿了近几年另一个重要的文本: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en)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该书已明确地为大多数近期民族电影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开端。在解释欧洲民族的出现时,安德森和多伊奇一样,甚至比盖尔纳更强调交流媒介在民族意识形成中的重要性。“积极的意义上,半偶然性地但是爆发性地,在生产力、生产关系、技术交流和人类语言多样性逐渐消失之间,使新的社区成为可想象的。”然而对于盖尔纳的论点,国家的教育系统产生的文化姻亲以及聚贤,安德森主要的论点是“印刷语言产生了民族主义,不是一个特定的语言本身”。因此,强调的是在假定合适的物质条件下,在想象共同体建构中传播媒介的重要性。
依安德森所说,“印刷语言”是通过书籍和报纸市场传播使特定方言标准化的方式。他的描述绝对是古登堡式的:移动影像带来的影响并没有被说明。机器复制的印刷语言整合了语言交换领域、固化了民族语言,创造了新的权力成语。安德森称,“民族主义叙事”与将“历法意识”作为组织原则的报纸,是塑造民族意识的两种关键媒介。通过协调时间和空间,这些甚至能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就阐明一个想象的民族共同体。
安德森思索过民族故事是怎样经过人口普查、地图和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在后殖民地国家被讲述的。虽然,不是安德森故事中的一部分,但是移动影像对形成后殖民地国家的重要演变作用,已被他人所强调。尽管安德森没有引用多伊奇的论述,他的方法依然很明显地处在社会沟通理论的框架中:想象的共同体处在社会文化和民族国家的沟通空间中,它是民族形成主要利益的内部过程。
安德森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争论以一个极具特色的解读方式被迈克尔·毕利希(Michael Billig)采纳。然而,毕利希强调的民族主义陈词滥调,就是把民族主义纳入日常生活的一些仪式和习惯这个可论证的命题。
毕利希认为,在当代世界,所有人只是把所在国家的代表性事物印入脑海。他们国家的国旗每天都在公共建筑物前飘扬,但是大部分都被当成装饰品;新闻报道将一些大事件分类成国内事务,而与外国的报道区别开;天气预报强化了人们对政治地理学的认识;体育英雄们体现出民族美德,调动了集体荣誉感;危急时刻,尤其是战争,政治领导人要进行爱国主义演讲;通过民族语言和历史的传达,人们滋生了共同体意识等等。这就是民族认同常规的、不引人注意的、不断重复的内在支撑。与盖尔纳和安德森一致,毕利希的分析填补了“沟通互补性”的空白,并且强调要牢牢把握住如何对世界进行分类。但值得注意的是,毕利希不像其他前辈一样,相比于民族是如何形成的,他对如何维系民族更感兴趣。
民族的边界与民族电影的范围
电影研究关注电影在民族中所扮演的角色,必然是内在式的,主要关注的是移动影像的生产、传播以及消费怎样构建了民族的集体性。然而,这种内在主义必然被把外在性作为一种塑造力量的认识所调和。的确,民族性实实在在地被好莱坞产品进口到本国的文化压力所影响,构成了民族电影在当下的问题。这些对民族理念的外部挑战被解释为文化、经济、政治甚至是意识形态。对于苏珊·海沃德(Susan Hayward)来说,她认为如何描述民族电影的这个问题深深根植于政治文化的发展,根植于“关于一个民族多样而特定机制的神话被创造”的过程,被国家主义范式所深刻影响:“电影的作用在于一个民族文化的融合……电影赋予一个民族语境,而后围绕一些概念建构一系列联系,首先,是国家与公民,然后是国家、公民与其他因素……一部‘民族’电影不可避免地被概括成一系列围绕两个基础观念的阐述,这两个基本观念分别是:同一性与差异性。”
在这种建构中,民族被视为单一的,特定国家的电影生产研究审视着“民族电影”。民族电影可通过对电影本身的分析、电影所引发的语篇,及体现在档案和展览中的遗产来研究。海沃德的观点深受法国塑造民族历史的自觉偏好和与好莱坞长期明确的对抗所影响。
“同一性”的概念强调了内向聚焦,而“差异性”的概念通过对比和比较,指明了民族电影的外在因素。对于海沃德来说,分析法国民族电影的可行办法就在于强调电影生产问题,以及包含在电影生产中的鲜明的电影文体论。莎拉·斯特里特(Sarah Street)在描述英国的情况时,提出了相似的对民族电影实用主义定义,也是最容易实现的,即强调本土生产,也就是理解为“在英国注册的电影”,考虑到在资金、合作制片人和电影制作创意性人才等方面的多国混合因素,这个定义有很多含混之处。然而,这种简化被英国风格(Britishness)的接受所调和,成为“一个在日益国际化、互文多样性的现代电影流派中的元素”。
基于相同的领域,安德鲁·西格森(Andrew Higson)提出,民族身份认同和民族电影都应该以一个过程化的视角来看。他提出,我们可能会用一些特征来界定民族电影,包括:电影产业和商业,在展示、消费以及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方面,在文化政策制定和评论界所使用的定义等方面,最后,特别是对(国家)特定流派的支持。西格森接着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如下描述:
“电影经常有助于展现一个国家的民族性。通过植入电影体验的基本框架,这类电影以戏剧化地表达人们当前的恐惧、焦虑、快乐和愿望,构建了一个将同一个民族的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想象的纽带。因此,一个多样和互相敌视的群体的人们认识到他们是一个有着共同文化的单一体,并与其他文化和共同体对抗。当然,这一点从来没完全成功过。”
当西格森提出应该如何定义英国民族电影并主张电影文化提供一种可以划分群体的方式时,他也明显持有政策制定者和民族文化知识分子所推崇却无法实现的文化保护观点。与海沃德相反,西格森让这种争议与电影的生产脱离,强调观众如何消费的重要性。于是,所有的问题都演变成了“观众是如何通过多样的国内外影视作品建立自己的文化认同”。
这一论点也有反驳者。例如约翰·希尔(John Hill)区分了保护民族电影产业的经济学观点和支持民族多元呈现的文化观点。他认为后者更需要认真关注,因为全球政治经济交流设定了好莱坞以外电影生产的贸易条件。他认为如按照西格森诉说的,为了强调消费而提升观众理解观看方式的重要性,是对民族电影概念无法成立的利用。希尔特别谈到了英国的情况,认为西格森的方法将会使好莱坞电影被划分为英国民族电影的一部分,仅仅是因为好莱坞电影被英国观众所消费。他反驳说,区分“在英国的电影”和“英国民族电影”很重要。保护后者要走向规范化,并认为民族电影应该代表文化的多样性,它没有必要承担民族主义的使命。
希尔指出,关于“民族”的同一化观点在面对英国日益明显的多样性的情况下分崩离析了。黑人电影和苏格兰及威尔士电影制作对狭隘的英国风格(Englishness)概念构成了挑战。希尔的观点可以解读为是一种请求,目的是保持批判性文化话语在思考电影在民族公共空间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与时代潮流相一致,但是将文化生产降低为经济问题来考量,的确严重限制了争论的可能框架。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承认消费如何可能构建集体主义身份并不需要放弃关于民族电影生产中文化价值的争论。相反,它提供了另一个平行的理解电影在民族空间中如何伴随着标准化和经济化观点运行的模式。这一观点被皮埃尔·索尔兰(Pierre Sorlin)所发展。他认为电影在代际的消费是理解意大利民族电影的关键,“看电影的四代人建构起一个巨大的对不同声音和影像的重写本,国内的和国外的,并用这些在意大利,他们所在的特定地方,来组织他们的生活。他们像欣赏国内电影一样欣赏美国电影,但是他们吸收和重新使用这些素材的方式是他们自己的,这就是他们挪用不同种类的电影素材来建立意大利民族电影产业的方式”。
这条评论反映了文化是天然融合的。与之伴随的是,许多当代的拉美人试图在文化和沟通理论方面思考文化依赖的本质。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对文化主导问题重新理论化下,对全球文化的挪用和重组的争论。
索尔兰概述了捍卫民族电影计划背后的本质上模糊之处,因为他发觉,一方面,“在它20岁前,电影延伸超越了民族前沿”,但是另一方面,“电影一直被认为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比制造和发行电影的机构和公司更复杂,但从根本上来说,仍是由民族传统所控制”。
当代对于“民族电影”的分析与关于民族的社会学已经确立的思考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它们同样是从根深蒂固的假设出发。社会沟通思考是对一个主权国家、世界民族国家文化地理学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表达。这是电影研究的基础,它在很大程度上衍生于对于民族主义和民族身份认同的社会学争论,并以此作为民族电影研究的必要起点。其主要兴趣在于民族电影现在是或应该是什么,这与建立民族集体性的政治问题明显相关。民族电影的主要任务就是定义和描述民族与电影文化之间的关系。移动影像不可避免的跨国流动已经成为关注的前沿问题,因为——除美国以外——电影研究总是在努力克服文化依赖造成的后果。
(《社会学理论下的民族电影》The Sociological Scope of National Cinema,选译自《电影与民族》Cinema and Nation,主编Mette Hjort、Scott MacKenzie,伦敦、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0年,第17页至第28页,翻译时有删节;王继阳系东北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摘自《电影艺术》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