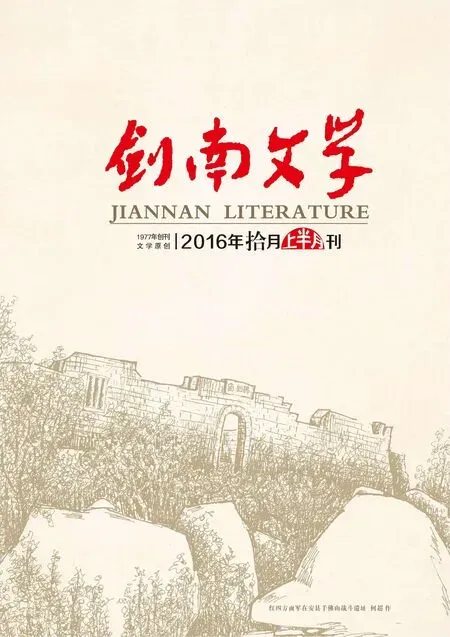温馨一刻
□吴春华
温馨一刻
□吴春华
走进这条街,男人的烦恼便不翼而飞。
这是条落伍于现代都市等待改造的不起眼的小街。小青瓦穿斗木结构的板壁房串连着,露出的窄窄的街心,全挤满了小商贩们,而且青一色的出售一些女人感兴趣的商品。于是引来了高贵的、中等水平的、下层的土著女人们选购各种所需物品,高兴而来,满意而去。这道亮丽风景自然吸引了男人的眼光,夹在女人们中消烦化食。
他早就知道这个极好去处,但还没有亲自光顾过。今天来此,是因为她住在这条小巷的一条支巷中,这条街又是必经之道。他从人群中穿行,女人们的特殊的馨香让他晕眩,男人们那种猜忌眼光让他不安。其实,他无意于街市的任意一位翩翩女郎,心中只放了一个人,一个他马上就要见到的女人。他的手不自主地捏成了拳头,手心出了汗。他想她不是喜欢在这条街闲逛的女性,不是见惯不惊,而是一种完全自然,不饰雕琢的气质使然。脑中浮现的黑发披肩、从来都素面朝天的她像一阵清新的风令他神清气爽。
迈着轻盈的步子跨上六楼顶层时,他发现大门紧锁,怎么还没回来?就站在这儿等等吧。从来就很谨慎的他四下里一瞧,向楼顶间到天台处跃了几级。习惯性地把手伸向牛仔裤袋。点燃了
一支烟,惬意地呷一口。抽烟的历史从无所事事的高中开始,天资聪颖,记忆超群的他无需像其他学子般埋头苦读,上完课便和几个哥子喝酒,并慢慢地学会了吸烟。吸烟是种很好的享受,不管在他高兴时,忧伤时,还是闲暇时,他总忘不了这个形影不离的“朋友”。上了大学再分配到小城一机关工作时,他的每日烟量达到一包。身边发生的每件事,心中掠过的每段情都会让他在烟雾中过滤,直到他明了世事,待人接物达到无可挑剔的练达。而立之年就是局里的中层干部,这在小城并不少有,但与他们的交往中发现,自己的睿智、成熟、常识仍是出色的。“优秀的男人”——他吐出一口烟,嘴角挂了一丝自得,很快地为自己下了结论。

还不回来,半截烟已在他的食指弹点下烟灰纷纷扬坠落中耗尽。他看了看传呼机,九点四十分,离出办公室“办事”快一刻钟了。
狠狠地吸了一口烟,思绪又缥缥缈缈地回到一年前的夏天,那个和她相识的夜晚。几个好友在护城河边一座阁楼上品茗,后到的家伙带来了位年轻的女士,一米六左右的个子身体单薄,清秀的面庞、齐肩的秀发。朋友给她介绍他,当听到他的名字,女孩笑了,说看过他写的文章,很不错的。坐在对面的他心底升起一股自豪,但不露声色的习惯只让他矜持地向女孩略颔首,视线落在她抿嘴时一闪即逝的酒窝上。随后的谈话热烈起来,男人们总是有些异性时显得亢奋,凡事发表一通自己的高见,朋友们称赞了不说,更重要的是博得女性青睐。唯他,平静地吸着烟,适时地插入两句,语调平和,姿态稳健,令这位女孩对他偶尔深深地盯一眼,好像他的话最有份量似的。
以后再见过几次,他们熟悉起来。朋友们讨论着办个实体,赚几个钱显示一下大家的经济头脑。在大家决意开家茶楼后,一友人问她,你愿不愿意喝我们十元一杯的茶?她端坐于竹椅,带了满脸的天真和虔诚回答说,我愿意。朋友们都觉得这个小妹妹的回答象是在教堂里的应答
声,纷纷效仿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凝重。她满脸窘迫,不明白这回答有什么好笑。他深觉她的单纯、稚气,心底有一丝怜意,觉得她可爱起来……
再后来,他得知她婚龄竟长达三年,丈夫在政府部门工作,因为她不喜欢带孩子,所以仍很自由地过着平等的两人世界生活。她对他的话多起来,说了许多闲事,发了满腹牢骚。而他总是兄长般地抚慰。沉静的外表,恰当的谴词,绝对的真诚使他在她心中越来越重要。他开始接到她打的传呼,没有事办,只是问候近况或心情。他总遵守自己的原则,有呼必回。被人惦记是一种幸福。而他厚重的男中音无疑会给她传过去一个信息,一个他与她同在的信息,这会给她一点快乐,带着恬静的青春的快乐。
楼下隐约响起了脚步声,他马上扔下烟蒂,双手在腰间埋了一下才穿第一次的浅蓝色的长袖体恤,轻轻地迈下台阶,站到了那扇久等未开启的淡黄色的木门前。
当她顺着又高又窄的楼梯爬上六楼时,遍体虚汗。气喘吁吁。她一只手按了胸口,又惊诧他的早到,眼睛里充满歉意。
“对不起,我去天然气公司报了气表。我们总是忘记把度数抄在门外。”
“我也刚来,累着了吧?”他微笑一下说。
这楼梯设计得真差劲。她摇摇头,把门打开。
这是一套极普通的两居室套房,走进客厅,他一目览过,粉红色与白色相间的矮直柜上放了一台21英寸的长虹彩电,转角黑沙发前立着一个极精致的褐色的玻璃茶几,茶几上一个乳白色的小茶瓶上插上了一支茶蕾儿。简单,他心里想着。
快请坐,她从厨房里提出水瓶,边泡茶边招呼边站在房中间的他。
“他到哪儿去了?”他明知故问。
“上班呀!”她一脸的自然,坐到了他的斜对面。双手从茶几下端出一盘李子,用小刀削起李子皮来。
“我不吃。”他看着她极富线条的脸,小巧而挺拔的鼻梁,说。
“吃一个嘛。”她头也没抬,声音轻得像蚊子在叫。一进门,她才发觉自己不知如何面对他的造访,便找这不值一削的细活儿认真地做起来。
很紧张吗?他看出了她的手在微微颤抖。
嗯,有点儿。她终于削好李子,递给他,眼睛很自在地轻轻看了他一眼。放下小刀,她的十根手指绞在了一起。想着早上他要来坐坐的电话,问道:
“有什么事吗?”
“没事就不能来吗?”他反问道,眼里充满温柔死死地盯着她开始发窘的脸。
“哦,不,不是。”她飞快地看了他一眼,觉得他的眼光异样,便把视线放到那红色的花蕾儿上。
“这段时间,你还好吗?”他还是那眼神,身子微侧过来,把那张黝黑、光洁的大脸面对着她。
“好,谢谢。这两天在耍公休假。”她笑了笑,还是兀自看花。
他再不吭声,一只手自然地搭在沙发上,另只手放到了腿间,只拿眼用心读她。屋里死一般静寂,她感到刚进屋的清凉没有了,浑身有一种无名的躁热和激动,好像全身的血液停止了流动一样,仅仅在一刹那间,她觉得自己必须找个话题。
“你们的茶楼选好地点了吗?”她终于问道。
“选好了。”他淡淡地说。
“什么规格?”
“一般。”他干脆地回答后,右手指尖在沙发上轻轻地敲击着。她看着他长长的手指,发现自己的话题并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只好又沉默了。
她喜欢他的大手,有好几次,有意无意地握手,她都能感到自己并不细嫩,也不白皙的手在
他手中变得细软起来。
她是个单纯的女孩。念书、工作、恋爱、结婚,一帆风顺。幸福这两个字,对她来讲,也不过平平淡淡,顺理成章而已。丈夫宽厚、活泼,只是因为工作关系,经常上山下乡,这无疑给好自由自在玩耍的她一些外出机会。她一直认为,没有爱人的家是不成其为家的,所以,只要他一走,她便会去约朋友玩。跳舞、喝茶、甚至溜冰、打台球,都是她的长项,跟年轻的朋友们一起,她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青春节奏的美好,生活充满阳光。丈夫是个很会欣赏她的男人,两个人的世界总是愉快的,尽管在偶尔,她会产生一点莫名其妙的无聊。
该带孩子了。丈夫曾多次提起,她没有答腔。实际上这两年她已暗地里多次征求母亲的意见,每次都被母亲义正严辞地批评一通。因为她很想两人过一辈子。面对生活的无奈,至今不会炒菜的她无法想象孩子出世后自己怎么承担得起繁重的家务,只好惶惶地避开问题,继续这没有负担,也没有寄托的小日子。
直到认识他和他的朋友们,她才觉得自己太幼稚无知、太空虚,活了二十几年,竟从没想过自己要干点什么。他们年轻有为、健康向上使她有了些震动。她开始沉静起来,许多次丈夫走后,她都钻进书房,在楼下喧嚣的声浪里坐读着电大的课本。
有几次考试后,她打传呼给他,讨论一下自己的答正确与否,他的回答总是让她满意。他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这一点,谁都无法否认。
嘿!他叫了一声,把沉思中的她惊醒了,只见他的左手伸在她的面前,眼里满是期待。她摇摇头,身体向后靠了一下,羞涩地微笑着。他平静地说,相信我,我不会伤害你的。他的手仍停留在空中,毫无收回的意思。她的头轰地一下又热了,手很想抬起来,即又觉得好像有千斤重,狠狠地,她像下了决心,缓缓地将手放到了他的手心。
握紧她的手,他趁势向她靠了过去。他离她很近,近在咫尺。他几乎能闻到她身上女性特有的气息,他的右手顺势抬起,轻轻地将她的头向自己这边一拨,她的头便靠在了他的胸前。他的手再顺势下去,搂住了她柔弱的肩。
看我!他带着命令的口吻对低头害羞的她柔声说道。
她温顺如猫,抬起了头,不得不正视着他那双热烈的、温柔的,一直没有离开过她的那双眼睛。她从没见他这样,在以前,他总是冷静持重的样子。也许是自己的热情鼓励了他,再不,他怎么会这么大胆呢,她暗自责备自己的外向性格。
她的手被揉得像面团一样,贴着他健壮的胸部,她觉得自己心碎了。身体变得轻如软棉,她干脆闭上了眼睛,极力控制着越来越重的呼吸声。
他像是找到了机会,松了左手,整个儿抱住了她。他的嘴唇贴到了她的嘴上,开始全身心的亲吻。
她把舌头伸进了他的嘴,他紧紧地裹了她的小舌,深深地吮吸着,他感到她的两只胳膊蛇一样在身后腰间缠绕。他更用力地抱住她,仿佛要把自己与她融为一体。这种天气里,与她如此相拥,他觉得自己快无法控制,浑身热得像烤着火,呼吸也越来越急促。他的手不安份起来,把她的衬衣从腰带里扯出,一把捏住了她的纤腰。
从彼得大帝开始俄国君王就充满了对蓝宝石的疯狂热爱,著名的“俄罗斯钻石宝库”即使在75%的宝石被盗流入民间的情况下,库存中还依然拥有总重1700克拉大颗粒蓝宝石和总重2600克拉小粒蓝宝石。
她仍在沉醉于他有力的亲吻,脑海里一片空白,太舒服了。她真希望时光在此刻停留,她可以什么都不在乎。
他的手提着她的大腿,想抱她到自己的腿上。可她的腿正伸在茶几下,身体的转动使她的小腿肚带着茶几转了几十度,“砰”的一声脆响,小花瓶倒在茶几上,摔成了碎片,瓶里的水顺着茶几滴到了彩磨石地板上。
她和他都感到十分惊恐,像一对狂奔的马突然发现脚底已是万丈深渊。
猛地推开他,她站起身来,走到阳台上,扯下抹桌布,提了塑料撮箕,把茶几上的碎片和水一起扫到撮箕里,又放在阳台上了。
等她回转身来,他已坐正了身体,微笑着看着她。她坐到他的身边,两双手又握在了一起。重重地,他捏了一下她的手。她转过头去,征询地柔柔地看着他。
我想抽烟,他悄声说道。
为什么?她不解地问,脸上还是一片绯红。
有种情绪,他的话只说了一半。
这是什么花?他看她从茶几上拿起的那支花蕾儿在鼻子边嗅着,吸了一口烟后,他问道。
不跟你说,她扭了一下身子,翘起嘴唇,撒娇似的回道。他懂了,还是又问:
为什么不买盛开的呢?
衰败得太快。你不觉得从花蕾儿开始,看到它盛开,再慢慢凋谢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吗?
倒也是,他点点头,又抽起烟来。
现在怎么办呢?他看了花儿一眼,问询道。
只要有水,它在哪里都可以开放。她挣脱他的手,跑到厨房,用一个细长的玻璃杯盛了大半杯清水端进来。把花蕾儿甩下去,花蕾儿便悠悠地掉下,亭亭地立在杯边,倒煞是好看了些。她傻傻地笑着,一幅很为自己得意的样子,又坐了下来。
他刮了一下她的鼻梁,怜爱地微笑了一下,什么也不说。
她转过身去,双膝开拢,半跪在沙发上,静静地看他吸烟。慢慢地,先前那种狂热消失了,一种宁静在他的烟头闪起,她知道,他和她都不是孩子了。现实里,他们不该面对太多问题,何况,得与失之间,谁能说得清楚:有时,暂时得到,却永远地失去一些东西。何苦为人生增添烦恼。她不知他在想什么,却把自己的心里摸了个透,尽管在感情上,她仍是非常非常难舍的。
他大口大口地吸着烟,并没再看她,他得等到自己完全平静下来才面对她。
当他吐出最后一口烟,把烟头放进烟灰缸,重重地把烟头按熄后,他站起了身,端起烟灰缸到阳台上把烟灰倒在了撮箕里。放了烟灰缸于茶几下,他盯着她,看了阳台一眼,用手向门外指了一下,说。
待会别忘了倒掉。
知道,她觉得他真可谓谨慎小心,这么个烟蒂也想得到。
我该走了,他没再坐下,站到门边向她说道。
好。她跳下沙发,向他走去。她主动搂着他的腰,把头深深地埋在他的胸前,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低下头,嗅了一下她的发香,再用粗壮的手臂抱住她,在她耳边低语:
好了,快十一点了。
她转过头,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极性感的厚唇,一只手在背后拉开门闩。
他向外看了一下,转过身,轻轻地捏了一她的肩,拍拍她的脑袋,说:
梳梳头。
她又笑了。看他迈着轻盈的步子走下了楼梯,她在楼梯口默然立了一会儿。正准备转身进屋,她的眼睛凝住了:
在家门与天台之间的一级阶梯上,赫然躺着一个烟蒂。
她几步上去,拾起烟蒂,转身进了屋。
门轻轻地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