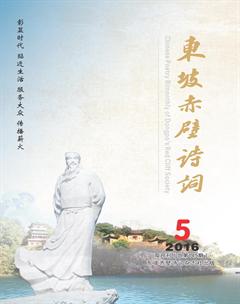诗,也要有点个性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有的张扬,有的沉稳;有的严谨,有的活泼;有的内秀,有的洒脱;有的刚毅,有的温柔。即使是一对双胞胎,虽然父母一眼就能辨出是谁,但性格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异。不同的个性特征,放射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人,如果没有独自的个性,岂不就千人一面了!
诗,或词,如同人一样,也要有一点个性。没有个性,就没有独特之处,也就不能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我国古今诗人,大凡有一定成就,都是其作品有自己的鲜明个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比如古代,我们一读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就会想到它的作者、忧国忧民的杜甫;一读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竹枝》)就会想到它的作者、沉稳凝重、对人生和历史有着深刻理解的刘禹锡;一读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题西林壁》)就会想到它的作者、充满禅思、亟具哲理的苏东坡。
再如当代,一读到“捆星背月归来晚,踩响荒村犬吠声”(《冬日打背柴》)就会想到它的作者、充满忧患意识、亟具穿透力的北京诗人刘庆霖;一读到“新媳妇,语惊人,谁能胜我任谁亲”(《插田》)就会想到笔锋尖锐而又幽默的湖南诗人伍锡学;一读到“冒雨顶骄阳,汗湿衣襟手茧香”(《赞背篓书记》)就会想到语言朴实、以意取胜的湖北诗人孙宇璋。正由于这些诗都有着与众不同的个性,才引起大家的感情共鸣,才为大家的认同和接受,才得以流传,才真正体现出诗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唐代乃诗歌盛世,《全唐诗》收录诗作者2873人,诗作9403首,但是真正流传、家喻户晓的也只有遴选了77位诗人、311首诗作的《唐诗三百首》了。
一个人的个性是怎么形成的?一是父母遗传因素的影响,二是环境使然。一首诗的个性又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常说,生活是诗的土壤,生活里蕴藏着诗。说明诗的个性与生活有关,是不同生活的体验,造就了诗的不同个性。试问,如果杜甫没有经历安史之乱,长安沦陷的痛苦体验,他能写出“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极富个性色彩的诗来吗?这也说明生活体验对于诗作个性形成的重要。正如沙子不是金子,但沙子里却可以淘出金子。所谓诗,就是从沙里淘出的有特色的金子;所谓诗人,就是生活的淘金者。我认同这样的观点:诗人, 如同正处于活跃期的火山,情感的岩浆在胸中奔突,一旦寻到能释放的喷口,有个性色彩的诗就诞生了。
(作者吴洪激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本刊前任主编)